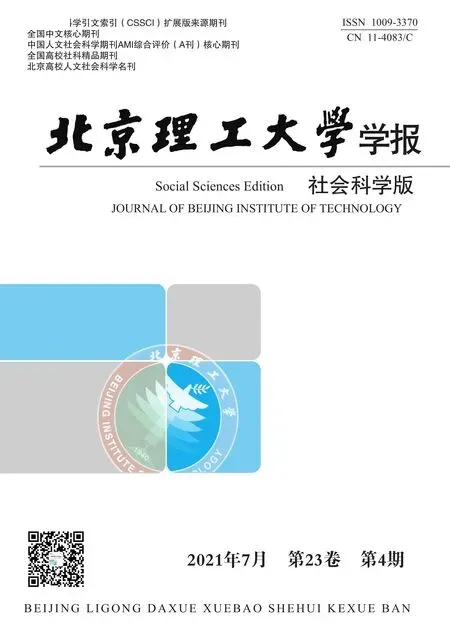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
——以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为中心
程 凌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要“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法制体系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相关领域的立法均已有序开展①在德国,社会保障法称为“社会法”(Sozialrecht),主要包括社会预护(社会保险)、社会扶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等四个方面,承继德国联邦社会法的构成观点,中国台湾地区“社会法”所涵盖的领域与之相同。对于下文“社会法”与“社会保障法”两术语,本文作同义使用,不作区分。[1]19-20[2]10-14,社会保障法制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非常充足。相较于西方国家已经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相关制度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可能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不同制度衔接、待遇给付等方面。于此背景下,在社会保障法领域如何保护公民对国家行为所产生的信赖利益则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信赖保护原则(Grundsatz des Vertrauensschuzes)是“典型的德式原则”[3]3,体现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信赖关系,是贯穿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4]13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于违法行政行为,德国恪守依法行政原则(Grundsatz des Gesetzmäßigkeit),采取自由撤销立场②Ruffert, in: Ehlers, AllgVerwR, 14. Aufl. 2010, §24 Rn.19。。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予以限制,在撤销违法行政行为时考量是否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予以存续保护③Ruffert, in: Ehlers, AllgVerwR, 14. Aufl. 2010, §24 Rn.19。[5]63[6]456。在公法领域,信赖保护原则主要涉及法律变更与废止中的法不真正溯及既往、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中的存续保护以及行政计划、行政契约等领域中“行政决定的改变应顾及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等三个方面[3]7[7]87[8]78。其中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不仅是信赖保护原则最初形成且典型的领域,而且是当前社会保障待遇追回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保障法中,社会保险费缴纳、社会保障给付待遇领取资格认定、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主要是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作出。追回相关的待遇给付,必然涉及相关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问题,在此过程中如何保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则值得深入研究。
在中国社会保障待遇追回的相关规定中,大部分规定未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予以考量,通常相对人只要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即应当退还相关待遇给付金额或者物资,比如《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2019修订)第25条、《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2011修正)第25条规定,“经办机构发现不符合条件……应责令其退还。”《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44条规定,“参保人依法不应当享受或者超出其应当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由市社保机构予以追回。”相似的规定还有《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2016修订)第65条、《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第48条、《黑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2006修正)第44条等。在社会保障法领域,只有部分规定体现了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如《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68条规定,“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由有关部门决定停止社会救助,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物资……”。相似的规定还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34条、《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第34条等。这些规定明确了在相对人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形下,其信赖利益不值得保护。对于在其他情形下,比如,与社会保障待遇认定相关的法律或者事实发生了变化,是否要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以及其法律效果如何调整等问题,上述规定未予明确。
目前,中国对于信赖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般行政法领域,主要涉及对信赖保护的渊源、意义、构成要件、与行政法其他相关原则的关系等方面。对于社会保障行政中的信赖保护问题,当前研究鲜有涉及。
一、社会保障行政中信赖保护的法理基础
对于公法中信赖保护原则,其法理基础存在法之安定性原则(Grundsatz des Rechtssicherheit)、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国原则(Sozialsstaatsprinzip)等观点,而且有的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并非单一,而是存在多个[3]4-6[4]134-151。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行政领域中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在于法之安定性原则[6]90[9]277,其强调既有法秩序之持续与平和,具体到行政行为,则意味着行政行为的存续力(Bestängigkeit)与可预测性。公民也因此而信赖行政行为,并对既有利益及未来生活予以安排。因此,行政行为不得任意撤销与废止,即使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也应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在法规范适用层面,公民因信赖行政行为而产生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则应该结合个案中涉及的基本权利予以衡量[10]219-220。法之安定性与基本权利保障作为信赖保护的法理基础,其不仅适用于一般行政领域,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保障行政领域,在此不予赘述,需予以说明的是社会国原则对于信赖保护的强化作用。
作为社会保障法的基本理念,社会国原则不仅是信赖保护的理论基础,而且使得社会保障行政中的信赖保护予以强化。社会国原则作为宪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其从魏玛宪法中的方针纲领条款,发展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具有拘束力的国家目标之规定,其因高度抽象性,具体内涵难以界定。对社会国原则之内涵,德国联邦社会法学者汉斯·察赫做出如下阐释:“国家对于经济上或因经济而导致的社会关系,加以评价、保障及变更,其目的在使个人能享有合于人性尊严之生存,以减少贫富差距,排除或控制从属的依赖关系。”[11]465由此可知,社会国原则要求国家承担对公民的生存照顾义务,保障人民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而国家对公民的生存照顾义务则是给付行政的主要内容。在给付行政兴起之前,国家奉行守夜人之角色,恪守依法行政原则,防止国家对公民的过度干预。1935年给付行政之父恩斯特·福斯托夫在其著作《行政作为给付主体》(Die Verwaltung als Leistungstra¨ger)中,提出生存照顾(Daseinsvorsorge)概念,严格区分社会给付行为与干预行政行为,并指出给付行政当以“保障德国民族之生活条件,作为行政之主要目的”[12]。而为实现生存照顾之目的,国家有义务通过社会国原则条款的宪法委托,建立最恰当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乃至其他社会权,并在此过程中充分考量公民对行政给付行为所产生的信赖[4]138。社会保障法为实现其立法目的,其待遇给付主要通过给付行政的方式实现。因此,在社会国理念下,社会保障法应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予以充分考量。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信赖保护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司法实践开始通过个案对信赖保护原则予以确认。1956年,德国柏林高等行政法院通过抚恤年金案(简称“1956年德国抚恤年金案”)在司法实践中首次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①OVG Berlin,Urt.v.14.11.1956-VIIB12/56-,DVBl1957,503 ff.。在该案中,原告为一名东德公务员遗孀,其向被告西柏林民政局申请抚恤年金,被告告知原告,其只要位于西柏林则享有抚恤年金申领资格;原告为此而迁居西柏林,被告也确认并向原告核发抚恤年金。后来,民政局发现原告不具备抚恤年金申领资格,便撤销了原先作出的错误决定,并要求原告返还已经发放的抚恤年金。对此,该案法院支持对原告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否定被告的撤销行为。该案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典型体现,在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中,依法行政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处于对立状态,而只有当公共利益大于人民对有效行政所产生的信赖利益时,违法行政行为才可予以撤销。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不断加大给付行政力度,公民对给付行政措施的依赖不断加强,对国家给付行政行为存续力的信赖也更加强烈[4]138。其后,信赖保护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位置也更加巩固。
二、社会保障待遇追回条款中信赖保护构成的要件检视
社会保障法以向相对人提供社会给付(社会保障待遇)为主要内容,其主要以行政行为的方式实现。行政部门对相对人授予或确认相关权利、法律上利益的行政行为,称为授益行政行为②Ruffert, in: Ehlers, AllgVerwR, 14. Aufl. 2010, §24 Rn. 11。。在社会保障法领域,对最低生活保障户、残疾人等资格认定是申请相关各项给付的依据,因而,上述各项资格之认定为授益行政行为;而违反法规相关规定给予过多给付或要求缴纳较少社会保险费等,亦属于授益行政行为③Schütze/Schütze, 8. Aufl. 2014, SGB X § 45 Rn. 22。。因此,授益行政行为的认定不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系‘受益’或‘负担’”,而是以该行政行为是否增加相对人的权益为根据[3]8。区分授益行政行为与负担行政行为的意义在于,对上述两种行政行为撤销或废止的限制程度不同:负担行政行为本身对相对人产生不利法律效果,若撤销或废止负担行政行为,则实际产生有利于相对人的法律效果,因而通常情况下,对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废止没有限制,不存在信赖保护的问题;而授益行政行为因本身对相对人有利,撤销或废止该授益行政行为会对相对人产生不利的法律效果,为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通常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废止予以限制。
在社会保障法领域,对于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如何进行限制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首先要明确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在一般行政法领域,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即信赖基础(Vertrauensgrundlage)、信赖表现 (Vertrauensbestätigung)及信赖利益的保护 (Schutzwürdigkeit des Vertrauens)[13]166。在社会保障法领域,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与之无异,同样包括上述三个方面。只是,基于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特殊性,信赖保护构成要件的判断内容存在差异。
(一)信赖基础
信赖基础是指足以引起人民期望的公权力行为[14]10,即国家行为。在社会保障法中,对于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信赖基础为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比如相对人不符合申领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金、失业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条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却向其核发相关社会给付的违法行政行为④该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常见,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9行终25号行政判决书、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2〕西行初字第29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8行终104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行初257号行政判决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8〕兵08行终13号行政判决书等。。另外,如果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相对人核发的养老金、伤残津贴、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等社会给付标准高于其应当享受的标准,该授益行政行为也具有违法性⑤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行终269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5行终89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2017〕豫0522行初43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申345号行政裁定书、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7行终96号行政判决书等。。对授益行政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以行政行为作出时为标准[13]675。就具有持续性效力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 mit Dauerwirkung)的撤销而言,其仅指自始违法的行政行为。在社会保障法中,存在众多此类具有持续性效力的行政行为,比如养老金、失业金、伤残津贴、最低生活保障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资格的确认与给付的核发,这类授益行政行为一经作出,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即会定期向相对人核发相关社会给付。此外,对于具有持续性效力的授益行政行为,还存在行政行为作出时合法,而事后因法律法规的变更及或者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状态发生变化而不合法(即开始合法嗣后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在社会保障法中,这种情形也广泛存在,比如领取失业金的相对人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此时其已不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而相会保障部门仍然向其核发失业金①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196号行政判决书。。对于开始合法嗣后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其不适用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而应适用行政行为的废止。在社会保障法中区分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其原因在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废止所产生法律效果不同。
(二)信赖表现
信赖表现,是指人民知悉且信赖国家行为将继续有效存续,进而对自身权益进行处置[9]283[14]11。因此,信赖保护不仅要求人民对授益行政行为具有信赖的心理状态,还要求人民将该信赖的心理状态表达为客观的具体表现②Stelkens/Bonk/Sachs/Sachs, 9. Aufl. 2018, VwVfG § 48 Rn. 136。。通常情况下,如果相对人对授益行政行为的给付予以消费或者进行财产处置,且无法恢复原状或者即便可以恢复原状但会导致相对人遭受不可期待的损失,则该情形均属于信赖表现③Stelkens/Bonk/Sachs/Sachs, 9. Aufl. 2018, VwVfG § 48 Rn. 141。,此为一般行政领域中信赖表现的认定。
在社会保障法中,基于社会保障给付目的的特殊性,其对信赖表现的认定相对更为宽松。社会保障的给付涉及金钱给付、实物给付及服务给付,不同的社会给付因社会保障种类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给付目的在于保障受救助人的最低生活标准,失业保险给付之目的在于保障暂时失去生活来源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工伤保险中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在于向工亡相关亲属提供一定比例的生活费,养老保险给付之目的则在于保障达到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等。虽然上述社会保障待遇的给付目的不同,但是,其金钱给付目的均涉及保障劳动者及相关人员的生活,而该金钱之使用极有可能涉及其日常生活费用的支付。因此,要评估待遇给付的返还是否会对相对人的生计产生严重影响④Schütze/Schütze, 8. Aufl. 2014, SGB X § 45 Rn. 41。。对此,相关学者亦认为,相对人将老年年金用以生活之消费⑤Ruffert, in: Ehlers, AllgVerwR, 14. Aufl. 2010, §24 Rn.30。,或者赠与孙子女,或者用以支付养老院费用,属于信赖表现[6]454;由于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退休金,相对人而放弃工作,此亦属于信赖表现⑥Schütze/Schütze, 8. Aufl. 2014, SGB X § 45 Rn. 41.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众多违法批准提前退休申请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相对人通常没有主观过错,因社会保障部门错误批准与核发退休金而放弃工作,此应当认定为信赖表现。但遗憾的是,我国司法实践未考量相对人此种情形下的信赖利益。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行初257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2行终146号行政裁定书、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203行初136号行政裁定书等。。另外,如果相对人基于对授益行政行为的信赖而承担某项任务,或者舍弃其他获益机会,也均属于信赖表现。比如,德国法定健康保险人(AOK)相对人可以配偶的家属身份加入法定健康保险,并可免缴保险费,相对人因此终止其私法上的健康保险合同而加入该法定健康保险,此亦为信赖之表现⑦Dörr /Francke, Sozialverwaltungsrecht, 2. Aufl. 2006, Kap.7. Rn.90。。
在中国社会保障待遇追回的相关条款中,虽然部分内容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但是这些条款通常仅涉及相对人主观存在恶意的情形,而未涉及是否需要考虑相对人的信赖表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行政恪守依法行政原则,在法律未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中鲜有案例对相对人信赖表现进行考量。
(三)信赖利益的保护
信赖是否值得保护,主要考察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即相对人的“善意信赖”值得保护,而“恶意信赖”不值得保护。相对人之“善意信赖”具有抽象性,难以判断,立法实践则通过认定相对人不存在“恶意信赖”(或信赖瑕疵),间接推定相对人之信赖为善意,值得保护。在中国社会保障待遇追回的相关条款中,对于相对人恶意情形的认定不尽一致,这些规定均强调获取社会保障待遇方法的不正当性或手段的非法性,比如《社会保险法》第88条、《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68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第35条、《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第34条、《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34条、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2008修正)第53条等。虽然上述条文规定,通过不正当方法或非法手段获取社会保障待遇的,相对人的信赖不值得保护。但是,上述规定仍具有抽象性,除《社会保险法》第88条初步规定了信赖不值得保护的具体情形,其余条款均未明确信赖不值得保护所包含的情形。结合域外立法实践,当前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应予以类型化。
第一,通过非法手段,促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该情形考察,对于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作成,相对人是否具有可归责事由。域外立法中,《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第3句以及《德国联邦社会法》第10编第45条第2款第3句均明确规定,如果相对人“以欺诈、胁迫或贿赂方法,促使行政行为之作成”,则其信赖不值得保护,否则无异于变相鼓励非法行为①Stelkens/Bonk/Sachs/Sachs, 9. Aufl. 2018, VwVfG § 48 Rn. 150 ff。。中国立法实践亦有相似规定,比如《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第35条规定,相对人“以非法手段获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其信赖不值得保护。对于何为非法手段,《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15条指出,《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第35条中的“非法手段”,是指“不具备或者已经丧失《条例》规定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条件而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中对“非法手段”予以扩大化解释,其所阐释的非法手段扩展至所有手段,而合法手段亦包含在内。比如,如果相对人已经不具备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条件,但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由于信息匹配出现错误而将其仍划归为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人员序列;在此情形下,该相对人并未实施非法手段,但是按照《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15条的解释,却属于通过“非法手段”骗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的行为。因此,本文认为《天津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15条对“非法手段”的解释有待商榷,对于“非法手段”的解释应该控制在文义解释的限度内,强调手段的非法性。
第二,在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据以作出授益行政行为的重要事实材料提供方面,当事人存在过错。是否核发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相对人提供的事实材料为依据。如果相对人对重要事实提供不实资料,则要考察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具体到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其主要考察相对人的主观故意状态,比如《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相对人以“伪造证明材料”的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其信赖不值得保护;《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53条规定,以“弄虚作假”获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其信赖不值得保护;《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第1款、《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68条规定,相对人以“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障待遇的,其信赖不值得保护。上述规定均体现了当事人“故意”的主观状态。但是对于在重要事实材料的提供方面相对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中国社会保障相关立法并未予以明确。在中国相关社会保障立法中,相关规定明确只要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要件,相对人的信赖即不予以保护,无论相对人对重要事实材料的不实提供是否存在过错,均在所不问。该方式有失妥当。
在社会保障法中,各项待遇给付之间关系复杂交错,一般民众对社会保障法有关规定及设置目的了解通常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行政面向的群体有相当部分为弱势群体,其对社会保障法相关条文的理解相较于一般民众更为不足。《德国联邦社会法》第10编第45条第2款对相关事实材料的提供设置了主观要件,即相对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②LPK-SGB X/Karl Lang, 5. Aufl. 2019, SGB X §45 Rn. 34。。在认定重大过失时,相关学者认为,评估相对人认识到错误的能力非常关键,这需要考量相对人的知识与教育程度、社会经验③Schütze/Schütze, 8. Aufl. 2014, SGB X § 45 Rn. 52。。
第三,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信赖保护着重于对相对人内心主观信赖的保护。中国社会保障待遇追回相关条款并未考量,在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下相对人信赖利益是否予以保护的问题。相应地,相关司法实践中,也缺乏此种情形的司法案例。但是在域外立法中,比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德国联邦社会法》第10编第45条均规定,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因为重大过失而不知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则该相对人的信赖不值得保护。首先,如果相对人知晓授益行政行为违法,则其应当意识到自己不符合待遇给付条件①Ruffert, in: Ehlers, AllgVerwR, 14. Aufl. 2010, §24 Rn.29。,于此,其当无信赖可言。其次,对于过失的衡量应根据个案情形进行判断。相对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取决于其对违法性是否具有相关知识;如果相对人具备特定的违法性知识,则对其所课予的违法性注意标准更高②Ruffert, in: Ehlers, AllgVerwR, 14. Aufl. 2010, §24 Rn.29。。比如,在德国,公务员、退休金领取人必须检查雇主的通知。如果行政部门发放的社会给付高于法定标准,而该公务员或者退休金领取人申请时未检查雇主的通知,则可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
三、授益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律效果
在社会保障待遇追回的过程中,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包括自始违法与开始时合法嗣后违法两种情形,应该如何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此涉及其法律效果。当前,在中国社会保障待遇追回的相关立法中,仅有少数规定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比如《社会保险法》第88条、《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68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34条等。这些规定对信赖保护的关注集中于相对人主观状态存在瑕疵的情形,未对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的法律效果进行层次化的细致考量。授益行政行为如果开始时合法,嗣后因事实或者法律的变化而违法,在其废止中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处于合作状态,因而对于其废止应无疑义,不涉及可否废止的问题。进而,在社会保障待遇的追回中,如果授益行政行为自始违法或者开始时合法嗣后违法,要落实信赖保护原则,则应从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否、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授益行政行为的失效时点)、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对信赖保护的法律效果进行调整。
(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否
在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中,中国社会保障法领域仅有部分规定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表现为如果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存在恶意,则其信赖不值得保护。在理论层面,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是否予以撤销,首先应判断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是否满足。对此,应着重考量相对人的信赖表现与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如果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未得到满足,则应当撤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如果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业已满足,则须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与所欲维护的公益进行衡量。对此,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涉及。理论上,如果信赖利益大于所欲维护之公益,不得撤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如果所欲维护之公益大于信赖利益,则是否撤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属于社会保障行政机关的裁量权。
在社会保障法领域,如何把握信赖保护中的利益衡量,此涉及信赖利益、所欲维护之公益的界定、社会保障法中公私利益衡量等三个方面。
第一,相对人信赖利益的界定。在一般行政法中,信赖利益的界定可参考民法中的信赖利益[15]372,是指相对人因信赖授益行政行为的存续,对所得给付进行相应安排与处置,但是如果授益行政行为被撤销,“相对人因为信赖落空所将蒙受之损失”③此与民法中的信赖利益之观点相吻合,民法中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因信赖无效之法律行为有效,所受之损害。[14]16[16]564,对此,预期利益或履行利益不属于信赖利益的范围。在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信赖利益主要表现为,相对人因对社会保障给付进行财产处置或生活安排而所遭受的损失。在社会保障法中,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中的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社会给付均涉及相对人的生活保障,如果相对人将上述给付用于生活消费,则上述给付的消费视为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此外,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还表现为相对人因信赖社会保障行政行为而对生活所做的重要安排,若撤销该行政行为相对人将承受重大生活变化,此亦为信赖利益。比如,在梁某某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案中④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2行终146号行政裁定书、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203行初136号行政裁定书。,社保局因自身工作失误,将梁某某所从事的油漆工种认定为可提前退休的工种,批准通过其提前退休申请并发放养老保险待遇;后来,社保局发现工种认定存在错误,便撤销了提前退休的审批并要求追回已经发放的养老保险待遇。在该案中,梁某某因为信赖社保局的提前退休审批而退出工作岗位,其生活来源也由工资转变为养老金,生活可谓面临重大变化,属于信赖利益的范围。
第二,所欲维护之公益的界定。撤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所欲维护之公益是指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撤销后,得以恢复合法状态或得以维护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贯彻依法行政原则而建立合法状态、避免行政机构不必要的支出(财政利益)[14]16。在社会保险法中,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所欲维护之公益在于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而在其他社会保障法中,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所欲维护之公益在于相关机构的财政支出。
第三,信赖利益与所欲维护之公益之间的利益衡量。在《德国联邦社会法》中,如果相对人对违法之社会给付进行了消费或者财产处置,则推定其信赖利益相较于公益更值得保护①Schütze/Schütze, 8. Aufl. 2014, SGB X § 45 Rn. 42。。该方式值得借鉴。因为就以金钱为给付内容的授益行政行为而言,通常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为一定数额的金钱,而所欲维护之公益为相关数额的财政负担,如果仅在两者之间进行衡量,则犹如“胳膊难以拧过大腿”,通常认为公共财政之利益大于个人的金钱财产利益。在利益衡量过程中,金钱数量的衡量仅作为一个方面,还需要就个案结合其他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量[17]279。在社会保障法中,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涉及相对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而还应该根据个案考量下列因素:首先,授益行政行为撤销对相对人的影响。在社会保障法中,尤其是社会救助领域,相对人通常为弱势群体,如果撤销社会救助金给付的行政行为,可能会对相对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影响其生存权,在此情形会倾向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其次,相对人的学历知识水平、对社会保障法规的熟悉程度。在社会保障法领域,由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较为复杂,而且一部分群体为弱势群体,其知识及社会阅历相较于一般群体更为不足,此时,应倾向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比如,在郑某某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案中②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8行终43号行政裁判书、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8行终44号行政裁判书、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8行终45号行政裁判书、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8行终46号行政裁判书等。,郑某某等作为一般的农民,就其学识而言,其对相关养老保险的政策缺乏认知。再次,还可考虑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程度、行政行为做出的时间长短、行政行为的作成方式等。授益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程度越轻、行政行为做出的时间越长、行政行为的方式越正式,则在利益衡量时,越应倾向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③Schütze/Schütze, 8. Aufl. 2014, SGB X § 45 Rn. 41。。
(二)授益行政行为撤销或废止后是否溯及既往失效
在社会保障法中,确定了授益行政行为撤销或废止后,还应当考量行政行为是否溯及既往失效的问题。
1. 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中的溯及既往失效与否
对于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其失效是否溯及既往,可根据授益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效力进行区分。一次性的行政行为不具有有持续性的法律效果,其仅存在撤销与不撤销的问题,无需考量是否溯及既往失效[18]147。而具有持续性效力的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则存在溯及既往的问题。其失效时点存在多种可能性,是否溯及既往要受信赖保护原则的限制。理论上,如果相对人的信赖不值得保护,则应撤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而且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溯及既往失效;如果相对人的信赖值得保护,而且在个案综合衡量情形下,信赖利益大于所欲维护的公益,则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不予撤销;而如果相对人的信赖值得保护,但是信赖利益小于所欲维护的公益,此时行政机关对于是否撤销违法行政行为享有裁量权。如果行政机关撤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则该行政行为的撤销仅能向后失效④Schütze/Schütze, 8. Aufl. 2014, SGB X § 45 Rn. 77。。
对于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中国社会保障立法采取溯及既往失效的做法,对于相对人主观状态不存在过错的情形,当前立法未考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比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12条、《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2019修订)第25条、《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2016修订)第65条等。在实践中,对于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作出,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自身可能存在过错,这种情形非常普遍。比如,在梁某某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案中,社保部门因工种认定错误而批准梁某某提前退休。在郑某某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案中,社保局相关人员在失地农民的认定方面未严格审核、存在失误,错将郑某某等认定为享受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在这些案件中,相对人自身不存在过错,其信赖应值得保护。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即便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为个人利益难以与公共利益抗衡而撤销授益行政行为,该撤销也不应当溯及既往失效,而应当向后失效。
对于公私利益的衡量,还可根据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时点进行划分,在两个时间段内对信赖利益进行考虑[14]21:第一阶段,自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作出至撤销阶段。在此阶段内,如果相对人对社会保障给付予以受领、消费、财产处置等,且无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此时相较于所欲维护的公益,倾向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在此方面,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未予以考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尚有少数案例对此阶段内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申345号行政裁定书、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196号行政判决书。,堪称允当。第二阶段,自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撤销至未来阶段。在此阶段内,相较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则倾向于保护公共利益,通常会于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撤销时失效,但是也会有例外情形。比如,某些城镇出台的养老金政策规定,具备一定条件且年满60周岁的相对人可缴纳一部分资金(假设为36 000元),然后每月从政府领取1 000元;但是,在相对人已经领取养老金2年之后,相关行政部门发现该项政策违法,则该情形下相关行政部门核发养老金的行为为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但是,该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何时失效才可以有效保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实践之中有的部门采取在撤销该行为满1年后失效的做法[18]148。此可作为社会保障领域,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于撤销后向未来失效的示例。
2. 授益行政行为废止的溯及既往失效与否
在社会保障法中,具有持续性效力的授益行政行为,比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领取资格认定与核发、失业人员的认定与失业金的核发等,可能会因相关事实或者法律状态的变化,而不再具有合法性。对此,则应该废止相关授益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废止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即通常情况下,授益行政行为自废止时失效,仅在特殊情形下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溯及既往失效。比如,《德国联邦社会法》规定,如果事实的发生不利于相对人,而相对人对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未履行告知义务,则该授益行政行为自事实发生时起溯及既往废止失效②§48 Abs.1. SGB X。。
检视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却通常溯及既往失效。比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12条规定,“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本人或他人继续领取待遇”的,相关部门应予以追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规定,“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追回相对人领取的款物。在社会保障法中,相对人虽然有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比如被救助人员对于人口、收入、财产等情况的告知义务,但是,相关行政部门也承担主动告知说明与核查的义务。由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领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于具体哪些情形属于告知的范畴,相对人很有可能并不知晓。如果行政部门未妥善告知相对人,则极有可能出现未完全提供信息或者所提供信息不符的情形。在此背景下,难以苛求相对人具备完全社会保障的相关知识。对此,涉及到授益行政行为因事实变化而废止的情形,应该将相对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作为授益行政行为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的标准。只有相对人主观存在过错而未告知的情形下,才对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溯及至事实发生变化时失效;如果相对人虽然未告知,但是不存在主观过错,则授益行政行为自废止时失效。在此方面,中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68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第1项的规定较为妥当,建议其他涉及到授益行政行为因事实变化而废止的规定,比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第2项、《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12条、《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2019修订)第25条等,在涉及溯及至事实变化失效方面,增加相对人主观存在过错的要求,对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进行考量。
(三)授益行政行为撤销或废止后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
在社会保障法领域,授益行政行为撤销或废止中的返还问题主要包括三种情形,即一次性行政行为的撤销、具有持续性效力的行政行为的溯及既往撤销及其溯及既往的废止③此处具有持续性效力的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溯及既往撤销,既包含完全的溯及既往撤销的情形,也包含不完全溯及既往撤销的情形。。对于社会保障待遇如何返还,中国立法未予以规定。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有的行政部门直接通过民事诉讼中的不当得利追回待遇给付④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终9 549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终341号民事裁定书、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8〕琼0271民初3 184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金民终字第381号民事裁定书等。,有的则是在行政案件中,阐明相对人不符合领取相关社会保障的条件,其所领取的待遇给付属于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以此追回相关待遇给付①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行终804号行政判决书、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7行终45号行政判决书、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7〕吉0702行初77号行政判决书、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7〕辽0603行初10号行政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0行终55号行政判决书等。。在德国法上,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发展包含三个阶段,即直接适用民法不当得利规定阶段、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öffentlichrechtlicher Bereicherungsanspruch)阶段—类推适用民法不当得利之规定、公法返还请求权(öffentlichrechtlicher Erstattungsanspruch)阶段②为表述之简洁,后文均采用统一表述“公法上不当得利”。[19]226。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乃针对没有法律根据而取得给付的返还,其目的不是补偿相关国家措施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而是返还没有法律根据所转让的财产[9]753[20]105,此公法不当得利之目的与民法不当得利之目的相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分析可参考民法不当得利的相关内容[6]1244。
须指出的是,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以依法行政为基础,同时受信赖保护原则之拘束,而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则是完全以私人主体间的利益平衡为基础,因此对于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不能完全适用民法不当得利之规定,而应当作合目的性准用,这主要体现在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方面。首先,对于不知无法律上的原因,当事人是否存在过失,在民法不当得利其在所不问[19]175。但是在前述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中,如果当事人对授益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悉,则其信赖不值得保护,社会保障行政机关得溯及既往撤销该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相应地,当事人则应返还自失效时起的待遇给付。但是,如果准用民法不当得利,则当事人可能会以不知该社会给付的违法性,而主张免除返还责任。若此,则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存在过度保护之嫌,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其次,对于所得利益是否存在,信赖保护原则与民法不当得利也存在差异。在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中,如果当事人对于所得利益已经予以消费或者作成不可恢复的财产处置(即使可以恢复,也将会使当事人遭受重大损失),则当事人的信赖值得保护。进一步,如果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大于所欲维护的公益,进而该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不得予以撤销,不会涉及返还问题;如果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小于所欲维护的公益,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使裁量权将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则其失效将面向未来,也不会涉及返还问题。但是,在民法上,尤其是当所得利益为金钱给付时,除非当事人可以证明该金钱已赠与他人,否则在其他情形下,通常难以证明所得利益已经不存在[19]179。因而,若适用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则又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存在保护不足之虞。由此,在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追回中,要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实现个人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则应当首先适用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众多通过民法不当得利而进行社会保障待遇追回的做法。对此,则应当坚持信赖保护原则的贯彻,尤其是涉及当事人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授益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主张对所得给付利益已经予以消费或者进行财产处置的的情形[9]756[21]124。
四、结语
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完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背景下,社会保障法不仅要贯彻依法行政,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更要关注对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增强公民对社会保障体制的信赖,以促进社会保障法中实质正义的实现。
第一,细化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考量相对人的信赖表现及主观状态,改变只要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条件相对人的信赖即不受保护的思维方式。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个案关注相对人的信赖表现,根据不同社会保障待遇的给付目的,评估社会保障待遇给付返还对当事人的影响。在相关规定中,比如《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2019修订)第25条、《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44条、《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2016修订)第65条等,建议明确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不受保护的情形限于其主观存在过错的情形,并予以类型化。
第二,对于授益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律效果,从可撤销与否、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是否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考量,采取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在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方面,通过利益衡量,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给予更加细致的考量。在授益行政行为的失效时点方面,严格控制溯及既往失效的情形,即通常仅限于当事人无信赖表现及主观存在过错的情形,尤其是对于授益行政行为因事实变化而嗣后违法的情形,其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应当着重考量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对于涉及授益行政行为因事实变化而废止的规定,比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4条第2项、《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12条、《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2019修订)第25条等,在涉及溯及至事实变化失效时,建议增加相对人主观存在过错的要求。在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方面,坚持适用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对于中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民法不当得利的情形,则应当以贯彻信赖保护原则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