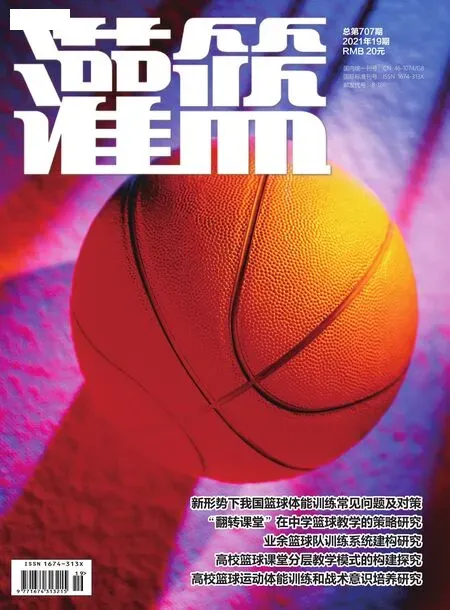社区治理困境:参与式治理不足
王名哲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一、分析视角:参与式治理
学界关于社区治理过程中参与式治理的研究颇丰。自1960年参与式民主理论被首次提出以来,至1990年治理理论研究的兴起,参与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这一概念被学界广泛认可[1]。学界对参与式治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内涵、参与式治理的困境与政策建议等方面。
有学者对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应然与必然进行研究[2][3]。也有学者以参与式治理的视角论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困境与解决之道[4]。还有学者在对新型农村社区进行研究时关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5][6]。
二、居民地位解构:主体与核心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即与农村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Y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主要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居委会)与居民。并且居民在Y社区治理结构中还应处于核心地位。
农村治理结构变迁至“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使得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得到了发展,这也标志着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开始步入制度化运作阶段。从Y社区治理结构上看,乡镇政府参与到Y社区治理当中去,一方面Y社区作为乡镇政府项目实际上乡镇政府也直接处理一些社区事务,另一方面关于社区出现的某些问题,村委会(居委会)难以解决也会通过镇政府寻求帮助。Y社区治理的第二个参与主体即村委会(居委会),城镇社区的治理机构往往是居委会,但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当中社区的治理机构往往是两个牌子一个班子。其职能是负责Y社区日常事务与调节居民关系与向上反映居民意愿,在社区治理结构当中居于主要位置。社区作为生活载体内在地服务于居民,社区的正常运转与和谐的社区环境不可不谓与居民有着直接的联系,可见居民之于社区治理是其主要的参与主体且居于核心地位。Y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有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可协调居民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化,通过解决各种矛盾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二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使得社区事务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公平与合理的处理关系到居民自身利益的社区事务也让居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
三、“三无”:主体核心地位缺失
新乡市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农民集中居住建设实践,使得农民的生活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与城镇趋于一致,社会与社区治理的急剧转型难与居民适应性、村委会(居委会)自身调整相契合。作为Y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核心地位的居民却缺位与社区治理,其现实呈现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无意参与”“无力参与”和“无路参与”,笔者调查发现居民社区治理的参与困境不单单使居民的需求得不到落实,社区治理成本也较为高昂且效率较低。
(一)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无意参与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社区参与呈现“参与意愿不高,参与率较低,强制性、动员性参与比例居高不下,决策参与比例较低”的特征,正是居民不愿参与社区治理致使社区治理呈现低水平参与的现状[7]。笔者在访谈中发现,Y社区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是老年人和妇女,且参与社区活动也主要是文娱活动。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年轻人白天大多出去打工或上班,很少有时间来参与社区活动,而老年人在家歇息或料理家务,时间较为充裕,因而较多的参与社区活动。“现在家庭的主要收入是孩子们的打工收入,白天他们都忙着打工呢,有时候都忙到很晚才回家,我们在家看看院子照顾孩子,时间比较多,有时候居委会组织活动我们就去参加一下。”(访谈记录)第二,在社区参与主体上存在定向思维定式,即人们总认为社区参与是老头儿老太太的事情而与年轻人不相干,因此就不自觉的将年轻人排除在外。第三,一些社区活动组织者有意识地侧重举办针对老年人的活动,无形中加重了这一趋势。
笔者发现Y社区实际参与率较低,“现在村里面召开会议或者是举办活动,再或者是迎接个检查,人都很难找。小的不在家,大的不愿意来,很多时候要靠给点好处才能找到一些人。”(访谈记录)主观上讲,大多数人忙于工作和事业,奔波于家庭和单位之间,因而无暇参与社区活动。从客观方面来说,一些活动内容与参加者没有利益关联,导致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参与和我们不搭嘎,去不去没有区别,要是规定必须去我们就尽量去,没有强制要求,我们是不会去的。”(访谈记录)笔者还发现居民社区政治性参与缺乏,其主要是参与社区的文娱活动。结合访谈笔者认为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居民认识不足,他们将社区管理和发展视为政府、居委会的事情。正如访谈中村民所言,“他们(社区工作人员)做的事儿跟我们的生活不搭嘎,社区管理都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做好就可以了,我们也没必要掺和,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访谈记录)二是与社区管理体制有关。近年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大面积铺开,社区管理与社区建设也被提上议事议程,这就要求改革和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格局,但“目前的情形是社区内大量事物仍由村委或居委会以行政方式来完成,居民难以介入。”[8]
“村民自治”曾经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通过对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却发现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较低,同时政府在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笔者在调查中发现Y集中居住社区建设实践过程当中镇政府主要关注社区住宅与配套设施的建设,却忽略了村民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主体地位与村委会自治地位,在损害居民与村委会集体利益的同时削弱其公信力,致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较低。与此同时,在Y农民集中居住社区之中居民表现出“原子化”倾向,血缘与地缘建构的治理单位转型至业缘关系,政府主导与核心主体的消极参与之间产生某种张力,规划的社区治理未能真正实施起来抑或实施较为艰难,并制约了社区治理的效果。
(二)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无力参与
居民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供给方,还是社区治理的受益方,换言之,社区治理活动均是为保护社区居民的权益和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贾燕等通过对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的研究发现,“农民家庭抚养人口比例、文化程度是农民福利变换的影响因素,同时还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9]”伽红凯等人对江苏省农户集中居住前后福利变化研究同样发现,最高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福利变化水平呈正相关影响。Y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尤其是硬件设施诸如居民楼、道路、绿化、广场等方面让村民享受到实惠,但短暂兴奋之后,面对复杂的社区治理环境,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居民则都表现出更多的不满和无助。村民虽转为居民身份但其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现代化信息技术不了解且学习难度大,其往往关注社区文娱方面活动而对国家关于新型农村社区方面的政策、内容不关注且不理解,HDZ镇政府与村委会尽管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宣传与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但居民却依然“读不透与读不懂国家关于新型农村社区的大政方针,也不能亲身参与实践”。
(三)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无路参与
居民参与治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参与治理的运作机制是否完善,尤其是参与渠道上,参与渠道通畅与否关系到各种意见和建议能否汇集到决策中心来。叶继红在对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社区参与的研究中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接受调查的农民认为参与社区治理较为‘顺畅’,而认为参与社区治理难度‘一般’与‘不通畅’的分别占接近五分之二和三分之一。研究发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Y社区参与渠道不畅通主要原因有:一是村民自下而上的表达通道不通畅。在之前的传统村落村民的意见表达往往是借助与村内精英而实现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内精英生产生活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的形态致使其精力较少的放置于乡土生活之中,村民传统表达意愿的通道也随之窄化。二是集中居住社区治理自上而下通道受阻。农村社会治理样态的急剧转型却给村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带来严重不适,究其原因主要是其文化水平不高且身份转换难以与当下准确对接,这些困难使得村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方面对社区事务关注不足,另一方面他们采取维稳策略,只要社区稳定,牺牲居民参与社区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至此,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通道被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