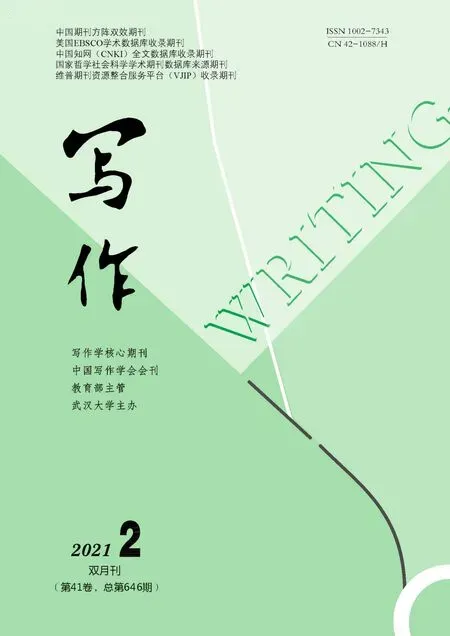“公安诗歌”的艺术
——论青蓝格格的诗集《预审笔记》
陈 卫
繁复多样的生活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激荡或深沉的感情,它们如何进入诗歌?对诗人们来说,其中有着来自时代、经验、智力与艺术等多维的挑战。尤其行业题材的写作,如果能够为当代诗歌增添可感的现场和独特的诗情,为想象充沛的诗歌添上一把人间烟火,那么这样的诗歌,可能会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
一、“公安诗歌”整体观
阅读公安诗人的作品时,不免有这种期待,他们的职业,总是与惊险、犯罪、侦破、安全等相关问题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生活在老百姓中间,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他们的着装、行为都不同于大众,更带有一种神秘感。就诗歌质地而论,诗人无须做职业的区分,优秀的诗人,能够自如地在职业与诗歌写作中完成转换。因为喜欢,我曾经朗诵过几位公安诗人的诗歌,如杨角早年一首《喊岷江》,“……我只要深情地喊一声:岷——江——/每一座山上,都站满了我的模仿/一声呼喊变成了一个队一个村的呼喊……”,浩然大气;李群的《活着就是春天》乐观气概,给不少病人带来过精神的支持:“……生与死近在咫尺/开与落只是瞬间/长路漫漫/天堂和阳光也都不远/秋水微凉/旭日和暖/我从天堂活着回来/才知道/人间到处是春天”;田湘的《坐在高铁上还嫌慢》:“……一切皆快,唯有自己慢/更可恨的是,看似活得很慢的人/忽然就老了,白发像雪片布满脑袋/且越老越急……。”
他们的这些诗歌,有着比一般人更开阔的精神世界,更为强大的力量支撑,虽然为男性,但是他们感知不乏敏锐。也有的诗人写公安这一职业,因为时代变化,知识的更新,对职业的感受也有了新的角度,不再是颂歌体形式。如川江号子的组诗《关于人民公安的词性》中有一首《交警的词性》:“交警不是名词/他一直站着/无论风雨还是暑寒/这个词从来没有倒下/他站在风雨中/风雨都有秩序/他伫立日月中/日月都被感动/这个词语很有魔力/一个微笑/酷暑变凉 严寒变暖/一个手势/天下整齐 路畅人安//正因为如此我随时随地/都在为这个钢铁般的词语担忧/这个词语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穿梭于车水马龙之间/我担心词性被风雨剥蚀/我担心词性的生命会戛然而止/这个词语一生都在走/可一直没有走出条条斑马线/这个词语一生都在转/可一直没有转出岗亭大的一块天//面对这个被辞海定性错了的名词/我只有拿出仅有的一点诗情/为这个历经风雨的词/伸去一把避雨的伞”。这首诗,借助语言学角度来描写警察特性,避免了直接的场景描绘和歌颂,把政治抒情诗歌较为成功地转换成具有学术特色的诗歌,给读者一种新鲜的感觉,而诗情并没有因此减弱。
公安诗歌队伍中不乏优秀诗人,他们写作时间长,有各自的写作兴趣并形成特有风格,在社会上已产生一定影响,如陈计会对乡土文化的挖掘,周孟杰诗的梦幻色彩,袁瑰秋、邓醒群取材警察的真人真事,对他们的英雄事迹进行歌颂,书写真诚、铿锵动人,他们的作品经常在中央电视台或公安人的舞台上演出,有催人泪下的效果。
二、“公安诗歌”的犯罪书写
与以上诗人相比,青蓝格格的诗歌,则为另一种风景。青蓝格格原名王晓艳,内蒙古人,现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就职。她入伍时间不算长,2014年才进入公安队伍,彼时的她,已参加过《诗刊》社第二十七届青春诗会,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两部诗集——《如果是琥珀》(2014)和散文诗集《石头里的教堂》(2015)。青蓝格格的诗歌总体上偏向思辨,由于思辨,形成系列的组诗相对多,如“XX之疑”多达43首,包括《醉酒之疑》《毒素之疑》《隐喻之疑》《口舌之疑》《痛经之疑》等,诗歌写作中不乏有性别的特征,相对关注家庭及其生存环境和终极问题,是擅长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的诗人。
《预审笔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于青蓝格格个人创作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于公安诗人的写作而言,无疑是一次特别的实验。这一部诗集,并非从大众视角描写公安人的工作和生活,诗人作为一个职业人(预审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因此诗歌有来自职业角度的观察;有审问时的记录;还有细节观察后的感受,如内心的揭示和对某一个相关问题的思考;表现方式接近小剧场性——这是我的阅读范围内,以往“公安诗歌”所不曾出现过的写作风景。
在中国,民众与司法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民众多是通过新闻了解司法,众所皆知,新闻中的司法,多经过一定处理以让民众从中得到“法网恢恢,罪有应得”的法制教育,这也是司法部门在处理重要案件后对民众的一个必要交代。因此,大多数民众认知的“警察”基本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铁面无私、大义凛然,他们是为国为民的英雄;那么,犯罪分子则是无恶不作、罪有应得的大坏蛋。《预审笔记》中的警察和罪犯并非如此简单的对立,给读者某种程度上的颠覆。如《慈悲的诗行》的第一节:“我一见到他就联想到/野花颓败的样子。/事实上,/他的长相非常帅气。/他的眼睛大得可以/塞满一个天涯和一个归期。/他的额头可以明亮如一片宁静的/湖泊。”这节诗歌中,我们并没有读到以往文学作品中对犯罪分子的狰狞、丑陋的描写。中国人相信“相由心生”这个词语,坏人的面相一定邪恶不堪,而诗中这么美好的面相,怎么可能是犯罪分子呢?事实是,他是。作为审问者的“她”也不敢相信,“他的灵魂是披头散发而千疮百孔的”,犯罪事实真实存在的——“他亲手杀死了/他的姐姐。”
在青蓝格格的诗集中,除了犯罪分子并非都是丑恶的形象,犯罪者的身份、状态也各有不同。从诗歌涉及的内容看,非常广泛,也就是说,犯罪的原因各种各样,诗歌的内容相应繁杂多样。这部诗集的可读性,就是建立在取材的五花八门之上——人有罪,罪有千种万种:有因恋人施暴,女人被男人打断腿的《施暴的爱情》;有丈夫杀害妻子的,如《影子》《一个纸人的影子》《深渊》《一场白色事件》等;有弟弟杀了姐姐的,如《慈悲的诗行》;有兄弟为女人仇杀的,如《一首物我两忘的诗》;有母亲杀死两岁女儿的,如《一首晴天霹雳的诗》;有父亲杀了亲生儿子的,如《天上的泡沫》;有儿子杀死父亲的《一个杀死父亲的男人》;有12岁女儿见证母亲的去世发生呆滞的《残忍的空》;有未成年人犯罪被审问的场景,如《提审一名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有写强奸而致死的女性的《由一个女被害者引申出的女人问题》;有杀人犯犯罪后,整容更换性别的《雕像,或者火焰》;还有在两个女人中间以不同面目出现的重婚罪犯者,如《无语之诗》;有要为儿子顶替杀人罪的《界限》;有写贩毒者的《与贩毒者论灵魂》;有写吸毒卖淫的,如《晨曦》《灵魂开花了》;有写偷盗者的《一个偷盗者的哲学》;有全副武装,腰上捆着十斤炸药炸桥的《如此戏剧》;有放火把房子烧了,也想烧了自己的,毁了一切的《灰烬的含义》;有写网络骗子以征婚形式骗女性的,如《残缺之诗》;也有女囚犯的爱情《一名女囚犯的相思》《与一名女囚犯谈论男人问题》《由一宗杀人案联想到的爱情问题》;有写女人去抠另一个女人的眼睛的,如《分裂手记》;也有写自杀者的《一名杀死春天的自杀者》;还有残酷的凶杀现场的《凶杀现场》……由这些诗的选题,大致可以看到诗集的内容:一部分有关暴力和谋杀,有亲人之间的谋杀,也有因爱情失败而发生的悲剧,还有的罪因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强奸、盗窃而起,自杀案件也有。所谓犯罪,即违背民众认同的日常伦理,采用非法手段谋害他人性命。犯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谋财害命还是精神状态出现问题,或是人性变异?探讨人性的罪恶,并揭示另类女性的生存及生理心理问题,是诗集最为鲜明的特色。
有的诗,把犯罪分子的心事写得很美。如《一名女囚犯的相思》中,事件是隐去的,写了一个天蝎座姑娘,她的日记中记录着对爱情的渴盼:“我喜欢用水彩作画,因为我喜欢用一颗五彩缤纷的心爱你”,如此浪漫的姑娘,却成为阶下囚。
有的诗,把犯罪现场写得很恶心。如《凶杀现场》“我被他折磨得一次又一次呕吐”,“我看到他/肾的一部分、肺的一部分/肝脏的一部分/头颅的一部分/甚至他/下身的一部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弱小的阴茎/凶残地袒露着”。
有的诗,透过事件,看到参与处理案件的警察的内心波动和思考。在这类诗歌中,警察更像诗人。如《杀人犯与煮鸡蛋》,诗歌写的是一个杀人犯在被逮捕前,在家吃一颗半生不熟的鸡蛋。“我”认为这颗煮鸡蛋“仿佛这个杀人犯漫无边际的命运”,这就是诗人的想象。当“我”向犯人提问“为什么不把鸡蛋煮熟了再吃?”后,自己展开各种联想,柔软,像月亮,像初恋,有古诗的意境等等;当“我”听到罪犯回答,“没有煮熟的鸡蛋/像我妈妈的/乳汁”,意识到“不能再诗情画意下去了”。等犯人把蛋吃完,给他戴上手铐,诗歌写道:“听到罪犯的呢喃,喊了一声‘娘’。”诗歌中用乳汁和娘,暗示犯人的母爱缺乏,他并未丧失人性。这首诗与其说是写犯罪,不如说是描写人性的复杂和苏醒。诗歌表现的并非警察与犯人的对话,更像诗人与另一个诗人探讨母爱的一个比喻。
三、“公安诗歌”写作艺术
由诗歌写作而论,诗集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首先,诗歌营造戏剧性场景。这种方式集中三种场合:其一,对犯罪现场的想象、描述;其二,审讯现场的再现;其三,潜意识的构建。戏剧性场景的营造,便于对诗歌内涵的理解。
《预审笔记》是诗集的第一首诗,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诗歌的语言接近独白,仿佛一个剧中人,面对观众讲一个犯罪人的故事,如一出折子戏。最开始的一幕是“见面”:“从听到他叮呤当啷的脚铐声起,/我的心就开始悬起来。/我想见到他,我想见到他。”如果这首诗没有标题和第一句的交代,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首爱情诗,抒情如此热烈——“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仪表堂堂的模样”,不仅如此,他“明媚的眼睛望着我”。“我”听到他说“我想死”这样的话,不是表情肃然,却是“想哭”,“再一次想哭”,但“强忍着”。接下来是二人对话,可视为第二幕“交谈”。虽然是警察与犯人对话,但更像是诗人与诗人,哲人与哲人之间的交谈:
我对他说:“春风的不可控
揭示出人性的泯灭。”
他对我说:“人活着就是人性的消磨。”
他对我说:“我总是梦见塔尖上的光。”
我对他说:“有梦就好……”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梦
就寄托在一碗
稀得无法再稀的小米粥里。
这一段对话,在我看来,是高度的虚构。诗人虚构的原因,目的不是探讨具体的罪,而是在探讨罪的来源,探讨现实与梦想的关联。诗歌还写到他们谈论“尼采和哥伦布”,这些信息,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警察与犯人的知识面广博,关系融合,没有敌对的立场,更是强调二人间的身份转变(非警察、非犯人)。也许读者会以为这个太假了,但这个交谈,是诗歌的转折处,也正是诗意的发生处。接着,诗人又转回“警察”角色,也就是第三幕“白发”,看到犯人的“毫无秩序的”白发——“这些被血/淹死的幽灵哦,/我听见它们‘呜呜、呜呜’的哭声。/他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但是,这些感受,却更像“诗人”之感,感性而非理性的,诗中使用了幻觉、暗示等诗歌的常用技巧,来表达谈话时对于死亡的感受。接下去的描写,写的是犯人擦脸的细节,可看作第四幕“擦脸”:“他打开纸巾,在自己/灰白的脸上/用力地擦……/他真的是在用力。”兼具警察与诗人身份的“我”,关注他擦脸的动作和细节,认为他这时的用力,“仿佛他身怀‘起死回生’的/绝技。”这四幕,比较完整地写了一次预审的过程,也是探究美的毁灭至死的一次过程。
其次,诗歌的语言通俗,有的近似大白话,有的突出诗歌意象,充分利用诗歌分行特点,情节跳跃,通过歧义的问答,构成诗歌张力。如《一场白色的事件》,诗歌力图突出色彩以及色彩之间的鲜明对比,达成隐喻效果。故事本身很简单,一个身怀六甲的女性死了,她的丈夫掩面哭泣。色彩在诗中起到渲染情感的作用,作者巧妙地利用了诗歌分行特点,虽然使用了大白话语言,在散文或小说中,会认为是败笔,而诗歌分行的形式,刚好突出视觉意象:
床的对面
是一面白色的墙壁。
墙壁的对面
是一张白色的床。
白色的床上躺着一个
穿着
白色睡衣的
女人。
白色的墙壁上挂着
一张结婚照,
新郎新娘都穿着白色的礼服。
在床边哭泣的丈夫,穿着“白色”衣服,掩面哭泣。他为何哭泣?诗人没有解释,只自顾自地反问“我如此这般地描述这场事件,/是不是有些/残忍?”这样实实在在的句子,诗歌写作本来也是忌讳的,但是这个句子与前后文形成一个呼应,构成留白,为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这恰恰也是诗歌的特点:谁杀死了孕妇?丈夫吗?诗歌最后,诗人表达的感受是“相对白色的事件,/我仿佛是一道——黑色的伤口——”为什么把自己比作伤口?这样直白的句子却这样含蓄,同样值得寻味——诗人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物来映衬白:白色的幸福,白色的死亡,白色的哭泣,其中“我”,是一个旁观者,这种种视觉上的震撼,让“我”受伤了。
《流水有毒》是一首“恶之花”。诗歌第一节写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一只脚站在水中,/一只脚站在岸上。/她试图将自己送入流水的怀抱……”。在营救这个女孩的时候,为转移姑娘的注意力,“我”对女孩说:“你长得真美”,女孩的回答,是诗性的回答:“我与流水有缘。/我要在水中为自己换上一件/有翅膀的衣裳。”这首诗安排了诗歌的正文本和副文本。副文本表明“我”的态度和听到对话的感觉,所以,这样的诗歌,读起来有画面感,很轻松,好读。接下去的对话:
“流水有毒。流水与
香水不一样。”
(我再一次转移话题。)
“我是想向下漂移,而不是湮没。”
(她的回答显得很哲学。)
两个人的对话,像是两个哲学家关于“流水”的对话。作为读者的我,则认为不要以为这是高深的罪犯在表达,而是诗人借助另一个形象,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营救者和下水者,为的是在对话中,更方便阐释关于“流水”——生命流逝的哲学思考,这纯粹因为诗人精通故事结构的技巧。可以看到她在诗歌中安排的转折:“我”试图激怒姑娘,告诉她“你要像鹅卵石那样移动一下,你就解脱了”。然而,姑娘没有听从,反而一动不动。诗歌于是转向了观察者自身,“我”感觉到流水,“仍然是身外之物”,这一感受与女孩表达出来的截然不同,而且“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我认为诗歌想要表达意思是:姑娘在流水里是想感受向下漂移的感觉,自己却是觉得站在水里,水会淹没自己,危在旦夕。这首诗并不是探讨犯罪的原因或是其他,而是借助两个不同身份和兴趣的人,面对流水,发生哲学层面的多角度的思考。
充分利用诗歌形式和修辞特点在《一个纸人的影子》中也很明显。诗歌第一节写了犯罪场面:“他用刀刺向他妻子/胸膛的时候,/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起来了。/他吓了一跳,/把刀扔到几米外的地方。/在他愣神的瞬间,他的妻子逃脱了/他的魔掌。”这是一段叙述文字,如果不分行,就是一个故事片段。诗人利用了诗歌排行的特点,突出一些重点意象,“胸膛”“魔掌”。第二节写的是,公安人来到现场的情况,前面三行是描述,“我们抵达现场时,/他正用手捂着头。/他说起话来轻飘飘的样子”,一般性的描述到这里,意思已完成。诗人用了一个比喻,突出了诗性特色“犹如一片/白色的羽毛”。增加这个比喻,是用来增强他说话时的状态和听话人的感受。后面有一段“我”和“他”的对话:
“你——刺向自己吧!
就像刺向
一只鱼儿的体内。”
听到我的话,他,怔在那儿——
仿佛变成了一只
离开池塘的
鱼儿。
我们不能确定,在严肃的现场,审问者能不能用比喻性语言进行如此严肃的、有关生命的对话,而且是有点过激的诱导。罪犯听了后,很理性地停住了。
我看他一动不动,接着又说:
“你就当自己是一种
固体吧。”
仍然不是明确性的日常用语和日常表达方式。接下去的话,更是哲人式的抽象:“如果能与生命和解,我还能变成/水平的吗?”审问者“我”关注他说话的态度,“他说出这句话时,我把他当成了一个纸人的/影子——//而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纸人——。”“纸人”是诗歌的一个关键词。何为纸人?有着人的形状,但没有血肉,没有情感波动的“人”。“纸人”和“纸人的影子”,也可以都看成被抽空血肉,不懂得疼痛、生死的所谓的“人”。
所以读这首诗的时候,虽然始于现场,通过诗人的诗性化加工和戏剧性场景的转换,最后抵达的是哲理之境。
青蓝格格诗歌中的诗意涌现,多来自联想、类比方式或比喻等修辞手法,情节跳跃、跌宕,在留白和转折处,对潜意识世界进行发掘、质问或反思,而不是停留在案件的来龙去脉上,也不对案件进行道德或社会评价。这种种方式,使一个个冷面无情的案件发生盎然的诗意转变——这不是生活,而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灰烬的含义》中写了一个纵火犯放火烧了房子,他表示:“甚至想把自己点燃,/烧成灰”。“我”在与他谈话后,“我突然对灰烬的含义也/一无所知了”。接下去是“我”对自己的反思,“我故意以此证明,/我是一个崇尚完美的人——”“我甚至故意将灰烬当成/夏天开的花,/秋天结的果……”,这里写出了“我”与“放火人”的差别。她没有把放火人当作穷凶极恶的人——诗歌到此,发生一个转折,“在我犹豫的瞬间,/他突然淡定地告诉我,/他的表/停止了转动——。”诗歌的情节似乎脱节,不发生直接关联,可是又隐藏着关联。诗人对“灰烬”进一步描述:从“烧房子”“烧自己”到“烧表”,“从而改变时光”。诗人没有对他进行精神状态的判断,而是把现实事件引向诗意的发掘,只说了“哦,他多么愚蠢啊!”这一个判断,好像是来自世俗的认识。然而,诗人又进行了另一层剖析,“但比他更愚蠢的是/我。——//我端着一个虚无的酒杯,成为一名/真正的//醉鬼。”诗歌表面上是围绕案件写,但是,诗人写的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在探讨导致案件发生的人性方面的问题,涉及善与恶,甚至超越道德而上升人性层面的东西。
再如《残缺之诗》,写的是一个网络骗子,身体是残缺的,“他仅有一只手可以用。/他仅有一只眼睛/能够看见光明。/他用残缺的身体承受着整个生命的负重。”不可忽略的是,他渴望爱。诗歌中写了“我”与“他”的对话,关于“爱”——“因为谁也离不开爱/所以谁也/得不到爱。”,“爱情中的你或许很美,但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这些对于爱的感触,不能不说真实或深刻。正因为这样,导致“我”“突然失去了/对爱情,/所有的记忆——”,因此自问“这个残缺的世界,真的还有爱情吗?”诗人仿佛不是为了诗而诗,而是一把锋利的刀刺向自己,让原有的观念世界发生震荡。
四、“公安诗歌”的成熟及发展
青蓝格格并不像新闻记者,为了体现案件的真实性,注重案件的过程和结果;她也非小说家和思想家,着重挖掘隐藏得很深的犯罪的根源。我以为,青蓝格格的兴趣并非写案子本身,她是为了写诗歌才去写各种案子。因此,评价她的诗歌,读者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假如以真实性作为诗歌好坏的判断标准,这个真实,是指案子发生的真实,还是诗歌中情感的真实呢?在青蓝格格的诗歌中,案子只是诗歌的一个引子。如果要设定比例,为了方便计算,她的诗歌大概三分之一描述现场或引出案例;三分之一,是警察与罪犯的对话,这类对话多是诗意的对话,有大量的虚构性质,这时的警察,发生了身份的转换——为“警察”+“诗人”,罪犯相应发生了转换——“罪犯”+“另一个对话的诗人”;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警察转换为诗人后的思考、推理或者升华。所以,我觉得评论青蓝格格的诗,从诗意的呈现和哲理的揭示的角度去判断,才能看到这些诗歌的真正价值。事件(案子)本身作为诗歌的引子,所以无所谓真实与否,美丑与否。往常的司法报道,中心人物多为犯罪分子,事件即为案例,大众要的是结果。青蓝格格的诗,罪犯尽管是一个重要角色,我以为,诗歌中的“我”,警察,也是诗人,更代表有思考、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类形象。如何看待种种犯罪,如何去理解他们,如何帮助他们走回正轨,也是这部诗集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所以,这部诗集,并非关于犯罪探究,而是关于人类如何生存与赎罪。
虚与实,问与答,拷问与反思,是青蓝格格的公安诗歌写作的内在要素,同时构建了她特有的写作模式。从写作层面,这种模式又为诗人提出了一个难题:成熟,意味着限制。一位优秀的诗人,创新是她永远的追求,这,将成为青蓝格格下一步必须突破的障碍,她需要更为广阔的天空和自由自在的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