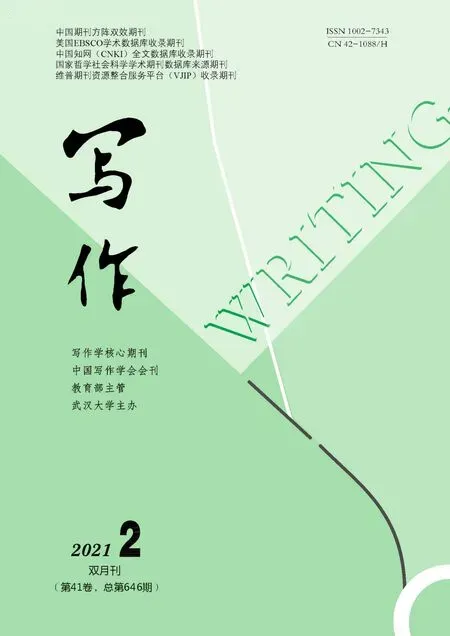从“后先锋”到编年体地理志写作
——夏商访谈录
张 娟 夏 商
夏商为中国当代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乞儿流浪记》《标本师》《裸露的亡灵》,另有四卷本《夏商自选集》及九卷本《夏商小说系列》。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对话夏商,试图对其文学启蒙、城乡写作、创作特色、海外写作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文学启蒙:翻译小说与民国文学
张娟:夏商老师,您好!在“五四”百年的背景下,鲁迅是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有的人对他是抗拒的,在写作的时候会试图反叛,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地受鲁迅的影响。我想了解一下,在您的创作过程中,鲁迅对您的意义是怎样的?能不能说说您的文学启蒙?
夏商:我接受应试教育的时间很短,初二就辍学了。鲁迅的小说不多,基本都读过,阿Q、阿金之类的形象印象很深。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阿金》里面的那句“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这句是上海话,充满了底层小市民的气息,挺有意思。从文学观念来说,鲁迅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对国民性这种问题没什么兴趣。
我的文学启蒙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复兴式的文学回归,大量外国小说的译本出现在书店,我们这代小说家中的相当一部分,所受的文学启蒙主要是西方作家的作品,严格说,是翻译过来的作品。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1949年以前,大陆的文学创作及电影、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并不是封闭系统,用今天的话说,也是融入全球化的。当1980年代我们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德、乔伊斯、蒲宁这些作家的作品时,老民国时期的小说家们早就读过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陆已经出现了先锋性和观念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所以1980年代出现的先锋派小说,其实是先锋派2.0版,只不过2.0版和1.0版间隔了半个世纪甚至一个甲子之久。在我们学艺的时候,不是说刻意要去崇洋媚外模仿海外小说,而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当然你可以说,可以去学施蛰存、刘呐鸥,他们也挺先锋的。问题是,施蛰存、刘呐鸥的新感觉小说是受了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的启发,包括鲁迅,他的《狂人日记》无论是标题和立意都借鉴了果戈理,那我还不如直接去读“母本”。再说海外小说并没有停滞,五六十年代又出现了更多的思潮。除了日本和传统的文学重镇英法德意,美国在二战前后也崛起了很多作家,甚至拉丁美洲的文学也“爆炸”了。
基于这些现实原因,加上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大量海外文学类社科类名著被译介进来,对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大陆文学人来说,真的有琳琅满目之感。卡夫卡、纪德、普鲁斯特、尤瑟奈尔、萨特、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这个名单可以放大十倍二十倍,这么多“老师”站在面前,你当然既不可能去学浩然,也没必要去学施蛰存。当然,我不认为浩然是和施蛰存同一个层面上的作家。上面那句话仅仅是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新一代写作者面对文学启蒙时所能做出的选择。
说到老民国作家,我对张爱玲评价更高一些,还有一些文学史家看不上的所谓通俗小说家,我也很喜欢。比方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故事就讲得很好,尤其对世事人情的洞察,是很多所谓的纯文学作家达不到的。鲁迅的小说,或许连文白转换尚未彻底解决,而张爱玲、周天籁的白话文已臻于成熟。当然,这是站在回望的角度,并不能苛责鲁迅,周天籁1939年发表《亭子间嫂嫂》,张爱玲1943年发表《第一炉香》的时候,鲁迅已作古多年,张爱玲、周天籁的白话文之所以不错,可能是出道晚获得了“文转白”的红利。就像张贤亮或冯骥才,今天看当然是我的前辈作家,再过五十年,或者再久一点,读者可能就觉得我们是同辈作家了,这样的时空坍缩是人的一种错觉。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作家们并不只是为同时代读者写作,而是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中同台献技。比起鲁迅,我更喜欢胡适,也可以这么说,目前学界对鲁迅谈得太多了,对胡适谈得太少了。
张娟:那么您觉得在阅读的视野里面,中国当代作家有没有让您觉得能够去体现文学的创新和先锋特色?还是说您的阅读资源主要还是外国作家?
夏商:应该还是翻译小说,更年轻的一批,比方说00后或者90后的小孩,语言能力比较强,可以直接读英文原版。我这一代作家还是受翻译小说影响比较大,确实从观念和技术上来说,翻译小说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小说归根结底是写人和人性,写人的情感,写人和时代的关系。我曾在一次讲座中说,现代中文小说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用方块字写的西方小说。中国传统小说是平面化的,像素描,对人的深层次的剖析很少,是完全靠情节,有时还是靠离奇或巧合的情节推动的。西方小说则像油画,是一层层渲染的,叙事方式并不仅仅靠情节,有很多旁逸斜出,比如风景描写、心理分析、梦境、日常百科、博物学知识等。
二、写作题材:城市前史与编年体地理志书写
张娟:您的写作有一个中国作家共通的东西就是对城乡问题的关注。鲁迅一开始写作,也是从乡村开始的,后来他革命和生活的地方都是在城市,他站在城市的视角反观乡村,形成一种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叙事的对立模式。您广受关注的长篇小说《东岸纪事》写的是浦东,却又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都市化浦东。我在阅读时会感受到浦东在开发之前的那种强烈的乡村气息,作为城市前史,当时您写《东岸纪事》的初衷是什么?从鲁迅以来,中国的乡土文学写作有没有对您造成一种潜意识的影响?您对中国当下的城市小说是怎样看待的?
夏商: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老问题,就全世界的文学作品来说,乡村、乡巴佬、边缘的小人物、小镇轶事,太多这样的小说了。我们先假设一下,你给中文系学生介绍一位小说家,说这位小说家喜欢写城市,故事里出现的场景是豪华酒店、赌场、豪车游艇、奢侈品店,俊男靓女坐在头等舱里满世界跑,然后你说这位小说家刚拿了诺贝尔奖或龚古尔奖,学生们肯定会小眼神迷惑,总觉得哪儿不对,对吧?你再给学生介绍另一位小说家,说这位小说家喜欢写乡村和小镇,故事里是野河、小树林、后院、猎枪、乡村酒吧、开了十年的皮卡,黑人农夫在小船里勾引了白人的女儿,中产阶级乡绅枪杀了神父,隔壁村的独眼寡妇在咖啡馆里坐了半个世纪。然后你说这位小说家刚拿了诺贝尔奖或龚古尔奖,学生们的小眼神或许就不迷惑了,这才是该有的画风嘛。
其实,严肃文学并不在于写乡村还是写城市,它的特征是呈现真实的日常,不炫耀、不浮夸,无论故事的场景是光鲜还是毛糙,叙事是向内的、自省的、充满怀疑的,基调是褪色的、怀旧的、反现代性的……为什么乡村叙事和小镇叙事会成为大多数严肃小说的背景,是因为这本身就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场景。以美国为例,除了纽约一小块土地上有曼哈顿这个繁华街区,大量老百姓生活在小镇或农村中;像洛杉矶、休斯顿这样的美国大城,除了CBD有一些高楼,车子开出去没多远全是平房,有些就散落在坡地和荒地里。美国还算是比较新的国家,欧洲就更别说了,不但是矮房子,还是几百年的老宅,小镇连着野地,野地连着小镇,所以很多移民在外的华人都戏称自己住在农村,我儿子留学的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就被叫作“布村”。我有一次去休斯敦,当地的华人朋友说:“欢迎来‘休屯’。”回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前,哪有什么大都市?就算北京上海广州,也不过是大一点的县城而已。你去看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老照片就知道了。北上广尚且如此——那时候还没深圳什么事——更何况内地边陲?所以大陆作家熟悉的当然也只能是农村和小镇,即便有些上海作家写了一些市区生活,也是发生在老城厢老弄堂,石库门里的七十二家房客,逼仄的亭子间,倒马桶,生煤球炉,公用自来水,满满的城乡结合部气息,和小镇也没很大区别。
张娟:我觉得中国从没有实现过真正的都市化,最近几年的状况可能发生了转变,但大概在十多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都市化。
夏商:不是中国一家,全世界都差不多。当然理论上说,作家不应该挑题材,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都应该拿得起,就像一个厨子,不能说我只做海鲜,不做猪羊肉,但现实中哪有全能厨子。从另一个角度说,都市是个伪命题,世上哪来什么都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都市,皆是空壳,世界的本质是土地河流,不是钢筋水泥马赛克。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北上广深5A写字楼里那些洋名叫“玛丽”叫“安吉拉”叫“汤姆”叫“约瑟夫”的,逢年过节就被打回原形,成了“翠花”“小芳”“铁蛋”和“二狗子”。这种情况其实曼哈顿也一样,来自外州各个郡,那些农业州、红脖子州的乡下小孩,考上了常青藤校名校留在纽约,发达后在中央公园旁买了豪宅,似乎也成了城里人,可本质上,他们永远是乡下孩子、小镇青年,说到底,玻璃幕墙的大厦只是皮相,乡村和小镇,才是绝大多数人的出发地。
既然乡村和小镇是绝大多数人的出发地,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乡村叙事的文本?那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那么不同,加上时代和历史的变化,乡村和乡村之间,小镇和小镇之间,会产生别样的经验。至少对我来说,写自己熟悉的场景更容易入戏,也容易使虚构有坚实的背景,相对而言,城市的钢筋水泥对我无法形成刺激。你刚才问我创作《东岸纪事》时的想法,我确实有过一些考量,比如写哪个时间段,多大的体量,有没有能力驾驭,完成度会不会好,这些想法在过去的写作中,是很少有过的。这是我写作心态的一个变化,不是自我怀疑,应该是更自信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写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老浦东,也就是钢筋水泥化之前的乡村浦东。能够写浦东编年体乡村志的小说家,有写作能力的或许没我了解浦东,比我了解浦东的或许没我这样的创作实力,这绝不是自大自满,而是实际情况。要知道,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运气遇到一个合格的书写者,编年体地理志小说虽然一直有人写,但佳作比例并不高。这里说的“编年”不是按具体年份来结构故事,而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概括。小说家的能力来自两部分,一个是天分,包括鉴赏力、语感、掌握写作技巧的悟性、对故事结构的控制以及天赋,这其中只有天赋是无法训练的,也是一个小说家段位的决定性因素。另一个就是材料,这个材料既包括间接材料,间接材料是无限的,每天都可以获得,尤其是信息爆炸的今天,每天层出不穷的信息扑面而来,要遴选其中有用的,成为小说素材,对小说家的悟性是一种检验;也包括直接材料,就是你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过的人或事,直接材料是有限的,人的阅历就这么多,所以那些虚构能力不强的作家,写了几本书以后,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把记忆里的存货都写完了。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既要会使用间接经验,也要会使用直接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有虚构能力,才能使自己的写作生涯有足够的长度。
如果让我写一个你们老南京的故事,我肯定写不好。这就是材料所带来的局限性。如果时空更远一些,让我写马尔克斯笔下的霍乱时期的哥伦比亚,或者昆德拉笔下被苏联坦克碾压的布拉格,那是绝无可能完成任务的天方夜谭。编年体地方志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几乎不具有回溯性,新一代哥伦比亚小说家回不到马尔克斯笔下的那个哥伦比亚,新一代捷克小说家回不到昆德拉笔下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同样,今天刚出道的上海小说家也回不到我笔下的那个老浦东。时过境迁,就像豆瓣上年轻读者对《东岸纪事》的留言,有的这么说:“那么原始的浦东,我不曾想过。”有的这么说:“老浦东的故事,在我出生前戛然而止,也算一出时代挽歌吧。”
另一方面,某些材料虽然具有时效,却又不能太新,写小说不是写新闻,无须争分夺秒,总要经过一定时间沉淀,就像一瓶好酒,放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拧开瓶盖才会酒香四溢。所以有人问我会不会写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我说不住上十年怎么写?前几天听说有人正在写以新冠为背景的小说,我只能笑而不语。
除了材料,还有就是写作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才华,因为才华不够从而把好材料浪费的情况太普遍了。相当于把一手好牌打烂,这当然很可惜,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所以我在读一些名著的时候,会反问自己,如果有同样的材料,是不是有能力写得一样好。材料决定了题材范围,思辨能力决定了视野,生活经历造就了对世界的看法。当然,一个缺乏外部生活的经验的人,也不是不能写小说,象牙塔作家可以写写校园小说,也可以用学问和思辨来弥补,往玄思和哲学上靠,比如博尔赫斯,比如艾科。但写编年体地理志小说可能就有点隔靴搔痒,写浓郁风土人情的小说,作家首先得是野生动物,具有丛林社会的深度体验。
三、创作历程:后先锋文学与知识写作
张娟:鲁迅小时候喜欢看绣像小说,文学资源十分芜杂,而且喜欢来自民间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我看您的成长经历也有这种“野狐禅”意味,初中辍学,喜欢看连环画和《镜花缘》《三国演义》《水浒传》,很早就接触社会,然后走上先锋文学创作的道路。鲁迅的《狂人日记》,与传统小说相比,更像是一部哲理作品:“狂人”充满思辨能力,心理活动丰富,关注人类历史的大问题,关注一个病态的、荒谬的世界……其实也是很先锋的。您在20世纪末命名“后先锋文学”,当时是什么一种情况?
夏商:命名“后先锋文学”之前,我一般被评论界归入“新生代作家”。最初的“新生代”主要是指60后出生的作家群,其实是模糊而懒惰的命名,因为等到70后作家出道,也被叫作“新生代”。按这个逻辑,80后90后00后都可以放进“新生代”这个大箩筐,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命名并不满意,我们这批作家在写作理念上和“先锋派”基本是一路,就是出道略晚,所以用后先锋来命名是恰当的,但也不是什么严谨的学术命名,就是客观陈述一下先来后到而已。其实,当时先锋派作家和后先锋作家都面临转型的问题,先锋派作家玩了几年花拳绣腿,该玩的形式玩得差不多了。后先锋作家也意识到有点生不逢时,挤末班车没赶上趟。小说也讲天时地利,我的《乞儿流浪记》刚写完的时候,就有批评家说,这小说要能早五六年问世就好了。我们常说,严肃文学没有时效性,其实是相对的,说着说着又要绕回到小说的文本价值和文学史价值。鲁迅的某些小说放在今天,恐怕发表都有问题。
先锋派作家比后先锋作家出道早一些,靠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文本积累了名声,作为尾随而至的后先锋作家,文学训练并不逊色于前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因为建立在形式主义的沙滩上,从崛起到式微,也不过十来年光景。命名“后先锋”的时候,在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这件事上,后先锋作家和先锋派作家其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无论是后先锋,还是先锋派,都在形式主义的余脉处徘徊,都呈现出回归传统的趋势,至少在文本上,新一批小说更趋于常态了。所以那段时间又喊出“回归日常叙事”“大踏步后退”等主张。处于这样一种挟裹之中的我,于1999年策划了“后先锋文学联展”,提供版面的是《作家》《青年文学》《时代文学》,加盟者除了同辈小说家,也有同辈批评家,小说家写小说,批评家写文论,加起来20人左右,算是世纪末一次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吧。
张娟:对,“后先锋文学”的命名一直延续到现在,大家仍然在做这样的划分,影响还是很大的。我在读您前期小说的时候,能看到非常强烈的先锋意味。比如说2001年在《花城》杂志发表的《裸露的亡灵》,就是先锋小说中经常见到的死亡叙事。这篇小说的创意也非常有意思,亡灵顽强地寄居在活人耳朵中,穿梭于阴阳两界。其实鲁迅在散文集《野草》里也有大量死亡叙事,也试图通过亡灵和阳间的不同时空,以死人的视角去讲述活人的世界。您写《裸露的亡灵》的灵感来自哪里?怎样展开死亡叙事的先锋性开拓?
夏商:《裸露的亡灵》是我第一篇长篇小说。2000年动笔,到今年刚好20年,时间久远,具体的写作动机记不清了,早期小说受先锋小说影响那是肯定的。亡灵视角可以使叙述空间放大。另外,纵深度和我过去的小说不一样,这部小说没有主角,或者说没有刻意安排主角。很多人没有读出我小说里的群像性,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小说的部分功能是还原现实,《裸露的亡灵》也没有安排不可或缺的角色。有人问我,这个人物看上去还蛮重要的,怎么半道就离场了?难道这很难理解吗?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一些看似很重要的人物不都半道离场了。
张娟:《裸露的亡灵》结尾安文理看到了彩虹,让我感觉有点刻意为之,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夏商:可能和人生观有关吧,我的长篇小说都比较忧郁且灰色调,基本上我认为人生充满了愁苦和迷惘。正因为这样,反而要活得更积极一些。如果知道如此,生活态度还很消极,就更没什么念想了。所以在小说结尾,情节允许的前提下,会尽量明媚一些,给人生一点盼头吧。
张娟:我觉得鲁迅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内心充满悲观,往往也会在小说最后添加一点亮色。他希望能够肩着黑暗的闸门,让后面的人过得更加快乐一点。
夏商:《野草》里有一句让我感触很深——“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张娟:鲁迅创造了很多现代文学的母题,《阿Q正传》里面的未庄就像一个中国的缩影。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乞儿流浪记》,故事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岛上,然后去描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也类似于一个人类生存的预言。您在写小岛的时候,写出了被文明开化前的状态,写出了野蛮的生命力,这跟您对于底层社会的了解有没有关系?
夏商:我觉得作家写到最后,归根到底还是写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接受应试教育时间短既有负面作用,也有好处。没有高学历,一直自谋生路,比同龄人会多一些磨砺,算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后来又痴心妄想成为作家,自学过程很艰苦。因为基础差,通读过1979年版《辞海》,为增加词汇量,把《同义词词林》几乎背了下来。但在遴选文学和社科书目时,则完全按自己兴趣来,不用考虑测验考试,就是为了喜欢而读。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自觉意识一旦形成,给我洗脑就很难了,因为不管你有多大名头,你提出的任何观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质疑,这已经成为一种本能。我想这是提前离开应试教育的一个最大收获,不崇拜,不盲从,不人云亦云。当然,质疑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结果。质疑之后,还要学会分析和甄别,才会接近真相,仅仅只有质疑,也会陷于偏执。
说到底层,看怎么定义了,事实上,在公权力为高层的社会等级划分中,我就算底层吧。我一度认为,自己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和机构,一直在做命运的主人,转而一想,其实还是在做命运的仆人。《乞儿流浪记》中很多像野狗一样活着的人物,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人生行旅中某个侧面或状态的投射。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一段人生是被浪费的。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每个人的命运都可以更好一些。虽然坎坷可以成为作家的创作矿藏,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当作家,更何况,文学也不是世界的全部。
当然,广义上说,每个人过得都不容易,过分强调自己的艰难也是矫情的。至少,我成年后没有经历很大的社会动荡。1949之后,大规模战争有“韩战”和“印战”,但从我出生的1969年到现在,只在1980年代发生过“越战”,而且发生在边陲,上海总的来说是比较太平的。从开埠以来,上海虽曾被称为冒险家乐园,其实一直比较太平。对普通市民来说,上海似乎一直是“法外之地”,淞沪战争那场恶仗打得那么惨烈,一旦接近租界,硝烟就淡了很多。四行仓库谢晋元部的阻击战,苏州河对岸的市民还看热闹呢,孤岛时期的上海可能是大陆最安全的地方了。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从未见过的祖父,是他把一家人从苏北乡下带到上海落地生根,单这一点,我就比那些至今仍在祖籍地的同姓族人幸运得多。相对于同龄人,我因为谋生早,要去做一些非常世俗和琐碎的事,偶尔也会产生自我怀疑。福利是,浸淫其中,对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比较熟悉,对人间冷暖的感受会更敏锐一些。
张娟:其实像《东岸纪事》这种小说,正因为您有这样的经历,才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您的写作。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东岸纪事》有很大的反响,大家的评价也非常高的原因。您这种生活经历其实赋予了写作一笔很大的财富,使得您可以写出非常扎实的生活细节。还有像您的另外一本书《标本师》,也是非常富有生活的细节和质地。您在写完《标本师》之后,提出“知识小说”的说法,包括您后来在写作里直面现实,而不是仅仅去关注写作的技巧,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事实上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您身上,其他先锋作家基本都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回归,您对当下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呼应是怎么看待的呢?
夏商:可能用“主义”来归纳小说,批评家更擅长。小说家在创作中,并不会想到“主义”这种抽象概念。有些小说家喜欢写文论,有的还喜欢写文本分析,我要说的是,很多作家的文本分析比小说写得好。小说是一种模糊的艺术,能够把小说分析得那么清晰,那一定是过度解读。我很少解读文本,只对自己正在写的文本考虑更多。对正在写的小说属于什么类型并不那么在意,写实主义也好,抽象主义也罢,在意的是最后的完成度。以《标本师》为例,它是《东岸纪事》之后我创作的一个新长篇,其实它有一个“前本”,叫《标本师之恋》,是一个中篇小说,很多年以前发表在《时代文学》上,花城出版社还出过单行本。为什么推翻重写,因为当初太匆忙没写好,刚巧遇到一个契机,认识了一位标本制作大师,了解了标本制作的过程,就产生了重写的愿望,不但是植入了大量标本制作的细节,故事的走向也是重新构思,使它成为一部全新的作品。
关于提出“知识小说”这个说法,是因为通过《东岸纪事》的写作,让我觉得小说中的知识含量非常重要。《标本师》是那种一目了然的知识小说,有大量标本制作的专业知识加持。但我说的并不仅限于专业知识,也包括民间风俗、生活常识和博物学小百科。这种庞杂的“知识”和专业知识是不一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东岸纪事》中写到炒螺蛳之前要滴一些菜油,放在水缸里养一个晚上,螺蛳才能吐出杂质变得干净,吃起来才没有泥土味。
张娟:这样的“知识”没有生活经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其实这几年知识小说非常受欢迎。大家在看虚构故事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干货。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开始去写现实主义小说?虽然说您不喜欢这种理论派的总结,但它事实上在文坛上形成了群体性现象。前几天我跟另外一个评论家也聊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谈到,有没有可能存在着“中年写作”这个现象,就是说当年的先锋和后先锋作家,在个人的生活经历里面,逐渐从青春热血希望变革的写作态势,转化到如今的去关注现实的这样一种写作。您对“中年写作”这个问题怎么看?
夏商:你说的“中年写作”是指小说遇到了瓶颈?
张娟:不是小说的瓶颈,而是您自己在经历中年的过程中,带来的对于人生体验,对于世界的关注方式的转变,甚至价值观的转变。
夏商:我之前有个讲稿的标题叫“写作是中年人的事业”。对写作我没有很大的迷茫,尤其《东岸纪事》写完以后,对题材的驾驭和对故事的调度应该说更得心应手了,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知识储备不够,看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道得少,看书有个怪圈,一本书会引出其他书,没完没了,这个怪圈既有乐趣,也很烦人。
张娟:“中年写作”带给作家的可能是正面意义,我在跟另外一个作家做访谈的时候,他也谈到年过五十以后——就像您刚才讲到的那样——对自己的写作更有掌控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夏商:可以这样理解,我认为接下去自己的文本完成度会更高。我现在越来越看重价值观和世界观,三观确实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高度和宽度。一些作家很有名,作品反映出的价值观却很奇怪,说奇怪是客气的,是很荒唐。小说其实就是你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三观不正,小说怎么会好?可能有些人不同意我这个论调,认为小说仅仅是一个讲故事的艺术,三观是不重要的,我不认为这样。
张娟:您是一位很接地气的作家,请问有没有对您影响很大的作家?另外,有没有编辑或者说刊物,曾给过您鼓励或者说强大的精神动力的,还是说您写作的精神动力仅仅来自于对文学的渴望,和文学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
夏商:也没必要把动机说得那么高尚,我之前搞文学,就是想改变命运,工厂太苦了,想离开工厂。后来通过自由投稿发了一些东西,发现在这方面似乎有一些才华,就坚持下来了。再后来,慢慢对文学就产生了真爱,说相依为命虽然有点矫情,也是实际情况,一件事你坚持了三十多年,显然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作为一门专业门槛很高的手艺,我当然有很多“老师”,这个名单很长,前面也提到一些,就不赘述了。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小说,应该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聚斯金德的《香水》吧。
张娟:您讲到《香水》给您的影响很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是个恶人。您的小说也塑造过肮脏丑陋的群氓,其实人性是微妙而复杂的,您如何看待善恶?
夏商:很多读者有个错觉,认为小说应该是唯美的,宣扬美丽人生的,认为小说就要写正能量。其实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好小说都是写假丑恶的,就是写负能量的,就是写那些不可理喻的、不可名状乃至肮脏丑陋的人和事,提醒你世间的悲苦艰辛。想宣扬真善美,写心灵鸡汤就可以了,我的小说中有很多人物按世俗标准看属于负面角色,我对他们的兴趣远远超出正面角色。其实日常生活中哪有那么多正面人物,人性之幽微,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我写小说追求一种“零度”,作家尽量不对人物进行评判,也就是说,他们的好坏与作者无关,作家只须客观地把人物的状态写出来即可。
张娟:再回到《东岸纪事》,我读的时候既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气息,某些地方又有《聊斋志异》的感觉,一种民间的神秘主义。
夏商:民间的神秘主义这个说法好,要知道在读西方小说之前,我接触最多就是《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聊斋志异》,先是读连环画,后来读原著,我还有一个一肚子故事的老祖母,从小跟着她看民间戏班子的野戏,有个草台班子经常来演江淮戏《追鱼》。《追鱼》的故事跟《白蛇传》差不多,无非就是把白蛇精换成了鲤鱼精,这种神道鬼怪的东西从小镌刻在脑子里,等到写小说的时候自然就会冒出来。另一方面,像《东岸纪事》这样的村野题材,我记忆中的老浦东,本身就包括了很多神秘元素。
张娟:在阅读您作品的时候,发现小说语言给人一种泥沙俱下的感觉,十分具有男性气息,站在女性视角来看,能感受到一种男性沙文主义,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夏商:近些年我其实越来越注重对语言的推敲,小说既是讲故事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另一方面,我对文字的使用是不设限的,俚语切口脏话,包括男女生殖器,该用的时候绝不含糊,也不允许编辑用叉叉来代替。所以我的小说语言就会给读者留下比较狂放不羁的印象,我用的每个字都是字典里可以查到的合法汉字,可能有些女性看了会感到不适,觉得露骨,但我只是想把生活中真实的样子呈现在文本上。而且我的小说中底层小人物占了很大比例,所谓的“粗俗”正是他们的生活状态,写成文绉绉的样子反而很假惺惺。
张娟:我觉得鲁迅的《阿金》与您小说中的底层泼辣女性形象挺相似的。鲁迅在上海的后期其实也写这种底层女性,还传达出来一种对女性问题的思考。
夏商:因为我最近在写老民国故事,了解了一些资料,当时很多文人去嫖娼,甚至娶妓女,很多军阀和政客娶的小老婆都是青楼女子,照样摆酒席大宴宾客,似乎也没人嘲笑,接到请帖的都会跑去吃喜酒。
张娟:《海上花列传》就写到这种状况,那时候中国人没有空间谈恋爱,到青楼去能够体会到恋爱的感觉。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些狭邪文本中的情爱话语更接近于现代爱情。
夏商:确实,有些人到妓院去,并不完全是解决生理需求,同时还有情感需求。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时的所谓嫁娶就是同居,《亭子间嫂嫂》就有这样的情节,男方只要在报纸登个消息,婚约就解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婚姻的看法并不那么神圣,不在于形式,而是更看重感情。
其实别看现在的姑娘尤其是大城市的姑娘,自觉意识很强,对婚恋特别有主见,结婚也越来越晚,其实中国人能自主恋爱的历史是非常短的。我祖父母这代人就别说了,基本是包办婚姻。我父母这代人,因为生活圈小,选择余地很小,大多靠三姑六婆介绍。我1980年代中期进工厂,团支部经常组织联谊会,召集幼儿园老师、医院护士、纺织女工来联谊,在食堂跳交谊舞,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异性。真正的自由恋爱,可能是最近二十年才有的。因为网络和各种社交媒体的普及,人的社交方式敞开了。
四、海外写作:中国故事与自由精神
张娟:到了美国之后,一个说英语的环境,您觉得对写作有没有影响?
夏商:老实说,我有足够的中国故事可以写,慢慢写,写个二十年都没问题,二十年以后可能对美国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会不会写一些美国故事我不知道。即便写,可能也是写华裔在美国的故事,或者说华裔和其他族裔之间的故事,纯粹的白人故事或非裔拉丁裔的故事想必不会写吧。我的兴趣点还是中国故事,毕竟我五十年都在上海,经历了很多也见证了很多,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来纽约生活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写一个陌生国度的异域风情,我也不是那种布尔乔亚式的旅行作家,对花骚洋气的题材没什么兴趣。但是换一个写作场景,又隔得那么远,我认为还是有好处的,比方说我当时写《东岸纪事》,就是因为离开浦东搬到浦西,去浦东少了,反倒有了一丝眷恋,产生了为老浦东立传的念头。如果一直住在浦东,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也就不会想起去写浦东。同样的,隔着太平洋遥望上海,距离感自然会产生乡愁,离开这个地方了,反倒看得更清晰。
张娟:您会有这种类似乡愁的感受么?
夏商:乡愁当然会有,每个人对乡愁的定义不同。对我这样一个吃货来说,最大的乡愁就是江南的菜肴吧。
张娟:我刚才也在想江南的菜肴可能是您最大的乡愁。
夏商:江南菜确实是我的一个牵挂,一些江南特有的食材,纽约的华人超市是没有的,像螺蛳、河蚌、黄鳝、鲫鱼、胖头鱼这样的河鲜,还有草头、白芹、鸡头米等农作物,还有我的最爱鲜蚕豆。不过我在华人超市发现了速冻蚕豆,当然不能和新鲜的比了,但多放点油多焖一会儿,味道也还凑合,聊胜于无吧。偶尔也能买到阳澄湖大闸蟹,据说是空运过来的,价格不便宜,是不是阳澄湖的就天晓得了。大陆这些年非常火的小龙虾倒是很常见,过去有个阴谋论,说小龙虾很脏,是日本人特地研发出来祸害中国人的。其实小龙虾是天然物种,原产地就在美国,具体是在新墨西哥州还是俄克拉荷马州我忘了,美国小龙虾可能水质原因,壳更硬一些,也蛮好吃的。除了江南食材,还有一个乡愁就是一些老朋友。不过因为有了微信朋友圈,大家都在这个空间里,也没有很强烈的疏远感。
张娟:您刚才讲到小说的语言,说鲁迅的语言是文白夹杂,还不是特别成熟的白话文。《东岸纪事》里把上海口语写入了小说,虽然不是特别多。这个跟您前期的普通话写作有很大的差别。最近几年大家其实对沪语写作还是比较关注的,您对写作语言是怎么考虑的?以后会选择尝试完全用沪语写作么?还有像您现在移民到了美国,虽然时间还不是很长,但语言环境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语言环境的改变会对小说语言发生改变么?
夏商:我手头在写一个苏北人在上海的大长篇,算是《东岸纪事》的姊妹书吧。当中除了上海方言还会有苏北方言,再加上上帝视角的普通话,等于文本中至少要呈现三种语境。从技术上来说,会有一些挑战,但还是可以解决的。北京作家写京味小说,天津作家写津味小说,上海作家写沪语小说,无非是一个作家正好出生或长期生活在某个地域,又准备写以这个地域为背景的小说。既然是地域小说,当然要有一些方言,如果用普通话来写,也不是说不可以,可能会欠缺一些味道。我认为方言对小说文本不会起到颠覆性作用,它只是一个味精,少量加一点会更鲜美。
张娟:您现在定居纽约,对海外华语作家也有了较多了解,目前也担任《海外华语小说年展》的策展人,在这样一个跨文化的环境下,您对海外华语写作有什么看法?
夏商:以北美为例,目前活跃的海外华语作家,移民前就是比较成熟的作家,比如卢新华、严歌苓、王芫、张翎、李凤群、虹影、施玮、薛忆沩、陈河。海外华语文学的增强主要得益于移民的大陆成名作家增多,而不是自发性的、原生态的变强。当然,也有在海外成长起来的作家,比如陈谦、袁劲梅、张惠雯、凌岚、李一楠,但比较少。
另外,我认为一些海外华语作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于看重大陆的文学界对他们的评价。你的作品在大陆文学刊物发表没有问题,说到底,文学刊物都是纳税人的钱办的,是公器,物理上来说,不过就是一个纸质媒介,印出来给读者看到而已。我觉得海外华语作家,应该在创作理念和立场上有更强的独立意识,专注于文学本身。如果试图谋求发表之外的其他好处,就很好笑了。
张娟:对,我认为身在海外其实应该更加自由地创作。我之前在采访陈河的时候,他也谈到,他现在之所以能一直写下去,是因为写作是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才能保持创作的活力,我觉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好的状态。
夏商:没错,海外华语作家理应是独立而自由的写作者。
张娟:谢谢您接受访谈,祝您在海外生活中获得新的写作资源,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南京—纽约
ZOOM视频对话+笔谈
2020年8月27日—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