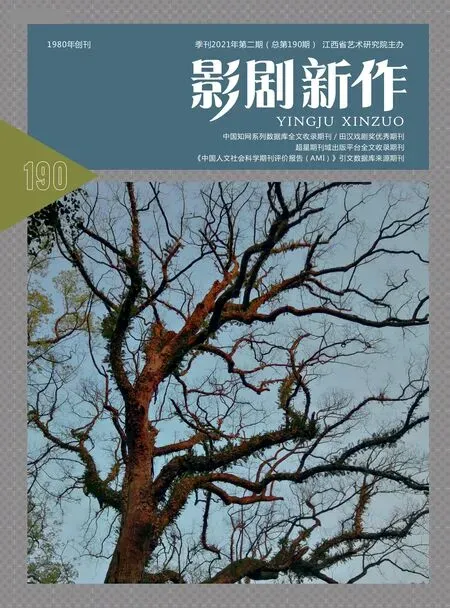新排话剧《父亲》中的人物形象嬗变
郑蕴蓉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其代表作包括《父亲》《朱丽小姐》《梦的戏剧》《鬼魅奏鸣曲》等。其中《父亲》是斯特林堡早期的作品,完成于1887年。这部自然主义悲剧是现代戏剧的奠基作之一,表现了两性之间恒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尉阿道尔和妻子劳拉因为女儿伯塔在何处接受教育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一事件成为二人冲突爆发的导火索,劳拉抓住了阿道尔脆弱多疑的弱点,让他怀疑自己不是女儿的亲生父亲,同时利用和亲友间往来的书信制造了丈夫精神失常的谎言,阿道尔最终精神崩溃,劳拉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孩子的控制权。
《父亲》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并非全是赞美的声音,也有批评。左拉曾就这部作品给斯特林堡致信写道:“说实在话,我对那些简短的分析感到吃惊。您大概知道我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我喜欢人物都有完整的婚姻状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和我们呼吸着一样的空气。而您的上尉名不符实,您的其他人物几乎都是凭空制造的,没有给我对生活的完整感觉,而这一点就是我所要求的。”[1]该作品的问题在于,斯特林堡为了强化两性之间的冲突,而将人物的个性剔除,使人物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概念化和脸谱化。[2]中国的戏剧人在2018年7月将《父亲》重新编排,再度搬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作品从原著中汲取养分,进一步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填补、还原、重塑了人物的个性,在当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下给人物以新的解读。
一、性格塑造:温和退让与傲慢专横的反转
斯特林堡本人婚姻不幸,《父亲》系在他第二次婚姻存续期间创作。彼时,他深受偏执狂症状的折磨。斯特林堡曾在信中写道:“对于我来说,它好像是我的梦游,就好像虚构和生活混在一起。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是虚构,或者是否我的生活实际就是如此。”[3]也就是说,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剧作家本人不幸的感情经历。斯特林堡从自己的主观世界出发,塑造了阿道尔这一人物,劳拉则是作家妻子的化身。毫无疑问,作家情感的天平始终向男主人公倾斜。
原作中,阿道尔善良、博学、充满智慧。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给女儿毫无保留的爱。虽因生活琐事和劳拉产生嫌隙,但仍然爱着妻子,一直保留着劳拉小时候的布娃娃和洗礼帽。但阿道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的性格有着极为软弱的一面。与女性共同生活、交往的过程中,他一直是一个受害者,母亲给了他先天不足的体质,姐姐要他低声下气,初恋女友害他生了十年的病。在他自己的家庭里,妻子劳拉是一家之主,在军营威风凛凛的上尉回到家却像“进了老虎笼子一样”。[4]149劳拉发脾气时,阿道尔甚至感觉“怕她”。[4]150夫妇二人虽然在女儿教育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阿道尔也担心劳拉不满,不安地征求女儿的意见:“如果妈妈不答应怎么办?”[4]166在两性关系中,阿道尔的态度大多时候是温和忍让的,只是在故事最后失去理智时才做出伤人的举动。
原作中的劳拉则是一个专横、非理性且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和占有欲的女人。"小时候,她经常在地上耍赖,直到别人按她的意志办才算完事。”[4]184-185任性、乖张的小女孩长大之后在家中掌权,控制一切,为了不让女儿离开自己的控制范围,执意阻止她去远方接受更好的教育,甚至不惜让丈夫怀疑女儿的血缘,不择手段地控制女儿的人生选择。当阿道尔最终被当作疯子穿上紧身衣时,她却对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要这样的事发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只是顺着你的路子去做。既是我犯下的罪,在上帝和良心面前,我也感到无罪。”最终,亲手把丈夫送上绝路时,劳拉也毫无悔意。原作中,这个人物被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加害者的形象。
斯皮瓦克认为,“斯特林堡始终将他多灾多难的生活比作如地狱一般,他的受难于地狱的想象力如同他一贯的厌女症,常常在不同的物体间转换”。[5]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斯特林堡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极端主义、尼采式的思想。诸如爱是痛苦,婚姻是战场,女人是邪恶的,而生活又如同地狱。[6]顽固的厌女症是斯特林堡的痼疾,不论在斯特林堡的真实人生还是在创造出来的文学世界中,他对内心强大的女性都抱有极不友好的态度。
剧作家本人的化身阿道尔是一个具有复杂个性的圆形人物,他表面是一个威严的军人,内心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而劳拉则被塑造成了扁平人物,狡诈邪恶,冷酷无情。用常理判断,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如果一直分别处于弱势和强势的地位,那么女儿教育的问题可以顺理成章地由强势的一方,即劳拉来决定,两个人物的冲突、斗争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因此,这个作品被一些评论家认为过于主观、抽象。新排话剧作者从斯特林堡的主观视角中抽离出来,从客观的视角“还原”了两位主人公更加真实的性格。
新排话剧重新塑造了阿道尔的性格,他对待妻子的态度变得傲慢无礼。劳拉向他索要零用钱时,他只顾做自己的事情,显得极不耐烦,还要求妻子必须留下账单。在被劳拉问到自己是否同样要留账单时,他说:“这不关你的事。”阿道尔待人待己使用双重标准,也根本不屑对此做出任何解释。这一改动非常符合人性,阿道尔的行为源自对自身的男子气概缺乏自信,因此,试图通过颐指气使的态度加以补偿。这一改动为男女主人公的斗争冲突埋下了很好的伏笔。阿道尔外在的傲慢无礼和内心世界的脆弱无助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他虽然履行着家庭责任,内心却希望把责任抛到一边,重新回到被奶妈宠爱的儿童时代。新排话剧中阿道尔被劳拉称为“巨婴”。“巨婴”指心理上仍处在婴儿水平、不够成熟的成年人。从妻子的角度看阿道尔,他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丈夫。这一改动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人物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
新排话剧中,劳拉的性格和原作也有很大的不同,她不再是原作中非理性的“恶魔”,而是温和而克制的。多年的婚姻中除了最初的甜蜜,更多的是男权的压迫和两性关系极不平等,爱情被消耗殆尽,最终由爱转恨。劳拉妥协过,也退让过,但所有的努力也换不来丈夫的理解和尊重,经济上却不得不屈辱地依附于丈夫,心爱的女儿也要被丈夫送去城里读书。失去女儿,劳拉将一无所有。第二幕,男女主人公的矛盾达到了顶点,争吵中阿道尔恼羞成怒,他“以男人的样子”把劳拉“当作女人征服”。劳拉的尊严遭到了彻底的践踏,她从此不再退让,两人正式宣战。“征服”在原著中并未明确描述,新排话剧中被处理成一段舞蹈,充满着控制与反抗、痛苦和挣扎,将人物内心世界做了诗意的外化处理,丰富了表现手段,为作品增添了一抹东方戏剧的写意之美。新排话剧中的劳拉被塑造成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性,她的形象变得更具有抗争精神的,也因此更加丰满,更加立体。
二、价值取向:解构二元对立的善恶观
除了个人生活经验的影响之外,社会思潮对斯特林堡的思想倾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斯特林堡在许多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的,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却是保守的。瑞典的妇女解放运动早在19世纪下半叶便已出现,女性逐渐觉醒,反抗男权社会的禁锢,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女性组成政治团体,要求在选举权、财产等方面被赋予和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力。北欧各国包括瑞典早在20世纪初,就立法给予妇女选举权,早于西方其他大部分国家。斯特林堡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在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同时,西方还出现了“男性危机”。相应的,在文学创作上,女性角色不再甘于一味充当“家庭天使”这样的角色,而是成为了“新女性”,她们“扰乱父权社会的性别秩序,威胁男性的社会地位和性别权威”。[7]对此,男性感到焦虑和困惑,产生出一种无力感,在遇到意志强大的女性挑战时,可能变得歇斯底里。这个时代许多男性作家(包括斯特林堡)笔下的女性人物多以加害者的形象出现,男性人物则深受其害。
原作中,男主人公意识清醒时在道德上是无可指摘的,精神崩溃时却做出袭击妻子,试图枪杀女儿的行为。当然,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妻子劳拉。可以说,原作中的阿道尔几乎是全善的。劳拉被塑造成了恶魔,她冷酷、狡猾、虚伪又无知,把丈夫逼入绝境。道德层面,斯特林堡毫无疑问地站在阿道尔一边。《父亲》是一部有着自传味道的作品,斯特林堡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二元对立的善恶观与“真相”之间的距离给现代戏剧人带来了创作空间。新排话剧将斯特林堡当作不可靠的叙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解构了原作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给人物赋予更加真实的色彩。
新排话剧受到了新时代风潮的影响。距离话剧《父亲》诞生百余年后,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真正地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女权成为了新的“政治正确”。相应地,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人公的形象也不再扁平而单一。新排话剧从上尉的不可靠叙事出发,顺着人物和逻辑,从真假参半的情节中还原了更加真实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塑造出了更加丰满、立体的人物,更加令人信服。
新排话剧中,男主人公在道德上不再完美无瑕,内心的虚弱让他对自身的性别身份感到十分焦虑,他恐惧女性的挑战,外在表现得对妻子很不尊重,独断专行,在家庭经济和两性关系上试图占领绝对的主动,掌握不容置疑的领导权,借此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阿道尔本性上的善良不再表现在前期对劳拉的退让上,而是表现为后期夫妇二人宣战后的种种不忍,在原作中情绪失控时用台灯袭击妻子的行为在新排话剧中被处理成了劳拉的谎言,试图指向女儿的枪口最终也对准了自己。新排话剧的处理没有改动人物的精神实质,反而使人物的善良更真实,更富有层次,更有感染力,令人更加同情。剧本将劳拉的行为动机处理得更为合理。在婚姻中得不到丈夫的尊重的妻子即将被迫与心爱的女儿分隔两地,她的反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道德上,劳拉不再是十恶不赦的加害者,变得更加值得同情,她的罪恶也因此被削弱。在和阿道尔临死前最后一次交谈中,她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忏悔。新排话剧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反面人物,现代戏剧人不做道德判断,而是从人性出发,刻画了细腻的人物情感。
三、结语
中国的当代戏剧人基于斯特林堡的男权视角的叙述,从中找到关于“真相”的蛛丝马迹,颠覆了原作背后的性别政治和男权话语,把带有原作者个人情感和道德偏好的人物塑造得更加真实、复杂,符合人性。男女主人公人物性格和道德层面的反转十分自然,且合情合理。新作品作者从真实的人性出发,用现代人的道德取向重新丈量了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的一场家庭悲剧,得到了和原作作者不同的结论。新排话剧对主要人物不做单视角的判断,从不同角度挖掘人性更为幽微之处,将判断的权力还给观众。作品通过重塑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价值观,打通了经典作品和现代观众的沟通窗口,引起观众的心灵共振。新排话剧是这个时代的镜像,反映出新的价值取向。此外,在戏剧冲突的表现手法上,《父亲》创造性地加入了舞蹈的元素,在台词之外,演员用戏剧性的肢体语言表现男女主人公绝望的纠缠,激烈的碰撞和痛苦的挣扎,把观众深深地带入上尉和劳拉家庭危机暗涌之中。这部作品在思想层次和视觉审美上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为未来经典话剧的新排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和值得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