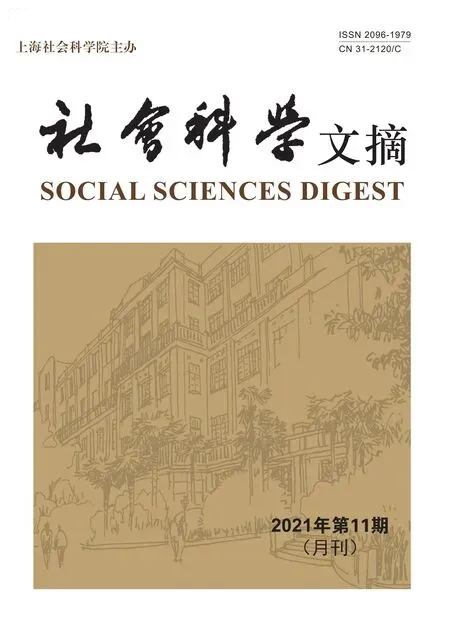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
文/冯俊
(作者单位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摘自《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回顾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特色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成就,正视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发展前景,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西方哲学在文化启蒙、解放思想、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三种资源: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这三种资源在交融互动中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同时又共同推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通过三个途径进入中国:第一个途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赴日本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传播;第二个途径是赴欧美留学生对它们的传播,最早是严复等留学英国的学者,后来主要以赴法、德等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为主体,此外还有来华的英美和欧陆学者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来中国讲学,直接传播相关思想;第三个途径是留俄、留苏的学生与共产国际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哲学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传入中国的。没有西方哲学和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大量引进和输入,中国人也没有机会发现马克思主义。
从百年来哲学发展的历程看,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一起参与中国文化启蒙、解放思想和社会变革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包含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达到高潮,产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20世纪初,戊戌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与此同时,严复对于穆勒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介绍,王国维对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研究,马君武对于黑格尔、斯宾塞、穆勒、狄德罗、拉美特利、托马斯·莫尔、圣西门等人思想的研究,章太炎对于古希腊哲学、经验论和理性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诸多哲学家的研究,蔡元培对于康德哲学尤其是美学的研究,张颐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对于柏格森哲学的研究等,都起到了“西学东渐”的作用。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大量翻译、引证和论述,使西方哲学在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五四运动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而奔走的同时,蔡和森、瞿秋白、陈望道和李达等也在翻译介绍和研究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除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之外,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也先后发表,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就是在引进西方哲学各种学说和社会思潮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引进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以来取得最为重大的历史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列主义被共产党人确认为真正能改变中国命运的真理。
西方哲学在文化启蒙、解放思想、推动中国社会变革方面的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引进推动了中国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让中国人再次开眼看世界,产生的重大事件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1949年以后,中国的哲学界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和来华苏联专家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苏联学习,使哲学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政治化和教条化;另一方面受冷战和“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思潮的影响,西方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批判的对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思想解放助推了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兴盛,反过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繁荣又助推了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启蒙、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发展。
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1979年在太原举行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是中国西方哲学界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大事件。“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在外国哲学研究和教学中突破“语录标准”和“苏联标准”的“禁区”,放弃了50年代以来苏联那种简单化和教条主义地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做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始对西方哲学史上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人物、著作、学说和观点进行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客观的而不是贴标签式的研究和教学。
80年代人们迎来了“尼采热”“萨特热”和“存在主义热”,“弗洛伊德热”和“精神分析热”,“生命哲学热”“结构主义热”“法兰克福学派热”和“哈贝马斯热”,波普尔、库恩和“科学哲学热”;继而90年代兴起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现象学热”,“分析哲学热”和“语言哲学热”,罗尔斯和“政治哲学热”,福柯、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热”等,相关哲学家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和介绍,大学里的此类课程十分热门和抢手。广大学生与社会青年之所以热衷于学习和了解西方哲学,不仅是要补足以往我们哲学研究和相关知识的缺失,而且是希冀能从中找到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1.学科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体现在三点上,一是学科自身的体系化,二是学术机构和学科点的设置,三是该学科提出和发现的新问题。
一是西方哲学学科自身的体系化。西方哲学学科自身的体系化有两个快速发展阶段:一个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时间。
在第一阶段,一方面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之后,学者们对西方的哲学开始进行成体系的翻译引进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唤醒国人民族独立意识、振奋国人精神的爱国情怀,因此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和新思想的启蒙,对西方的主流哲学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翻译和引进。从古希腊哲学、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哲学、18世纪启蒙思想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到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哲学,几乎都有译介。随着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学成回国后,他们开始从单纯翻译介绍转为用中国人的文化视野研究西方哲学,产生了可观的新理论成果。
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化的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经过中国学人40多年来的努力,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重要哲学家和主要学说、主要著作几乎都被引进到中国,都有人在研究。
从研究的领域来看,从改革开放之初单纯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而发展到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经验论和理性论哲学、启蒙运动哲学、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科学哲学、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过程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心灵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分析的和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伦理学,以及大数据与认识论、人工智能哲学等。另外,还有犹太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等广义的西方哲学,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可以说,凡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到的领域,中国的西方哲学界也都已涉猎,并从“跟跑”逐步接近“并跑”状态。例如,苗力田、汪子嵩、叶秀山、姚介厚、范明生、陈村富等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付乐安、赵敦华、段德智、王晓朝、黄裕生等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陈修斋对经验论和理性论哲学的研究,冯俊对笛卡尔和法国近代哲学的研究,周晓亮对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张世英、王玖兴、杨祖陶、王树人、杨寿堪、钱广华、邓晓芒、李秋零、张志伟、谢地坤、韩水法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江天骥、夏基松、涂纪亮、刘放桐等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靳希平、庞学铨、倪梁康、陈嘉映、孙周兴等对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现象学的研究,洪汉鼎、何卫平等对伽达默尔哲学和阐释学的研究,姚大志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俞吾金、张一兵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韩震对西方历史哲学和社群主义的研究,高宣扬、杜小真、尚杰、冯俊、莫伟民、汪堂家、钱捷、孙向晨、杨大春、汪民安等对现代法国哲学的研究,王路、江怡、陈波、韩林合、叶闯、陈亚军、陈真、费多益等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傅有德对于犹太哲学的研究,高新民对心灵哲学的研究,王齐对克尔凯郭尔的研究,等等。
二是学术机构和学科点的设置。从北京大学1912年设立“哲学门”开始,中国就有了专门的哲学学科点。1952年国内院系调整,只有北京大学一家有哲学系。从1956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先后开始建设或恢复重建哲学系。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以贺麟先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研究部,这是国内研究西方哲学的重要学术机构。1964年设立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专门机构。此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的外国哲学教研室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重镇。改革开放后,在恢复哲学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哲学一级学科下面划分出八个二级学科,外国哲学为其中之一,与其他七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哲学并列。在八个二级学科中,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俗称“中、西、马”,它们是哲学学科的主干。据教育部高教司的相关报告称,2020年全国现有98个哲学专业点,有哲学专业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教研室。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这两个学会在推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西方哲学学科体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该学科提出和发现的新问题。学科体系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否提出本学科特有的问题。中国特色西方哲学学科在引进和传播西方哲学的过程中,除了引入西方哲学提出的一些问题外,也开始对西方哲学进行中国式的解读,或者运用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形成了中国语境下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独有的问题。赵敦华教授曾经归纳出十个问题,包括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西方哲学术语中译问题、中世纪哲学性质问题、康德与黑格尔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问题、中西哲学会通问题、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启蒙与现代性的是非功过、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评价问题、政治哲学中“左”“右”之争、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问题。其实,问题远远不止这十个。韩震教授讲道:“欧美哲学界学术研究的论题,都被中国学者们给予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有些西方命题通过我们新的解释转换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怡教授也概括了40年来中国对于分析哲学的四条研究路径:历史路径、视角路径、问题路径、方法路径。
2.学术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学术翻译,二是教材建设,三是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学术翻译问题。翻译西方的原著原典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40年来,除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哲学类图书已经累计出版了282种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出版了很多外国哲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选集,如《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卢梭全集》《康德著作全集》《费希特著作选集》《杜威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萨特文集》《列维-斯特劳斯文集》《拉康选集》《布尔迪厄作品集》《海德格尔文集》《克尔凯郭尔文集》等,正在翻译出版的有《谢林著作集》《黑格尔全集》《胡塞尔文集》《尼采全集》《舍勒全集》《梅洛-庞蒂文集》《罗兰·巴尔特文集》等。
二是教材建设问题。从新中国70年的学术发展来看,我国西方哲学的教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译介出版的哲学史著作有葛力先生翻译、梯利著的2卷本《西方哲学史》,贺麟和王太庆等翻译、黑格尔著的4卷本《哲学史讲演录》,何兆武和李约瑟翻译、罗素著的2卷本《西方哲学史》,罗达仁翻译、文德尔班著的2卷本《哲学史教程》,冯俊等翻译、帕金森和杉克尔主编的10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周晓亮翻译、托马斯·鲍德温著的2卷本《剑桥哲学史》;有代表性的单卷本哲学史有童世骏等翻译、G.希尔贝克和N.伊耶著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20世纪》,洪汉鼎等翻译、D.J.奥康诺主编的《批评的西方哲学史》,韩东晖翻译、安东尼·肯尼著的《牛津西方哲学史》,冯俊等译、安东尼·肯尼著的《牛津西方哲学简史》等。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最早是由洪谦等人编写的《哲学史简编》,以此为基础汪子嵩等改写了《欧洲哲学史简编》,后有朱德生和李真编写的《简明欧洲哲学史》,李志逵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刘放桐等编《现代西方哲学》,陈修斋和杨祖陶著的《欧洲哲学史稿》,夏基松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冒从虎等编著的《欧洲哲学通史》,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于凤梧等人主编的《欧洲哲学史教程》,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新世纪以来有赵敦华著的《西方哲学简史》,张志伟主编的《西方哲学史》,邓晓芒、赵林著的《西方哲学史》与由赵敦华和韩震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大部头多卷本哲学史主要有: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冯俊主编的5卷本《西方哲学史》,还有汪子嵩等的4卷本《希腊哲学史》,涂纪亮的3卷本《美国哲学史》,黄见德的2卷本《西方哲学东渐史》,等等。我国西方哲学的教材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与时俱进。根据目前状况,中国大概是世界上非西方国家中编写《西方哲学史》最多的国家。
三是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我国老一辈的西方哲学学者如贺麟、洪谦、任华、严群、庞景仁、全增嘏、熊伟、王玖兴、江天骥等有出国留学经历的老师,和苗力田、王太庆、陈修斋、汪子嵩、张世英等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老师,他们都既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又有很高的外语水平,既能翻译西方哲学的原著原典,又能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50年代至7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代,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都没有机会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外语,但还是出现了像杨祖陶、叶秀山、梁存秀、刘放桐、夏基松、姚介厚、王树人、陈启伟等出类拔萃的学者。80年代之后,随着国民教育体系的逐步健全和对外开放,中国学习西方哲学的学者又有机会出国读学位或做访问学者,使我们的西方哲学师资水平得到了整体提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西方哲学师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从世界名校哲学系毕业的优秀博士陆续归国任教,很多高校还直接招聘海外师资。国际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国内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上几乎是同步的,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大。另外,中国的西方哲学界创办了《外国哲学》《哲学分析》《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德国哲学》《法国哲学》等学术刊物,还有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前沿》杂志。
3.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包括西方哲学在中国产生的标识性概念,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影响,西方哲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首先,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国原本没有的一些标识性概念。中国学者通过翻译西方哲学原著,让西方哲学说现代汉语。在中国出现了本体、理念、形式、质料、主体、理性、知性、感性、直观、意志、自由、现象、先验、超验、绝对、异化、纯形式、生存、沉沦、应然、概然、此在、证实、证伪、身体、他者、解构、延异等核心概念,这些术语被引入现代汉语。它们是中国译者们不断思考、研究的结晶,既深刻、准确地表达了西方哲学的原意,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形成了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
其次,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面貌。例如,价值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之争、主体性问题、社会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发展观问题、公共性问题、生态问题、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等,成为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波普、库恩、罗尔斯、查尔斯·泰勒、桑德尔、利奥塔、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名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文中出现的频率甚至超过了在西方哲学论文中出现的频率。西方哲学对于时代性问题的思考、许多重要的哲学范畴和研究方法、很多概念和话语,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吸收借鉴、转换融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提升了理论思维水平。
再次,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促使中国哲学改变了面貌。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20世纪上半叶,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运用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和方法建构起中国哲学史的框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学界也展开了讨论——到底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到底是跟着讲、照着讲还是自己讲、讲自己?这些讨论增强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二是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例如,杨适对东西原创文化的研究、王树人对“象思维”的研究等。再如张世英晚年思考中西哲学的结合问题,以世界性的视野,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万有相通论”。陈来就本体论、生命哲学、价值理念等在中西之间进行比较,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一些理念,创建了“仁学本体论”等。三是对中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张祥龙、张汝伦、倪梁康、王庆节等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致力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这些西方哲学的学者也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力量。
最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们要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发出声音、占有一席之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康先生就曾自信地说,要让西方研究希腊哲学的人以不懂中文为遗憾。洪谦、金岳霖、沈有鼎、王浩等中国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逻辑学等领域作出了贡献。邱仁宗考察了波普尔对卡尔·马克思思想的批评,陈波关于克里普克的只存在“后验偶然命题”、不存在“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批评意见等在国际哲学界引起了关注。江怡还被推选为国际分析哲学史学会执委,这些都是国际影响力的证明。
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成就蔚为大观。然而,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发展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赶热点、赶时髦现象。研究和教学存在着“冷热不均”,这些反映出学术的浮躁之风。
其次,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日益专业化职业化的同时形成了新的学术壁垒,彼此隔绝、自说自话。学术领域越分越细、越来越专,研究英美哲学的不懂大陆哲学,研究大陆哲学的不懂英美哲学。在英美哲学内部,研究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心灵哲学的互相也不懂;大陆哲学中,研究德国现象学的人不了解法国现象学,研究现象学的也不懂社会政治哲学。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些领域已经出现支离破碎、画地为牢的现象。
再次,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研究正日益脱离社会现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工作者要观照现实、参与现实,要关注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不能单纯以西方人的问题为问题,不是为了帮西方人发展他们的哲学,而是要从哲学上回答中国当代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我们反对政治化、标签化、简单化、公式化等错误倾向的同时,在一定程度又产生一种“去政治化”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几乎失语、失踪了。
最后,中国的西方哲学越来越被社会边缘化。一方面,有些学者用一些生僻甚至怪异的名词概念将自己变成了让圈外人听不懂、社会大众望而生畏的“洋学问”,将自己与社会大众隔离起来;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流量文化也远离和遗忘了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越来越被边缘化。
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学者为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进一步努力,对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未来前景充满希望。从目前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看,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生活世界。胡塞尔在20年代到30年代提出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从30年代中期开始,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往的舞台,生活世界又是在交往活动的实践中形成的。20世纪后半叶,存在论现象学、精神分析学、阐释学、社会批判理论、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等都重视生活世界,认为哲学必须要解决人类生存所面对的问题,应该面向现实生活。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为了克服学术壁垒,突破哲学日益脱离社会现实、被社会边缘化的现状,也开始提出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强调哲学应该关注现实,研究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生活条件,思考人及其生存的环境,人自身的创造性活动、生存意义及现实中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
第二,未来哲学。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增长,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之中。人类对未来的关切前所未有,所以有些学者提出我们要注意研究“未来哲学”。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第一个提出“未来哲学”概念,尼采的《善恶的彼岸》一书,副标题就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孙周兴教授提出具有世界性的“未来哲学”应该研究三个问题,那就是文明对话问题、人类政治问题、技术困境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技术问题。
第三,汉语哲学。近几年来,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圈内展开了关于汉语哲学可能性的讨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提出了“让哲学说汉语”的口号。这种汉语哲学,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古代哲学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板”,不是西方哲学史的“再版”,也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翻版”。这种汉语哲学,不是西方哲学的汉语翻译,但是它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丰富内涵;汉语哲学不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简单重复,但它包含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这种哲学是说汉语的,但它是世界性的、是可以翻译的。建立这种汉语哲学的任务靠单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或靠单纯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学者是完成不了的,它需要以精通西方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学者为主体、结合其他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第四,翻译、教材和研究的统一。在今天我们仍需要翻译,翻译仍然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在今天,西方哲学的教材还需要写,任何哲学史都是当代史,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视野的扩展,我们要写出这个时代新的哲学史和哲学教材。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史要不断地被重估,哲学史的叙事总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为视角的,哲学的反思又总是以一定的哲学史叙事为基础,并为自身重新确立思想坐标。所以说,哲学史和教材是常写常新的。还有学者正在进行“21世纪西方哲学史编纂学研究”,认为哲学史编纂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西方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一定是让翻译、教材编写和研究统一起来,而不是三者的分离。
第五,中、西、马哲学的对话和会通。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要发挥中、西、马哲学的对话和会通的优势。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能给我们分析评价西方哲学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中国特色西方哲学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并存,是中国当代哲学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当代哲学的特色与优势。这三种哲学形态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能力独立完成建设中国当代哲学这一艰巨的任务。中国传统哲学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西方哲学需要“中国化”,与中国哲学交流融汇,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在用好中、西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实践创新中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西、马哲学的对话和会通必将能够产生出无愧于这一时代的当代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