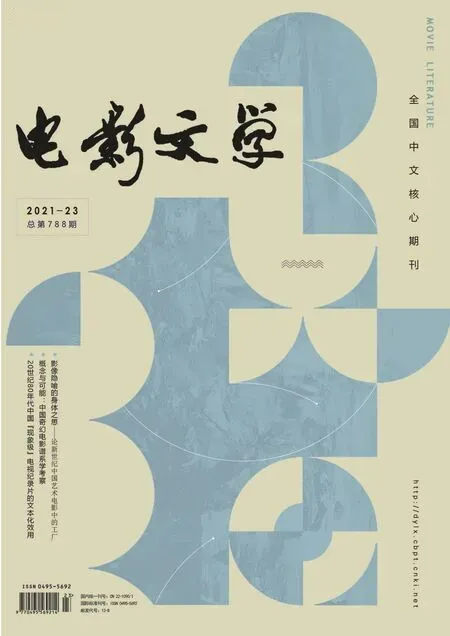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福尔摩斯小姐》的改编逻辑与现代意识
张 强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福尔摩斯小姐》上映于2021年,作为一部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故事的延伸文本,它在创作构成上、改编逻辑上以及价值观的选择上都充分展现了其创作者的个人倾向。和过去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有很大的不同,《福尔摩斯小姐》作为一部衍生电影,它并没有将叙事的焦点放置于大名鼎鼎的侦探福尔摩斯身上,而是将光环都聚焦于福尔摩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小妹妹伊诺拉。影片以伊诺拉的冒险为主线,叙述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年轻侯爵被追杀的案件;一条则是伊诺拉寻找离家出走失踪的母亲的案件。作为一部商业片,《福尔摩斯小姐》在叙事的策略上也呈现出平直的、典型化的特点,一方面它想通过伊诺拉寻找离家出走的母亲,来呈现女主角自我意识萌发和个性成长的剧情,迎合年轻女性群体;另一方面它也落入了普通少女电影的窠臼,英俊的年轻侯爵这一角色的设置,不经意消解了伊诺拉追寻母亲的路线所包含的寻找真实自我的意义,使许多桥段成了普通浪漫电影的边角料,影片在概念阐释层面的虚浮无力也就此出现。
基于《福尔摩斯小姐》影片自身,对比南希·斯普林格的原作小说《伊诺拉探案集》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将会从变动的内容和改编的方向中,发现当下的剧作创作者们所聚焦的焦点,也能够借由这些差异,分析影片《福尔摩斯小姐》中所展示的重重视觉化表征及其表征能指背后所发展和延伸的所指。
一、身份的假装:伊诺拉的伪装迭代的意义与阐释
《福尔摩斯小姐》改编自南希·斯普林格同名小说的第一部,作为一部依托《福尔摩斯探案集》诞生的衍生作品,第一部电影必然要给予福尔摩斯小姐——伊诺拉诞生、存在与参与的内在动力的解释,在影片《福尔摩斯小姐》里,这种动力被完整地展现了:伊诺拉一方面需要寻找离家出走的母亲;一方面她需要逃避迈克罗夫特和夏洛克两位哥哥带来的规训的压力。
影片非常直观地展现了伊诺拉所面临的困境,当两位兄长从伦敦回到家中时,伊诺拉首先被质疑的是她作为个人的身份意义。迈克罗夫特请来一位女校校长规训伊诺拉,女校长的台词从社会意义和个人价值评估两个层面揭示了本片的第一层主题,她在评估完伊诺拉的身材后要求伊诺拉穿鲸骨裙,并强调:“这不是囚禁,这是自由,它们能让你融入社会、享受其中的乐趣,去夺人眼球。你将会为社会所接受。在我的学校你将进一步学习如何做一位名门淑女。”换言之,一个人之所以不能成为他自己,是因为成为自己意味着就得付出被外界视为异端以致无法融入社会的代价,电影中“身份”这一隐形主题的出现,实际上昭示着后段中,躲避追杀的年轻侯爵、反复变装的福尔摩斯小姐所面临的真正困境。
在随后伊诺拉的出逃中,伊诺拉变换了三次身份:在离家进入火车时,她首先变装成了男孩,因此,她几乎毫不费力地躲开了迈克罗夫特的追查,来到了伦敦;第二次变装,则是变装成了一位贵族小姐,华丽的打扮使她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特权;第三次变装,伊诺拉变成了寡妇,因为“没有人想要靠近寡妇”,她得以安全。如果说前文中女校长的劝导是对个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的强调,那么伊诺拉在后续的变装,则成了对女校长劝导的实践。伊诺拉每次变装成功,实际上依靠的并不是独特的化妆技巧,而是某种社会规范的成见。
身份变化的主题从伊诺拉离家出走延续至此,影片实际上构筑了一个表征的世界,角色间的互动实际上是通过这些隐喻的聚焦得以实现的。在这种表征囊括的概念意义下,个体的特征丧失了它的能动性,成为被刻板解读的表征。影片主线里消失的侯爵是一个与伊诺拉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孩,作为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的年轻侯爵,实际上也在种种变装游戏后失去了身份的遮蔽,他先后经历流浪汉、花农、小厮等身份,甚至在部分身份中找到了自己热爱的方向并与伊诺拉产生了情愫。然而他一旦回到了侯爵的身份,他和伊诺拉的情感也面临着终结。尽管影片没有出现二人分别的桥段,但是在议政院前的一场,已经充分说明,在社会身份标签下,二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部分作为自然人的自由,又一次进入了身份的场域中,成为不能表达自我的人。
二、精神分析的召唤:两条案件线索的对立与重叠
《福尔摩斯小姐》的内容线索虽然繁杂,但是串联起伊诺拉命运的内容却非常明晰。伊诺拉追寻失踪的母亲是贯穿主线的核心线索。影片将母亲的离家出走作为暗线来铺排,伊诺拉沿着母亲留下的字谜线索,寻找到母亲离家的真正原因。伊诺拉寻母的过程,看似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路,但实际上被分隔成了多个不同的阶段。伊诺拉在最开始并没有打算自己寻母,而是试图让夏洛克和迈克罗夫特这两位兄长代替她找到母亲;在第二阶段她走上寻母之路时,其动力实际上来自不想去迈克罗夫特强迫她就读的淑女学校。在伊诺拉真正寻母的过程中,伊诺拉寻母的步调一再被延宕,而帮助被追杀的年轻侯爵以及寻找侯爵被追杀的原因一度成为剧情的主线。从找妈妈到帮助同龄的侯爵,这两个目标的转换,实际上可以看到伊诺拉真正的自我被唤起。对母亲的依赖和寻求庇护,转向到伊诺拉开始寻求自己的生活(个人生活与爱情生活)。
从精神分析批评角度来看,《福尔摩斯小姐》中设置了几个形象和身份上非常特殊的配角,来完成主角这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自我成长。首先,观众应该看到电影中缺位的父亲,从影片开场,观众就可以了解到,伊诺拉是跟随母亲在庄园里长大的,母亲是她的朋友、玩伴、老师;父亲一开始就不存在。但父亲这种精神分析理论中普遍象征着外部压力的符号并不是不存在的。在影片中,伊诺拉的长兄迈克罗夫特实际上就被设计成了一个虚构的父亲。当夏洛克尝试为妹妹辩白时,迈克罗夫特相当专制和坚定地认为妹妹需要送去女校管教;而当伊诺拉离家出走时,迈克罗夫特的盛怒远远甚于同为哥哥的夏洛克。迈克罗夫特所象征的权威实际上是伊诺拉开始寻求自我身份的原初动力。
基于这重立场,再度回归于伊诺拉自我身份探索的过程,就可以看到《福尔摩斯小姐》在叙事改编上的第一重魔力。和家喻户晓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相比,伊诺拉显然更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侦探,探案固然是其故事主线的一部分,但福尔摩斯小姐将焦点更多聚焦于内部。《福尔摩斯探案集》集中讨论的是犯罪的手段、犯罪的目的以及令人目眩神迷的动机;《福尔摩斯小姐》则更倾向于塑造一个不完美的、年轻的、有成长空间并可以和观众共情的关键角色。刺杀侯爵案的悬疑程度并不高,而伊诺拉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这一案子,才是故事逻辑里更为深藏不露的一环。在影片的后半段,伊诺拉发现火药、女人的秘密联合会和母亲失踪真正的关联时,电影对其选择处理也相当含混。伊诺拉首先选择的是拯救与她投契的年轻侯爵,并在与侯爵冒险时,摧毁了埋藏在议政院的炸药,最后通过私人人情式的讨论和要求,使得年轻侯爵真正投下了妇女权益修正案的一票。
后半段中,伊诺拉的角色成为矛盾尖锐的两派的中间调停者,但她调停双方矛盾的方式是传奇式的、虚构式的,是一种基于想象的完美和解。少女伊诺拉从“情感”层面感化了年轻的侯爵,使其对“伊诺拉们”的处境产生了同情和理解,并为此牺牲了自己同阶层的特权,转而支持伊诺拉,这样的和解路径,实际上也提供给观众以不真切的幻想。影片也就从前半段中女侦探的冒险,转向到了一种基于罗曼史的机械降神式的幻想。而在影片末尾,当一切尘埃落定,尝试如同英国历史上真实的妇女参政论者一样的母亲再度回归。这无疑是对影片后半段展现的浪漫幻想的一种刻意遮蔽,结尾将观众再一次拖回了幻想,沉浸于整个故事弥漫着的一种浪漫的、大团圆的却并不真切的氛围之中。
三、主题的回归:福尔摩斯小姐对福尔摩斯的戏仿与改编
从文本看,《福尔摩斯小姐》《福尔摩斯小姐与失踪的侯爵》《福尔摩斯探案集》三者的关联强度是逐渐递减的。南希·斯普林格原著的结尾和影片《福尔摩斯小姐》不大一致,也缺乏影片里的浪漫氛围。而《福尔摩斯探案集》作为整个衍生故事的底本,福尔摩斯的形象被福尔摩斯消解部分继承。因此在影片中,伊诺拉的形象既像《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形象,又与福尔摩斯的背景故事出现了很大的差异。电影则更加直观地展现了这一点,使得《福尔摩斯小姐》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关系更接近于一次戏仿。
在《福尔摩斯小姐》中,曾经扮演过超人的亨利·卡维尔饰演了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不再是不苟言笑、追求极致理性的大侦探,他常常与迈克罗夫特结伴出现,在伊诺拉的母亲失踪的背景下,福尔摩斯与迈克罗夫特结伴出现,将夏洛克的“替代”母亲的身份揭示得更为明显。外形阳光的亨利·卡维尔显然不再是贝克街阴郁、谨慎、处处讲究推理和逻辑的侦探,他更像是少女侦探的辅助者和故事的叙述者。当观众在追寻伊诺拉的探案过程时,福尔摩斯的作用往往是消解剧情里血腥的、不安的因素,将故事的叙事步调带入一种安稳的、确定的、稳操胜券的叙事语境中来。在夏洛克与黑人女仆对话的一节中,就直接揭示了影片的主题内涵,因此,从改变的层面来看,真正的夏洛克更像是一个功能性角色,而福尔摩斯小姐实际上才是承继了福尔摩斯精神,并真正将角色的特点发散下去的主角。剧作中,伊诺拉和夏洛克二人的角色形成了第二重的倒置,互相成为映照彼此身份的标记物。
影片似乎有意放大这重戏仿的趣味,如在侯爵家中访问老侯爵夫人一节,夏洛克的警官朋友此时成为伊诺拉的合作对象,两人对暗号的情节和柯南·道尔《闪光暗号》中的对白如出一辙。年轻侯爵利用蓝色勿忘我作为标记,指引伊诺拉找到自己藏身处的情节也和《赖盖特之谜》中华生的行为颇为相似。伊诺拉和夏洛克双面一体,似乎成为剧作内外的双面映射。甚至影片为了加强这种可疑模拟的趣味,将夏洛克和伊诺拉设置成一母同胞的兄妹,也颇值得玩味。夏洛克和伊诺拉一样充满着常人眼中的怪癖,从角色设置层面来看,二者是一体两面的,然而在剧中夏洛克的许多怪癖被伊诺拉所继承时,戏仿与讽刺的效果就被呈现了,伊诺拉被指为一个行为习惯糟糕到需要进入淑女学校矫正的女人;而夏洛克仍旧是“伦敦人人知晓的大侦探”。在影片中,伊诺拉不停丢掉与摆脱的身份,借助于夏洛克的存在得以阐发,身份作为影片的隐形主题也得以凸显。影片中夏洛克和伊诺拉依靠暗号、标记、密码相互寻找不如说是一个幌子,而在表层之下,《福尔摩斯小姐》借助少女电影的外壳,向观众展示了一个自我认同的故事,伊诺拉既通过向外界探索来寻找自我,也向内寻找自我。在影片最后,伊诺拉决定去议政院门口见一见福尔摩斯,虽然二人最后并没真正相见,但本质上已经实现了和解,这份和解既是伊诺拉与哥哥们的和解、和男性主导世界的和解,同样也是对自我的和解,和对自我身份不再固着于认同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