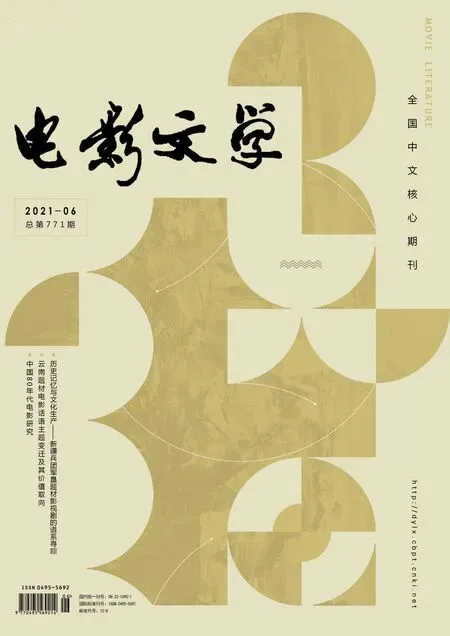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四重叙事机制探析
杨晓军(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即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数千年的传统农耕社会的确奠定了乡土社会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乡村实际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寄托无忧无虑生活的原野,是我们想象中的精神家园。随着我国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乡村,成为一个“衰落”的文化意指和想象空间。乡村的衰落导致村庄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村落终结”(周锐波等,2009;刘梦琴,2011;田毅鹏等,2011)。在此背景下,乡村再一次成为影视关注的焦点。
《乡村里的中国》是2013年由中央新影集团出品,焦波导演的纪录片。影片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最佳长纪录片”等诸多奖项。可以说,《乡村里的中国》是近年来我国乡村题材纪录片中较为成功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影片的学术探讨,从2014年开始便热度不减,仅2020年(截至11月中旬)就有6篇相关研究文章发表,其他年份的发表情况分别是:2019年3篇;2018年5篇;2017年6篇,2016年10篇,2015年1篇,2014年两篇。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乡村影像与国家形象建构(胡满江,2020)、乡村记忆与影像表达(陈新民、杨超凡,2020)、影片所反映的农民问题(钟凯,2018)、影片的叙事策略(代辉,2018;张端霞,2017;陈晓波等,2016)、影片中的农民生命观(褚兴彪,2016)等。不得不说,《乡村里的中国》得以被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原因,除了影片作为“乡村”题材纪录片具有一定典型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叙事手法和叙事策略的独特性。《乡村里的中国》通过多线穿插并行的锁链型结构、二十四节气所创设的时空节奏、人文关怀下的平民叙事视角、矛盾冲突与细节呈现结合的叙事手法,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鲜活的、真实的、充满张力的中国“三农”景象。
一、叙事结构:多线穿插并行的锁链型叙事
素材是一部纪录片的血肉,而叙事结构则是一部纪录片的骨架。只有搭起了影片的整体“骨架”,将“血肉”合理分布,纪录片的结构布局才能精巧,内容才能始终对准主题,叙事才能清晰准确。《乡村里的中国》采取了三线穿插交织、顺序并行的“锁链型叙事结构模式”,将家长里短、婚丧嫁娶、夫妻相处和邻里矛盾通过农民杜深忠一家的家庭生活线,村主任张自恩的基层工作线和大学生杜滨才与父亲杜洪法的代际相处线组合延伸展现出来。三线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不同人物的生活交织对照紧密呼应着纪录片的乡村主题,形成了统一的逻辑情感。
(一)农民杜深忠的家庭生活主线
农民杜深忠在年轻时拿过枪当过兵,在鲁迅文学院培训过写作,早年就爱泼墨挥笔、写写小说,镜头下的他闲暇常常拿着毛笔写写画画,或者拉着一把走音的二胡,心心念念地想买把琵琶,长年读报看新闻关注国家大事。虽然是村里难得的文化人,却很少花心思在农活儿上。因此家中生活清贫,女儿小梅也只能辍学打工负担起家庭重担,杜深忠的这些想法在大字不识几个的妻子张兆珍眼里,自然是“头顶火炭不觉热”,尤为不切实际,不务正业,为此,夫妻间总有唇舌之争。杜深忠和其他乡民生活方式的大相径庭,以及对精神的追求,一改大众心中的农民形象。他的精神哺养追求在贫瘠的物质现实面前几乎溃不成军,杜深忠的遭遇是不少农民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命运,作为贯穿全片的主线索,串联起另外两条线,让受众跟着杜深忠同呼吸,共命运,直击人文主题。
(二)村主任张自恩的基层工作辅线
村主任张自恩主持日常村务,忙着调解邻里矛盾,还在为招商引资奔波,为杓峪村做了不少好事,却仍有各种反对和不解。为了改变村容村貌修建小广场,张自恩安排施工队砍树时和村民发生冲突;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多次去旅游开发公司洽谈,村民却怀疑其贪腐,不断上访要求查账;直到后来他家的秧苗都遭到“有意残害”。村民对张自恩的这种反对与不解,更多是由于老百姓对官员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张自恩在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时,在醉酒与反思中不无心酸地说出了“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的话。这条线衍生出了其他村民的柴米油盐、大事小情,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让整个村子的民风民俗立体起来,使得农民的性格形象也更为真实,既不高大也不卑微,有深明大义的一面,也偶尔崭露一角人性弱点。
(三)大学生杜滨才和父亲的情感辅线
大学生杜滨才一线揪出了中国人隐秘的、不容宣之于口的、心口不一的情感表现。杜滨才的父亲杜洪法多来年一直罹患精神疾病,有时候控制不了冲动,因此母亲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这个家。虽然父亲对他竭尽所能付出,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杜滨才,怨恨又想念母亲,和患病父亲的相处充满着情绪的宣泄。而纪录片记录下了杜滨才对母亲的和解,与父亲相处的软化,把深藏多年的感激和爱最终用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条线承担着全片的感情线,得到了观众的一致情感认同,填充着纪录片的泪点。
这三条线索穿插并行,形成锁链型的叙事结构,加强了叙事情节的故事化,适应了观者的观看要求,三线结构互为补充,将各个小叙事串联成最终指向主题的完整叙事。
二、叙事节奏:二十四节气创设自然时空节奏
电影可以用色彩、线条、构图等种种可捕捉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可见的、直接的内容。但还有一部分暗流涌动、隐藏着的意境无法直接表现,言语会曲解,书写也不足够,是一个难以越过的障碍。对于这部分不可直言的意境,在电影中通常体现为情节转变带动人物情绪和动作的变化,或者使用不同景别、不同快慢的镜头组接,在一动一静的规律剪辑中,在镜头的推拉摇移里,在光影色彩的变化里,形成独特的叙事节奏。节奏是电影艺术的个性,“把握好叙事节奏,可以增强纪录片的可视性和趣味性。”《乡村里的中国》对总体节奏和基调把握自然得当,叙事的起承转合、急缓疏密往往都依据线索人物的生活际遇发展,呈现一种和日常生活节奏协同的叙事节奏。
影片按农历二十四节气划分,用远景、中景、近景镜头组接,表现不同岁时节令杓峪村的不同风景人事,构成了一种自然的时间节奏。影片从“立春”开始,翻开就是沂蒙的山水远景,冰雪消融,河滩上群鸭嬉水,村民们在羊身上刷红漆“打记号”,撰写大大的“春”字,一派欢欣景象;“惊蛰”开篇,是旭日初升的山景,杜深忠为苹果树修剪着枝条;谷雨则配以山花烂漫、鸟在繁枝筑巢的盎然风景,村民们忙着“点苹果花”;小满时,巢中鸟蛋特写,野刺猬爬行在草丛里,苹果到了“套袋”的时候;大暑,山中雷雨驰行的远景,张自恩的工作也迎来了更大的矛盾;寒露,火红流云在群山蔓延,苹果也迎来了丰收,却迟迟卖不出去;冬至,小山村银装素裹的大远景,村民在雪地里逮兔子,孩子们玩雪玩得不亦乐乎,杜深忠喜迎嫁女……全片用明丽的风景把村里的大事小情链接对照起来,将叙事推进寓于时空表现,四季变换,三条叙事线索也在循序展开。除此之外,影片主角杜深忠家里的那台电视里出现的神九发射、奥运会举办、习总书记讲话以及春晚的新闻画面,也是影片节奏的另一个体现。电视里的“重大事件”将这个看似封闭的小山村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隐喻。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指出:“节奏是至关重要的,永远是至关重要的。”节奏有迟速之辨,吟猱有缓急之别。《乡村里的中国》叙事节奏是顺其自然的,人景和谐统一,更是匀速的。三分钟一个情节,五分钟一个节气,无痕过渡。每个段落下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都叙述得清楚详尽,一气呵成,节奏均匀。这种缓缓的时序节奏,让观者拥有了一种平静和轻快的观感。它将小村里琐碎冗杂的事与情,隐藏在舒缓如水的节奏中,余音回响在观者的脑海里。
三、叙事视角:人文关怀下的平民视角
(一)客观视角与乡村里的真实中国
纪录片的叙述视角是指对记录对象采取的观察和讲述角度。法国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将其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著名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则将其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而我国学者陈平原把叙事视角分为“全知视角、限知视角以及纯客观视角”。这几种分类实质上是大同小异的,我国纪录片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由倾向全知到限知,再到纯客观的转变。全知视角又称云端视角,开创英国纪录片学派的格里尔逊把纪录片中的解说词形容为“上帝之声”,生动地为纪录片的全知视角做了注解。这种视角固然自由灵活,却缺少对人内心世界的关注,显得高高在上,太过冷漠。
《乡村里的中国》拍摄时间长达373天,在一年有余的拍摄中,摄制组进村成了这里的第168户村民,像农民一样种地、生活。这种弗拉哈迪式的全程参与拍摄方式,消除了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感,让人们对镜头习以为常,大事小情都纳入镜头,确保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因此《乡村里的中国》有了无限接近真实生活的客观视角,叙述代替说教,摄像机直接将人们的生活场景和对话纯粹地展现给观众,不加任何干扰。并和观众一起探索未知,最大限度融入了乡民集体,呈现了乡村生活原貌,还原了质朴本真的村风民俗。比如呈现村里过年咬春的游戏,老人“给小孩头上缝豆子,小孩不生痘子”,小梅出嫁时家里烧喜包袱祈祷婚姻和顺的镜头,一切真实自然且妙趣横生。
结尾杜深忠对儿子教诲道:“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海龙我给你说,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你得好好读书,千万千万的,这个土地不养人,我和你说,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血的,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这些直接的对话,没有一句解说词,既不渲染,也不煽情,只是纯客观记录,但给观众的震撼也十分强烈。正如焦波所说:“我从来没导演过任何一个场景,没写过一个字的策划,没编过一句台词,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自然流露。”这种记录,直击人物内心,用镜头语言搭起了观众和影片之间交流的桥梁。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也评价道:“《乡村里的中国》是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二)浓厚人文关怀的平民视角
导演焦波和团队在杓峪村扎根,和村民同吃同住,这种极度的贴近,使得《乡村里的中国》选择了平民化的视角和审美趣味。村民自己的俏皮话,就能足够精准地为事件下注解,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张兆珍和杜深忠争论村民卖树这件事情说出了“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坯”;把苹果入库的张自恩感慨“苹果入了库,还不知道是娘娘还是爷爷呢”;在杜深忠家讨论苹果卖价的村民春田则一语中的说出“你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这些农民的自嘲,是用平民化视角对农民自身的生存空间做出的深刻反思。这些场景展示着农民的精神风貌,挖掘出了农民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这种平民视角的聚焦,彰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带着对社会的深深焦虑。《乡村里的中国》高度贴近农民生活,对农民声音的倾听,对农民视角的关注,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四、叙事技巧:矛盾冲突与细节叙事的双重“勾连”
《乡村里的中国》使用强化矛盾冲突的叙事手法,三个线索人物身上本身也具有强烈的矛盾张力,使得片子的情节性和故事性很强。最重要的是:这种叙事手法使得社会现实问题在乡民矛盾冲突的因果关系里不断凸显出来。可以说《乡村里的中国》关注的绝不仅是杓峪村村民的个人命运,而是在映射着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
(一)矛盾冲突呈现乡村问题
1.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贫瘠
杜深忠的精神追求,改变了人们对农民形象的认知,而正因他的精神追求造成的家庭矛盾,才揭示出当代农民的精神文化追求得不到保障的现实问题。影片里杜深忠一家的生活不过温饱而已,种苹果一年到头收入不过七八千块钱。杜深忠买琵琶花了690元,都要给妻子撒谎少报200元;女儿出嫁,喜糖多买一袋都要犹豫不决;爱写写画画的杜深忠,为了省钱,只能在水泥地上练习书法。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很难支持其文化爱好。外出打工不幸身亡的张自军,刚入土为安,家里人就为他的赔偿款争得不可开交。在物质贫瘠的时候,亲情开始变得冷漠无情。
固然杜深忠在清贫里仍旧保持着对精神文明相当执着的追求,无谓钱财,但包括妻子在内的其他人被物质贫瘠所困,来不及重视精神世界的荒芜,也实属无奈。杜深忠说“这个人需要吃饭是吧,他得活着;这个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哺养”,妻子却只觉得“也不当馒头吃,也不当衣裳穿”,而大多数村民对精神文明的态度当属于后者,由此也能窥探出农村精神文明贫瘠的现状。
2.男女地位的不平等
在杜深忠夫妇的冲突中,乡村里男女地位不平等现象隐现。杜深忠是开明的,儿女婚事无所谓穷富。但从两夫妻的对话里,妻子张兆珍总在埋怨丈夫,心疼女儿,话里话外,可以了解到女儿小梅十五六岁就外出打工供弟弟上学。姐弟俩年龄差不多,但清贫之下,只能女儿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赚钱补贴家用,男孩则被叮嘱好好读书。杜深忠和妻子的日常拌嘴中,也说的是“庄户娘儿们的素质太低太低,不和她一般见识”。杜洪法不怎么会给苹果套包装泡沫,手法笨拙,被儿子抢过来做,他对儿子说的也是“这是妇女干的活儿,男的没有干的”,侧面佐证了乡村仍旧存在思想上的性别歧视。
3.农民经济增收困难
杓峪村的村民依靠种植苹果养家糊口,哪怕是村主任张自恩,也得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但农资及涉农服务价格过高,苹果带来的经济效益微薄,依着老农民杜深忠的话来说那是“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熬得很心疼”。而且涉农服务不知真假,经常有骗子冒充科学院的教授兜售化肥。因为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农民外出打工,也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杜深忠给人收玉米,累掉了13颗牙,“拿着人肉换了猪肉吃”,而青年张自军干脆连命都丢了。村主任想开发农业旅游,改变产业结构,但障碍重重。
杓峪村作为中国普通村庄的缩影,它面临的问题,就是全农村亟待解决的问题。杜洪忠说糟蹋粮食的獾是保护动物,妻子张兆珍却疑惑并问出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三农”问题的 “三个最需要”: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些需要,仍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去改善。
4.城乡二元化之下环境和发展的冲突
农村的建设还没有完成,但城市对农村资源的掠夺一直存在。农民没钱,挣钱的路子也少,就打树的主意,把树卖进城里去做绿化。杜深忠说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农村要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建立在畸形的供求关系中,是以压榨农村生态为代价去保证城市环境,这个问题值得反思。
5.基层干部工作的信任危机
张自恩作为村主任,实实在在为村里做了不少事情。虽然作风粗野强硬,但是为了招商引资,四处奔波,还贴上了自己的钱拉关系。却被几个村民联合反对,要查他的账,影片中,几次冲突争执都和这件事有关。他的强势和尴尬尽数落到镜头里,直到管区书记出面,查账的事情才告一段落。但这种群众对基层干部工作不信任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是长期存在的。
6.家庭情感表达的缺失
杜滨才一线是本片的泪点担当,因为父母离异,抚养他的父亲又有精神疾病,他的成长经历是相当坎坷的。童年留下的心理阴影,一直影响着他和父亲、母亲的关系。因为一点小事,父亲把淄博说成了卷舌,他就会大发脾气。虽然对患病的父亲,爱之深,但说出来的话总是针锋相对。想和19年不见的母亲会面,却一直说“以后吧”。虽然影片最后,母子相拥而泣,父子互相理解,一切重归于好。但影片中反映出的“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孩子”成长中情感沟通缺失的问题,值得深入反思。
(二)细节叙事捕捉农民真实情感
《乡村里的中国》在叙事技巧上,极为注重细节刻画,通过细枝末节凸显各色人物性格形象,再经人物与事件共同发酵,推动情节发展,渲染气氛,深化人文主题。
生活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记录,但要让生活变得生动起来,唯有细节。杜深忠把投进房门的一束阳光当作一张宣纸,毛笔蘸水在阳光投射的地上写字,这个细节就让他身上多出了一股文艺气息,这幅画面在此刻也显得分外静谧美好,一个穷困但仍旧保有精神追求和生活趣致的人物形象跃然于银幕。
村主任张自恩的形象也在多个细节之下,显得立体丰满。他不辞辛劳地多次为村里的项目奔波,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村干部。但并不高大全,面对无理取闹的反对和查账,张自恩也会不顾形象,破口大骂。既有放狠话的强势,也有借酒浇愁的辛酸,嘴上不饶人,年底了还是自费买了东西给反对他的村民送了去。这些性格的多面性,片中没有任何回避。通过细节的堆砌,多处着墨,把张自恩这个基层干部的形象,一点一点塑造了出来。
而在张自军的葬礼上,孩子天真地跪着问爷爷“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爷爷回答“不小了,这里头很宽敞”,接着微不可见地叹了一口气。这段对话,小孩的天真与现实的悲悯着实戳痛了观众的心。而爷爷回答之后的叹息更是将观众情绪推向高潮。这段细节对故事情节推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还有一些平淡的生活情节,在细节的烘托下显得温暖无比。杜洪法卖了苹果拿到钱,马上给儿子杜滨才打电话报告。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苹果怎么卖,铺垫着最后一句话“没钱了跟我说一声”。一个在别人口中犯病了要打人、骂人的父亲,全片从头到尾没有对儿子说过一句重话。重重细节铺垫之下,动人的情感默默流淌在这通电话里。
《乡村里的中国》的创作运用了多重叙事策略,既充分展示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变迁,又全面体现了新时代下小人物平淡生活的朴实旨趣。它所呈现的中国农民形象,虽然苦,虽然难,虽然无奈,但不可谓不坚韧。他们一直保有对精神的不懈追求。纵使希望不断落空,却总能再度生出热情、打起精神接着笑对生活。他们用半生心血总结出来的经验,哪怕只言片语,也耐人寻味,朴实无华,也本真感人。本片把一个宏大的命题用个体的生活细节和际遇感受回答了出来,细腻且真实,在平民化的视角下折射出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引人深思,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包含对题材真挚而充沛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里的中国》那种自然、平实、遵循真实原则的叙事机制对纪录片创作有现实借鉴意义。而片子忠实记录农村的发展与变化,反映农村农民的心声,树立农民形象的主题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不得不说,《乡村里的中国》只是一个个案,对此个案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如何透过“乡村”题材纪录片,去探讨其中关于“乡村”的影像建构、纪录片中的乡村“群像”记忆以及“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是一些更值得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