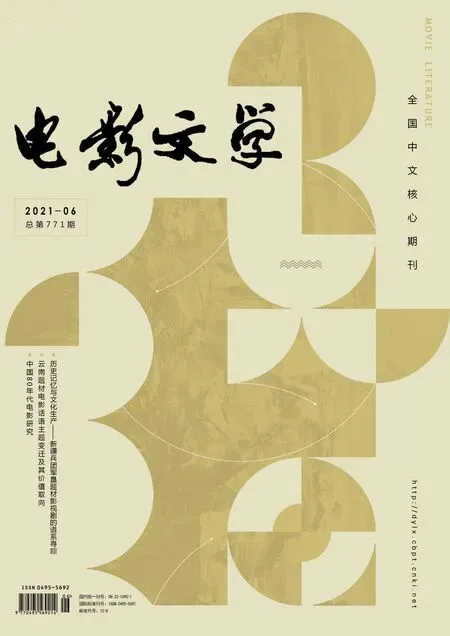桑弧电影美学:空间景观、主体型构之后的走向现代性
王诗秒(西南石油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影坛出现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创作现象:文艺界人士、精英知识分子涌入电影界并逐渐成为创作主力军。“这些文化精英很多有西方留学经历,因而具备了一种世界的眼光和兼顾中西方文化精华的胸怀,他们倾力于创造一种属于中国独有的现代电影模式。”处于这一时期的创作者也同时呈现出了不同的电影风格,其中由“文华”影业公司创作的一批艺术电影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文华’的独立精神以及它所执念的一种人文电影风格,一直为后世关注。”“文华”在电影艺术价值的追寻上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中国电影企业的存在与发展的价值没有被否定的话,我们得承认,今日的电影企业商,他们所负荷的使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更重大的。……希望中国电影事业真的成为电影艺术……成为一种社会事业。”而“桑弧是文华的基本导演,过去导演《不了情》与《太太万岁》,其清丽隽永的手法,在中国影坛上,是罕有的奇珍”。在40年代后期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同时充满了“海派文化”的魅力。《西北文化日报》报道:“一个导演,不仅是摄影场上技术,他还是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艺术家,这样他的成就方才是全面的、综合的。桑弧是一个创造力的导演。”商业性的收获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影响范围也不止上海、天津等地区。《贵州商报》上也能看到广告:“《太太万岁》场场客满。”甚至出现了黑票:“光明放映《太太万岁》八时场楼间座卷,黑票喊价五十万元,而向隅者犹大有人在。”《大公报》(上海版)1947年12月14日出现了观后文章《所谓“浮世的悲欢”〈太太万岁〉观后》,之后包括影讯之内的热度持续了近两个月。《大公报》(天津版)从1948年2月19日起不间断地出现《太太万岁》的影讯,及至1948年5月5日依然能看到相关影评信息。在对桑弧电影所取得的商业价值上很容易得到论证,而在影片的艺术价值的深度挖掘,尤其对导演的价值美学认知上还有待商榷。
“电影最初的情形是怎样的?一方面,取景是固定的,因此镜头是空间的,形态上是静止的。”空间是电影最初被认知的形式,镜头被认知为一个静态的空间范畴作为始初。而取景作为“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的界定”,包含了在影像空间中的所有内容。胶片时代的电影作为一种影像形态而存在,但是在取景框中的影像承载了连通与系统之外的意义存在时,空间影像成为一种导演力图展现的“空间景观”。《太太万岁》和《哀乐中年》中,桑弧所展现的空间影像“整体是开放体”,所指向与关乎的是“时间甚至是思想”,完成了从空间影像走向“空间景观”的意义生成。在“运动—影像”的认知维度上可以将艺术认知回归到“镜头”语言的最初来重新认知桑弧的两部影片的影像密码。
超越“运动—影像”之后的电影完成了本质的进化,电影不再是一个空间范畴,作为情感的诸因素成为完成影像构成的重要一环。桑弧的两部影片中的主体性型构成为完成“情感—影像”的核心表达。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型构所完成的,是在一个极度抽象的现实影像中的“情感”编织,同时将诸多情愫纠缠于这一型构之中,完成“情感—影像”的虚拟建构。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的现实主义表现是对时代的真实反映,那么桑弧导演的影像景观则是完成了走向现代性的诉求表达。德勒兹认为:“真实不再是被重现或复制,而是被‘直击’。”《太太万岁》所直击的是暧昧的真实,不是被反映的现实家庭,而是被抽象的中产阶级家庭。《哀乐中年》不是复制了一个真实的中年生活,而是编码了一个有待破译的真实中年人生。现代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一个未竟的事业,那么在作为“思维—影像”的维度看来,桑弧所呈现的是一种走向现代性的趋势化的景观式影像思考。
一、空间景观的意义生成
影像的运动源发于摄影机的运动,镜头是空间范畴的影像生成的基本。桑弧两部影片中的导演风格与意识所建构的空间系统,既抽离了多变的现实空间,同时又附义于电影的叙事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空间影像在导演的精心构思之下完成了一种“空间景观”意义的建构。
空间之于电影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电影画面被摄像机捕捉下来的空间,二是观影空间,三是现实存在的客观空间。在“空间景观”的意义建构上所主要讨论的是第一种空间,在桑弧导演的电影文本中,空间表现在结构、场面调度等方面都被学者所关注。而空间话语的表现则并非对空间结构等内容的分析和评述,而是透过视觉文本内容来阐明其背后的反思式个人主体表达。
《太太万岁》和《哀乐中年》之中的空间呈现以文本叙事空间为主,空间在影片中主要服务于影片的内容叙事。影片的主题主要聚焦于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日常,因此,在话语表现中着力于对家庭空间话语的呈现与演绎。在这两部影片中,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展现,也没有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历史图景。而是展现典型、简单的都市景观,围绕主题、人物的叙事内容铺展开简洁的空间话语。这也印证了桑弧导演的理念:“场景不要太多。电影……时间、空间可以自由跳跃。”
(一)都市景观的穿插
都市景观在叙事之中主要服务于文本叙事和营造出都市生活的基调,因此,都市景观空间话语并非作为电影主要空间表达存在,而是服务于叙事,穿插而连贯地呈现在电影中。在都市景观的塑造上,两部影片更多是完成一个忠实的记录并达成叙事表意。都市景观自然而然地呈现并成为空间话语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样态和这一时期上海市民生活的印象真切地呈现在画面中。在《哀乐中年》中陈绍常在路边刮胡子偶遇儿子的场景,就是一个典型反映都市空间的场景话语。但电影语言中,空间本身承载的是一个“记录式”的文本表意,而非完成“意义式”的叙事达成。“记录”成为影片中最好诠释都市景观话语的概念,迥异于对历史事件的介入式映射,作为协同电影叙事存在的都市景观话语显示出另一种电影风格。“记录这样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在此的人的心灵空间同样具有价值,没有这些影像,中国电影的空间表达是不完整的、残缺的。”
中产阶级的生活样态展现是《太太万岁》中的典型空间话语之一,而处于都市生活中的生活样态成为在电影中既零碎又统一,既典型又弥散的话语表现。在《太太万岁》中有两个场景的空间属于都市空间:一是出售胸针的店门口,另一个是在香山咖啡馆。第一个空间场景主要承载了叙事意义,本身的空间话语呈现中并没有完成都市景观的建构。电影语言主要通过特写、中近景来完成空间展现,空间中没有过多隐喻性的文本内容。这一时期的都市景观建构往往通过现代都市生活的典型场景来完成,如外滩的建筑、林立的百货大楼、路边的咖啡馆、夜晚的舞厅、闲适的公园和跑马场等。而在《太太万岁》中是以香山咖啡馆来达成文本的叙事转折和都市空间的典型呈现。
“作为一个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30年代的上海被证明为同样流行。像电影院一样,它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休闲场所。”咖啡馆本身就是作为一个空间话语而存在,代表了现代都市生活,也是都市文化的象征。空间存在本身对于电影而言就是意义所在,意义的进一步达成和诠释则在于空间中的文本叙事表达。没有“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奢靡,而是简单的咖啡馆场景和一个明显的“BAR”的字标就构成了电影中咖啡馆场景的全部。“坐咖啡馆里的确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事业取得成功的唐志远独自跟朋友去往咖啡馆接受做媒,都市景观的话语叙事表达由此铺展开来。在对空间场景的认知中,存在这样一个前提:“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亚于鸦片和酒’;其次,咖啡馆提供了与朋友畅谈的地方,‘此乃人生至乐’;最后也很重要的是,咖啡馆里有动人的女侍。”夹杂着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多元文化赋予空间话语和其中的主体以复杂的隐喻象征。“不仅把咖啡馆当作‘现代城市生活的点缀’和‘一个很好的约会地点’”,咖啡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同时也被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电影画面“茂远企业公司”的特写画面与香山咖啡馆的空间画面的连贯,隐喻了作为“成功人士”的志远结识姨太太是顺其自然的,但地点又发生在咖啡馆,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埋藏在现代性都市生活和文化中的个人的非现代性认知之间的冲突。在电影的最后也证明了这一矛盾冲突隐喻的存在,唐志远邀请律师和太太一起在香山咖啡馆庆祝,因此他认为他是从香山咖啡馆开始堕落的。
显而易见的是:《太太万岁》中咖啡馆与家庭空间在电影中成为被隔离和隐喻的两个空间话语。而其中咖啡馆的空间话语承担着典型的都市文化生活话语表达,而日常家庭生活空间作为叙事的主要场所,则完成了主要的表意达成和主题建构。这使得发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故事既处于都市景观空间之中,又显得游离于社会历史洪流之外。
(二)叙事空间的聚焦
空间话语在桑弧导演的电影中场景展现往往让渡于内容文本叙事,因此,典型而统一的叙事空间话语表达成为电影中的核心表达诉求。三个典型的空间场景足以完成电影的核心内容叙事:日常性的家庭空间,意志型的学校空间和反思式的目的空间。“《哀乐中年》和《太太万岁》《假凤虚凰》一样,展现的城市空间具有很强的认知作用,更可贵的是影片开掘了市民趣味中诸多正面因素。”
1.日常性的家庭空间
家庭空间的复刻与描绘,成为电影中场景空间展现的核心之一。影片叙事内容主要围绕家庭中恒常的话题展现:父子冲突、婚姻问题等。由此铺展开的对诸多观念性话语的表达与传递。在桑弧的电影美学中,一个典型在于其忠实地呈现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空间及其家庭状况。区别于作为“他者”的电影日常影片空间塑造,桑弧导演给予摄影机捕捉的空间以一种简洁,忠实于现实世界的空间场景表现;同时,在空间话语表达削弱或是消弭了空间场景的话语情感色彩,家庭空间还原为日常的生活表意,而非承载具有倾向性话语的功能性表达。
聚焦于家庭空间中的人和事的展示使得在电影创作中,回归叙事本体的理念。作为试听艺术的电影让部分导演在艺术创作中关注于画面的表现,而非文本内容的叙事。而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电影,叙事是影像文本艺术表现和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太太万岁》中小洋楼的家庭空间展示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样态。而《哀乐中年》里,家庭空间从一开始是楼上楼下的里弄格局,到之后小洋楼式的生活空间。在两部影片中,作为日常空间话语聚焦的家庭空间场景回归了场景的本意话语表达,家庭环境一目了然,空间话语在此让渡于叙事文本内容。代表生活空间的家庭空间在视觉呈现上也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复刻或典型性描摹,在整体的观感上塑造出无限地接近现世生活的气质,透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2.意志型的工作空间
在工作空间的表现中,《太太万岁》中有唐志远的总经理室,《哀乐中年》中陈绍常的校长办公室。电影中呈现的工作空间,主要聚焦人物职业身份所对位的空间来展开。在这类空间的话语表现上依然服务于叙事表意。相对而言,《哀乐中年》中的校长办公室承担了更多的叙事内容。
《哀乐中年》中陈绍常人生轨迹的转折均发生在校长办公室这个工作空间:陈绍常离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离开学校和重回学校不仅是人生轨迹的变化,更体现了主人公对个人价值认知和观念的变化。人到中年的陈绍常被子女要求在家当老太爷,享清福。但陈绍常觉得中年人的生活不应该这样,在与刘敏华的交流探讨中,选择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男女主人公刘敏华和陈绍常之间的观念交流除了墓地,基本也发生在这个工作空间中。在这个工作空间中所体现出的是一个主体个人意志观念的话语表达,但这种话语表达并非通过空间单独表意完成,而是同文本内容叙事协同来实现意义的生成。在这个空间话语中更多的是同主体性的建构一同来传递出主题思想。
3.反思式的墓地空间
墓地是电影《哀乐中年》中具有隐喻象征意义的一个场景空间,在这里完成了叙事主题的升华和人生价值观念的探讨。《哀乐中年》中的家庭、墓地、学校的空间话语呈现中,墓地是游离在主体叙事之外的空间场景,相对于叙事功能而言,意义表意的隐喻式空间话语更能得到体现。主人公陈绍常在墓地中完成了个人价值的反思和个体认知的确立,从而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建构。
墓地本身作为具有指向性意义的表意符号,在电影中以空间话语的方式呈现。墓地象征了死亡、黯淡、无为,正如当时社会主流认知一样,体面家庭的中年人生活就是老太爷的生活、消弭主体的价值创造,中年就是半只脚已经踏入墓地的人生。而儿子送给自己的寿坟暗示了以建中为主的人群的观念认知中,步入中年的陈绍常的人生应该像老年人一样:种花、养鱼、玩鸟、念佛、收集邮票、游山玩水——用陈绍常的话来说就是——“待在家里等死”。在电影中导演用连续快闪的组合蒙太奇段落来表现陈绍常对这些活动的尝试。过尽千帆皆不是,在诸番尝试之后,陈绍常“得不到快活”,就连跟女儿的抱怨之后依然处于对个体认知的迷惘中。此时,亡妻的墓地偶遇让刘敏华和陈绍常在情境空间中完成对个体人生观、世界观的探讨,让陈绍常实现自我反思式的意义领悟:作为人生最成熟的阶段更应该通过工作来体现人生价值。而最后在儿子送的寿坟上新建的学校实现空间话语的转换,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新的价值创造,教室外窗棂旁,原来墓地的用地上树枝上的新叶象征了新生。
二、主体性建构与主体间性的型构
在桑弧导演的电影存在论之中,如果说简洁明了的空间影像的建构是之一的话,那么主体型构系统中观念的导入和历史不在场的替代性表达则是之二。镜头在超越“运动—影像”之外的存在建构上,作为此在的主体性建构及主体间性的表达是不可被忽视的。在主体的建构这一点上,两部影像中的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承载了导演的话语表达及观念的导入而实现建构的。“一切沉进了‘浮世的悲欢’。在这‘浮世的悲欢’里,陈思珍究竟有过无过,抑是制度的错失,一切都是无力去追究的。”而超越主体性建构之外更为特别之处在于桑弧运用主体间性的型构来实现历史不在场的替代性表达。通过在不同人物的主体性建构之外的主体间性展现,完成一个系统化的封闭式型构,既能跳脱复制现实的必要性,又能实现对现实的“直击”,从而实现历史的不在场替代性表达。
(一)观念导入
桑弧导演透过生活化的叙事视角,表现了细碎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再运用场景的隐喻性表现来实现观念价值的导入和诉说,从而完成影片主体性的建构。在“情感—影像”的表现中,情愫的载入或是观念的导入在两部影片中显得尤其明显。中年的缺失是《哀乐中年》中集中所传达的一个核心观念话语。而刘敏华这个角色除了承担主体性之间关系的叙事推进,更重要的是作为反思性话语的承载。在与陈绍常关于人生价值讨论的对话中,刘敏华说道:“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好像没有中年似的,其实最宝贵的是中年。”在对个体价值认知上,倡导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而非享乐主义。作为人生宝贵的中年,“学问有了,经验也够了,这个年龄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是不好好利用,那就太可惜了”。在对中年人生的认知观念上,刘敏华作为一个女性主体来达成现代性话语观念的导入,引导陈绍常的理性选择与启蒙意识,完成对个人的认知的理性选择。正如作为真正的主体性建构的承担者刘敏华的直接性话语表达,她对陈绍常说:“你不能把旧的东西看得太宝贵。”刘敏华评价以建中为首的反对的群体时,认为他们是一群未老先衰的人罢了。意识到传统话语观念中中年缺失,对自我个体价值认知的反思和领悟,是重要的现代性启蒙,通过女性主体的传达和探讨,最终实现了对作为“人”的主体的意义的认知表达。
而在主体性关系的认知上,也体现了作为观念符号主体的理性觉醒。陈绍常在对婚姻关系的认知上,极具理性意识。主人公对婚姻自由的态度与主张是:双方愿意,父母便不要干涉子女的婚姻。这个认知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中是与主流的价值观念相悖的。除了观念认知,在行动上也表明了主体对理性意识,对“人”的认知的启蒙,陈绍常与刘敏华的婚姻成为主人公践行其主观意志的最好证明,而自我发现的过程与自我认知的启蒙正是在默默无声的琐碎叙事中来完成的。
在主体性的建构上,场景的隐喻性表现也是重要的手法之一。对社会的伦理道德的认知态度会通过场景性隐喻进行表现。尤其在体现人物态度性的场景之中:子女反对陈绍常和刘敏华的婚姻时的场景;敏华后母所展现的对他们婚姻的态度。当婚姻遭受子女的强烈反对时,电影中陈绍常与四个小学生拔河的场景,具有强烈的隐喻性作用:“来来来,我一个人拉你们四个人。”通过正反打的特写镜头表现,展现出人物的现实状态:努力与传统认知观念的抗争。而他们结婚之后,墓地上新建学校开学第一天,他说:“我觉得我的生命刚开始,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正如陈绍常的口中的永不停歇的“12个学生的故事”。影片最后透过窗棂一个拉镜头的表现,意味深远,再转向窗外的绿树,象征了勃勃生机。
(二)历史不在场的替代性表达
作为历史中存在的“人”的主体,本身就是历史最好的代言人。历史、社会空间的表现对于电影语言而言并非只能通过宏大的镜头场景表现,或只是通过历史叙事的手段来表现。电影中作为叙事核心的“人”的存在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叙事主题。
在《哀乐中年》《太太万岁》中,家庭式的叙事是主流,城市景观也呈现一派生活化的视觉感受。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画面和现世的历史事件的淡化,使得叙事中并没有过多的历史事件的介入,而实质上我们不能否认人物依然处于历史背景的时代话语之中。历史深度的宏大背景在桑弧电影中被悄然隐匿,以平凡的生活描绘当时中产阶级生活,在“家庭”影像中展现出有质感的人生,进而在不经意间带领观众捕捉人生的意义与真谛。
更为重要的是,桑弧导演在对人物主体性建构中有意识呈现出来的耐人寻味的人文精神。在《哀乐中年》中刘敏华、陈绍常所表现出的勤勉的市民精神,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们身上所寄寓的是市民文化的正面精神。也正如《太太万岁》中思珍的父亲,施咪咪这样的人物身上所映射出这一时期所存在于社会中晦暗的人性。市侩与庸俗的形象映射也是对历史社会中现世的映射与书写。
日常生活的叙事视角成为对历史书写的替代性表达的重要方式。“40年代电影对现实主义的深化,还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和生活化。……在艺术创作中,无论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细节选择等方面,都能追求逼真、自然、质朴、生活化。”通过婚姻观念、家庭人际观念来反映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以及主流观念话语,在《太太万岁》中,隐忍而“顾全大局”的太太思珍,在丈夫背叛了婚姻之后,依然帮助丈夫解决包养姨太太之后的遗留问题。
“家庭”式的影像话语在历史的替代性话语表达中通过细碎微妙的人际关系映射出在温情的家庭空间话语中,也存在细碎而复杂的人际关系。通过人际交往与关系的细微勾画与描写来升华叙事内容主题,从而引发更为深刻的反思内容。细节运用是完成“家庭”式叙事的巧妙手段,因此,特写镜头在两部影片中在重要的转场或叙事表达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细节运用上,桑弧导演认为通过适当运用细节的重复,可以以此增强戏剧效果。《哀乐中年》中,陈绍常所讲的“12个学生”的“创业”故事,通过不断的重复,最终在影片结尾处:墓地上修建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完成了“新生”的话语表达。《太太万岁》里思珍不断编造的“善意的谎言”,象征性的重复式行为表现成为刻画这个人物形象的核心手段。所以“对于喜剧来说,单有喜剧性性格的刻画是远远不够的。细节是喜剧的灵魂。换句话说,对于一部喜剧影片来说,是否有独具匠心而又富有喜剧色彩的细节的设计和运用,往往是影片成功的关键”。
三、走向现代性
在桑弧导演的两部影片中,所展现的机智与风趣,完成了一种从“家庭”式的影像话语中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性质与文化质量的过程,这一种别样的呈现方式也成为理解其走向现代性的“思维—影像”一个不可忽视的切入点。海德格尔认为会思维的人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确保一定会思考。电影“强迫思维”和“刺激思维”的共同力量提供了开启某种精神的可能性。桑弧导演两部影片完成是从“运动—影像”的“空间景观”的意义生成之后的“情感—影像”中的主体性建构,在实现主体间性的型构之后的系统上,生成一种实现能达成观众被“强迫”“刺激”的“思维—影像”。在这个“思维—影像”的系统中,核心密码在于家庭景观的文化内涵表达,与对叙事母体的重构:展现隐藏在时代背后的人。
(一)新市民文化:一种家庭景观
纵观影片的组织结构,在平凡、狭窄而有限的家庭空间中,通过市民生活的情景,来揭示生活的悲喜剧,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市民文化样态。桑弧电影影像中的公共构造和空间,恰是理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很好切入点。公共构造与空间中的话语呈现是在桑弧导演两部影片之中,没有大气磅礴的历史事件的呈现,没有讽刺批判黑暗社会的表达,而是在一派脉脉温情的“家庭”空间之中,完成对一种新旧交替的新的市民文化的描述与展现。“一个时代不应提出其自身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对现代来说,问题就在于要求完全中断或能够完全中断与传统的联系,而且也在于对这种要求与不能完全重新开始的历史现实性之间的关系的误解。……我们要是循着概念史来考察‘现代’一词,就会发现,现代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在对现代的理解中,审美批判的明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在桑弧导演的影像表现中,作为家庭中的“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审美表现批判核心。
“家庭”成为主体性建构的核心空间,而家庭映射的是由千千万万家庭组成为都市空间。都市空间既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的乐园,也是精打细算的普通市民的栖息地。一种新的市民文化的呈现在桑弧导演的影片中呼之欲出——家庭景观。
家庭景观领域中成为平凡人生中喜怒哀乐的碰撞之地,在冲突与碰撞中渗透出人性的本色。主体性的呈现中,家庭空间话语成为一个大熔炉,在这里熔炼的是做“人”的自我认知与理性启蒙。而“家庭中的人”是完成一个主体最为回归本体、回归自我叙事方式的认知途径,在家庭空间中,任何被赋予其他符号话语的人在这里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在这个话语中,所回归的是一种本真的作为“人”的体现,而现实中的人都是平凡的人,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超凡入圣。因此,这种家庭景观的呈现是一种走向现代性中的隽永式的审美呈现。
主体性的建构之外的另一个重点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通过这种呈现来反映人际的永恒叙事问题。“永恒的三角”这样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电影的常规处理中很难打动中国观众。因为,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认知中,对老人怀有深沉的敬意,在这种不言自明的伦理语境中,很难以与常理不同的逻辑来处理电影中的“三角”矛盾。但是《哀乐中年》其中一个重要的表达就是父子冲突。但是在这里作为父亲、长辈的陈绍常与作为大儿子的建中在出现矛盾冲突时,作为年轻人的大哥恰好与中年人的父亲之间代表了在传统空间话语中相反的文化符号。中年人父亲是突破传统观念桎梏的理性启蒙,年轻人儿子建中恰好代表了旧有文化认知中的阶级观念、形象。在父亲退休后,家庭话语权掌握在拥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建中手里。
“家庭式”的话语与观众具有天然的亲近性。这种天然的特点使得这种平凡而隽永的表达话语能相对轻易地被观众理解和接受。正如基于当时的电影传播媒体生态环境而言,桑弧导演说:“因为电影是一种‘一次过’的艺术,银幕上的画面转瞬即逝。如果在放映过程中,稍有令观众不懂或费解的地方,他们很容易散神或‘出戏’,这样势必影响后面的戏的感受。”在这样的电影传播生态中,构建出一个简单而意味深远的家庭景观则显得尤为不易。
作为家庭悲喜剧式的桑弧电影,透过一种“圆满式”的结局来完成或是回归家庭温情。“在中国,美国电影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电影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除了美国电影的奢华普涨、高妙的导演和技术,中国人也喜欢我们绝大多数电影结尾的‘永恒幸福’和‘邪不压正’,这和许多欧洲电影的悲剧性结尾恰成对照。”这种家庭式的温情回归也成为一种桑弧式的家庭景观构建,在这种家庭景观中通过完成主体性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构来展现一种新的市民文化,切入走向现代性中的审美批判的自我确认。
(二)叙事母体:隐藏在时代背后的人
在对历史社会的时代性叙事中,“家庭式”话语呈现并不常见。而在同样的叙事母体表现中,“家庭式”话语展现出的是通过隐藏在时代背后,回归到家庭空间话语中的人的表现,来映射社会和文化中的现象及问题。《哀乐中年》中两个年龄悬殊的中年人的爱情,实则表现的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叙事母题:父子冲突。诚然,父子冲突的叙事主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深入分析整部电影的艺术表现来看,在实质上叙事上的父子冲突所凸显的是植根在时代生活中深层的观念冲突。《哀乐中年》所投射的是一个在复杂文化冲突、博弈中所展现出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复杂面。在对桑弧导演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桑弧导演的影片中缺失对历史、社会的书写,影片叙事剥离于时代之外,这实质上是一种误解。桑弧电影画面中虽然没有对历史变迁动荡的突出书写,转而书写处于时代洪流中的某一群人、某一个阶层。对“人”的着力表现看似没有坎坷、颠沛的人物命运,但是主体并未脱离于时代之外。反而透过对某一阶层的生活的平实表现,以力透纸背的电影叙事深度来隐喻处于复杂文化冲突中形形色色的“现世的人”。我们很难断定庸常琐细的日常生活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间谁更能展现时代、社会的真实面,或是更为正确的电影表现:成为杂色的人间众生相。
“家庭式”的空间话语之中的一个核心在于对“人”在世事沧桑变幻的人生际遇的变化之外,而其之于社会和人生的意义呈现则通过人际互动来展现和完成。家庭本身就是一个作为恒常的存在空间,而家庭就是浮世中的一个映射面来呈现其中的悲欢离合。当然,在恒常的叙事母体中通过不同的媒介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呈现依存于不同的创作者。“麦克唐纳指出,媒介直接促成了一种完全‘同质化的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甚至就像‘同质化牛奶’一样被加工出来。这种同质化反映在一种现象中,他们的趣味和情感需求被大众文化的技术专家们高明地操纵。”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艺术传播中,创作者完成的只是部分创作,而剩余的部分则依赖观众完成。电影在这一时期、这一方面似乎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
桑弧导演创作与观众的契合不仅是叙事母体在建构上所呈现出的悲喜剧样态的叙事话语,更是一种导演个人文化内涵的展现。桑弧导演的创作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养料。其次,在平凡化的“家庭”空间话语中完成与叙事母体再建构的弥合。“家庭式”空间叙事所具有的优势使得在这个空间叙事中,观众更能融入叙事母体之中,更能一同来完成叙事呈现。这一时期观众的构成更为复杂和多元,海派观众所呈现出与传统艺术观众不同的特征,使得他们也成为一种创作的源泉。
真正电影叙事的完成不仅是电影文本本身,更是影片本身在空间话语呈现与叙事母体的再建构中,完成了让观众产生共鸣的力量,使得影片本身的呈现内容与主题直击心灵,恒常而永恒地被一代代观众所细细品味。“要理解现代电影的性质,就要估量对现代电影敏感性产生影响的某些主要力量。”因此,所需要确立的核心在于:需要从现代电影理论中来较为系统地阐明桑弧导演40年代后期两部作品的存在论。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桑弧导演电影作品中所烛照和映射出这一时期走向现代性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氛围。现代性理论电影研究滥觞于电影工业伊始,作为工业的电影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代表;而作为艺术的电影的现代性一直到电影艺术地位的确立才真正开始走向启蒙。桑弧电影《哀乐中年》确立了导演艺术的地位,在电影中所展现的是导演对个体、社会乃至整个文化的哲理性思考,展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理性主义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