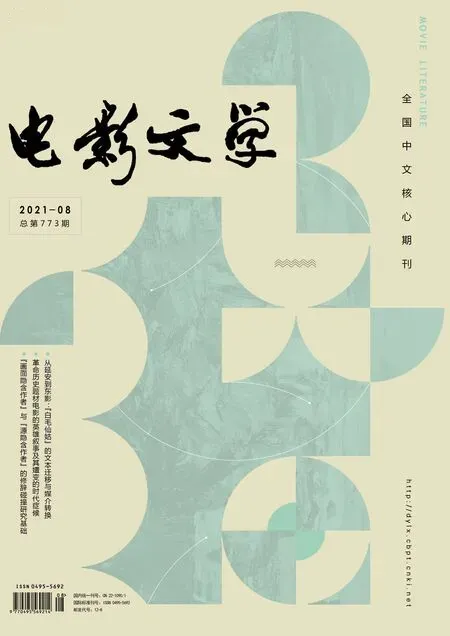《气球》:超现实场景中的多重对话解读
陈蓓蓓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万玛才旦是藏族本土导演之一,他的上一部作品《撞死了一只羊》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初次尝试,获得了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最佳影片提名奖、第1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电影提名等一系列荣誉奖项。新片《气球》也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引起了关注,该片主要讲述了因传统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冲突而引发来自灵魂深处的思考。影片风格整体上偏向现实主义,但其中出现的三个超现实场景对命运、生命、人性进行了更加深刻隐喻性的诠释。
第一个超现实场景出现在两个弟弟让江洋脱衣服看背上的痣时,这颗痣与他们过世的奶奶身上的痣长得一样,所以江洋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在超现实场景中,弟弟拿下哥哥背上的痣当玩具,透过江洋的视角我们进入了一个江洋追逐着两个弟弟的场景;第二个超现实场景出现在爷爷意外去世后,依旧是从江洋的视角中我们进入了他寻找爷爷的世界,在这个场景中,所有的画面都是从水的倒影中呈现,他最终还是没能追上爷爷,但在道路尽头他与一只羊相遇;第三个超现实场景出现在卓嘎送妹妹离开前,在卓嘎的视角中出现了她与长发妹妹温馨幸福的场景,但显然妹妹已经深深受到情伤而选择在寺庙剃发当尼姑,现实中不再可能出现如此欢快的场景。还有两次一闪而过的超现实场景分别出现在达杰去朋友家借种羊喝醉之后,随着外面的电闪雷鸣他看到窗外的奇妙景象,奠定了影片中达杰的情绪基调;卓嘎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徘徊于信仰与生活中不知该如何抉择,她看向水中的自己,迷茫而恍惚。
在多个超现实场景的视觉语言上,导演均采用升格画面、非正常色调影调以及模糊等手法来表现特殊情境,这种情境可以视为故事中人物的“梦境”,也可以是一种导演为了营造相应的氛围而使用的技巧。在听觉语言的运用上,没有对话,没有一切外界声音,只有迷幻而悠远的音乐,与其他现实场景中的自然音响、人物对话、几乎没有背景音乐铺陈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渲染了悲凉庄重的场景氛围,另一方面更加突出这几个超现实场景,且迅速带观众进入其中。好莱坞商业片中超现实场景通常依托于特效等科技手段呈现,带给观众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以博取观众眼球。而万玛才旦导演《气球》中的超现实场景,则是另一种不同的表现。《气球》在运镜上十分平稳,也没有人物间的对话,升格镜头与空灵平缓的背景音乐凸显出超现实场景的特殊性,符合影片整体营造出来的现实主义氛围,也同时是万玛才旦本人的镜头语言风格。
万玛才旦导演一向聚焦于书写小人物的身世命运的迂回辗转,借助自己藏族本土导演的优势描绘着一系列藏族人独有的民俗、仪式,《静静的嘛呢石》刻画古老的世俗文明与新兴的外来文化的冲突下人们的不同迷茫状态;《寻找智美更登》以藏戏为引讲述寻找自我的故事;《老狗》则通过卖不卖纯种藏獒这一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对商业利益驱使下人们的原始信仰也受到冲击这一问题的思考;《塔洛》深刻探讨着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对纯粹藏族身份、灵魂的吞噬与裹挟。在《气球》中,他再次直击藏族人灵魂深处的痛楚,加入超现实元素,并且采用气球这一多重意象性指代的物质为线索讲述藏族现实故事。
一、人类对话生灵:命运的映射
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指出:“动物的生命不会与人互相混淆而被视为和人类生命平行。因此只有在死亡状态下,这两条平行线才互相交叠,或者再因互相交叠而再度平行;这就是‘灵魂转世’这种普遍的信仰之由来。由于二者的平行生命,动物能提供给人们一种互相为伴的感情。”在影片《气球》中,除了“气球”本身之外,“羊”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元素贯穿故事始终,首先种羊作为男性力量的代表,去选择自己满意的母羊作为交配对象。而不能继续下羊崽的母羊被拽出羊群,被人类所抛弃。在江洋视角下的超现实场景中,他跟丢了去世的爷爷却在道路尽头与羊相遇,一方面印证了约翰·伯格所说的人类与动物两条平行线交叠,另一方面也隐喻着生灵对于人类命运的投影与映射:无法掌控自己而被支配的命运。在影片体现的现实世界中,羊有两种命运:其一,作为物种延续的生产者,被迫配种;其二,被人类宰杀成为食物或者被贩卖维系生活。动物不仅在自己的世界中,存在着竞争与选择,同时它们还面临着人类的控制与掌握。羊尚且如此,人类也并不例外,要忍受同类与传统道德规范夹持的双重压力。在卓嘎身上,没有“气球”照样被丈夫达杰逼迫着与自己结合,意外怀孕之后又被逼着留下孩子,不能去堕胎。达杰认定这个孩子是死去父亲的转世,而卓嘎出于身边人的劝阻及对现实生活困境的考虑,不想留下这个意外得来的孩子。达杰所代表的观念是传统信仰下的转世轮回观,而卓嘎则立足现实试图抛弃传统。但卓嘎并不是坚定的,在医生反复劝阻下,她没有自己决定选择与丈夫商量,刻意避开远道而来的医生不想面对这一现实状况。
同时,卓嘎在发现自己怀孕前告诉达杰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只不能产崽的母羊突然下了一只湿漉漉的羊羔。这段情节虽然没有用超现实场景表现,但在卓嘎的叙述中,也十分具有说服力。在人类与生灵的对话中,生灵任人宰割没有自我话语权,此时生灵命运是人类命运的映射,两者都无法自己掌控。与此类似,在万玛才旦导演的《老狗》中,老狗作为传统藏民精神的依托,以生灵老狗的命运为引,老人拼命想要留下作为牧人朋友的纯种藏獒,而儿子在利益驱使下要将藏獒卖到小贩手中,在传统与现实的较量中,老人选择亲手结束老狗的生命。“在影片中,父子对比、冲突与和解始终贯穿影片,老人出现时,总是骑马,而儿子总是骑摩托车;老人抽烟袋,儿子抽香烟;儿子喝酒、打台球,老人手持念珠念经”。现代文明对于藏族文化的冲击体现为摩托与马两种交通方式互不相容,儿子不想面对不能生育的事实,藏獒被老人亲手扼杀,老人最终显然是没有向现代文明妥协的,所以将藏獒留存在过往的文化中。
约翰·伯格在《看》中还提到:“若说动物是最原始的隐喻,那是因为人和动物之间的基本关系是隐喻性的……无论何处,动物提供我们以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借它们的名字或性格来让我们形容某些特质。”藏族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其孕育着牛、马、羊等这些动物,万玛才旦在《气球》中通过对动物生灵命运的书写,映射着人类自身的命运走向。
二、生者对话亡灵:生命的延续
《气球》中出现的第一个超现实场景就体现了生者与亡灵的对话,两个弟弟拿下了江洋身上象征着奶奶转世的痣当玩具,江洋在后面追逐着两个弟弟跑向山坡尽头,随着两个光着身子的弟弟消失在山坡上,江洋停下了脚步。这个超现实场景暗示着江洋是奶奶生命的延续,在爷爷和爸爸的日常对话中,也在反复感叹与强调着这场生命的轮回。两个小孙子问到爷爷他们是谁的转世,得到的回复是暂时不知道,但一定是某个生命的转世。在这个超现实场景中,两个小孙子没有穿衣服隐喻着他们暂时没有受到生命轮回转世的牵绊,无忧无虑,甚至去任意拿下奶奶转世的标志性象征。而在故事后面,父亲去世,达杰从上师处得知他会转世到自己家中,碰巧达杰的妻子卓嘎怀孕,故而达杰认定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父亲的转世。
另一个超现实场景是江洋追逐着已经去世的爷爷,所有的画面都在水的倒影中呈现,在道路尽头爷爷消失。在这场生者与亡灵的对话中,生者是被选择的一方,生来就是某一生命的延续。生命的轮回转世观体现着藏族人民深刻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只是在另外一个新生的生命中继续生存。卓嘎基于现实生活状况,试图反抗传统信仰的行为被达杰深深抵制,他宁愿生活极度困难也不愿抛弃信仰。伴随着这种转世观念而来的是藏族人民自我认同的身份困境,他们与生俱来的“他者转世”身份,赋予了他们一场特殊的使命:生来就是另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要带着另一个人的信念生存下去。
张杨导演作为非藏族本土导演以他者言说的“外视角”来阐述藏族故事,在《冈仁波齐》中也印证着生命的轮回转世:一心想要替哥哥洗去罪过的杨培老人在朝圣冈仁波齐的路途中安静离世,新生命丁孜登达的诞生仿佛就是老人生命的轮回。“现在的西藏,早已不是过去神秘且封闭的世外空间,而是一个逐渐被外来的现代文化改变着的新的西藏,关于西藏身份的体认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外来的文明并没有要求藏族人摒弃原有的传统宗教信仰,而是希望他们基于传统信仰的层面上,寻求与自我身份认同两者间的平衡。万玛才旦的另一部优秀作品《塔洛》同样在探讨身份缺失问题,塔洛身边的所有人甚至想不起他的名字,只称他为“小辫子”,为证明自己的社会身份被迫办理身份证。他的记忆力极好,能清楚记住自己什么时间养了几只羊,甚至完完整整地背诵出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段落。但随着爱上了镇上的一个姑娘,他剪掉了小辫子,被姑娘欺骗丢失了一切财产,因发型与之前办好的身份证不一致被要求重新拍照补办身份证,他彻底迷失自我,成为现代文明的牺牲品。
“罗兰·巴特在阐释爱森斯坦的电影时讲到所谓‘第三意义’。他把一个场景的意义分为三个层次:信息层次、象征层面和第三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意义通过参照必要的事实和现象产生。在第二个层面上,意义通过联想来获得。第三个层面通常由突兀的结构,奇怪的表征和过度的形式构成,意义很难明确。”在这里提到两个超现实场景,信息层次即我们所看到的江洋追逐弟弟、寻找爷爷;象征层面则是他们都是不同的亡灵的转世,死亡即意味着新的开始;第三层面指代生命轮回转世观这一藏族的传统信仰毋庸置疑,凡违抗都是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行为。
三、本我对话超我:人性的救赎
在卓嘎视角下的超现实场景中,妹妹香曲卓玛恢复了往日的长发,笑容天真烂漫,整个画面充斥着欢快与自由,而这种场景也正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万玛才旦的原小说《气球》中,并没有以妹妹为线索再展开一条故事线,影片在有关妹妹的这部分故事中增加了很多书写空间。虽然影片中并没有直接阐述发生在妹妹身上的往事,但我们从身边人与她的对话以及影片中的中学老师为她写的《气球》一书等种种行为下,可以推断出妹妹曾经所犯的过错导致她选择当尼姑来弥补。影片中刻意强调了妹妹痛彻心扉的爱情经历这条线索,用来增加卓嘎这一人物形象的戏剧性,卓嘎对于那位中学老师来找妹妹这件事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不允许妹妹再对过去有丝毫留恋。与此相反,她在自己意外怀孕对于是否堕胎的选择上却徘徊不定,这也体现了卓嘎这一女性角色的矛盾性:既迫于世俗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又想要从中试图反抗获取一丝女性的自由。
弗洛伊德提出三重人格理论的概念:“一是本我,指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部分。基本由性本能组成,代表人的本能欲望。二是自我,是理性的代表,是来自本我经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形成的知觉系统。三是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和伦理观念方面的要求,它要努力达到的是完善而不是快乐或现实。”在《气球》中的两位主人公卓嘎和达杰身上,本我体现为两人对彼此的欲望,在原始的冲动下,他们在没有找到避孕套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彼此结合,抛却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选择当下的欢愉。卓嘎意外怀孕后,在达杰身上,自我是缺失的一部分,他根据传统信仰的要求当机立断觉得孩子是父亲的转世并执意留下孩子,正因为他遵循过往经验得出了如此判断,故而与拥有自我的妻子产生剧烈的冲突矛盾。由于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再生第四个孩子不仅会被罚款,给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困难,而且会影响现有三个孩子的成长进程。卓嘎的自我体现在她既考虑到了传统信仰下的伦理规范,又结合当下情况做出了进一步判断,而她身边的人对堕胎一事有支持有反对,更加阻碍了她最终抉择的方向。最后的超我在卓嘎身上也有所体现,影片最后卓嘎躺在手术台上准备堕胎的刹那,被慌忙赶来的丈夫和大儿子所阻止,她跟随妹妹一起去寺庙生活一段时间后,最终导致了自我的迷失。
虽然影片设置了开放式结局,没有呈现出卓嘎究竟是否仍选择堕胎,但在丈夫、妹妹、儿子的态度中,观众能够想象到更可能的结局,这里万玛才旦在惯用的水面表现空间中映射出卓嘎孤立无援的复杂心境。卓嘎是希望遵从内心追求个体自由的,但她却始终在被迫着选择传统信仰下的道德规范,被动实现所谓的“超我”,进而达到人性的救赎。在这个超现实场景中,她与妹妹的欢乐互动场景与现实困境形成鲜明对比,虚幻场景使得拥有原始快乐的本我和面临现实困境的超我相遇,最终在他者的指引下得到了救赎。关于人性的救赎是藏族题材影片一直在探讨的主题,松太加导演的《太阳总在左边》中的主人公意外将母亲碾死车下,在朝拜拉萨的路上完成自我心灵的救赎;张杨导演的《皮绳上的魂》中,塔贝在护送天珠去往莲花生大师的掌纹地路途中放下过去,寻找真正的自我,完成生命的轮回与人性的救赎。在人性救赎这一永恒主题下,藏族题材电影提供了一个典范,也深刻地彰显出民族精神与时代文化。
《气球》中三处超现实场景的作用更偏向于增加影片对于命运、生命、人性的刻画程度,展现了故事中人物在现实场景无法实现的另一种结果,从而上升到对影片主题的书写:传统信仰与现实生活产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下藏族人民的不同抉择。除了颇具想象力的超现实场景,对于影片本身来说,其中的“气球”意象第一层面指的是两个儿子的玩具气球;第二层面指的是避孕套,为了遏制本我欲望冲动所产生的后果,同时也意外地被两个小儿子当作玩具;第三层面体现在精神上,在传统的意识观念中,由于避孕套作为“性”的象征成为藏族人民不可言说的一部分,也使它变得神秘而不可触碰,所以在两个小儿子当玩具玩的时候才会立刻被父亲扎破,因其本身特定的功能成为藏族人民遵守传统信仰的精神符号,当这种精神符号消失时,留在原地的人就会与现实生活产生难以协调的矛盾。与此同时,“气球”这一意象在电影中并不少见,在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一一》中,洋洋在老师面前拿出“气球”,此时,洋洋眼中的玩具与老师眼中的避孕套形成电影的戏剧张力,体现了儿童世界和成年人世界的巨大差异;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由于调皮的马小军不小心扎破了父亲藏在抽屉里的避孕套而感到格外害怕,描绘出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对于性的遮蔽;在2018年德国同名电影《气球》中,红色的热气球是带领主角一家人逃离黑暗走向光明与自由的唯一希望。由此可见,“气球”本身所具备的象征含义也是极其丰富的。
万玛才旦导演说:“我并不拒绝现代化,我的作品呈现的也并不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只是一种现实的状态。”他用现实主义叙事方式来表现传统与现实的冲突这一主题早在《静静的嘛呢石》《老狗》《五彩神箭》等作品中就有所呈现,新片《气球》融入了超现实场景和藏族女性试图争取自由的反抗意识两种新元素,使得藏族题材影片不仅在画面风格、视听语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藏族故事的主题及叙述上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新世纪以来,藏族题材电影发展迅猛,呈现主题多元化、视听语言多样化的趋势,一批优秀的藏族题材影片导演也应运而生。万玛才旦的多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关注,他用这种方式拉近藏族故事与世界各民族观众的距离,加之松太加、拉华加、张杨等多位导演不同视角下对藏族故事的书写,彰显着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对藏族本土文化走入全民族视野无疑是意义重大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