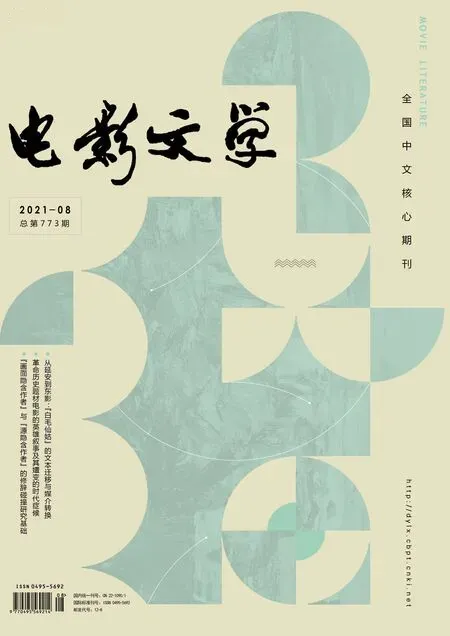《八佰》中家国情怀的历史化表达
庞书纬
(1.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2.青海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青海 西宁 810000)
由著名导演管虎执导的影片《八佰》经数次延期,于2020年8月21日上映,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在评价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化倾向。赞赏者将其称为“华语战争片的新高度”,认为其“以更加微观的视角,选择一些‘小人物’作为故事的切入点,透过小人物折射出每个国人在家国危难之际的选择与觉醒,不仅更加震撼,也更加令人动容”。批评者则认为“‘创作人’想法太多,想说的太多,这恰恰违背了艺术创作和表达的基本原理:什么都说等于什么都没说”。与此同时,根据猫眼电影的数据,上映不到4天,《八佰》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2020年国内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
作为一部取材于真实历史的战争片,《八佰》沿袭了国产战争题材电影中几乎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值得关注的是,《八佰》中对家国情怀的讲述,规避了以往常见的本质化与去历史化的叙事策略,着重呈现了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主体的多元、资源的丰富和过程的曲折。
一、上海:东方摩登与乡土“前身”
《八佰》取材于全面抗战初期淞沪会战中的最后一战,重现了1937年10月26日至31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官兵420余人(号称八百人)奉命死守四行仓库达五天四夜的悲壮故事。作为故事发生地的上海四行仓库,与租界仅一河之隔。在电影的前半段,一边是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另一边则依旧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晚唐诗人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上海代表着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主义现代性。正如李欧梵在其著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的开篇,通过对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现代性物质载体的描绘,着重呈现了上海超脱于乡土中国的“摩登”特质,并将其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诞生的重要公共空间。
上述观点总体上显然成立,然而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情况要复杂得多。电影《八佰》中的语言除普通话和上海方言外,至少包括湖北、湖南、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四川及东北等地的方言,另外还有团长谢晋元辨识度极高的“广普”。不仅四行仓库中的官兵操着南腔北调,对岸租界里的中国人也是口音各异。电影开头,涌入租界的难民大多衣衫褴褛,其中不少是农民打扮。湖北籍士兵“老葫芦”试图进入租界被拒后,换了个通道继续“闯关”,并声称“我是农民”。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规定,上海正式开埠,随即带来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据学者邹依仁研究,1852年,上海只有54万人口,其中城镇人口不超过20万,但到20世纪初已突破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抗战爆发的1937年突破380万,1942年则增加到近400万,外来移民占比始终保持在80%左右,籍贯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超过100万的为江苏、浙江两省,超过10万的有安徽、山东、广东三省,超过1万的有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江西、河南等近10个省。上述移民中,约90%为失地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人在上海总人口中的占比即使最多时也未超过5%,且更多集中在租界。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在沪外国人中,东欧、中欧难民比例居高不下。
在上述过程中,原本服务于传统血缘、地缘认同的会馆、帮会、行会、社团等组织,在新的城市空间中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成为城市公共性的重要渊薮,共同服务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正如日本学者小浜正子在《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中所说:“在同乡认同、同业者伙伴意识之上,民族意识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运动和意识两方面都以社团等组织为基础,近代国家集结起人们在社团中显示出的能量,有力地实现了国民统合。”
回到电影《八佰》不难发现,在租界支持“八百壮士”的人群中,出现了当时上海乃至国内重要帮会——恒社的掌门人杜月笙及其门徒。为了给四行仓库运送电话线,恒社青年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前赴后继,不少人献出了生命。正是那根电话线,使四行仓库中的一切为外界所知。在现实中,恒社是中国传统帮会发展到现代的产物,既适应了帮会及其首领自我“洗白”从而提升社会地位的需要,同时也服务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是传统血缘、地缘、文化认同向现代国家认同转变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在电影《八佰》中,每当夜幕降临,涉世未深的“小湖北”常常倚靠在窗边,呆呆地望着对面租界中的景致,一切犹如镜像。横亘的苏州河却仿佛冰冷的镜面,将两者截然隔开。上述场景,构成了对上海租界历史角色的隐喻。在近代史上,租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害,这一点不容辩驳。然而租界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他者而存在,却符合历史事实。“外国的影响及与之对应的民族主义,在全国范围内,都以上海最为有力。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权力的多元化结构和受到外国正反两方面影响这一条件变得极为重要和可能”。换言之,作为“镜像”或曰他者的租界及与之相伴的外国人特权,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同时租界内外多元的权力结构,客观上为国家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多种资源。
二、报纸: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媒介
关于四行仓库之战,《八佰》在呈现其悲壮的同时,并不避讳背后的残酷与荒诞: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求谢晋元和他的五二四团死守四行仓库,为的是让外国观察员和记者看到中国军队仍在坚守,从而在即将召开的“九国会议”上争取权益。然而弱国无外交,欧美列强丝毫没有干涉日本的意思,甚至连“九国会议”本身都因主办国比利时发生国内党派斗争而延期。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等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尽管向上海派驻了为数众多的记者,但其在战争初期奉行的“孤立主义”甚至绥靖政策,使报道更多持所谓“中立”立场,除让西方受众了解战争本身的进展外,并无太大意义。
与外国记者的作壁上观形成鲜明对比,《八佰》中的《申报》记者方兴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角色。原本与日本人有接触的他,在四行仓库采访期间切身感受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坚韧,被“八百壮士”的精神所感动,记录了他们面对战争与死亡时的状态,为其中的断后者捎带遗书,最后和大部队一道冲过大桥撤到租界。
电影中的方兴文尽管是个虚构角色,然而其供职的《申报》及其代表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中,作用却非同小可。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曾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要经历“想象”(Imagine),该过程是一个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依靠两种媒介,一是小说,一是报纸。“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实中,关于“八百壮士”的提法,正是来自《申报》的报道。10月27日,《申报》第五版在报道《保卫大上海》中就曾提到了五二四团,而在28日第三版中,《申报》以《悲惨壮烈可歌可泣 我孤军誓死抗日》为标题,用颇具感染力的文字,记述了战争的残酷与“八百壮士”的英勇:“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战也……”两天后的10月30日,《申报》在第三版刊发报道《国旗飘展气壮山河 我孤军四次退敌》,介绍了在四行仓库楼顶举行的升旗仪式及其影响:“六层高楼之屋顶,昨日傍晚前,并由我忠勇将士,高揭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压倒四周之太阳旗,发扬我大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与国家无上光辉。此八百忠勇壮士之壮烈义举,已博得全沪中外人士无限之钦敬,并引起最热烈之注意。”
《申报》的上述报道,影响到当时国内其他媒体,如在《国旗飘展气壮山河 我孤军四次退敌》刊发次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闸北一高楼国旗招展 我壮士八百人孤军奋斗到底》为标题报道了升旗仪式。根据笔者统计,从10月27日到31日,在《申报》刊登的报道中,涉及五二四团和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至少有16篇,并配发多张新闻照片,除介绍战况外,还包括题为《谢团长略历》的人物特写。
另外,《申报》在当时健全的发行网络,使其报道足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从而让自身成为构建并维系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根据学者邵绿研究,《申报》在20世纪30年代已在北京、天津、南京、武昌、南昌、安庆、广州、成都、重庆、长沙、杭州、福州、青岛、保定、西安及香港等40余个城市建立了分馆或代派处,并且本埠与外埠报纸价格相同。到了抗战前夕,《申报》每期15万~20万份中,外埠销量已占到64%左右。
借助方兴未艾的现代传媒,“八百壮士”的故事得以广泛传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新闻热度,并引发音乐人、电影人的关注。1937年底,由桂涛声作词、夏之秋作曲的《歌八百壮士》(又名《中国不会亡》)迅速流行开来。次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电影《八百壮士》上映,票房位列当年国内前十。几乎同时,位于香港的中南光荣影片公司也拍摄了同名粤语影片,传播效果进一步扩大。
三、地图、英雄传奇与戏曲: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八佰》中,战斗间歇的一个夜晚,一位山东籍士兵按照地球仪上的轮廓,在白布上画出了一张简易的中国地图,并将其作为背景,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士兵唱了一出皮影戏,主人公是三国名将赵云。皮影上的赵云,转战大江南北,背后地图上标注的,却不再是三国时代的徐州、荆州、益州,而是近代以来逐渐固定下来的地名:四川、湖南、山东、陕西等,也包括上海和西藏。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地图与人口调查、博物馆当作维系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具体而言,在民族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地图有助于民众形成关于领土完整的认同,为“想象的共同体”构建了地理上的边界;人口调查有助于民众形成关于国民的认同,为“想象的共同体”构建了族群上的分野;博物馆在这里所指相对宽泛,应当包含形形色色的历史记述和传说,正是这些记述和传说,为“想象的共同体”构建了历史的合法性。
电影中的上述场景,同样包含着家国情怀的隐喻。在《想象的共同体》出版后,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赞赏之余,指出至少在中国和印度,“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相互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无论是在印度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这些认同一旦政治化,就成为类似于现在称为‘民族身份认同’的东西”。换言之,对中国人而言,现代意义上“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转化、自我更新的过程,必须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转化和扬弃,从而将以血缘、地缘特别是文化为主要纽带的“天下中国”认同,转化为以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为内容的现代国家认同。
电影中,“八百壮士”常以赵云的忠义精神激励士气,而关于赵云的忠义精神,从史传到小说再到戏曲,经历了一个丰富化、细节化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历代受众对忠义精神的解读。在陈寿《三国志》中,赵云与关羽、张飞、马超、黄忠一道被写入《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中,其中赵云的部分仅293字,长坂坡一战记述为:“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东晋、刘宋时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时,增加了赵云拒绝赵范提亲和“截江救主”的故事,忠义形象进一步凸显。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不仅戏剧化地描写了长坂坡之战,更加上了赞诗:“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
电影《八佰》中,在“端午”和“小湖北”等人脑海中,曾多次出现戏曲舞台上的赵云扮相。租界中的戏园老板目睹了对岸战况,临时将演出剧目改为《长坂坡》。在一般人印象中,京剧传统、国粹的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不难看出,与武术、书法、中医等稍有不同,京剧不仅形成时间较晚,而且其大发展、大繁荣是在清末民初,与之相伴的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换言之,京剧的发展尽管包含众多传统元素,但其诞生更接近于立足近现代背景对传统的“重构”,更接近于一种现代的“发明”。类似的情形,同样适用于沪剧、粤剧、黄梅戏等其他地方戏曲。随着现代剧团管理、演出机制特别是明星机制的引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戏曲甚至成为现代都市娱乐的重要载体。正如学者徐剑雄在《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中所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京剧经过短暂改良风潮后,迅速走上市场化、通俗化、大众化发展道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成为大众流行艺术,一批海派京剧名角应时而生”。如果说赵云的故事为家国情怀提供了“素材”,那么戏曲则为家国情怀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在戏曲不断重复的唱腔中,杜赞奇所说的“群体表述”得以一次次被强化。上述“群体表述”在抗战环境中,借助形成中的现代动员机制而被政治化,构成了国家认同的文化资源。
“在中国文化中,家国观念向来是重要内容。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书写方式,也记录了这一刻入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烙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家国情怀一方面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叙事策略和美学风格,另一方面分享着一脉相承的知识谱系和情感结构。需要说明的是,《八佰》中将家国情怀历史化的文本策略绝不意味着解构,相反,其中包含的恰恰是对真实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民族新生的渴望。电影开头的“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一句,出自鲁迅的散文诗《墓碣文》,而在《墓碣文》中,“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句子更为大众所熟知,这也似乎可以作为对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一种概括。为此,《八佰》在片尾特别以字幕的方式交代,中国以伤亡3500万军民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反帝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从这个角度而言,《八佰》也是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经历抗日烽火,古老的中国涅槃重生,开启了现代国家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