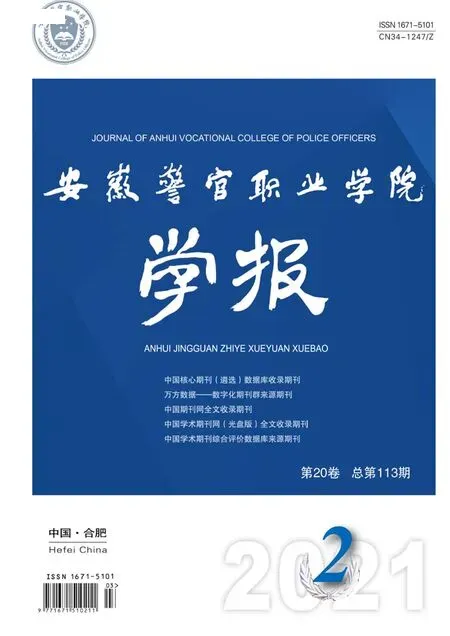不能忘却的民国初期的监狱学研究
连春亮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8)
经过清末监狱改良、民国北京政府的监狱改革,民国南京政府启动了中国监狱现代转型的步伐,催生了中国监狱学理论研究的繁荣,为中国监狱在理念上和实践中走向现代形态做出了突出贡献。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的因素,民国初期的监狱体制改革和监狱学研究的成就,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无人提起。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2003年监狱体制改革以来,促使人们对于监狱现代化建设问题进行深度反思,寻求近现代监狱的历史渊源,由此,民国初期监狱体制改革,才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重新审视民国初期监狱体制改革对现代监狱制度建设的历史价值。
王志亮和王平教授通过对清末民初的监狱体制改革的长期研究,特别是对民国初期监狱协会和监狱学刊物的资料收集和编纂整理,编辑整理了《民国初期监狱学研究论文集》(以后文中简称《文集》),向我们展示了民国初期中国监狱近现代转型的历史烙印。《文集》共分为“关于刑罚与行刑”、“关于国外监狱状况”、“关于监狱改良”、“关于监狱建筑及监狱分类”、“关于犯人教育教诲”、“关于犯人监管”、“关于犯罪及其预防”、“附录”等八部分,收录各种题材的文章95篇。应该说,这是研究民国初期监狱学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研读,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西方现代监狱理念主导民国初期的监狱改良
从清末监狱改良始,中国的监狱改良在理论上以西方国家的先进刑罚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上,主要以日本为师,先后参照日本的监狱法,拟定了《大清监狱律草案》,复制颁布了《监狱规则》和《民国监狱法》,以日本监狱体制为模板,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模范监狱,使民国初期的监狱不仅具有了近代的品性,而且初具现代监狱的元素和特质。
(一)监狱价值属性的多元化
笔者认为,清末民初监狱改良的首要意义,就是颠覆了监狱的传统价值理念,展现了现代监狱价值理念的雏形。在监狱价值属性上,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监狱是统治阶级暴力工具的属性,具有了多元化的价值解读。在理念层面为中国监狱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是1929年《监狱杂志》第3期编者按对“监狱是一个什么”作出了这样的回答:“监狱是一个感化院;凡有劣根性、恶癖及顽梗不化的人,到此可以使他身心清洁、性情仁慈,变成一个善良的国民。监狱是一个医院;凡行为上有病态的或心理及生理上有病状而影响行为变态的人,到此可以使他病魔消除,言行就范,变成一个健全的国民。监狱是一个学校;凡未受教育,无识无知,寡廉鲜耻而冒犯法律的人,到此可以使他读书写字、通达礼仪,变成一个文明的国民。监狱是一个工厂;凡身无一技,贫困失业而逼罔法纲的人,到此可以使他博得技能,因才授艺,变成一个有用的国民。”由此可以看出,监狱改良倡导要把监狱建设成为感化院、医院、学校和工厂,强调通过对罪犯的教育感化,培育罪犯良好的道德品质;通过对罪犯的心理矫治,把罪犯塑造成为心理健康和行为规范的人;通过对罪犯的文化教育,提高罪犯的文化素养;通过对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使罪犯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
(二)现代刑罚理念的介入
在《文集》的第一部分“关于刑罚与行刑”,共收录了15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现代刑罚思想和行刑趋势,特别是陈应机的《刑罚之时代的变迁》、蔡枢衡的《教育刑主义概观》、Trorsten Sellin著,李述文译的《欧洲之最近行刑思潮》等,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刑罚思想,包括报应观念、道德报应观念、刑罚观念的转化、纯理的客观主义、功利主义刑罚观念、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刑事人类学、刑事社会学、刑事心理学、目的主义刑罚观念、刑罚与教育、感化与社会教育、人格调查、罪刑法定主义与教育刑、行刑改革等。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合社会”状态,这些现代刑罚思想可以说为监狱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助推了监狱改良运动。
(三)以感化与教诲思想为主题
在《文集》的第五部分“关于犯人教育教诲”,共收录了22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现代监狱对罪犯的教育和教诲问题。其中有王子正1934年在《中华监狱杂志》第2期发表的《刑罚与感化》,论述了刑罚与感化的内在关系,阐述了现代运用教育感化方法处置罪犯的价值,介绍了国外用于教育感化罪犯的监狱劳动制度、感化院、假释制度、缓刑制度、犯人自治制度等。尤其是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关于儿童犯罪的矫治问题。足见对儿童犯罪问题的高度重视。刘蕃滋在1934年《中华监狱杂志》第3、4期合刊上发表的《行刑感化问题的检讨》一文,不仅介绍了行刑感化的实践基础,而且详细介绍了行刑感化生活的方式,尤其重点阐述了行刑感化的实质属性:“行刑的本质,首重感化主义;而感化的对象,即在改善囚徒之生活;但改善之程度,非使罪囚能享受一切物质,和精神上的美满,并须有舒适闲逸的生活,使他们由非人的生活,——奴隶和机械——进了人的生活。……故欲实践感化囚徒,当设计改善他们的生活,从精神,教养上,下一番实际建设,和训练的工作;使他们受了种种熏陶与刺激:能达于反省自新之域,得以同化于社会正常之生活;在囚为良好的罪徒,释放为良好的公民,能于是,则行刑感化之目的,可算完成。”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犯罪学家严景耀教授也在本期发表了《监狱教诲与教育之方法》,对监狱教育感化的方法改进提出了教诲以增进囚犯德育为目的、根据罪犯智力状况分类矫正、罪犯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发挥罪犯自我教育的能动性、社会适应性训练等。同时,《文集》收录了工作在监狱改良第一线的专业的教育感化人员和教诲师的一些经验总结,介绍了对囚犯实施教诲的亲身体验,提出了改进教诲教育的意见,归纳总结了监狱教诲的具体内容。比如廖志鸣的《教诲经验实录》、钟亦赓的《改进教诲教育意见书》、郑庆芬的《监狱教诲之经历》等。
(四)心理科学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应用
在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历经波折,直到近代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心理学在监狱教育感化罪犯中的应用也源于民国初期。在《文集》中,萧孝嵘的论文《监狱心理学中的中心问题》是其典型代表之一,他提出了“监狱心理学”概念,并认为监狱心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人为什么进了监狱?”;二是“人如何才可不再进监狱?”,也就是人为什么犯罪,犯罪的原因和深层次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如何改造罪犯并使之不再犯罪?这既是心理科学在监狱领域的应用,也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寻求犯罪的心理根源、研究控制犯罪和改造罪犯的早期尝试。其实,这两个中心问题直到今天也仍然困扰着监狱学界,人们仍然在寻求答案。与此同时,王书林认为一个人的品格是犯罪原因中的重要因子,撰写了《品格测验》一文,将几种著名的品格测验进行了介绍。包括陶纳的意志性情测验、马豪的激进测验、暗示测验、濮来西的考察情绪的团体量表、马根、毛尔和华煦朋等的乐观悲观、愉快抑郁测验、哈特的社会态度及兴趣测验,以及爱钱性、公平心、诚实性、美感兴趣、性情态度兴趣等,这是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方法在监狱研究中初步应用。
(五)关于监狱改良的制度设计
在《文集》的第三部分“关于监狱改良”,共收录了22篇文章,主要是对监狱改良的深化研究。监狱改良肇始于清朝末年,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因受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影响,各地政令不通,监狱改良处于时断时续状态,到1929年时,“统一告成,训政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时期,各项改革和法制建设呈现出良好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全国监狱均待改革,监狱协会亟应恢复以助进行”,监狱改良又重新纳入了人们的视野。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1929年在《监狱杂志》第2期发表《司法现状及将来计划》一文提出:“政府对于监狱之改良,亦亟注意,除由司法行政随时派员前赴各省切实调查指导改善外,并颁布各种法规,以资整饬。”并提出建立具有现代元素的“新式监狱”和“新式看守所”。《监狱杂志》1929年第1期编者按《司法部关于监狱之工作》提出筹设少年监、普通监、累犯监、外役监、肺病及精神病监等全国各种新监狱。这种按照罪犯的不同类别对监狱进行分类,相较于封建制的老式监狱的“混押制”,无疑是监狱制度改良的质的飞跃。同时,中华民国法学家钱国成在《中华监狱杂志》1934年第3、4期合刊发表《监狱之科学计划》、严德中在第1期发表《改进新监计划书》、许伯华在1929年《监狱杂志》第2期发表《监狱卫生要言》等,都提出了监狱改良的措施,对监狱改良的相关制度从理论上进行了顶层设计。
二、监狱协会和监狱学刊物相继兴起
从《文集》的文章选编和相关介绍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监狱协会和监狱学刊物,促进了中国监狱学的发展。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监狱协会和监狱学刊物的发展过程归纳如下:
(一)法学会与法学期刊的隆兴
随着清朝末年的改革运动,中国国门大开,西风东渐,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经过19世纪中国社会的孕育和戊戌维新运动的胎养,在20世纪初期法制改良的背景下,诞生了中国近代法学。极具代表性的是《湘报》第5号刊出了戊戌维新领袖梁启超的重要论作《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该文章发出了中国“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震耳欲聋的疾呼,呼唤国人重视法学、发明法学、讲求法学。他间接给出的方法之一便是设法学会,“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接着,《湘报》第43号刊登唐才常撰《公法学会叙》,第48号登出毕永年撰《公法学会章程》,第60号载出施文焱撰《法律学会令程》等。在维新变法的呼声中,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相继创建。尽管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公法学会、法律学会存在了极其短暂的几十天,但为中国法学会的后续发展和壮大开启了先河。
法律的改良转型,必须伴之以法律教育、法律研究和法律知识的传播,才能使法律的改良转型不会成为空中楼阁。在法律的改良转型、法律教育发展的同时,各类法律或政法、宪政杂志也随之破土而出。最早的法律杂志是1900年日本东京留学生所创办的《译书汇编》(1903年改名《政法学报》),后续创办的法律报刊有《政法杂志》、《政法浅说报》、《法政介闻》、《预备立宪公会报》、《法学会杂志》等。与此同时,各类法律学会和法律研究所陆续成立,1910年冬北京法学会成立,沈家本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这是中国近代全国性的法学学术团体。诚如沈家本所意识到的那样,光有良法,还不能达成良法之治,立善法而天下之人共守之,法治才能圆满,而法律的遵守需要社会人人都有法律素养。社会人人都有法律素养,就需要以各种法律报刊、各类法律学研究会传播法律思想为前提基础。1911年5月,法学会刊物《法学会杂志》创刊,中外法学家纷纷为之撰写文章,推动了法律研究的深入。各类法律报刊的创办,各种法律学会、法律研究机构组织的建立,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观念的更新和法律研究的深入进一步促进了立法、司法的发展。1912年,清朝政府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政府诞生,因辛亥革命中断的《法学会杂志》复刊。沈家本亲自为《法学会杂志》续刊作序,“吾国近十年来,亦渐知采用东西法律。余从事斯役,延访名流,分司编辑,聘东方博士相与讨论讲术,复创设法律学堂以造就人材,中国法学于焉萌芽。”“异日法学昌明,巨子辈出,得与东西各先进国媲美者,斯会实为之先河矣。”表明了学会对法学的促进作用,对法学会的发展和中国法学的未来寄予殷切希望。
清末民初的监狱改良依附于法律改良,是和法律改良相伴而生的,因此早期的监狱学研究也散见于法学研究之中。在《文集》收录的论文中,陈应机的《刑罚之时代的变迁》发表在1925年3月《法律评论》第87-89期;胡长清的《假释制度比较论》发表在1925年9月《法律评论》第115期;Trorsten Sellin著,李述文译的《欧洲之最近行刑思潮》,发表于1931年1月《法律评论》第8卷13-14合刊;苏克友的《缓刑研究》发表在1933年5月《中华法学杂志》第4卷5-号合刊;蔡枢衡的《教育刑主义概观》就发表在1933年9月《法律评论》第10卷第52期等,这些都是发表在法律期刊中。
(二)监狱协会和监狱学刊物的诞生
在清末中国法律现代转型肇始、民国继续推进的大气候下,法学研究蔚然成风。《东吴学报》、《清华周刊》、《北京大学季刊》等高校学报类期刊以及《法政学报》、《法学季刊》、《法律评论》等专门性法学期刊日益繁荣,刊载了大量的法学论文,也有少数篇目涉及监狱学及犯罪学。法律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为监狱期刊的出现创造了学术氛围,提供了经验借鉴,起到了引领作用。在法学研究兴盛之势的浸润下,以监狱改良为实践基础的监狱学研究也随之勃兴起来,除了开展监狱学教育之外,不仅出现了监狱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监狱学会、狱务研究所,也出现了监狱学研究的学术咽喉——监狱学刊物。这两者不仅成为监狱学研究的两大支撑,而且是当时监狱学研究的主要形态,其中监狱学会、狱务研究所是研究的专业主体,监狱学刊物是研究的专业阵地。
1912年3月20日,司法部发布《司法部批筹办南京监狱改良进行总会发起人孔繁藻等请立案呈》指出,改良监狱最为文明各国所注意,现当民国初建,尊重人道主义尤应实行;该员等研究有年,热心组织,所拟该会简章亦属可行,殊堪嘉许,应准认案;同时,对组建该会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如名称宜称“学会”或“协会”,不宜称“总会”等。根据这个批示,孔繁藻等人重新修订章程,该名为“中华监狱改良协会”,就此司法部正式批示“准于立案”。1912年3月31日,中华监狱改良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王宠惠为中华监狱改良协会会长,吕志伊、陈英士为副会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监狱为研究主体的学术团体。
袁世凯执掌民国政权后,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监狱协会,山东、湖北、广东等省也设立监狱协会支部,中华民国监狱协会的章程把办理监狱杂志作为协会的事务之一。可惜的是后因“政局不宁,交通梗塞,会务随之停顿”。1921年4月1日,民国北京政府发布《狱务研究所章程》,用12个条文规定了狱务所的工作事项。其中,关于宗旨与管辖,明确设立狱务研究所的宗旨是促进狱务,狱务研究所由司法部监狱司司长监督管理。关于研究制度,要求委任典狱长及分监长、各监看守长等应分期入所研究;研究科目分为两种,甲种为普遍科目包括官吏服务令、监狱官特别注意事项、现行监狱法规,乙种为特别科目包括实习指纹、新式簿记、监狱统计;研究期限为3个月,其中2个月为学科研究期,1个月为实务研究期。《狱务研究所章程》规定对监狱行政官员进行狱务研究的培训,积极拉动了狱务研究工作的开展,许多监狱长纷纷撰写监狱情况的研究报告,如民国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王元增编辑的《京师第一监狱报告》、万家祯编辑的《山西第一监狱报告》等。
民国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训政开始,全国监狱均得改革,沿用民国北京政府狱务研究的做法,在1932年颁布了《狱务研究所章程》。《狱务研究所章程》不仅比北京政府的增加了一个条文,而且内容也更加完善,对狱务研究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其中,关于宗旨与设置,明确为改良狱务起见设立狱务研究所,狱务研究所附设于法官训练所,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由法官练所所长兼任。关于研究制度,要求典狱长及分监长、各监看守长、各县管狱员等应分期入所研究,但典狱长在职五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不在此限;研究科目分为六种:第一种为基本科目包括监狱学(沿革、作业、监禁教化、戒护卫生)、监狱规则、刑事政策、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刑事诉讼法、法学概论(公私法概论)、会计法;第二种为补助科目包括感化法、劳动法及工场管理法、教育学(社会教育、成人教育、低能儿教育)、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伦理学概论、社会政策、保护概论;第三种为监狱实务,包括阶级处遇法、被告人处遇法;第四种为教育训练包括修养、训育、操练、国术;第五种为实习包括狱务、统计、簿记、教务、营缮、指纹;第六种为科外包括国民经济、警察行政、监狱建筑、科外讲演、社会事业。研究期限为六个月。在研究结果方面,研究期满举行成绩考验,平均分数满八十分以上为甲等,满七十分以上者为乙等,满六十分以上为丙等,不满六十分为丁等,对成绩考验甲等或丁等者另由司法行政部分别奖励或降调。从一定角度看,《狱务研究所章程》对于监狱官员的狱务研究培训提升为业绩考核的一项内容,并给与相应的奖励或降调,无疑发挥了促进狱务研究深入发展的作用。
民国南京政府继续推行全国监狱改革,亟需监狱理论作为支撑,为此,监狱协会得以恢复。中华民国17年8月25日,以许伯华、李竹动、屠濂、王文豹、徐正奎、吴魁、郑燦、万家祯、罗贤宝、王元增、吴棠、王晋庭、梁锦汉、陶礽、严景耀等为发起人,筹备恢复中华民国监狱协会,暂设通讯处于江苏第一监狱。中华民国23年5月15日,《中华监狱杂志》第一卷第一期问世。在筹备复建全国监狱协会的过程中,河北省率先在1928年冬设立河北省监狱协会,并将“研究监狱与犯罪学术”、“刊行监狱杂志”作为重要事务付诸实践,创办发行了《监狱杂志》。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监狱改良以来,总体情况是实践操作多,理论学术研究少。监狱改良实践需要本土化的理论予以指导,全国监狱改良需要各省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专门从事监狱学术研究的《监狱杂志》,因应了时代的呼唤而创立,为监狱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专门的平台。
三、监狱学刊物的历史价值
民国初期最具代表性的监狱学刊物当属河北省监狱协会创办的《监狱杂志》和中华民国监狱协会创办的《中华监狱杂志》。在《文集》收录的95篇各种题材的文章中,《监狱杂志》被收录44篇;《中华监狱杂志》共发表各种题材的文章79篇,被收录46篇。其中尤以《监狱杂志》最具时代意义。
《监狱杂志》创刊于民国18年11月,即1929年11月出版第1期,是由河北省监狱协会创刊发行的关于监狱学术研究的专门性杂志,第2期在1930年2月出版,第3期在1930年10月出版,第四期在1931年4月出版,并于1931年4月由于经济困难和稿件缺乏被迫停刊。历时3年,共出版4期,发表各种题材的文章102篇。主要登载关于犯罪学、刑罚学及监狱学范围内各种论著、研究、报告及翻译。在内容体例栏目安排上,《监狱杂志》分论著、报告、翻译、监狱法令、监狱界消息、监狱协会纪事等六个栏目;此外,在正文空白处,插空刊载有关监狱书目的广告及评价,刊载监狱产品的推销广告,添加有关监狱的小论文。主要特点:
一是以推动监狱改良为宗旨,力求推动全国监狱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学说,改变民众落后的监狱观念。在全国监狱协会正式成立前,希望成为我国犯罪学界、刑罚学界及监狱学界进行学术研究的论坛。《监狱杂志》在第1卷第1期上,河北监狱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梁锦汉所做的“卷头语”声称,“……朝野人士深知改良监狱当务之急,相与组织机构以为辅助,如中华民国监狱协会并与北京、山东、湖北、广东等地均设支部,蒸蒸日上大有日新月异之势,嗣因政争频仍会议中辍,去岁统一告成训政伊始,首都监狱协会应时恢复,而河北监狱协会亦于冬间成立。”
二是体例编排合理,栏目设置比较完备。《监狱杂志》共出版四期,栏目包括卷头语、序言、论著、翻译、报告、监狱法令、监狱界消息、监狱协会消息、讨论、编辑后等栏目,涵盖了监狱学专业期刊所应刊载的各方面内容,以监狱专业为标尺,科学的划分了登载的文章,使得读者一目了然,科学合理。正如河北监狱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梁锦汉在《监狱杂志》第一期“卷头语”中对体例编排的说明:“厥类有六:发为言论,事实之母,亦有著述以资研究,譬彼刍荛,献可替否,譬彼他山,攻错良友,载论著第一;近年吾国改良狱制,纯用感化,胥授工艺,沿革迁流,兴利除弊,举起大凡,敢告当世,载报告第二;欧美狱制,日新其德,愈变愈精,不遗余力,抉其精华,归我象译,取人之长,以为程式,载翻译第三;法令滋章,渊海浩浩,种类纂繁,颇费论讨,别为此门,一鳞一爪,玉律金科,以备参考,载监狱法令第四;畇畇禹甸,南北西东,山川云远,风气不同,互相传播,藉悉内容,无远弗届,精神斯通,载监狱消息第五;蔼吉人,彬彬学士,方以类聚,令闻不已,以我慈祥,式化奸尻,泽及圜扉,相助为理,载监狱协会纪事第六。”体例编排的依据和目的非常明确。
三是编辑刊载内容兼顾理论界与实务界。从刊载文章的总数上看,理论界与实务界基本上是平分秋色。一方面有理论界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和对国外先进行刑理念、监狱制度等的介绍。如严景耀、蔡枢衡等人的论文《教育刑主义概观》、《刑罚之时代的变迁》、《刑罚概论》、《死刑之研究》《论出狱人保护会》等;Trorsten Sellin著,李述文译的《欧洲之最近行刑思潮》、何基鸿译《万国监狱第十次会议案》、苏克友译《监狱待遇犯人之最低限度规则》、《二十世纪的美国监狱》、庄干之译《现代苏俄的监狱制度》等。另一方面也有实务界人员以罪犯感化和教诲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对策以及工作经验的总结为主题所撰写的文章、报告,如《教诲经验实录》、《监狱教诲之经历》、《监狱教诲之改良意见》、《关于监狱教养之谈屑》、《福建监狱之概况及改进意见书》等。选择题材的多元化,使《监狱杂志》的内容丰富多彩,符合监狱刊物的特点,体现了监狱理论与监狱实务相结合的科学要求。
四是吸纳在监人员以文章的形式“现身说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刊载在监囚犯的文章是一大创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最典型的是囚犯陈志禧发表于《监狱杂志》1929年第1期的《入狱七年之回顾》,以洋洋洒洒15000多字,详细记述了他从犯罪入狱到受到的不同的待遇,实时记录了监狱改良所带来的监狱的变化,监狱的感化教诲对他心灵上所产生的冲击,社会各界仁人志士、亲戚朋友、专家学者等对他的帮教使他思想转变的过程。为此,潘守信在《监狱杂志》1929年第3期上发表了《对于陈志禧入狱七年回顾之感想》一文,作为评论。《监狱杂志》这种多元互动性、参与式的创新做法,符合监狱改良中“囚犯自治”的理念,对于革新民众观念、促进监狱改良有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效果。
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监狱杂志》缺少专门的创刊经费和专业的编辑人员,以致于从第二期开始每期杂志都未能按时出版发行,最终仅办了四期就被迫停刊。尽管如此也抹杀不了《监狱杂志》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监狱学专业期刊,是后世监狱学刊物的鼻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是为民国初期的监狱改良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狱改良的“学术饥荒”。正如《监狱杂志》第1期“编辑后”所言:“我们在这百废待兴的建设时代,感到监狱界极迫切的学术饥荒,我们自己很惭愧,因为我们自己居在监狱界,不知道监狱到底要如何着手改良,才可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感化犯人的目的。自从近20年前由日本输入了监狱知识以来,直到现在老没有将别国的监狱最近的学理与方法介绍进来。”《监狱杂志》担当起了解决“学术饥荒”的重任。三是作为我国监狱期刊的嚆失,《监狱杂志》开拓了期刊编辑业务的新领域,为研究探讨监狱学术理论与监狱实践操作提供了专业平台。四是传播了犯罪学、监狱学、刑罚学等新的思想理论,转变了社会公众对于监狱改良的观念,对监狱改良起到了助推作用。“藉以输人各国监狱学说与进行方法”,“希望藉本杂志以唤起民众,打破传统的监狱观念,使对监狱发生信仰而与以热烈之援助”。这正是《监狱杂志》第1期“编辑后”中所期望的。五是作为中国近现代第一份监狱期刊,《监狱杂志》作出了办刊方面的诸多探索创新。正如有学者所评:“《监狱杂志》作为我国监狱期刊的肇端,开拓了期刊编纂的新领域,为总结犯罪学、监狱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中国近代监狱学的发展,推动了全国监狱改良的进程。其划时代的、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足以在中国监狱近代化的过程中和学术期刊编纂史上写上重要的一笔。尽管它前后只发行了四期便憾然而终,留下了不尽的历史慨叹,但其办刊的探索创新精神及刊载的那些高水平论著,颇值得今天我们在期刊编纂及监狱改良的过程中很好地学习与借鉴,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