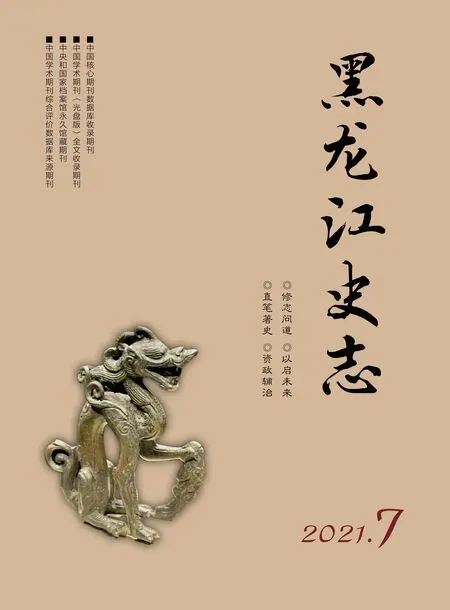南宋义臣李芾相关事迹考论
王宝森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南宋长江防线失守后,元军从中路突破攻取襄樊后,进展迅速。“宋元关系进入军事决战时期,元朝对南宋占有全面的空前的压倒性优势”。李芾被宋廷授职湖南,知其“是行必不免,惟一死”,毅然赴任,最终以身殉宋。作为晚宋时期自杀殉宋群体的一员,其忠义精神值得赞扬,“这种忠义观是超出了民族殄域的”。然而,学界目前未有关于李芾研究的专文,故笔者不揣谫陋,对其事迹作一梳理考辩。
一、李芾的为学交往
李芾(?—1276),字叔章,号肯斋。祖上为广平人,后迁徙至汴京。高祖李升“大观三年登进士第,累官朝奉郎,卒于靖康之难,赠太中大夫”。到曾祖李椿时,全家便迁徙到湖南衡州。李椿字寿翁,“以父泽补迪功郎……以敷文阁待制致仕”,被朱熹誉为“逆知得失,不假蓍龟,不阿主好,不诡时誉”。“祖父或为李正夫”,“为宣義郎、广南西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其父李大谦,“端平元年曾任浙东提刑”,以“直宝章阁致仕”。
(一)为学
在一个祖上有功勋遗业的家庭熏陶下,李芾自小聪明机警,志气果敢,其书斋名“无暴弃”斋,取其自强向上之意。或因祖上勋名,魏了翁称李芾承袭祖上遗风,并受李芾之请,魏氏将其书斋易名为“肯斋”,为之书写的肯斋铭曰:“嗟嗟李君,不自暴弃,我铭肯斋,康庸尔志”,鼓励其树立高远的志向。李芾后以“肯斋”为号,为学生涯中,拜魏了翁的弟子王爚(号修斋 )为师,修习理学。随着自身学问阅历的增长,收曾渊子、王义山为弟子。
咸淳元年(1265),李芾 “以朝散大夫、直秘阁、浙西提刑兼提举除将作监兼知(临安府)”,并以提举之职“建燕居堂以奉先圣,建时习斋、持敬亭”。鉴于地方盗乱太盛,便有借助书院来更化当地社会风气的想法。李芾重新修整虎丘书院,并且设“置学官,亲为学规以教之”,使当时“学者甚盛”。
(二)不同时期的交往
观察李芾的社会交往不妨把视野扩大,将魏了翁、牟子才、文天祥的交互关系放进来看李芾。
1.魏了翁、李大谦与牟子才。魏了翁与李芾父亲李大谦有书信往来,《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广平李氏观书所见序》中言:“既自叙所以作,厥七十年,其(案:指李椿)孙大谦守邵,则公观书之地也。是书久失而俄得,故不无烂脱,大谦又叙所以然而属予申其义”,记其文字方面的交往;绍定三年“魏了翁记并书篆广平,李大谦立石”。这些往来或许成为魏了翁和李芾关系相近的重要基础。而魏了翁和牟子才为师徒授业关系,《宋史·牟子才传》言:“牟子才,学于魏了翁”,又“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门受业”。
2.牟子才、文天祥与李芾。牟子才和文天祥则是在吉州时,“文天祥以童子见,即期以远大”,与李芾相交,则是李芾咸淳年间被罢废后,因牟子才推荐起复,重新任职。
文天祥与李芾的交往更多一些,任职吉守期间,便和文天祥有书啓往来。文天祥与李芾有书曰:“某居庐陵南陬,盖受蔯之最远者。其于当世人物无所交际,惟从田间侧听舆论,则天下伯淳(案:宋程颢,字伯淳,以伯淳谕李芾),虽隔在僻远,乌得不闻风稽首?”虽有客套之语,亦可见李芾学问之声誉。李芾也回信给文氏,述说自己为官施政的情况,文氏在《回吉守李寺丞芾啓》云:“公有异政,为百姓而一来”,鼓励他只要是为百姓做事,自然会“新令风驰,欢声雷动”。足见对李芾施政为民的信任。咸淳二年九月,“李芾被罢浙西安抚使后”,与文天祥更有了同为苍生百姓之事反被罢斥的相惜之感。二人“棹酒壶,三十里而饮饯之……回首江空,明月千里”,不亦乐乎,乃至文氏在契阔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有“每一念此,神爽飞驰”之感。德祐元年八月,李芾被加“知潭州兼湖南安抚湖北镇抚使”后,湖南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能去赴任已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此时文天祥发书信与李芾,鼓励他说,“明公当世人物,卷韬山林,四方颙颙,望其一出。方时多艰,嫠纬忘食然见王茂弘者,固以为江左有管夷吾”,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认为李芾有像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才能,挽救时势。并在其后附述,“如闻闭门谢客,雅意绝尘,然待故人,固自有情”,以待李芾胜利归来。
二、李芾历任官职情况
李芾任职的时间次序及为官的阶段情况,《宋史·李芾传》中的记载疏漏不详。以下将李芾的为官分三个时段,考证其前期任职的时间次序,澄清被罢废的时间,并对起复后的任职情况作一分析。
(一)前期任职
就笔者目前所搜集的现存史料,对李芾前期任职时间大多都没有明载,故只能简就所知对前期任职次序作一梳理。
李芾以恩荫补南安司户,选为祁阳县尉,主管一县治安,赈荒方面颇有能力。代理管辖祁阳县时,因治理有方,被选升为湖南安抚司的幕官,为上属出谋划策。后又主管湘潭县,征收赋税遇“大家”多有阻碍,包括他前任的县令遇到征收这些“大家”的赋税时,也不敢冒犯。唯独李芾“稽籍出赋,不避贵势”,致“赋役大均”。
景定年中,李芾受职德清县。时浙西闹饥荒,李芾在基层设置保伍赈济灾民,救活了数万的饥民,因功升主管酒库所。李芾在司法治理,平息地方盗乱方面能力突出。知德清期间,“有妖人扇民为乱,民蜂起附之,至数万人。遣芾讨之,盗闻其来,众立散归”。此时,李芾的名声足以令“匪盗”溃散。景定三年,任职浙东提刑知温州。时“州濒海多盗,芾至盗息”。并在其后“以知吉州除,仍兼权知温州,”“于景定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交割职事……五年二月初四日除浙西提刑。”咸淳元年闰五月,李芾“以朝散大夫、直秘阁、浙西提刑兼提举除将作监兼知”。咸淳二年二月,“除司农少卿依旧兼知”。后不久,被升为浙西安抚使。其间,因为与贾似道的矛盾,咸淳二年九月,李芾被罢官废弃。
(二)被罢废(咸淳二年九月至咸淳十年十二月)
此处关于李芾被罢废的时间,需要做一辨析。《昭忠录》言李芾“列之赃籍,坐废十年”。后来的元人文集,“方且斥公十年,”“李公本以忤似道,一斥十年”,都提到李芾被罢十年。实则其论都是以讹传讹,李芾被罢官实际不到十年。《宋史·度宗传》载:“咸淳二年九月丙辰,浙西安抚使李芾以台谏黄万石等言,削两秩免”,同《宋史·李芾传》中“似道大怒,使台臣黄万石诬以赃罪,罢之”。即是李芾于咸淳二年九月,在浙西安抚的任职上被罢。另据《宋史·瀛国公纪》载:咸淳十年十二月,“起李芾为湖南提刑”。故李芾被罢职的时间当为咸淳元年九月至咸淳元年十二月,实际被罢废时间只有八年零三个月。
李芾与贾似道的矛盾。时贾似道当国,虽然常年深居不出,但“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若不禀述贾,则不敢实行。唯独李芾“无所问”,以致和贾产生矛盾。后来又连续发生两起事件与贾似道矛盾加深。一是“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为营救,芾以书往复辩论,竟置诸法”。二是福王府和贾似道家人不遵守临安防火条令,“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两个事件令李芾对贾似道怨言颇多。私下谈论贾似道“揣制弄权,事多不从”。此事令贾大怒,“嗾言者论击,遂被重劾”。实际李芾为官清廉,所列“赃籍”完全是被诬陷所致,如元朝使臣评价“平生居官廉,及摈斥,家无余资”;亦如后人所评李芾是以“公忠受谪”。
(三)起复后的任职
咸淳十年十二月,元军在伯颜率领下从襄樊突破,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压力及招降政策的威逼利诱,致使宋襄阳守臣吕文焕最终投降。不久,长江失守,宋廷“诏天下勤王”。其后,“吕文焕以北兵攻鄂州”,乃“起李芾为湖南提刑”。
李芾被罢废后的起复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其门生曾渊子,“登朝祈贾似道得洗叙”,李芾之赃籍得以洗除冤屈。另一个是时任兵部侍郎的徐卿孙,“拔李芾于久废”,但《宋史·忠义传》中都只字未提。究其原因,即是二人的形象都不太光辉。曾渊子在德祐元年正月,时“大军以迫畿甸,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知临安府曾渊子……台谏徐卿孙数十人并遁,朝中为之一空”。宋廷后来对此二人分别采取“削两官,夺侍从恩数”的惩罚措施。二人如此行为,如果书写与李芾的相关事迹中,必然有损李芾的形象。
咸淳十年十二月,“起李芾为湖南提刑”,李芾被重新委以重任。时“郡县盗扰,民多奔窜,芾令所部发民兵自卫,县予一皂帜,令曰:‘作乱者斩帜下。’民始帖然。”初步显示李芾在被起复后的能力。
德祐元年正月,“京师戒严,朝臣接踵宵遁”,虽然已发“诏天下勤王”,甚至“大军已迫畿甸”,但“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数十人并遁,朝中为之空疎”。宵遁之朝臣令宋廷十分生气,认为朝廷“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但“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下令:“尚书省别具见在朝臣在京文武,并与特转二官。其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其榜朝堂,明吾之意。”此情况下,湖南提刑李芾“乃号召发兵,择壮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奋忠将之勤王”。是年五月,因此功被升为知潭州。
三、潭州之战及记载相异之分析
《宋史·忠义传》中关于李芾忠义形象的塑造,来源于他在潭州城抵抗元军,最终与城俱亡的事迹,经后世辗转流传,成为史书中不可多得的忠义之士。如何从忠义形象的视角看待这些?以下笔者就潭州之战中李芾的表现及战争过程作一论述,并通过元人文集分析,其“死节”事迹记载的差异原因。
(一)战争过程
宋廷在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天下起兵勤王不久,贾似道率军在丁家洲与元军决战,十三万水路人马溃败,关键时刻,贾似道逃往鲁港。当时的“京湖宣抚朱禩孙,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以江陵降,京湖北路相继皆下”,湖南地区亦危如累卵。李芾虽知湖南无兵无财,但是君命难违,或因“世受国恩”,毅然赴行。
李芾到潭州后不久,被宋廷特授“依旧知潭州兼湖南安抚湖北镇抚使”。当时潭州“城中壮士皆入卫临安”,李芾仓促间招募不满三千人,并且和溪峒蛮相互声援,修缮器械,准备粮草。时“吴继明自湖北至,陈义、陈元自戍蜀归,芾奏请留之戍潭,推诚任之,皆得其死力。”另外,将本升为衡州知府但未及上任的尹穀留在潭州,“礼以为参谋,共备御策”。元军在右丞阿里海牙、副万户张兴祖的指挥下,先派“游骑进入湘阴、益阳诸县”,然后“下江陵、分军戍常德遏诸蛮”,扫除潭州城外围阻力后,元军“以大兵入潭”。期间,宋将于兴战死湘阴,“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乔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断之。”以此阻挡元朝水军南下潭州。但元军铁骑进展神速,吴继明未及出兵,已经包围潭州。
元军主力集结潭州城以后,“为书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则屠矣。’不答。”于是元军展开进攻。史载:“兵攻西壁,孝忠辈奋战,芾亲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尽,有故矢皆羽败,芾命括民间羽扇,羽立具……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元军在初战失利情况下,改变作战方略,据《元史·崔斌传》载:“彼军小捷而骄弛,吾今焚其角楼,断其援道,堑城为三周如此则城可以得。”分析当时战争的相互利弊后,元军采取围城、并“断其援道”的战略,以火攻其楼、云梯登城,宋军“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
三个月的持续进攻后,元军破宋朝“铁坝、石心台”,采用元军副万户张兴祖的建议后,“乃决隍水,部分诸将,以礮攻之”。宋潭州统军刘孝忠被伤倒地不能起,其他诸将似乎被元军的“礮”所震慑到,泣请李芾投降于元。李芾以忠义勉励他们继续作战,但战争的态势已经完全被元军扭转,宋军大势已去,最终元军“蚁附而登”,衡阳知府尹穀自杀。
此时李芾已下了必死的决心,烧掉房舍和仓库。他下令:“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沈)忠泣而诺,取酒饮其家人尽醉,乃偏刃杀之。芾亦引颈受刃。其以身殉城,更是殉宋,显得颇为悲壮。
(二)“潭州死节”记载相异之分析
潭州城破后,城内“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而关于城破战死事的记载在《宋史·李芾传》《钱塘遗事·潭州死节》《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德祐二年记事部分,细节上却略有差异。如王瑞来先生校勘《钱塘遗事》,比对三书记载该事的史源后认为:《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德祐二年所记与本条(即《钱塘遗事·潭州死节》)记事之主要部分同出一源,而个别事实则详于本书。《宋史》卷四五〇《李芾传》所记,则细节于本书《钱塘遗事》及《宋季三朝政要》略异。如此细节本无细究的必要,但笔者在翻阅另一史料时,发现这样细节的差异却反映了晚宋时期,史书所记载的自杀群体,不完全是亲历自杀现场者所书写,亦有可能是后人在辗转传播的臆想中所书写。
如钟蜚英,后世文献对他在潭州城破后的记载云:“转运判官钟蜚英……以城降”,而实际的情况或许并不如此。《长沙死事本末后序》中记:“(钟蜚英)死而不得其名,更得谤,虽公心事上通于天,自靖自献于一祖十四宗者,浩然无愧怍,天下后世之知与否,非所计。”如此记载完全颠覆了以往史书传达的固有印象。关于李芾的记载,当时作为李芾心腹的就数人而已,而“数人之中,生存者无几”,幸而有李元美“亲在围城中,亲见公死,非他人传说者比”。但当时人却因为李元美为李芾的女婿,故“论出于其婿,谁能信之?”致闾巷之说依然盛行。假如民间臆说之言日久成为定说,被不了解内情的人所记录下来,见诸文字,最终会以讹传讹。
李芾承袭祖风,为官重学,研习理学。从荫补南安司户、尚书兵部员外郎,至湖南安抚安抚湖北镇抚使,不畏权势,为民分忧。任职期间得罪贾似道,最终被罢职。在宋朝面临元军进攻的颓势背景下,虽经罢官废弃,犹思所以报国。最终在潭州死节,以忠义节气传诸后世。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爱国精神,也正是靠着这些忠义之士不断传递,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