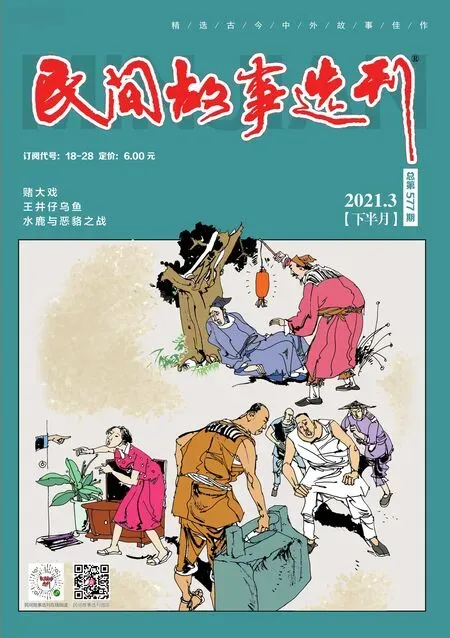扔弟弟
我不清楚父母如何做的那个决定,但清楚那个决定做得有多难。那年,喂了好几个月的年猪被父母卖了,所得的钱全交给了我。“一路给狗娃吃好喝好,坐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你就……一个回来算了。”父亲咬牙叮嘱我。
父亲的话像大书法家写字,留了一长溜空白。
可二十三岁的我,完全懂得那空白处的意思。
走出家门时,太阳还没升起,父母在给生产队干活。每天晚上胡摔乱打,使弟弟的状况看起来很差,可听我要带他坐火车、吃长面,仍是高兴得不得了,乖乖随我挤上了进县城的班车。
“想吃啥,只管说。”我对弟弟庄严承诺。
首先想吃的是臊子面。弟弟当然不会说臊子面,可走出县城车站,被那浓烈扑鼻的香味吸引,看见饭店里大吃二喝的顾客,弟弟便叫着嚷着要进去。
四两粮票,六角钱。给弟弟买了两碗。
弟弟爬桌上尽情享受的时候,我陪在旁边啃黑谷干饼。父母说给弟弟吃好喝好,没说给我吃好喝好。我清楚二两粮票三角钱的一碗面,对家里意味着什么,心甘情愿地啃黑谷干饼。
弟弟的吃相、弟弟的模样,引起了顾客的厌烦。端了饭碗的他们,无不躲开弟弟坐的桌子。个别刚进店门买饭的,扫一眼弟弟,嫌恶地躲了出去。很快,穿白衣的服务员过来,催我们赶快离开饭店。
等弟弟喝了最后一点儿汤水,我领他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眼看到了数九寒天,弟弟穿了母亲缝补得很厚实的棉衣,被两碗热腾腾的臊子面吃得满头大汗,痴傻的样子越发不堪。在省城无尽的繁华中,痴傻的弟弟唯独看上了街边的五香猪蹄。我铭记父亲的教导,毫不吝啬地买了三只。瞅着弟弟坐在街边旁若无人地啃嚼,我真想趁机溜掉,可心肠被泪水泡得瘫软,脚下总是抬不动步子。
我又带弟弟坐上了发西安的火车。
也许肚子吃饱吃好了,也许环境太陌生,弟弟双手抓了我,睡梦当中也不放松,不像在家那样,天黑以后便大喊大叫,打门砸窗,整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甚至在内急的时候,也憋红脸忍着,要我领他找地儿,不再随便拉在裤裆里,双手抓了四处乱抹……
我必须无视弟弟的改变,必须想办法把他扔掉。我奉命拿那么多钱出门,就是为把他扔掉的。假如无法完成任务,其他的不说,我回家后只有打光棍儿一条路了──在此之前,极个别准备跟我相亲的姑娘,只要听到弟弟是痴傻,全都踩了急刹车。
在西安,扔弟弟的机会实在不少,可我仍是下不了手。西安太大人太多,把弟弟扔下我老不放心。
找旅馆睡一夜,找饭店吃两顿,我又带他上了咸阳的班车。
一到咸阳汽车站,我立即领弟弟找了个墙旮旯,把紧抓我胳膊的手撕开,把装了馒头和烧鸡的布袋让他拿着,板着脸让他乖乖坐那儿,我去趟厕所就回来。
我逃上了回西安的车。点没到,车不走。远观墙旮旯的弟弟,开始确实很听话,乖乖坐那儿等待。后来便站起身子,四处张望,疯了似的。再后来,紧抓的布袋也不要了,边张望边抬起手臂,左一下右一下在脸上擦拭。
班车准备挪窝儿了,发动机隆隆响。我从将要关闭的车门跳下,跌跌撞撞跑过去,紧紧地将弟弟抱在怀里……
还是扔到西安吧。我找理由对自己说,又带弟弟上了班车。
痴傻透顶的弟弟,也许有心灵感应吧,重回到班车上以后,不再紧抓我胳膊,也不再叫嚷好吃好喝,而是静静坐在座位上,那般可怜,那般无辜。
在西安,我还是没扔掉弟弟。
在省城,我依然下不了狠心。
重新带弟弟往县城走,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兜里只剩五元的一张钱了。在县城车站,我领弟弟又吃了两碗臊子面,带他步行往家里走。
进村的时候天已大黑,家门开着,父母木头般立在里面。看见我,又看见我身后的弟弟,父母竟痴傻似的愣了,随后一把抱住弟弟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