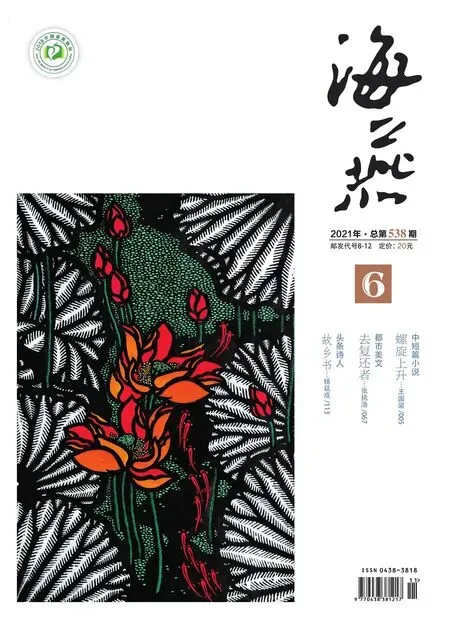老房子
文 逊
某个周日下午,忽然想去姥姥家早年所在的那片地界看看。我知道,那块地儿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动迁开发,老房子全都荡然无存,但就是想去看看。
围合那片区域的几条主街还在,名字依然叫长春路、黄河路、黄河街、大同街。不过,姥姥家那幢楼门前的南昌街不见了。我沿着几条街道兜了两圈,不时在街口停停,闭起眼睛,再睁开眼睛,把脑海和眼前的影像尽量往一处重合,然后锁定记忆。噢,那边原是一爿小商店,这边原本有家理发馆,现在第六中学操场的位置上,曾经有间街道开办的小工厂,姥姥在里面做工的样子,便很清晰地浮现出来了。最后断定,眼下那家很豪华的饭店,就是姥姥家过去的所在。
姥爷去世早,姥姥守节近六十年,只有母亲一个女儿,真正叫相依为命。哥哥自小在姥姥身边长大,我也总要到姥姥家住住,熟悉姥姥家就如同自己家一样,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着姥姥家的门牌号码——南昌街66号。那是一幢三层楼,楼上楼下住了十四五户人家。姥姥家住一楼,是全楼条件最差的一间房。首先是小,总共十六七平米的面积,隔断成三个空间。进了门先是三平米多的一个过厅,右手一张盛米面杂物的柜子,挨着柜子是口水缸;直走过一扇门,是同样三平米多的一个灶间,盘着日常生火做饭、冬天烧炕取暖的炉灶;走过过厅右手一扇没有门板只挂着门帘的门,是唯一的睡屋,不到十平米,一铺火炕,一平一高两张柜子,几把椅子,便不剩下多少空地儿了。过厅上方有一处夹层,我们当地人称作“吊铺”,许多人家都有,用来堆放各种物件,人口多的总要住人。1982年哥哥结婚,就先是和嫂子在“吊铺”上住了两个月,但每天爬上爬下着实痛苦,铺里空间又极其狭小,坐起来都会碰头,两个人也顾不得和姥姥在一铺炕上方不方便了,坚决下了“吊铺”。
“小”还在其次,那间房子最差处在于不见阳光。那幢楼是集合式构造,中间一处类似天井的中庭。姥姥家睡屋前后两扇窗,一扇朝东,对的就是那个不大的中庭,由于是三层楼的一楼,从来不会有阳光直射进来。朝西的窗子,对着的竟是另一栋楼的山墙,间隔只有一米左右,堵了个严严实实!姥姥一生劳苦,省吃俭用,从来不舍得点盏大瓦数的灯泡,通常都是十五瓦以下的白炽灯,所以姥姥家每日里不是黑暗,便是昏黄,简直是暗喻了姥姥一生的苦日子。所幸的是,哥哥特别爱读书,还喜欢晚上躺下看书,却一点都没有近视。哥哥上大学时,发现班里同学尽是戴眼镜的,还曾很乐呵地和我们讲同学们戴眼镜的趣事,我没搞清他是多少有点羡慕别人戴眼镜显着有学问,还是自豪于自己眼睛好。
那楼房是日本人统治大连时建的。那时候日本想把大连搞成他自己的领地,渐次往大连移民,据记载,到1940年前后,有大约二十万日本人生活在大连,战后陆陆续续回去了。有不少后来的日本名人,比如东京大学原校长向坊隆,日本众议院原议长樱内义雄,丰田公司总裁张富士夫等,都出生在大连。大前年,日本女影星藤原纪香到大连参加时装周活动,首先提出要去大连大学附属医院参观,原来她父亲当年出生在那里,那时叫满铁大连医院。
日本人挑了大连城区东部最好的几处地方为他们自己建了几大片住宅,后来被大连人称作“日本房”;中国百姓聚居的区域也盖起成片住宅,自然被叫成“中国房”。姥姥家所在的那幢楼就是典型的“中国房”。“中国房”和“日本房”有着明显的差别:“日本房”大都是挺漂亮的“独栋”,屋内铺有地板,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上下水,有煤气,条件更好的还有暖气;“中国房”则大部分是十几户甚至几十户群居的筒子楼、大杂院,屋里是“洋灰地”,厕所都是共用的旱厕,即便有自来水,也是全楼共用一个水龙头,煤气、暖气一概没有。跟所有中国人家一样,姥姥家要备着水缸、盘着火炕。我每次到姥姥家很喜欢帮着拎几趟水,偶尔为之,还觉得挺好玩儿,压根儿体会不到经年累月的不易。那时的人家能换到一处“日本房”住住,就是很大的改善了。姥姥始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在老房子里生活了近四十年。
我们家倒是几经倒腾住进过“日本房”。所谓“穷搬家”,父母在文革期间那段最拮据的日子里真就没少为换房折腾,自从有了我,到我七岁,就搬过五次家,1974年,搬到洛阳街69号一处“日本房”,算是安顿下来。
“日本房”战后被分配给当地百姓后,几乎全部改掉了早先的格局,原本只住一户家庭的单元,大都被分成两三户甚至更多,我家搬去的这栋房子便是一户劈成两户。我家在一楼,南北两间睡屋,都不大,但前后少有遮挡,挺亮堂;有上下水,有煤气,只是没有暖气;还有个后院,父亲在那里搭了个“偏厦子”,置放一堆大部分永远也不会用得上的“破烂”。二楼邻居祖孙三代七口人,爷爷姓李,奶奶姓张,叔叔是军官,婶婶是船厂工人,姑姑也是工人,姐弟俩一个和我同岁一个小我三岁。这是户极好的人家!两家人很快熟识交好后,我便三天两头往人家里跑,现在想来,真是有太多不懂事讨人嫌的地方。比如在人家看电视,竟然看到只剩下奶奶打着盹儿在陪我,但人家从没给我半点难看的脸色。
能遇上这样的好邻居真是难得。
我们家之前至少有两次搬家的缘由都是因为同邻居闹不和。原本一户人家居住的房子分为两户三户,厨房厕所常常要共用,水电表却无法分户,那时俗称这种情况叫“处对面房”,要处得好,真是太难了。各家日子都局促不堪,水电费的分摊难免锱铢必较,还时常会有无意或有意地私占了公共或对方空间的龃龉。都过着穷日子,有几个人顾得上“知礼节”?一来二去,邻里纠纷甚至殴斗司空见惯。父亲有次差点将同一户“对面房”的文争升级为武斗,还托人请了几个练拳脚的师傅来家吃饭,想让人家届时助阵。我那时三四岁,不记得武斗发没发生如何收场,只是很清晰地记着他们四个人吃喝的场景,一桌过年才能见到的好吃的,我却只能眼巴巴望着,心里忿忿。
洛阳街是条窄街,只七八米宽,那年月几乎没机动车跑,仅时而过过自行车。各家各户便在街上洗衣裳、晒米面、脱煤坯,夏天铺上凉席横七竖八地纳凉,哪里还是街道,简直就是个院子。最热闹的是孩子们的戏耍。孩子也多,几乎每家两个以上,只要不是上学时间,便成群结队地玩着五花八门的游戏。当时没琢磨过,后来想想,那一大群孩子是可以分出类别的。一类是家庭条件较好的,个别还是干部家庭,家长管得严,家里的孩子就不怎么和其他孩子一般玩闹,有点儿“深居简出”的派头;第二拨孩子人数最多,普通家庭,不少还是文革后自乡下回城的,每日聚在一起“山呼海啸”,时不时还会搞些“鸡鸣狗盗”,或者闹得你追我打你哭我嚎;还有一帮孩子,间或也会与上一群孩子一处厮闹,但家里显然也多有管教,甚至寄托了“成龙做凤”的愿望,不少孩子有正经“营生”。我家楼后一幢三层楼,每层各有一家孩子在学习吹号,一个小号,一个圆号,一个长号,每天早晚听得见他们的号声,一楼练长号的那个后来进了歌舞团。街角一楼那家的老三,动不动开着窗户练嗓子,也想入歌舞团,总没能考得进,便有孩子戏谑,他是因为长相不行才不被录取。他们家楼上老安家也三个男孩,老大是文学青年,立志作家,买了好多书,我总去他家,看他的书,听他讲书。我要谢谢他!自己后来也喜欢买书读书,包括也爱写点什么,受了他许多影响。隔壁一楼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男孩是位“革命小将”,几次把我们几个一二年级的孩子划拉起来学毛选,有时就在我家门洞里,每次都是学了前两篇就半途而废,但让我牢牢记住了两个篇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知那个男孩后来做了多大的干部。
我们家在那处老房子里住了将近十八年。我结婚前,父母用它换了地角远不如这里但居住条件要好一点的一套房子,给我做了新房。后来每当路过这里,总想走过去看看,也确实去看过几次。后来明白了自己的心境,我童年、少年的喜乐和偶尔的小心酸都在这里,也算是乡愁罢。这里早就没了当初的热闹,我家楼前楼后的老房子都拆没了,只剩下我家这一侧七栋楼还在,现今大都派了经营用场,有一家二手奢侈品店,一家印章店,一家烤肉店,一家花店,一家便利店,我家是一个“男士理发馆”,装修得还挺有品味。一些没有“商用”的空间还有人住,但一定都不是早先的主人了。我家西侧那栋楼一楼墙外伸出的一节烟囱竟然还在,当年我曾经往里面扔过点燃了的炮仗,忘了究竟是遭了那家大人的训斥还是受了他家孩子欺负之后的报复。
当年从来没有感觉,如今仔细端详,这几栋小楼居然各具特点、饶有风味,几处墙体、房檐、窗棂纹饰的设计颇为考究,透着心思。早先住着的时候,家里人都盼着能快点动迁,现在我倒是很希望它们能留下来,如果有人愿意照原样翻建一下,会是很不错的一处风景。但一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过去大连街头这样的老建筑太多了,拆掉的也太多了,在乎的人好像并不多。当然有人会为此痛心,认为一并拆掉了大连的历史符号和城市记忆。后来,关于东关街的拆与不拆便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东关街是“中国房”最集中最典型的一片街区,日本占领时期,那儿是大连最大最热闹的中国居民商业娱乐生活区。这儿有妻的“故居”,也住了近二十年。她曾和我说,小时候常像男孩子一样往楼上一趟一趟拎水、搬煤坯。我问她,你家也是共用的旱厕吗?她赶紧堵我的嘴不让往下问,说想想就恶心。2016年“十一”,听说东关街马上就要整体动迁了,我鼓动妻跑到那里怀怀旧,其实是我想去看看。我转了几条街道,拍了一百来张照片,意犹未尽。妻却没什么兴致,反复催我离开。难怪,她在那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当时家里一间睡屋、一间厨房加起来只有十平米,四口人,老房子留给她的记忆全是拥挤破旧,谁还会去琢磨历史印记、建筑文化这类雅事。而且那些房子乍看起来也确实没有惊艳之处,不像人家宽窄巷子、三坊七巷等有名的街区,一望就夺人眼球,东关街的“美”需要细细地发现和体会。那群建筑现存二百来幢楼,将近一百年历史了,岳父母家这样的老住户陆续搬离后,又长期由各色低收入人群和外来人口杂居,到处斑驳残缺,破败不堪,却毁不掉或潜藏或外露的精巧。总体民国风格,又随处杂糅了西洋、东洋的建筑元素,有一条巷子,我越看越像在伦敦走过的一趟街区。给中国平民盖的房子,当然不会雕梁画栋,但多处楼房上利用砖块的参差错落凹凸长短摆成的腰线、檐口、窗围,透出一种朴素别致的精美。别说,还真有雕梁画栋的细处。妻“故居”所在的那幢两层的筒子楼,在整个街区的东南角,不知道最早时是个什么特殊处所,还是因为处在门面位置,大门两侧竟然立着两座柱头堪称华丽的石柱,我在网上查证了,居然是古希腊科林斯柱式。门上头是一座阳台,铁栏杆的纹饰绝对比白宫阳台漂亮。
东关街这片老房子可是差一点就消失不见了。我和妻去的时候,发现绝大部分住户都撤出了,各处立起了围挡,贴了不少通知告示。后来,一个知情的干部和我说,当时拆除的指令已经下了,但负责拆迁的一个单位为点小事动作慢了。就在这当口,一群文物保护志愿者锲而不舍地呼吁,终于惊动了国家部委,不让拆了。后来确定了类似上海新天地那样的修旧如旧、保护性开发的方案,去年年底已经动工。我刚又去看过,不少房子已经被脚手架围拢起来;有些破损严重墙体上的老砖被完整拆卸,整齐地码在一旁;有两栋可能是用来做样板的房子,已经整修完成了!
破旧与好古真是不好平衡的难题,老房子的拆与留实在难以简单给出标准和定论,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学识、不同财富的人持有的观点必然不同。虽然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但具体起来情形千差万别,尤其经济账难算,属实没有一刀切下去的办法。
东关街的保留复原我是极赞同的。它的历史符号太独特了,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是那段特殊的侵占史和生活史的实体记载,是一段跨越百年的空间形态的地方史志。它的建筑符号也非常别致并值得体味。当年侵略者按日本人、朝鲜人、满洲人、中国人的顺序来区分人种。我不知道东关街的设计者是谁,但惊叹且敬佩那一位或一班设计师为“末等公民”设计“经济适用房”,竟也饱含审美情愫。走进东关街,可以发现遍布各处的设计构思,面对狭促的布局,设计师尽力利用了墙体高低的错落,檐脚方圆的交替和规格体量的差异,使每座建筑少有雷同,楼群组合和谐适当起伏,整体格局富于变化,找不到“长”成一样的两条街巷和两栋楼房。再看看这些年遍布城区的诸多楼盘,几乎用一栋楼的图纸拷贝了整个小区,整齐划一得单调乏味,到处都是“抄来”、“拿来”,很少见有独到的意匠。今天的设计者们应该汗颜。
几十年来,太多的老房子被拆除了,但替代它们的许多却是建筑垃圾。我们曾诟病过某一历史时期大量出现的“火柴盒”,但后来蜂拥而起的一排排形如孪生的各式“洋房”,却并未使城市的建筑审美升级。我经常诧异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老房子,哪怕是很普通的民居,即便已经残破零落,却依旧可以生成唯美的画面;但我家现在住的房子,2002年才建成,如果不考虑财务的浪费,没人会从审美价值的角度反对立即拆掉它。从“火柴盒”到“假洋楼”,凡此种种,折射出一个令人叹息的事实——我们出现了数十年的审美断层。初期的物资乏匮和长期的美育缺位,使得大部分人只看实用,不论审美;各个阶层的人出奇一致,不懂得美,不追求美,不珍重美,不守护美,亲手毁掉了太多美丽、创作了太多丑陋而不自知。
东关街的“波折”证明了我们城市审美的进步,让人看到了其他老建筑和城市遗产得以善待的希望。我羡慕妻,她的“故居”可是要永久性地保留下去了,洛阳街的老房子恐怕迟早会被拆掉。我偶尔胡想,会不会想些法子,比方说允许私人出资动迁、原样翻建、长期自持,兴许会是保留某些老房子的一条路径。我曾和身家丰厚的同学提过这想法,也曾梦到过我们家老房子翻建的场景。
百度关于“故居”的词条上说,“故居是出生后童年时期与父母等长辈一起生活的地方,通常只有一处;而旧居是除故居外的住所,可以是多处”。网络上的释义我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我确信,洛阳街69号就是我的唯一。即使那老房子哪一天被拆掉了,它也将一直在我心里留存下去。即使我真的有一天要离开故乡,心是永远走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