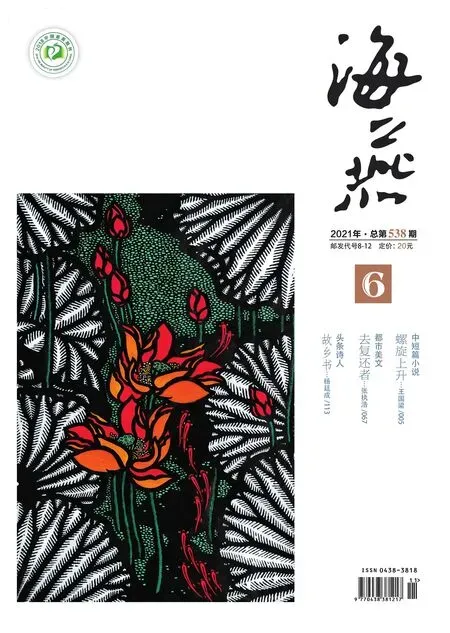我们公认的逍遥派
向 迅
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他。最初有一点不敢确认,毕竟距离还很远。我尚未从那团像棕熊一样移动的人影里辨认出他的五官。我不敢贸然开口。是过去的一些教训,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变得相对慎重。一次,我在村子里遇见父亲的一位远房表叔,不及细想,“表叔”二字就已条件反射般地从我的唇齿间跳脱而出。待我意识到口误想拦住它们时,它们早已钻进对方的耳朵。另外一次,就发生在他身上。那天,我路过伯父家的院子时,恰好看见一个头发灰白、面目模糊的男人提着一只黑色木桶从猪圈门口走出来。凭借某种类似直觉的意识,我远远地对着那个人叫了一声“伯父”,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只见他弯着腰身提着木桶,站在原地愣怔了几秒钟,然后像陌生人一样走开了。我边走边纳闷,伯父怎么不理会我呢?直到他提着木桶穿越一块弃置多年的空地走回自己家的院子,我才发现认错了人;而他也坦陈,之前并没有认出我。他在记忆里没有搜索出一个称呼他为伯父的侄子。他的大儿子在一旁提醒我,他的耳朵有点背,说话要大声一点。
待他从马路的那个拐角处朝我们家的院子踱过来时,我方才确认是他无疑。事实上,是他已然谢顶的脑袋,嘴中隐约叼着的一个褐色烟斗,棕熊一样浑实的影子,不疾不徐的步行姿势,先于他随着距离的缩短而渐次清晰的五官一步,让我确认了他的身份。那时,我双手象征性地搭在立于院子边沿的乳白色栏杆上,嘴唇欲启未启。是与他寒暄一番呢,还是在他看见我之前及时溜回房间?我一时颇为踌躇。我有些害怕见到他。害怕他站在我的对面或是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再一次想方设法地把话题引向那件我无法为他提供任何帮助的事情上。于是,我摆出一副并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以便随时可以转身撤退且不失礼貌,但我的耳朵却不受控制地收集着他逐渐变得响亮起来的脚步声,尽管它们显得遥远而又微弱,像是从某个只有在幻想中才存在的角落传来。我的右手食指也不自觉地敲击着乳白色栏杆,就像敲下一串摩斯密码,给一个悬浮在空中的隐形人传递信息。
我决定跟他打一个招呼,即使他旧事重提。毕竟我现在很少回到村子,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上一面。早些年,觉得他还年轻,见不见面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而现在,他已一跃成为我们这个大屋场里年纪最大的长者了。那些比他更为年长的同辈人,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一个接一个,相继羽化为供子孙祈求财富、权力、健康与平安的神灵。应该有一副无形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头。借着眼角边界模糊的余光,我瞧见了那颗头顶光秃而周边镶着大半圈杂乱无章的花白头发的脑袋,正以某种难以计算的速度朝我站立的位置晃动过来。
我管理了一下面部表情,隔着一段悬置在我们之间像水纹一样波动的空气,热情地喊了他一声“姑爷爷”。他猛地抬起那颗硕大的焕发着赭红色光泽的脑袋——仿佛吃了一惊,刹住脚步,继而伸出右手从嘴角取下那个褐色烟斗,立在原地,操着那口永远也无法改掉的来自另外一个村子的口音,与我寒暄起来。他脸色红润,大腹便便,像极了一个罗汉,只是连嘴唇上方的两撇胡须也花白了。两个饱满的眼袋,挂在起着肉褶子的脸颊上,分外突出。深褐色的双眼,浑浊如雨后的池塘,眼角含混。我按照小镇上的待客之道,客气地邀请他到家中小坐——事实上,我依然害怕。他用那双浑浊的深褐色眼睛望着我,犹豫了一会儿,象征性地吸了一口烟斗,宣称要到镇上办事,便告辞了。我猜他此番肯定还是去镇政府,与以往无数次一样,请镇长或某位对他的来访早已感到厌恶的办事员为他解决那件事情。为此,我悄悄地吐出一口气,但立即又感到几分失落。
我们这一代人,都毫无例外地叫他姑爷爷。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我们这个大屋场的第一个上门女婿。他来自一个我从未拜访过的高山地区的村子。据说那个村子终年云雾缭绕,冬天特别漫长,奇寒无比,而夏季又特别凉爽,适合避暑。那里的人,都操一口抑扬顿挫的搬家子腔说话。因地下富含铁矿,每个人张开嘴巴,都是一口铁锈色牙齿。母亲以前也是那种口音,然而数十年的河下生活早已让她的舌头发生改变。她现在与我们一样,说一口纯正的蛮子腔。但他始终不改乡音,尽管鬓毛已衰。这成为辨认他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许多时候,生活在大屋场的人,尤其是长舌妇们,擅于在私人聚会中捏着鼻子模仿他的腔调说话。虽然都是种地为生的农民,但大家似乎都具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学舌学得有鼻子有眼。他的妻子,一个勤劳朴实的农妇,是我父辈们的嬢嬢。只是追溯起她和我祖父的血缘亲疏关系,现存于世的长辈,没有几个能说得清楚。不管怎样,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我们有两个姑爷爷。一个是男姑爷爷,一个是女姑爷爷。
他早年喂养过一匹马,两匹也说不定。当然,那也有可能是骡子。它有一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比黑夜还要黑的鬃毛,健壮有力的四肢,优雅高贵的蹄子,一条粗大而又光滑发亮的尾巴。它生着一副人的脸孔,一副会思考会表达喜怒哀乐的脸孔。我时常见到他牵着这匹马到南山去放牧。他们一前一后沉默地行走着,像一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伙计。但他并不守候在那里,而是把马拴在一块青草丰茂之地,待到太阳落山之时,再把它牵回家去。这匹安静的就像是来自画中来自想象中的马,给了他一个特殊身份——马夫。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受人之托,去镇子西边一个产煤的村子驮煤。那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村子。他三四更就得爬起来,掌灯给老伙计喂好玉米,然后披着星月赶路。我们家是他前往煤窑的必经之地。于是,我时常会在睡梦中拾得一串清脆的马蹄及铃铛声。过不了多久,准会有一支声腔高亢浑厚而又变化多端的小曲儿自森林般庞大无涯的黑夜深处——更像是从身体内部的一块空旷之地传来。他天生一副好嗓子,装在肚子里的小曲儿也多,随意掏出一支,遥遥听来,都像是神仙挑着酒壶在月下恣肆唱歌。多年以后,我仍然会想起,一个马夫和一匹马孤独地行走在乡村公路上的画面。那些快活潇洒的小曲儿,也会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像夜晚的星星一样若隐若现。
当过马夫的他,骨子里是一个逍遥派。那份逍遥,可能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也可能是他的老伙计传染给他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屋场的小孩子都喜欢偷偷往他这个逍遥派的家里跑,尤其是春节前夕。不仅因为他喂有一匹英俊的枣红马——整个漫长的冬季,它都垂眉低首地立在院子里一丛落光了叶子的石榴树下沉思,看上去就像是一件从州博物馆借来的展品,还因为他们家开有一个烟花作坊。作坊不单单制作烟花,还制作号称能永远响个不停的鞭炮、能把耳聋之人震得重新听见万物生长之声的爆竹和拖着一个长尾巴能把星星击落到梦中的冲天炮。他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心灵手巧的作坊工人。方圆数里的人家在春节期间燃放的鞭炮与烟花,那些持续半月之久的爆炸声与绽放在夜空中的九千九百九十九种绚烂色彩,都来自他们灵巧的双手。他们把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色彩和随时随地迸溅而出的灵感,都通过那双魔术师般令人惊叹的手悉数加入到正在制作的烟花之中。也不知道,他们家的这门古老的手艺从何习得。许是文华叔,抑或朝云叔——他的次子,从别处拜师学来。
虽然如此,我是说他时常在劳作之余驮煤贩卖,家里还开有一个手工业小作坊,但他们家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
那些年,他们一大家子六口人像灰头灰脸的土拨鼠一样挤在两间逼仄低矮阴暗的老宅里生活。那两间继承自祖上的老宅被左邻右舍牛角般结实的房子死死抵在中间,生存空间十分狭窄。许多人都对他们家可能面对的一个尴尬问题表示过完全相同的担心——实则是疑虑抑或好奇:要是家中来了一位或两位需要留宿的客人,他们该如何安排床铺呢?更不幸的是,左邻右舍都是性格强悍之人。那个年代,为了芝麻大小的一点利益,亲兄弟都能反目成仇。何况他是倒插门的女婿。于是,他与左右邻居的干架事件,如同家常便饭。我亲眼目睹过一次,为了牛圈的地界问题,他与邻居闹翻了脸。恼羞成怒的他,手持一把锋利的长柄斧头,与同样恼羞成怒的邻居拉开了拼命的架势。如果不是其他人拉架,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类似的事件,直到文华叔和朝云叔长大成人以后,才成为历史。但或许那些事件留给人的记忆太过深刻,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在追忆有关大屋场的往事之时,依然会为他们家那时面对的恶劣环境喟叹不已。
正因为这样,许多年里,如何从那两间逼仄的老宅,从那种压抑的氛围中逃离出来,成了他和他家人共同的一块心病。但这谈何容易呢?两个大人四个孩子六张嘴,光吃饱饭就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而且,不幸的事情,酷似雨季挥之不去的乌云,一直笼罩在他的头顶和他们这个家庭的上空。一年,文华叔扛着一杆火铳到田野里打猎,就在他瞄准猎物扣动扳机的那一刻,火铳走火,他的右手顿时被炸得血肉模糊,自此失去了大拇指。另外一年,朝云叔在采石场工作时,放了一个哑炮,次日抑或是第三日,他匍匐着前去现场探视,哪知刚一碰到导火索,就是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村子都震动起来,无数块碎石随之从天而降,所有人都被吓坏了。还好朝云叔命大,并无大碍,但整张脸都被碎石击打得坑坑洼洼。
新房终究盖起来了。三间漂亮的平房,还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厨房。但不能算是他盖起来的。那笔用来挖地基和修建房子主体建筑的钱,是他大女儿从深圳汇过来的。他的大女儿,那位我们很多年也见不到一面的嬢嬢,十七八岁就到深圳去了。她大约是小镇上最早前往沿海地带的淘金者。无论是在我们的眼里,还是在父辈们的谈话中,她都更像是一位传说人物。那个时候,对大多数小镇上的人而言,外面的世界与日夜悬浮在我们头顶的浩瀚无垠的星空一样,还是谜一般的存在。这也是几年之后,当她的妹妹独自一人乘坐九天九夜的长途汽车——据说中途在十八个不同的城镇各自换乘了一次——前去深圳投奔她时,所有人都认为她的妹妹不会再回来了。这倒不是说她的妹妹安全抵达了深圳并在那里顺利地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更不是说她在那块传说中的黄金遍地之地乐不思蜀,而是说她在前往深圳的途中就被擅长迷魂术的人贩子给拐了去。他们每每在炎热的夏日午后或皓月当空的长夜谈起这件事情,就不免摇头以示遗憾。而当数月之后她的妹妹安然无恙地回到村子里时,他们无一不感到惊奇。或许是同一年,文华叔也去了深圳。年底回来时,他西装领带,黑皮鞋,一头时髦卷发,神采奕奕,而且说一口怪模怪样的只有在广播里才听说过的普通话。他的父亲认为他忘了祖宗,愤怒地抄起一根扁担追着他满院子打,追到第三圈时,他的舌头才猛然清醒,记起了被他遗忘数月的说话腔调。正是这位容易被新生活全盘同化的文华叔和他最终在州府当了出租车司机的弟弟,共同筹集钱款完成了房子后续的修建工作。
许是约定俗成抑或代代相传的评价标准作祟,小镇上的人都认为能在有生之年盖一栋新房子,是在自己留传给子孙的那本无形的功名簿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没有留下这一笔,就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因他家的新房子与他无甚关联,所以大家并未对他在往日的基础上生起多少额外的敬意。在大家看来,他和小镇上另外几个大名鼎鼎的人一样,一生毫无建树,而且既没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也没有多少荣辱心,属于典型的甩手掌柜。就连他的儿子也这样说。
但不管怎样,自从他们家搬进新房子的那一刻起,他便迎来了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尤其是在儿子相继成家,女儿相继出嫁之后,他真正过上了神仙般逍遥快活的日子——尽管文华叔的婚姻十分不顺,让他们操碎了心。他的嗓门原本就大,现在愈发响亮起来;他的脸,大约也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变得饱满而又红润的;他的腰杆,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了。他的大女儿在深圳买了房,他和女姑爷爷不时会轮流乘坐长途汽车前往省会武汉,然后在天河国际机场转乘航班飞过去,帮忙照顾外孙。更令人羡慕的是,几个子女为他们老两口各自购买了一份年满六十就可以按月领取退休金的商业保险。现在,他们每月可领两千块啦。
于是,无数人都对他们老两口重复过同一句话:每天坐在家里喝喝茶打打牌就有工资可领,何须继续劳心劳力种地?他们对此置若罔闻,不仅把自己家的地种满,还租种邻居家的地。而且还喂养着几只雪白的羊。时不时地,可以见到几片雪白的会叫喊的云朵拖着他往田野里一路飞奔。毕竟年事已高,为了防止因跟不上羊的速度而摔倒在地,他不得不把发福的身子拼命往后仰,握着羊绳的双手被一股股无形之力牵扯得笔直,脸上也因憋着一股劲儿而涨得通红。
六年前吧——也有可能是七年前,我回到小镇上过春节,他听闻了,专程登门拜访。我以为他前来拜访的目的,是为了与我交换他对当前时事政治的看法。他平时十分关注国家大事,也对村坊间各种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兴味甚浓。可自从他进门张开尊口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谈话内容就没有离开那一块土地。
对于这块成为谈话核心的土地,我是陌生的。我既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它的形状。但显而易见,这块土地,完整地存在于他的脑海里。他肯定偷偷地用脚步丈量过它的面积,用眼睛目测过它的每一寸泥土。他或许还记得它的气息以及它的滋味——稻米的滋味。事实上,这块土地与其他好多块我同样不知其具体位置与形状的土地一样,是政府在离新集镇不远的地方划给他们家的,我们家也有一块。由于距离遥远,我们不可能亲自耕种与管理,都是租给当地的农民,每年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稻谷以充作租金。他家自然也一样。
也不知具体什么时候,他和村子里另外一户人家,为了两块地的地界问题产生了纠纷——他们原来都把地租给同一农民,那农民为了耕种方便打破了原有的界线,时间一久,记忆出现了偏差,而又没有界碑作为凭证,他们便各执一词。他前往镇政府寻求帮助,或许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他自此日夜都想着这件事,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精神上也备受折磨。
他此番前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为他撰写一篇有关地界纠纷案的文章,并尽可能地推荐到县镇两级地方行政长官都能够阅读到的新闻媒体发表。那个时候,小镇上的人都传闻我供职于邻省省会的某家报社,在本省报界也有一些人脉。他想借我之笔,制造出一点舆论影响,以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因我并不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想介入他们两户人家之间的纠纷,便拒绝了他的请求。只是给他建议,如果其他途径解决不了,可以诉诸法律。
他虽点头应允,但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
第二年抑或第三年冬天,他在我祖母的葬礼上悄悄地将我拉至一旁,再次满含希望地提及此事,盼我能助他一臂之力。我依然告诉他,诉诸法律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一切听凭法官决断。他听完戚戚然,默不作声。
来年夏天,当然也有可能是秋天,或是其他什么时候,我意外得知,为了这块土地的事情,他竟然每天不辞辛劳地徒步五六里地,前往镇政府上访,请镇长出面为他主持公道。一时间,他成为了小镇上人人皆知的名人。政府曾派专员将两家人召集在一起进行调解,但他对调解结果并不满意,依然风雨无阻地前去上访,甚至在一怒之下,悉数拔掉了那户人家地里刚刚栽下去的秧苗。此种行为触犯了法律,被逮去拘留了好几天。
当然,这件事也可能发生于他首次将有关那块土地的纠纷案告诉我之前。这是极有可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记忆越来越不可靠。时间会让记忆中的时间发生偏移,甚至会让事件本身变得扑朔迷离。
现在,他已经很老了,诸如高血压之类的毛病纷纷找上门来,时不时得去照顾一下医院的生意。但据说他一直没有放弃那块土地,虽然他不再对别人提及与之有关的种种往事,尤其是那段被拘留的经历,也不再去镇政府上访。
那块土地,现在荒着,什么庄稼也没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