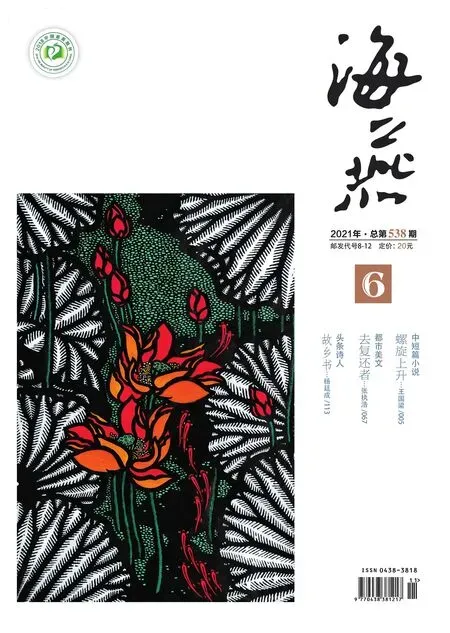读诗记(十二)
刘向东
砍光伐尽
清点
这是我的帽子,
这是我的大衣,
还有刮脸用具
放在麻布袋里。
装食品的罐头:
我的碟子、杯子,
我的白铁皮上
刻着我的名字。
我刻字用的是
我珍藏的钉子,
我不让看见
免得别人眼馋。
干粮袋里放着
一双羊毛袜子,
还有我不对任何人
透露的一些东西;
夜间我就拿它
当作我的枕头。
在我和地面之间
铺着一块厚纸板。
我最心爱的乃是
我的铅笔芯子;
白天它给我写下
我夜间想好的诗。
这是我的笔记簿,
这是帐篷帆布,
这是我的手巾,
这是我的缝线。
(钱春绮 译)
有评论家称以艾希为代表的诗歌风格为“砍光伐尽派”,而这首诗就被誉为“砍光伐尽派”的开山之作。所谓的“砍光伐尽”,是对艾希诗歌话语特性与写作者心理特性的统一概括。
《清点》写于1945年美军战俘营中,是打开德国战后“废墟文学”先河的作品之一。它通过一个卑微的战俘清点他可怜的“财物”,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战争在给别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它没有正面写战争,也没有直接议论式的反思,而是历数着一个个物象,就更为惊心动魄地将一个受动于不义战争、为法西斯所利用的小人物——盲目的牺牲品——的心灵、肉体、物质的艰难困苦表现了出来。从这个受害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缩影。疯狂而痛苦的战争留下了无数废墟,与人的物质生活一样,人的心灵也是荒芜贫瘠的。使用简劲甚至“干枯”的口语写作,恰好达成了语言与生存现状的合一。这里,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互为表里的。
你瞧,这个卑微的战俘,在机械木讷地“清点”他那根本无须清点就可一目了然的可怜“财物”:除了遮体的破衣服和睡觉时充作“褥子”垫的烂纸板外,还有什么呢?一只破罐头盒既当杯子也当碟子,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为防被“盗”,“我”得用一枚钉子在它的白铁皮上刻上自己的姓名。而那枚钉子更属我的“细软”,别人望着它眼馋呢,“我”得藏匿好。在这些“财产”中,有“我”最心爱的东西——一截铅笔芯。夜里“我”心潮翻涌,想着诗句,白天它帮“我”记下来……
这首诗仿佛客观纪实,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但内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一个个物象代替诗人“说话”,客观纪实与内心独白混而难辨了。“砍光伐尽派”诗歌中强劲滋生的骨肉沉痛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谦恭未免过晚
我们整好了房间
挂好了窗帘,
地窖里有足够的储备,
煤炭和油,
在皱纹中间用小药瓶
把死亡藏起来。
从门缝里我们看见世界:
一只被剁掉脑袋的公鸡
在院子里到处跑。
它践踏了我们的希望。
我们在阳台上扯起了被单
表示投降。
(绿原 译)
这首诗的标题就告诉人们,对世界血腥战争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而言,为败势所迫仅仅谦恭地“在阳台上扯起了被单/表示投降。”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挖掘导致荒唐、罪恶战争的根源,痛彻地反思、忏悔,以免人类历史的灾变再一次出现。
这首诗写得极有层次。第一节是战争的准备,貌似战备物资储藏丰富,殊不知,死亡的可能也在同步积累着。第二节写战争那疯狂残酷的非理性性质:“一只被剁掉脑袋的公鸡/在院子里到处跑。”这个骇人的意象,将战争的性质说尽了。这可怕的一刀,其实既砍向了全世界无辜的受难者,也砍向了挥刀的人群。第三节写战争给物质和精神遗留下的无穷的灾祸。物质的灾祸毕竟可以弥补,那难以弥补的是“它践踏了我们的希望。”
是的,“谦恭未免过晚”,但愿人今后不要在制造了巨大的灾难后再被迫谦恭,而是要时时保持对理性、和平、慈爱的恭谨敬护。艾希的诗总是在极度简省的笔墨里倾注着直指人心的力量。死亡的小药瓶——剁掉脑袋疯跑的公鸡——阳台上投降的白被单,这三个精审的意象,以其严密的历史逻辑和痛苦的情感,不仅为二战也为一切血腥的战争进行了命名。诗人反思的深刻和诗艺的精湛一同呈现出来。
承受孑然一身的孤独
1926年5月9日,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在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信中,异乎寻常地写出了这样的话:“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也许意味着)去超越诗。”
其实里尔克早期的作品,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一朵凋萎的花可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少女,一颗眼泪也能成为洞察天宇的星辰。这是一种“寓言”式的作品,由彼及此,本质上还是以抒情主体为中心的诗歌品格。
对于早期的诗,里尔克曾自我评论说:“那时,大自然对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刺激物,一个怀念的对象,一个工具……我还不知道静坐在它面前。我一任自己内在心灵的驱使……就这样,我行走,眼睛睁开,可是我并未看见大自然,我只看见它在我情感中激起的浅薄影像。”
中年里尔克认为诗不再是情感,认为“诗是经验”,他的诗,也发生了质的转变。
“经历和体验”,它不是一种纯熟的技艺,而是通过对艺术献身的“工作”去寻觅和发现被遮蔽的事物中原始的内涵,是置身真理中的一种创造。
冷静地面对世界而达到客观化,超越情感的层面。在这样的诗中,不是“我喜欢这”,而是“就是这”。
豹——在巴黎植物园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冯至 译)
这首诗是写豹子还是写人?整日被关在笼子里的豹子怎会有这样复杂的心情,会感到“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显然这是里尔克将自己的心情移至豹子身上的结果。豹子是豹子,也是人,这种人与豹合而为一,不知何者为豹、何者为人的一体状态,或也可称之为移情的例证。
预感
我像一面旗帜为远方所包围。
我感到吹来的风,而且必须承受它,当时下界万物尚一无动弹:
门悄然关着,烟囱里一片寂静;
窗户没有震颤,尘土躺在地面。
我却知道了风暴,并像大海一样激荡。
我招展自身又坠入自身
并挣脱自身,孑然孤立
于巨大的风暴之中。
(陈敬容 译)
里尔克强调写作首先要对事物进行长期而多样的观察,并把观察结果烂熟于心:“为了写一行诗,必须观察许多城市,观察各种人和物,必须认识各种动物,必须感受鸟雀如何飞翔,必须知晓小花在晨曦中开放的神采,必须能够回想异土他乡的路途,回想那些不期之遇和早已料到的告别;回想朦胧的童年时光,回想双亲,当时双亲给你带来欢乐而你又不能理解这种欢乐(因为这是对另一个人而言的欢乐),你就只好惹他们生气;回想童年的疾病,这些疾病发作时非常奇怪,有那么多深刻和艰难的变化;回想在安静和压抑的斗室中度过的日子,回想在许许多多的海边度过的清晨,回想在旅途中度过的夜晚和点点繁星比翼高翔而去的夜晚。即使想到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回忆许多爱之夜,这些爱之夜各个不一,必须回忆临盆孕妇的号叫,脸色苍白的产妇轻松地酣睡。此外还得和行将就木的人做伴,在窗子洞开的房间里坐在死者身边细听一阵又一阵的嘈杂声。然而,这样回忆还不够,如果回忆的东西数不胜数,那就必须还能够忘却,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等待这些回忆再度来临。只有当回忆化为我们身上的鲜血、视线和神态,没有名称,和我们自身融为一体,难以区分,只有这时,即在一个不可多得的时刻,诗的第一个词才在回忆中站立起来,从回忆中迸发出来。”在这一大段文字中,里尔克揭示了一首诗诞生的艰难前奏。其中的核心环节是观察、体验和回忆。回忆被里尔克视为诗歌诞生的策源地,里尔克强调一定要使回忆成为身体上的某个器官,它必不可缺但是常常不被察觉。直到有一天,这种回忆突然自动涌现出来。只有这样,才会转入文字表达阶段。里尔克认为表达就是对客观事物做冷静描述,并使自己的特定心境弥漫于描述之中,从而借助客观事物象征诗人的整体心境。因此,里尔克的诗歌被称为“事物诗”,《预感》就是其“事物诗”的代表作。
在这首诗中,诗人把旗帜作为自身的象征,把风暴作为灾祸或苦难的象征。全诗可以分成两个阶段:风暴来临之前与风暴来临之后。所谓“预感”指的是风暴来临之前,并和后一阶段的真实感觉互为映照。诗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包围”,它体现出来的是远方带给诗人的压抑感。诗人之所以说包围自己的是“远方”,是因为远方是酝酿风暴的地方。“包围”和后面的“承受”相应。“承受”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焦虑感。事实上,无论是“包围”还是“承受”都处于“预感”当中。也就是说,这时候并没有风暴。但是,敏感的诗人已经预感到它就要来了,因而心里时刻处于有意识的“迎接”状态。以下几句用“下界万物”作为反衬,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诗的空间。到第二阶段,风暴真的来了,诗人试图像大海一样与风共舞。但是,在风中飘扬的旗帜却又返回了原地。结果,诗人只能像旗帜一样在挣脱自身与返回自身之间来回翻腾。苦难之中的诗人既感到不由自主的无奈,又承受着孑然一身的孤独。
灵魂像河流一样深沉
黑人谈河流
我熟悉河流:
我熟悉那些像地球一样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里流的血液还要古老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我在幼发拉底河中沐浴,当朝阳还是年轻的时候。
我在刚果河畔盖小茅屋,河水抚慰我进入梦乡。
我眺望着尼罗河,在河边建起金字塔。
我倾听密西西比河的歌唱,当亚伯•林肯顺流而下新奥尔良,我看见它的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中闪着金光。
我熟悉河流:
那些古老的幽冥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曾卓 译)
兰斯顿·休士,美国著名黑人诗人。他的《黑人谈河流》,是一首不同凡响的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强大艺术表现力的佳作。
此诗写于他的中学时代,是他发表的诗歌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诗人怀着无比自豪的感情,以世界著名的大河为喻,展现了黑人繁衍的地方,深情地歌唱了曾为世界和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黑人种族。对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现实、他们勇敢的生命给予了热情的赞美。河流的呼啸就是黑人古老种族生命的呐喊。更深刻的是,这首诗还把黑人形象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奴隶的形象联系起来,从而使诗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普遍价值。作者礼赞河流,更讴歌黑人,在人与自然浑然合一之中,使人深入理解了在漫长历史背景下伟大的黑人种族顽强的精神。
为了烘托凝重的感情,诗中还写了流淌在广阔土地上的那些河流的朝阳、落日和黑夜,诗人以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不同景物,渲染出一派雄浑绚丽的色彩。
这首诗把爵士乐的韵律和节奏融会于自由体诗歌之中。反复吟唱,极具黑人通俗民谣的风格,准确地体现了黑人诗歌的精髓是“声音”而不是印刷符号这一特征。
时间是流动的,历史是流动的,生命是流动的,血和泪也是流动的。这首短诗,竟含括了如此博大的内容,如此广阔的空间!
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
圣诞驶车送双亲回家
穿过风雪,我驶车送二老
在山崖边他们衰弱的身躯感到犹豫
我向山谷高喊
只有积雪给我回答
他们悄悄地谈话
说到提水,吃橘子
孙子的照片,昨晚忘记拿了。
他们打开自己的家门,身影消失了
橡树在林中倒下,谁能听见?
隔着千里的沉寂。
他们这样紧紧挨近地坐着,
好像被雪挤压在一起。
(郑敏 译)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怀着善良又惊奇的诗心,体味着大自然及人伦亲情。读这首诗,我们感到宁静的心音清晰,却又有微微的怅惘涌动。短短十几行,时空交错,意绪纷飞,将我们引向了亲情——家——积雪的山谷——橡树林……甚至更远的地方。
在风雪的圣诞之夜,诗人送二老回家。看来父母真的老了,“在山崖边他们衰弱的身躯感到犹豫”,这种至为细腻的体察只会出自一个孝子。诗句是最不能骗人的,它运行在诗人的血液里。一对相依为命的慈祥老人,悄悄地谈话,在琐屑的日常细节及难舍孙儿等“不重要的话题”里,恰恰涌动着最本真的亲情。诗人感受着这一切,温馨而伤怀:爹娘已过秋风迟暮之年,他们生命的旅程已是最后季节的沉寂冰雪,“他们这样紧紧挨近地坐着,/好像被雪挤压在一起。”最后四行诗,在写实的场景中“深层意象”翩然跃起,生命与大自然构成了彼此的观照,直觉与推测凝而为一。这是诗人对自己诚朴而复杂的警醒:让“我”常常看望他们,度过对二老来说已所剩不多的共同时空,因为“橡树在林中倒下,谁能听见?/隔着千里的沉寂。”
诗歌不应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现,但也决不能成为枯燥的生活小型记事。
考虑放弃所有的野心是多么奇妙!
突然,我清楚地看见
一朵刚刚飘落在马鬃上的
洁白的雪花!
(彭予 译)
读《饮马》,想起了王维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它们有相同的凝神感。《饮马》的后三句是对第一句中提到的“放弃”的真正放弃。不知道勃莱是否读过道家的哲学,这诗的感觉是深入、安静。短短的四句,实际走出了很远,最后雪花那个词也不像终点,像开始。这种灵光一现,回归自然的体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
反对英国人之诗
风穿树林而来,
像暮色里骑白马奔驰,
是为了国家打仗,打英国人。
我不知道华盛顿是否听树的声音。
整个早晨我坐在深草里,
草长得能遮住我的眼睛。
我从树下抬头,听树叶里的风声。
突然我发现还有风
穿过深草而来。
宫殿,游艇,静悄悄的白色建筑,
凉爽的房间里,大理石桌上有冷饮。
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
(王佐良 译)
这首诗题名为“反对英国人之诗”,其成诗背景可能很复杂。但诗就是诗,我们只能把它当诗来读。因此,在诗中勃莱写了一系列带有幽静、隐秘、清畅之美的大自然画面。伴着阵阵清风的吹拂,使我们领略了一种有着清风般活力和美质的诗学立场的真义。要注意,这里的“为了国家打仗/打英国人。”可能只是一种幽默的说法。
“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它既是自豪,又是反讽:对诗而言,那种连风声和自然之美也不听不看的“大诗”,难道就真是“富有”的吗?那些丧失了对情感和自然的敏悟的诗人是“不好”的,而能“听着风声”的贫穷诗人,才是真正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