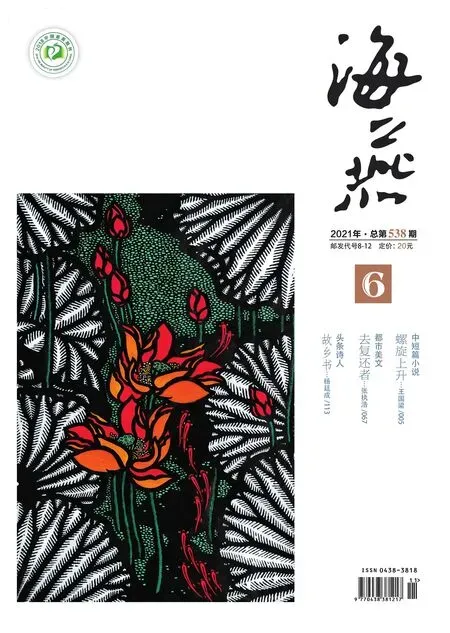去复还者
张执浩
孟浩然兴许是盛唐诗人群中最爱唱和的一位吧。如果我们把应景诗也纳入到酬和的范畴(事实上,他的许多应景诗也是酬和之诗,譬如《洗然弟竹亭》《题长安主人壁》《宿桐庐江寄广陵诸友》《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等),那么,在他流传下来的两百多首诗里,这类作品竟占去了相当比例。这位年过40才萌生出科举入仕念想,从家乡襄阳出发前往长安一探究竟的诗人,一生中写下了许多充满矛盾的诗篇,始终在入仕与归隐之间徘徊缱绻,辗转反侧,他似乎对入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又好像对入仕以后能有什么作为毫无计划。仕也好,隐也罢,他感兴趣的或许是那些与朋友们觥筹交错的日子,活在欣赏他的人群之中,如果无人欣赏,他情愿独自去欣赏山水,从身边的自然风光中获得慰藉。当同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大都少小离家,奔往仕途,或流离颠沛,或客死他乡时,似乎只有他在挫折之后,全身而退,尽管心有不甘,但还是部分笃守住了早年的心愿,最终回到了他心仪的“把酒话桑麻”的暮年。从这个方面来看,虽然人生并不完全遂心如愿,但孟浩然在人世间的52年光景也应算是圆满的了。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时代,很少有人能像孟浩然那样赢得诗人同道的广泛爱戴:“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这是李白对他的热情赞美,还为他题赠写过一首名作《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开阔空旷的人间情谊,在云天之间流淌,折射出人生的豪迈与感伤;孟浩然落第之后,王维给他写过劝慰诗:“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浩然归襄阳》)后来,王维还把孟浩然的画像绘在了郢州的刺史亭里,被世人称之为“孟亭”。正是在王维的笔下,我们领略到了这位世外高人的容姿:“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凤仪落落,凛然如生。”(《新唐书·孟浩然传》);“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馆,春雨馀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诧。”这是杜甫在他身后写给他的诗句,杜甫甚至称赞孟浩然的诗超过了鲍照谢脁;此外还有张九龄、王昌龄,张说等诸多诗人对他的赞誉。当然,孟浩然也回赠了他们更多的诗篇。到了晚唐,他的同乡皮日休将孟浩然与王维并列,仅次于李杜:“明皇世章句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介其间能不愧者,唯吾乡之孟先生也。”(《郢州孟亭记》)此后,孟浩然便被大多数论家选者置于王维一旁,将二人同列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孟浩然的个人性情、诗品之外,很有可能还附加了许多别的因素,譬如,他诗歌里弥漫出来的散淡、清癯又清新的自然风格,很容易给人以隐士典范的印象,而这种隐逸的人设正是古代士子们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宇文所安的说法是:“同时代人最感兴趣的不是孟浩然的诗,而是他们所认为的孟浩然的个性,那些诗篇是接近这一个性的媒介。”我深以为然。与孟浩然同时期的唐人王士源也是一位高蹈之士,特别崇拜孟浩然,赞美他“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在孟浩然死后,王士源四处搜求编辑了孟浩然文集,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为不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孟浩然集序》)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孟浩然早年的隐逸也不是故作姿态,他的确有风流浪漫、任性适意的一面,为人真诚豪爽,也善于社交,而正是这种亲近自然、旷达放浪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世人的一再侧目,让他在天才济济的大唐诗坛葆有重要的地位。
公元689年,孟浩然出生在襄阳一个家境殷实的富户之家,家有良田多顷,还有祖传的园庐,他曾在《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一诗中这样描述家乡风貌:“弊庐在郭外,素产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一幅生气盎然的田园牧歌景象。孟浩然就是在这种风景秀美的环境里长大的,平日里和兄弟们一道侍亲读书,过着恬静怡然的生活。这里不仅风光秀美,而且还是人文荟萃之地,有当地百姓为西晋著名政治家羊祜建的“堕泪碑”,有种种关于东汉隐士庞德的传说,还有后汉习郁所凿的习家池……孟浩然早期的作品,包括他晚期的作品,甚至是他后来间或去江南一带写下的行旅诗中,都深深打上了这里生活的烙印。田园,乡村,美酒,怀人,基本上构成了他写作的母题,他的重复,单调,以及在有限的题材中追求无限意味的写作方式,在盛唐一代的诗人中是少有的。他很少写七言诗,大多为五言体,基本上不写古风乐府。相对闭塞的生活现场,使孟浩然的整体语速显得不疾不徐,轻缓有致,虽然偶有沉雄廓大的笔触,如“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晚泊浔阳望庐山》)但很快又回到了怡然自得的舒适状态:“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过故人庄》)我在阅读他的这批主题性相对集中的诗篇时,时常惊叹于诗人的耐心和定力,他的许多诗都是在追求层层推进的声音和视角效果,如雾中之山在等待云开雾散,依凭的是自然造化之力,以及诗人的耐心,而不像同时期的大多诗人那样,主动地朝向高迈宏阔之境狂飙突进。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文风,那么,他的生活态度又会不时改进这种文风。孟浩然亦当如是。为了克服题材的局限性,孟浩然经常会改变作品风格,或者将多种风格互相混杂,形成一种看似复杂的文风。他骨子里是一个隐逸的人,却始终不甘于永远隐逸的生活状态,每一次寻求改变的过程其实都是对理想生活的背叛,而这种自我伤害越深,他内心中的愁闷就越重,但他却又不得不极力维护着那样一种既定的散淡而隐逸的“人设”。在进京之前,孟浩然也曾有过几次漫游的经历,他先后去过扬州、宣城、武陵等地,在途中结识了李白,并成为好友,但他似乎从未在外地羁绊太久,总是踌躇着出门远行,然后又匆匆回家,沉醉在故土的田园风光中。他的许多诗都最后落笔于“归来”主题,这几近成了一种写作模式,这一点也是在同代诗人中少有的。可以说,在40岁之前,孟浩然仍然处于蓄势待发状态,为即将应举入仕做着准备,却始终心存忐忑,因为他一直没有想清楚入仕的目的性何在,然而,既然自己已经获得了这么大的名声,且朋友们都在朝中,那么,还是去试试吧。
大概也是受到了开元盛世“英特越逸”气象的激励和鼓舞吧,公元728年,孟浩然决定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一路上他都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就在考试临近之日,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关戍惟东井,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乐建寅春。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不难看出诗人当时喜悦的心态,就打算一举及第之后,在柳条新绿的时候回家报喜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落第了。“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南归阻雪》)这大一把年纪求仕不成,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家,孟浩然实在是有些心有不甘,于是,他干脆就在长安城内待了下来,吸取落第的教训,一方面等候机会干求,一方面广交诗友。此时的长安城内已是高士云集,张九龄在做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王昌龄在秘书省做校书郎,王维也从外地回到长安候任,储光羲、綦毋潜、崔国辅等都已及第。史书里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秘书省诸公集会赋诗,是夜,秋月新霁,孟浩然随口吟道:“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当他念出这两句诗后,“举座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其实,这两句诗并无什么漂亮的词藻,但正是这种平淡自然、清水洗尘般的语言状态,一下子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说,“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作为盛唐诗人,孟浩然的诗在清晰自然上可谓下足了工夫,他的许多句子都给人以清丽脱俗、生机勃勃的印象:“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夜归鹿门歌》)这里没有一句是虚飘的,句句落到了实处,语境结实,语义细密,但却如针脚般构织出了一幅活泼生动的生活画面感。
孟浩然在长安盘桓了一年多时间,始终干求无门,终于起了归心。关于他在长安不第,《新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可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孟浩然在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过得很窝囊,虽然收获了王维、王昌龄等一干朋友,但长期处于仕途无望状态,让他以前的远大抱负逐渐化成了一丝丝怨气:“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贤。……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这首《题长安主人壁》的诗里就充满了愤世之情。虽说开元盛世举贤成风,但任人唯亲的不公现象,哪里是孟浩然能够理解的呢。“风泉有清音,何必苏门啸。”(《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当孟浩然终于明白自己可能终生都无法踏入宫门宦海之后,他做出了“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东京留别诸公》)——这明智又极其痛苦的决定,回到了属于他一个人的自在天地。临行之际,他还特意写了首《留别王侍御维》,感念这段日子王维对他的照拂之情,也表达了心中对朝廷的失望:“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重返鹿门回归田园生活,并不能很快抚平孟浩然在长安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在稍事休整后,他再次开启了漫游生涯,先北上洛阳,然后南下吴越。正是这一路的漫游,让诗人的心态得到了调整。孟浩然在这期间写下了一批具备某种崭新气象的作品,无论是结构还是气势,相对于从前都有了更开阔雄浑的色彩和格局,譬如这首写钱塘潮的《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百里雷声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语言如旁白一般,在杂声中营造出清音,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令人浮想联翩。中国古典诗歌尤其讲究风骨和气象,风骨主要是指建安风骨,气象当属盛唐气象,如果说孟浩然早期的诗风骨具足,气象稍欠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挫折和磨砺之后,他的这批作品在气象方面也有了长足精进,完全融入到了盛唐诗歌的整体氛围中。孟浩然擅长描绘景物在时间刻度里的变幻效果,通过光线的变化与位移,找到事物之间的幽微联系。这是一种需要耐心的写作,与当世流行的泼墨抒怀的风格有明显不同。最能体现孟浩然这一时期变化的是这首《早寒江上有怀》:“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没有任何用典,也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情景交融,朴素,真挚,诗意自现,读罢回味无穷。作为陶渊明诗歌在唐代的追随者,有不少论者注意到,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始终无法摆脱主观性太强的尴尬处境,即,他始终在隐逸状态中感到某种不适,或者说是憋屈,尽管隐逸的姿态是明显的,尽管有些诗句流布甚广,也具有很强的带入感,但给人的感觉是,这位诗人似乎缺乏一种进退自如的能力,没有完全融入到业已置身其中的生活现场里,因此也给人进退两难之感,如这样的诗句;“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夏日南亭怀辛大》)前一联明快自如,但后联则回到了惯有的愁闷状态,自怨自艾的情绪弥漫在字里行间,失志的迷惘感如影相随,这使得他总给人感觉是靠姿态写作的诗人,既无法做到像陶渊明那样彻底的归隐,“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在山水人间找到真正惬意的生活方式,又无法像王维那样遗世独处,沉醉于田园山水之间,成为一个物我两忘的人,而这种求而不得、得而不够的情绪,几乎如梦如魇伴随了孟浩然的一生。
公元736年,因受李林甫的谗害而被罢相的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刺史。张九龄一向欣赏孟浩然的才华,于是趁机就近召他入幕。这是孟浩然一生中惟一的一段仕途生涯,但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以思乡心切为由辞幕归家了。回过来想想,他当初投赠给张九龄的那首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清,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将这首诗中所流露出来的心志与他这次短暂的仕途相比照,我们很容易发现,孟浩然的济世报国之念其实带有很强的虚妄成分,也就是说,他当初参加科考积极干求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光耀门楣,至于入仕之后如何济世他也许完全不曾有过考虑,更无经略可呈。这有点像他终日置身田园,却不事农耕,只是一味观望一样。孟浩然诗歌的整体视角大多处于这种观望状态,他的很多诗都是站在“远望”或“近眺”的角度,从诗意的缘起到起转承合,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譬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远近虚实相间,干脆利落,孟浩然特别善于从侧面烘托渲染诗意,以简传神,微妙的情绪,细节化的处理效果,所谓不着一字风流尽得,都是世所少见的。相传襄州刺史韩朝宗特别爱才,有一次约孟浩然一同入京,打算举荐他。那天正好有一个老友前来探访孟浩然,席间,有人提醒他别忘了与韩公之约,孟浩然说:“业已饮矣,身性乐耳,遑恤其他。”于是,继续和朋友喝酒,根本不理会此事。韩朝宗见此情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这件事说明,孟浩然本质上是一位性情中人,即便真有机会让他步入仕途,也很难在复杂的人事官场上立足。那么,他耿耿于怀的“鸿鹄”之志也只能视为某种人生态度了,当不得真。孟浩然身上的真情与放诞在当时的士人中确有相当大的蛊惑力,这个外省诗人不断通过强化个性和风格,超出了京城诗人原有的审美规范和经验,他的“归家”主题,他的隐逸飘忽的姿态,都突破了京都诗人自我预设的精神桎梏,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声。然而,孟浩然身上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他的诗整体局限性太强,姿态性也过于明显,显而易见的是,他似乎对成为一位大诗人缺乏足够的信心,尽管他在面对一首具体的诗作时耐心十足,但诗歌水准也给人起伏不定之感。苏轼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孟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意思是,孟诗多少有些眼高手低,取材也流于单调狭窄了。
公元740年,王昌龄前往襄阳游玩,此时孟浩然背部得了痈疽毒疮,本来都快要好了的,但见到老朋友不免欢喜,饮酒欢宴几日,吃了河鲜,尤其是他最爱食的汉水查头鳊,“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疾疹再次发作,在他家的涧南园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同年,王维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主持南选,路过襄阳,写下了《哭孟浩然》一诗:“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作为一位天真疏放、清俊高澹的隐士诗人,孟浩然这一次终于彻底融入到了故乡的田园山水之中。
时至今日,仍有一代又一代蒙童在林间、在溪畔,对着春光摇头晃脑,诵读《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美好的声音轻拂过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光滋养着美好的人儿。诗人若泉下有知,定能感受到他创造过的精神世界依然魅力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