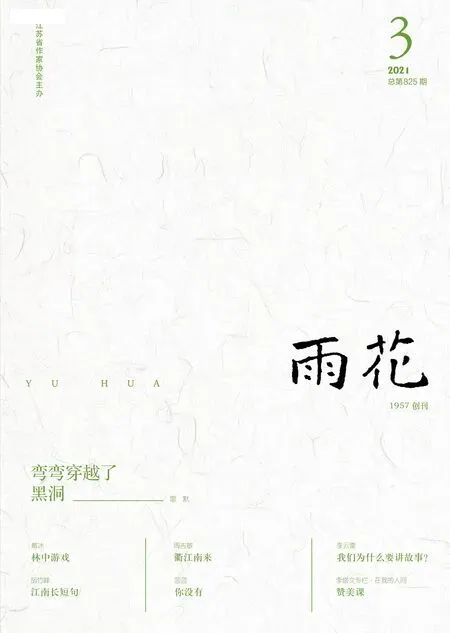河东记
小三花
在众人离开之际,阳光扫描地板;
一只小三花从窗台下探出身躯来。
人的脚越来越少,最后一双似乎
有所留恋又最终离开,门关上了。
面包之屑、一块舌状花瓣,
迷你小刀,牙齿亮着光点。
黑橘白在安谧的光中走动。
空气中难道还有偏头痛的灵魂?
周未,“鱼类有如女性形式”——
某一个昏头昏脑的男人这么说。
然而上天给了他谄媚者样貌。
陡然间的中断使时间空下来。
人间的物质变少了,陨石与
石榴皆可用来食用?桌布上——
众人,在食物上留下了刻度;
美的星球物质如烫伤的言语。
黄昏
当人间万物还在天上飞;
快乐为的不是快乐,而是更胸有成竹。
我也不是,向万物有灵提请诉求,以稀释
彷徨无地的状态。
河鱼带了玫瑰色的长牙,在空中走;
纯真的孩童带来全部的养料和空间。
为什么,开始喜欢上活生生的生活?
我从粗糙中获得乐趣并且延续下去。
人们都在死去,选中不同的时间;
你,不要告诉我,是命运在选择;
我们都在选。婴儿们艰难地落地,
长成孩童、少年、青年、中年,或老年——
这些不同的物种啊,我曾在某个不好的时候倾听。
他们是不同的,又仿佛身影重叠互相指认。
我那时看到,不同的我在某一条道上窜动;
而黄昏,正等着一人在阳台上坐拥愁城。
河东记
眼前,大桥的栏杆如流动的铝线,切割;
赣江,一块水的蓝,阴冷的蓝晃荡——
水中,被围的一小片狭长秋绿;车移动,
它慢慢展开,越来越平白无奇。
二十年前我曾在此地嬉游;在井冈山大桥下,
两块黄带子般的沙滩无限延长,水,在收缩。
为了存身于记忆而消失;那一批一批的人体,
都是年轻的,不带任何体重。
被观看的东西,一直要被看到,
变化而循环;而我看过了哪些?
或许已经忘了,我自负于修整
诗歌观念;热爱生活就是浪费。
因为记忆,或者因为记忆而终结的一些东西;
这个地方还有意义吗?河的东面,有一块由
山包堆起的处所;教室、宿舍、红土、人事。
1994年夏初我到此地找工作,之后再没离开。
同路人
同路人与你说过什么?没有,我甚至
不曾见过他,他只是宽泛的所在。
花园里有迷失的宠物看着到拂晓。
夜露沉睡,它们,并不知晓谈论的话题。
我也不想,你显露的博学其实不怎么样,
徒有一副先知框架。远非智识可以达到。
我今夜去垂钓了,你知道,
晚上有晚上的鱼可钓——
一位年轻时患过肿瘤的人如此说。
我曾为这句回答恼火不已;
但现在,我从中学到更多。
入侵
植物的花序,鸟的羽翎,
以及其他可想到的;
在开始的地方,水涌动而为泉流;
人的声音,示爱者
轻手轻脚抖去身体上的罪孽;
鸟类的轻灵醒着,隐入黑暗。
幽魂们蹉跎了漫长光阴——
以自身的虚幻轮廓模糊名物界限;
梦是入侵,而不是渗透。
在同一性的结构感中,我们
认同精致、协调又可怕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