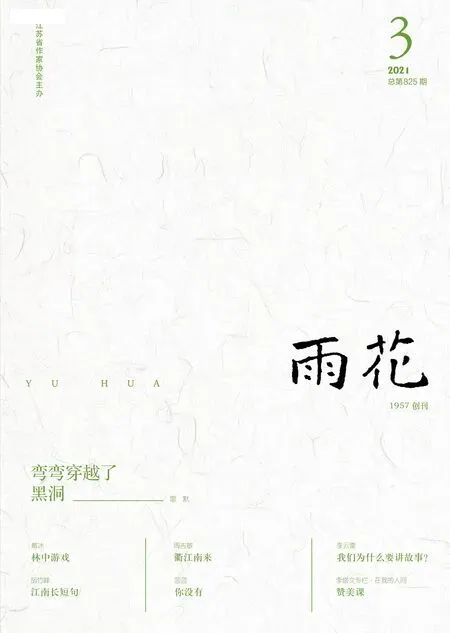郭先生的湖
八月的一天,南方F 城异常热,满街都是发烫的房子、车子,夹缝中绿化带里的树木,也被晒得软绵绵的,叶片上泛着惨兮兮的白光。
米珠坐在自己的写作室里,喝一口蜂蜜菊花水。她的眼睛酸涩,还有丝丝血红,心中更是窝着一股莫名其妙的火。她干脆放下手中的稿件,把身子靠在椅背上,闭了眼睛,脑袋里千头万绪,各种想法交织在一起。她的手从额头滑下,摁了一会儿太阳穴,又滑到锁骨。那是一对漂亮迷人的锁骨,撑得起任何一粒绝美的珠宝。米珠的手滑到这里时,嘴角牵起一丝冷笑。刚刚过去的一夜,被推醒后的大约半小时,她也是一直闭着眼的,妥协、机械、义务、被打扰、被侵犯……她想起很多这样的词语,却知道这些词语永远都不会有机会被说出口。等米珠睁开眼时,惊了一下,差点从椅子上跳起,天居然变了。玻璃窗外的世界,已是一片灰黑,接着电闪雷鸣,然后“轰”的一声,大雨下来了。
在清脆的雨声中,米珠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没有新消息。米珠看了一会儿雨,好雨啊,这么蓬勃、决绝,像是要以自己的身躯将这个世界的一切砸碎。只是,雨下成这样,还能上山吗?
午后,米珠的手机“嗡嗡嗡”地振动了一下,是一条新消息,李砚说,我一会儿过来接你,带你去山上淋雨。米珠笑了一下,倏地从午休的折叠床上爬起,整理好衣服,拿着化妆包到洗手间的镜子前,细心地化了淡妆。
真是一段美好的旅程。雨下得那么大,车子在盘山公路上绕来绕去,像在跳旋转舞,两旁是高大英俊的树木,其中有很多羊蹄甲,它们在三四月时绚烂过,现在花谢了,依然美。米珠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全都热烈地在雨中欢歌,米珠真想与它们一一拥抱。
经过一个小瀑布时,米珠说:“谢谢你,砚,我还以为你要说,下雨了,改天吧。”
李砚扭头看了她一眼,戴着眼镜依然能让人感觉到他眼里有亮光。他继续开车,说道:“那你岂不是会很失望?下雨天上山也不错吧?”他一边拐了一个弯,一边接着说,“这是雷阵雨,一会儿该出太阳了。”米珠心里有点吃惊,她从未见过一个人这样开车,经常只用几根手指搭着方向盘。李砚清清瘦瘦的,说话轻柔,身上却有一种笃定的、让人镇定的气度。单单这气度,就让米珠感觉极好,她感受过太多的惊恐。
他们到达山岭后,在游步道走了一会儿,雨真的停了,一下就收住,太阳也出来了。李砚突然跑到前面,回过头来,给米珠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米珠笑得很开心,她的身后有两束光,正好在她的肩边,好像一双翅膀。
贪玩一下午,等他们发现在森林里迷了路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李砚说:“别着急,一定是刚才那条岔路走错了,我们应该走另外一条。”太阳已经彻底不见,森林里已有几分湿冷,米珠又饿又累,可跟着李砚,她一点都不害怕。周围,高大的杉树、桦树一棵棵耸立着,米珠昂着头,用手向树上指着,笑眯眯地说:“砚,快看,森林里的月亮特别美。”
李砚刚要抬头去看月亮,忽然“呀”地叫了一声,拉起米珠的手就跑。米珠一边喘着气,一边小声地问怎么啦。跑了好几十米,李砚才放开她:“不好意思,刚才有蛇。一条青色的蛇,很细,很长,我好怕它跃起来咬你。”两个人相望了一会儿,米珠先笑出来,把手很自然地抽开,两人的笑声融进月光里。
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李砚似乎有很多话要跟她说,是月光一样的声音。他说:“我小时候就特别怕蛇。那时候,我才九岁,我爸爸一个人搬到山上去住,他自己在山上盖了一座小木屋。我都要瞒着我妈,偷偷带点吃的给他。有一天晚上,我走到半道,停下来看月光,忽然感到我的腿上凉飕飕的,很快,我的脖子就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低头一看,老天爷,是蛇。过了一会儿,蛇居然溜走了,好像只是没事逛一下而已。我过了好久好久都不敢动,右手就一直僵硬地举着,手里还有一支半明不明的手电筒,左手是一小塑料袋的米。我蹲在路边哭了一会儿,就慢慢下山了。”
米珠过了很久才接话:“我不怕蛇,我家在海边,有一年夏天,下暴雨,家里来了一条大蟒蛇,我妈不让任何人赶它,还切了一些肉给它吃,它后来就悄悄走了。我爸妈倒是少见地恩爱,我爸爸一辈子都宠着我妈,可是我爸爸很早就过世了。我妈现在老了,脾气很不好,耳朵也不好,每天打电话来,听不懂我说的话,只说她自己的,不是让我买药,就是要我寄钱,还吵着要买各种新式电器。”李砚笑了一下:“那你有空就多回去看看她。老人,多半都是寂寞的。”然后,他用修长的手指指向不远处:“米珠,你看那是什么?”
一片湖。好美的一片湖。
米珠小跑了起来,径直跑向了湖边。李砚紧紧跟着,他怕米珠有危险。等到两人站在湖边时,谁也没有说话。他们都被这一刻的宁静之美镇住了,在山岭上,月光之下,居然还有这样一片湖。他们一直盯着湖水看,生怕一眨眼,湖就消失了。
米珠先开的口:“太美了,砚,我们在这一直等着,一定会有位仙女下凡来洗澡。”李砚一听乐了:“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吗?我会帮你看着衣服的。”米珠脸上的神情却忽然变得凝重,她叹了口气:“你见过快四十岁的仙女吗?”李砚依然笑着,盯着米珠发呆:“米珠,你很特别,你到五六十岁都还会很迷人。”这下,米珠也忍不住乐了。
他们对着湖,拍了好几张照片,就怕下次来,找不到这个位置,更担心湖其实不存在,不过是两人又饿又累后的一场幻觉。当他们在离湖不远处看到一栋房子时,更加确信这一切都是幻觉了,因为实在是太过理想。
顺着灯光走近,这还是一栋新房子,一共两层楼,还有一个宽阔的院子,青石白墙、干干净净的,院子里还种着许多花卉,紫薇、茶花、栀子花、兰花等,二楼外墙则是落地窗,米色的窗帘让灯光透出一些暖意。确切地说,这是一栋很现代的小别墅。
神奇的是,周围再也没有别的房子了。李砚看了看四周,说:“这里其实就在游步道入口的不远处,哈,我知道怎么走到停车场了。”
米珠却在墙边站住了,低声唤道:“砚,你快过来看。”李砚走近一看,只见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有房出租,郭先生。下面还有一行电话号码。
米珠从未那么认真地布置过一个房间。当安装师傅和送货师傅的大卡车开来时,连房东郭先生都忍不住过来看了一眼。衣柜、书柜、书桌、沙发、角几、衣帽架、鞋柜、换鞋凳、地垫……只有床是郭先生的,因为郭先生的房子是新近才装修好的,床和床垫是新买的,床垫的塑料膜还是米珠亲手撕开的。这让这栋房子显得愈发理想。李砚进来看的时候,心中一下涌起满满的幸福,米珠把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变成了一个温馨美好的家,所有家具都是白色烤漆实木的,线条简洁又有设计感,搭配的布艺品一律是米灰色的,放的位置都妥妥帖帖的,特别是靠窗边的那个书桌,特别好看。李砚在书桌边坐下,这才注意到,椅子是米灰色布艺加原木色的,椅背上还随意搭着一条米白格纹的大披肩。他顺着敞开的窗户望去,居然可以看到湖。他想象着自己以后就坐在这个书桌边工作,或翻书,累了就可以抬头看看那一片湖,多么幸福。李砚又站起来,看到床品是纯粉色的,一点图案没有,就是纯纯的玫瑰粉色。床头靠着两个白色抱枕,上面缀有星星。沙发旁边是角几,角几边有株一米多高的阔叶绿植,种在白色陶瓷盆里。
米珠笑眯眯地说:“这叫琴叶榕,专门养在室内的。”
李砚满眼宠溺地望着她:“真好看。谢谢你,米珠,你把这里布置得这么好。”
米珠走到书桌边,望向窗外:“要谢谢郭先生,造了这么好的房子,还有这么好的湖。这个位置实在太好了。湖,简直就是郭先生一个人的。”说完米珠自己先笑了起来。
李砚走到米珠身边,捧着米珠的脸,为她轻轻整理好耳鬓的几丝垂发,笑道:“现在也是我们的。”
李砚说得没错,湖周围就只有郭先生的这一栋房子,现在二楼租给他们,一楼自住。房子真好啊。冬天来临,米珠有时候干脆搬了沙发到走廊,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做,书也不翻,就放上轻音乐,躺在沙发上看天空看白云,再看看那片湖。
那天,米珠正躺着沙发上,听见楼下有动静,她赶紧收回倒立在墙上的双腿。原来是房东郭先生的妻子回来了。郭先生家的人基本都不在家。郭先生原来是开饭店的,就在山岭的那个公园边,游客很多,可是不晓得什么原因这几年生意越来越差,索性关了门,用之前攒下来的钱,把湖边的老宅重新装修了一番。他倒也没有闲下来,常常一大早开着车下山,进城,好像在城里有别的生意。正因为他常常进城,所以眼光不一样,装修出来的房子,简洁好看。而且他断定,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房子,这么好的房子是不愁出租的,租金就是他的稳定收入。他的妻子则是个手脚极勤快的人,煮得一手好菜,饭店关了门,她就想办法在公园游客多的地方,盘了一个小店面,卖些简单的拌面米粥,生意不咸不淡,也算有事情忙。他们的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假期也总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不来几天。她还年轻,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城市的繁华显然要比自然风光更有吸引力。她至少还要再过十年才会懂得山岭老家的好。
郭先生的妻子也看到了二楼窗户边的米珠,热情喊道:“小妹,今天上来了呀!好久没看到你们上来了。”
米珠整理好衣裙,笑眯眯地趴到玻璃窗边:“是呀,大姐回来了呀!”
大姐脸红扑扑的,手里抱着好几个佛手瓜,说:“晚上要在这里吃饭吗?这是我们自己种的佛手瓜,我刚摘下来的,你拿一点去炒。”
米珠第一次看到佛手瓜长在藤上的样子,就是在郭先生家房子的旁边。郭先生特意用竹竿搭了好多棚架。佛手瓜的藤蔓就沿着竹竿到处爬,有叶子的地方就可以结果,果子一颗接一颗地冒出来,风一吹就长大了。就算不用来吃,光看着它们如此蓬勃的生机,也够喜气的。
山里的天黑得早。米珠听到汽车的声音,跑到院子外,原来是郭先生回来了。郭先生停好车下来,许久不见,他的头发竟白了不少,看来生意不好做,但身体还是笔挺的,他看见米珠挺高兴:“你们今天上来了呀?”大概山居的夜晚多寂寥,能见到别人的面孔也很新鲜,何况米珠很注意分寸,从不穿睡衣下楼。那天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羊绒宽毛衣,一条黑色的羊毛阔腿裤,留着蓬松的短发,瘦小的脸庞上,有着精致的五官,看着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动人。郭先生真猜不到这位女房客的真实年龄,签租房合同的时候,只有她男人的信息。米珠点了点头,还是站在院子门口,向着长长的林荫路张望。见郭先生疑惑地看着她,这才说道:“我在等……我先生。”郭先生没有留意到中间的那个停顿,他看了看四周,说:“天黑了,你还是进去等吧。”米珠裹了裹衣服,摇了摇头,郭先生便自己进屋了。
李砚终于回来了。米珠看到那辆熟悉的黑色车子徐徐开来,脸上漾出笑意。李砚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捧着好大一束鲜花,粉玫瑰搭配桔梗,包装纸是香槟色底钩花,束带是玫瑰粉色的,都是米珠喜欢的。他将花举到米珠面前:“米珠,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最后一节课拖了点时间,又碰上高峰期。”
米珠什么也没说,一把抓起李砚的手,笑道:“你回来就好。”
晚饭是真正的青菜小粥。米珠熬的米粥,米珠炒的佛手瓜。这房子四周没有其他人,所以千好万好,就是没有好吃的。米珠又不擅长做饭,或者说,她懒得张罗三餐。她的饮食如同她的穿衣风格一样,都是极简的。李砚不在乎。他和米珠有默契,上山来难得清静,就尽量减少人间的事,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的时间都觉得不够。他看着灯光下米珠的脸,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可以融化一切的笑容呢?他真想捧出所有,换得这样的笑容朝夕相伴。
夜里,李砚站在阳台上,看向那片湖。郭先生夫妇还是保持着山居人的习惯,早已歇下。此刻,万物安静,似乎连风都停了。只有一弯细瘦的月亮,静静地看着这人间。
米珠洗漱好,轻轻走过来,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她的手臂那么细长,像个孩子。
李砚握住她的手,问:“冷吗?”
米珠摇了摇头,想起李砚看不见,就低声说了一句:“不冷。”只是两人十指相扣得更紧。
李砚转过身来,将米珠轻轻搂在怀里,见几丝碎发飘落在耳鬓边,就伸手帮她别到耳后,却听到米珠“哎呀”的呻吟声。
“怎么回事?”李砚紧张地问。
“没什么。”米珠拂开他的手。
“他对你动手?”李砚的声音透着悲戚,他没想到,刚才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这么快就被打散。
“也不算是。他喝多了,推我的时候用力了些,我自己撞到桌角的。”
李砚将米珠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生怕一不小心,米珠就会从他的怀里消失。他想起自己十来岁时,被寄养在外婆家,有一次,几个本村的孩子围攻他,第二天,他在自己身上披了一块布,把图钉反插在布上,书包里放着两把菜刀,埋伏在路口,等着他们。那时,他的样子实在是太过凶狠,才得以在外婆家继续把小学念完。现在,他感到无能为力,他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拿出亡命之徒的架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这是生活,充斥着现代文明的生活,拳头是最低级和无力的武器,更讽刺的是,岁月已经把他规训成一个看上去风度翩翩的教古典文学的副教授。
冬去春来,转眼又入夏,到了第二年的八月。
他们上山的时候,能常常见到郭先生了。他的那辆车已是好久没挪动,似乎连城里的生意也完全放弃了,常常是窝在家里打牌,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牌搭子。大姐的脸依旧红扑扑的,倒是不肯闲着,就算在家,也要拿着扫把在院子里扫来扫去,可惜了那些落在地上的紫薇,也被她全部清理了。她依然在公园那边卖拌面米粥,只是据说没有几个人喝她的粥,一天卖不了几块钱。米珠有次跟她说,喜欢喝粥的人不会有闲情来山上游玩,要做就要做有钱人的生意。大姐叹口气说,都不好做了,我们家饭店本来开得好好的。米珠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赶在她的扫把到来前,捡起地上的紫薇。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令人不舒服的是,郭先生将房子出租给了更多的人,出入这栋房子的人一下子变杂了。二楼原本只有米珠他们住着,旁边还空着三间房,郭先生居然有本事,连同楼下的自住房子也租了出去,自己和大姐两个人挤到原本堆放杂物的一个小房间。如此,那些牌搭子就不难解释了,多半是房客。
那一天,他们上山的时候,还未走进房子,就听到喧闹声。宽敞的院子里摆了两张桌子,一张是房东郭先生带着三个男的在打牌,一张是大圆桌,上面蒙着红色的塑料膜,放着一大盆的汤匙和筷子。郭先生看到米珠手里的一大捧花,夸张地笑了几句。他们简单地打了招呼,就上楼来,看到房间门口的走廊和阳台居然摆了好几把躺椅,直把房间给包围起来。李砚注意到米珠微微皱了下眉头。
进到房间里,米珠将花小心地放在白色烤漆的角几上,整个房间立刻有了甜蜜的气息。李砚一边坐在鞋凳上换拖鞋,一边说:“他们是上山来避暑的,大概就住这一两个月。九月应该就会清静了。”
米珠点了点头,李砚总是什么都知道。她沉默而温柔地看着他。
李砚注意到米珠变得越来越寡言,两腮瘦削,一张脸显得更小了,两只大眼睛像深邃清亮的泉底,仔细一瞧,却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李砚也说不清那里面是什么,可能有惊惶,有忍耐,还有迷茫。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捧着她的脸,轻轻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将她的脸靠在自己的心口。
“砚,你知道吗?我们第一次上山是去年的8月12日,那一天是七夕节。”米珠忽然低声说。
李砚大为惊奇,居然还有这么巧的事。那一天,是他们第一次牵手。那算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吧。如果说他这么多年的人生曾经发生过什么奇迹的话,那就是米珠的爱。他居然还重新有了写诗的冲动。他在赠给米珠的一首诗中写道:“新雨之后观微茫/只有你和我的人间/如云雾空山,流动着无言的沉湎”。
时间过得真快,这就过去一年了啊。第一次和米珠上山,迷路、发现湖,一切种种,犹如小时候山上晨光中叶片上的露珠,晶莹水灵,令人欢欣,胜却人间一切的美。自从有了米珠的陪伴,他只恨一生太短。
“时间过得真快。”米珠轻叹一声,又接着说,“我马上就四十岁了。”
李砚笑道:“你还是那么美,一直都年轻啦。”
米珠也笑:“最近我照镜子,发现原来的腰窝已经消失了。再过两年,恐怕连脊柱沟也没了。”
李砚认真地说:“那岂不是更好。就没有那么多人盯着你了。”
米珠也认真地说:“谢谢你,砚,带我上山,每次上山我就可以把山下的烟火琐事都忘了。”
午后,下起雨,难得不是雷阵雨,而是那种细细绵绵的雨。米珠俯在李砚耳边,轻声说:“砚,下雨了,我们去湖边走走吧。”
李砚还在睡。他睡觉的时候要抱着米珠,米珠起来后,他不知什么时候又搂住了米珠买的那个有星星图案的靠枕,弓着身子,脸上干净,长长的睫毛卧在眼睑,像个小小的孩子,未经伤痛,不曾与生活较量过。
米珠在他耳边哈气,李砚“扑哧”一声笑出来,一把将米珠搂住:“我的好米珠,让我再睡会儿。我昨天夜里两点才睡。”
米珠说:“不要告诉我,你去给哪个美女学生补课了。”
李砚哈哈大笑,笑完才说:“我去处理了一点事。卖了套房子。”
米珠一下惊住了:“什么房子?买房子还是卖房子?”
李砚轻轻地说:“卖呀。”
米珠的心一下灰冷灰冷,她知道李砚只有一套房子,早年买的,四房一厅,两个阳台,还有入户花园,小区里有草坪、喷泉、假山、水池。她当然没有去过李砚的房子,但是从他在社交软件晒书、晒花的那些照片中,都可以看出来。而且,她还看出来,李砚非常喜欢这套房子。毕竟人到这个年纪,能有一个优雅的安居之处,才不会惶恐。
但是,现在,李砚告诉她,他把房子卖了,为了还债。没有任何征兆,李砚之前一点都没有透露这样的想法。这实在是太突然了。米珠感觉内心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火在往上蹿。米珠了解李砚,他对发财没有那么大兴趣,根本不会去做投机的事,所谓的炒纸黄金亏损八十万的,只能是另有其人。李砚只不过在陪着那个人一起跳悬崖。
米珠尽量保持平静,问:“那你们以后住哪里呢?”
李砚也坐起身来,手里依然抱着那个星星抱枕:“租房子吧。”
米珠的心一下就疼起来。租房子,那完全是另一种阶层的生活,每月数千元房租,油腻腻的灶台,不知什么人用过的马桶,不知多少人躺过的床铺、拉过的窗帘,随时都可能进来检查房子和涨房租的房东……按照现在的房价,再扣掉八十万,买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李砚一个大学老师,何时才能再积攒一大笔钱,再买一套房?租房倒并不是说就过不了了,那么多人还租房子住呢,问题是,米珠布置过湖边的这个房间。她知道,她一生也就只能拿出这一次的热情,往后是再也拿不出来这样浓烈的爱了。她现在最担心的是,李砚在那个人手里过得委屈。一生是如此漫长,真不知将来要如何收场。以前米珠看到李砚晒自己书房的照片,还暗暗嫉妒,嫉妒他所在的那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没有她,现在她为着自己曾经有过的嫉妒之心,悔恨得快要哭出来。她特别不愿意看到李砚的生活质量就这样一下子掉下去。
米珠到底有些年纪了,她没有哭出来,只冷冷一问:“你可真宠溺她。房款打到谁的卡上?”
李砚看着米珠说:“我要上课、写论文,懒得跟银行打交道。”他看到米珠的脸色,继续说道,“米珠,我一向觉得,我们不要太在意钱的事。人最重要。”
事已至此,米珠觉得多说就没意思了,她走到衣帽架边,拿好自己的小挎包,又到门后的架子上拿了一把白色透明的雨伞,朝李砚勉强笑了一下:“那你再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一个人去湖边走走。”
沿着林荫路,米珠慢慢走到了湖边。她的白色耐克鞋鞋面被雨水淋湿了,但鞋底是气垫的,一点都不湿。米珠长年穿着这样的鞋,拖鞋只在室内穿,出门是不穿凉鞋的,衣服就更讲究,只穿R 家的,冬天是宽松款的羊毛、羊绒的大衣和毛衣,夏天则是真丝、三醋酸的浅色衬衫和长裤,写作室的椅背上还要搭一条玫瑰粉的桑蚕丝披肩,以免吹空调时间长了脖颈受凉。她还有专门的洗脸师和发型师,全身脱毛、种睫毛、雾眉、修指甲、点痣,这些都是要做的,香水是范思哲的,每晚挖一大勺眼霜敷在眼周,用指腹轻柔按摩,左右各三十圈,好了以后再贴一张纯桦树汁的面膜,喝一杯温热的鲜奶,在晚上十点前入睡。李砚说她一直都那么美,哪里晓得她这些年来丝丝入扣的讲究和努力。她把自己赚的钱全都贴在自己的身体上,为的是不想在自己人生没有成功之前,就让一张脸先被岁月打败。
米珠站在湖边,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站在湖边,也是第一次在山上还感觉到孤独。刚才原本想好到湖边大哭一场的,谁知到了湖边,一点哭的欲望都没有了。米珠不禁自嘲地苦笑了一下,看来,有年纪的人,酝酿一场痛哭,比遭遇一场爱情还要艰难。她撑着伞,静静地站着,脑袋里又出现了那种“千头万绪,却又一片空白”的感觉。她用空出来的左手抚摸着自己的耳环,翡翠镶钻的耳环,只要这样抚摸着就能感觉到它的美,这还是当年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她送给自己的礼物,正阳接近帝王绿的翡翠,简直要和这湖水一样美了。平常她也舍不得戴,只有在特别的日子才戴。摸完耳环,她又摸到自己的锁骨,她早就想好,四十岁的生日时,要送自己一条翡翠的锁骨链。当下,她的锁骨那里什么饰品也没有,只有几个牙印,米珠清洗过好几遍,但仍旧隐约能闻到酒气。当然,李砚并没有发觉,刚才午休时米珠特意将窗帘拉紧了。李砚那么理解米珠的灵魂,却还是有一些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角落,那里充满暴力和谜团。
米珠还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也对李砚说不出口。原本今天,米珠想和李砚说的是,今后我们再也不要上山了。我不想再这样忍耐下去,我想要勇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我想要,每天晚上都和爱的人有一个晚安吻。
不远处,李砚也撑着伞,静静地在雨中站着,他的手上还搭着一条披肩。忽然,他口袋里的手机振动起来,是房东郭先生的电话:“我还以为你们下山了呢。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说明年的房租我们可能得加点,你也知道,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不好意思啊。”李砚犹豫了一下,稍微问了几句,就没有再和房东多说什么。
挂完电话,他看向湖边,米珠扔掉了雨伞,慢慢地向上举起左手,又慢慢向上举起右手,好个米珠,姿势这么轻盈而曼妙。
李砚的喉咙像是被人用利剑割过,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愣了一秒后,也扔掉了伞和手机,以生平最快的速度穿过一场细雨,向湖边跑去,向郭先生的湖边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