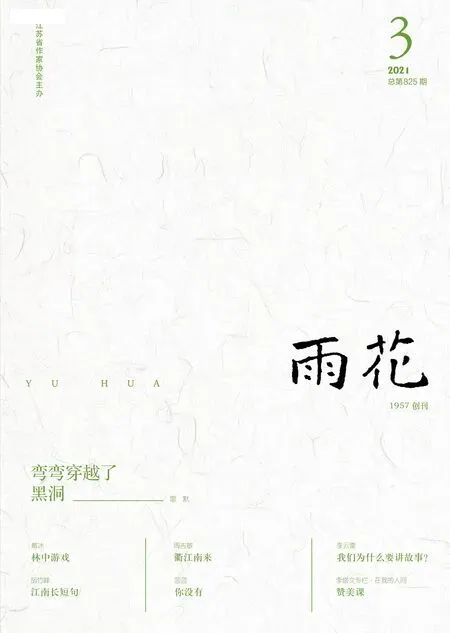花红莺飞五月天
1
程晓莲是被哥嫂房间里发出的动静惊大的。
晓莲记得那是草长莺飞的五月,夜晚天还有些凉。晓莲喜欢看电视,白天黑夜都窝在电视机前。大哥特意给她买了大彩电放在她房间里,她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晓莲喜欢看动画片,那是陪春望养成的习惯。偶尔也看古装剧,那里面一定有男人和女人谈恋爱的场景,波波折折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晓莲喜欢把声音开得很大,声音大就有一种热闹感。大哥大嫂和邻居们都迁就她,就连要读书写作业的春望,也适应了姑姑房间里奔涌而出的喧嚣。
这天晚上晓莲关了电视机,带着肥皂剧主人公花好月圆的美好心境躺下了,裹紧了毛毯。月色浸透印花的窗帘,虫子的鸣唱和作物生长的气息也搅和在月色中,晓莲觉得这样的夜晚有点异样,异样得使人想生出点什么事来。
什么声音?是嫂子在哭吗?晓莲勾起脖子听,那声音确实来自哥嫂的房间,声音怪怪的,含混却又清晰,似风在树梢盘旋,又像是在电视里听过的琴弦上的颤音,还伴随着板床“吱吱呀呀”的呻吟。后来,那声音陡然爆破,像气流冲出了橡皮的瓶塞,呼哧呼哧,好像要出人命的样子。晓莲赶紧掀掉毯子坐起来,找她的鞋子,以她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把自己搬到了哥嫂的房门口。咚咚咚,咚咚咚,她一边使劲擂门,一边紧张地叫着“嫂子”。过了好一会儿,嫂子的房门才开了一条缝,嫂子用手掩了胸襟,满脸潮红地站在她面前。
晓莲,有么事?嫂子问。
你们在打架吗?晓莲紧张地问,还把脑袋挤进门缝朝里张望,一床大花的毛毯把大哥整个盖着,现出一个蜷着的身形,无声无息,好像已经睡着了。
打架?嫂子的脸突然更红了,忙说“没有的事,是你哥打呼哩,快去睡吧”,便去推晓莲回她自己的房间。晓莲再次躺下时,分明听到隔壁房间里有“叽叽咕咕”的私语和压抑的笑声。她突然醒悟,大哥和嫂子……晓莲的脸也火烧火燎起来,火从脸上烧起,慢慢地烧到心里去了。这个晚上,晓莲在床上折腾来折腾去,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晓莲都二十五岁了,该找个婆家了。第二天早上,嫂子看见晓莲哈欠连天,就跟哥这么说。
后来,每到晚上,她都会有意无意地侧耳捕捉哥嫂房间里的动静,任何可疑的声音,她都把它们想象成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的快乐声。
2
给晓莲找个好婆家不是件容易的事。程晓莲原本就是和大家不一样的人。
她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三岁?或者五岁?
那时她总是摔跤。踮脚够桌上的馒头,突然就歪倒了;弯腰捡地上好看的树叶,也会栽下;平坦的路面,趔趄一下,也会摔倒。母亲常常撵着她喊,慢点,慢点。母亲也常常把她搂在怀里,无端地抹眼泪。那时她以为她很快就会死去。她不知道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很恐怖,怕某一天会突然被鬼抓走,被鬼抓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像隔壁小五的奶奶。晓莲不明白的是,摔跤碍鬼什么事呢?值得母亲这样担惊受怕?再大点她知道了她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小五和兰芬她们可以风一样卷过留有禾茬的稻田,可以“扑通”跳进池塘里捞菱角菜,可以让皮筋在两只脚上倒腾来倒腾去,欢快地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而她呢,只能站在开满蓝色小花的土埂上看着她们,或者只能靠在粗糙的枫杨树上为她们绷皮筋。小五和兰芬她们一不高兴,还会骂她“瘸子”。
是的,她是瘸子,她患过小儿麻痹症。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子,两条大腿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捆绑了,走路时只能勉强岔开小腿,而且臀部严重后伸,使她原有的身高无形中矮了一大截。和她一样大的小五和兰芬她们背着书包去上学,晓莲也想和她们一道去,母亲心疼她走路吃苦,便说,念书有什么用?白瞎了钱。母亲不识字,以为做女人不识字也没什么。程晓莲不上学,也就不知道上学的好。
程晓莲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十一岁时母亲胃癌去世,大哥把晓莲领到身边。大哥说,还是去上学吧。
十一岁的女娃子去读一年级?这回是晓莲不干了,小五和兰芬已经读四年级了。况且晓莲那时已知道害羞,她不愿意出门展示她的残疾。大哥起初带她到处看病,希望她那条肌肉萎缩的小腿能正常发育。钱花掉不少,可惜都没能让晓莲的腿正常起来。大哥带晓莲走在路上时,总有人误以为他们是父女,大哥笑笑,也不解释。
那时嫂子已经生了春望,晓莲就窝在家里逗春望玩,陪他看动画片。嫂子也教晓莲做家务,说女孩子不能什么都不会。但大哥一旦发现嫂子教晓莲做家务,就黑了脸,说晓莲身体不好,是领回家照顾的,不是领回家当帮佣的。万一她摔进了水里或者被热水烫了、被火燎了,怎么向死去的父母交代?怎么有脸在乡邻们面前抬头?嫂子自此便不敢叫她干活,她拿把扫帚扫地,嫂子也会赶紧夺下来。后来春望背着书包上学了,程晓莲还窝在家里。
3
嫂子说该给晓莲找婆家了,事情就放进心里了。
不久后的一天,大哥从外面干活回来,在院里井台上洗了手,擦完手就坐在八仙桌边的木椅上,说晓莲你过来,哥想跟你说件事。晓莲那时正在帮春望削铅笔,她削出的铅笔跟卷刀卷过的一样,规整、好看,还比卷刀削出的好使,铅笔芯粗细匀称,不那么细,不会动不动就折断。春望用的铅笔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晓莲帮他削。晓莲以为哥又要跟她说,春望的事要他自己做。晓莲应道,把这支笔削完就不帮他了。但哥还在叫,说你过来坐下,笔先放下。
晓莲只好放下削了一半的铅笔,吹掉手上的铅笔灰,一拐一拐地走到桌边,半个屁股贴着椅子坐下。大哥说,晓莲你也不小了,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哥不能留你一辈子,就是母亲活着也不能留你一辈子。哥想给你说个人家,给你找个可靠的男人。哥想听听你的意见。晓莲的脸早红了,勾了头用一只好脚不停地踢着地面。她心里有些害臊,她想要有个婆家,小五和兰芬她们早结婚了,丢下刚会走路的孩子,跟她们的男人一道南下闯世界去了。她又有些难过,她知道自己拖累大哥大嫂了,他们是不是不想留她了?她给不了意见,她习惯于听从大哥。
过了两天,住在桥头的柳婶就领过来一个男人,那男人皮包着骨头,大龅牙,眼睛凸得好像随时都会蹦出来。他凸出的大眼球不断往程晓莲这边瞟。尽管媒婆柳婶早把晓莲的身体状况告诉男方了,但嫂子依然叮嘱晓莲,相亲时坐着别动,千万别动哦。晓莲面容白皙,五官清秀,坐着不动的话也是一尊美人。晓莲只看了对方一眼就不想再看了。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坐下就像一根木桩子,谁稀罕?晓莲心里嘀咕。
柳婶不停地说话,总也不见要走的意思,晓莲很想用大哥的臭袜子把柳婶的嘴堵上。柳婶说话时,晓莲用一只好脚不停地踢着地面,屁股下的竹椅也连带着“吱呀吱呀”地叫唤。嫂子看了她几眼,阻止的话都在目光里,晓莲装着没看见。在柳婶说到“晓莲要是过了门,钱由她管”时,晓莲离开了椅子,在嫂子惊恐诧异的目光中,撅着屁股迈出一只左脚,然后右脚划了一道圆弧,脚背蹭着地,身子猛然向右一歪,又迈了一步。她就这样一摇一晃地在大家静默的目光中招摇着走了一趟,回自己房里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柳婶来过几次,站在河边说话,晓莲疑心嫂子和柳婶背着她在鼓捣什么猫腻,看样子嫂子是要甩掉她这个包袱了。晓莲躲在房间里抹眼泪,心里对嫂子的怨恨像门前的丝瓜藤一样爬上了架子。有时看见路上有迎亲的队伍走过,她总担心那队人马会突然来到大哥门前。晓莲知道,倘若大哥要她出嫁,她也只有顺从。晓莲心沉沉的,日子好像压了一块砖,怎么过都不舒服。
晓莲想讨好嫂子,不再跟嫂子顶嘴,即使嫂子织出的毛衣花样不好看,她也能说出十条好看的理由来。晚上,晓莲电视机的音量开小了,关机也早了,想让嫂子看到她在省电费。白天晓莲抢着干活,不仅帮嫂子烧饭做菜,脏衣服她也主动搓好,就连用锄头翻菜地这样的活她也要干。嫂子拦着不让她去菜地干活,家里的手边活也就由着她做了。过了半年,她才无意中从嫂子那里得知,那大龅牙男人,干活没有力气,还死能吃,脾气还坏。听人说是得了甲……什么病,大哥很干脆地回绝了那门亲事。晓莲这才缓了一口气。
但是日子依然沉闷,晓莲早上起床就开电视机,等着嫂子喊她吃饭。吃过饭洗了碗,还是坐到电视机前。看累了,起身去收拾一下屋子或者帮嫂子洗洗下一餐要准备的菜……天黑了,开灯,依然是坐到电视机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今天复制昨天,仿佛一潭凝固的死水,要生出丝丝缕缕的臭气来。晓莲房间里电视机的音量也越开越大了。
日子就这样又熬了一年多。正月里,晚饭后,天边火红的云彩还没有褪尽,柳婶领来了大贵。大贵比晓莲大了五岁,好手好脚的,竟然也还单着。他瘦高个,大长脸,眼角的笑纹像小芭蕉扇似的。他爱笑,从进门时就一直嘻嘻哈哈的。嫂子端出自己腌的生姜招待客人,他二话不说,伸手捏了一块就往嘴里塞,一边辣得直吸冷气,一边直说好吃。他的活泛让晓莲也绽开了笑脸。嫂子端出茶叶蛋时,柳婶客气不肯吃,大贵又是二话不说,伸手就抓起一个剥了。剥了一半蛋壳,几个手指捏着带壳的部分,送到晓莲面前,也不说话,只看着她笑。晓莲顿时红了脸,也羞羞怯怯地接了,却不敢张口吃,只低头小口地啃着。晓莲不敢看他的脸,目光却不知不觉要往他那边瞟,她看见两条修长的腿笔直地伸着,一双大脚至少也要穿44码的鞋子,翘起的两只脚尖不停地相互碰撞着,晓莲觉得它们是在表达相互欢喜呢,不由得又红了脸。柳婶偷瞅大贵和晓莲那神色,心里明白了八分,仍然不停地跟她大哥和嫂子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仿佛压根儿就想不起还应该抬抬腿回去。程晓莲觉得柳婶就是会说,平常话到她嘴里都带了喜剧色彩,不由得让人发笑。柳婶从天还没有黑时说起,说到月上柳梢头还不走,晓莲一泡尿憋着,始终坐着不敢动弹。
大贵来过后,晓莲就一直盼望柳婶来向她要回话。她不知道当初小五是怎样回媒人话的,问兰芬肯定是问不到的,兰芬是自由恋爱。要是有小五的电话号码就好了。依照晓莲的性格,她会直接说“我愿意”,这样说会不会让别人笑话她不够矜持?嫂子会不会以为她想嫁人想疯了?那么就委婉一点吧,说“让我再考虑考虑”?要是这样“回话”,大贵会不会以为她没有看上他?算了算了,还是直接回答“我愿意”,看大贵那样就是个爽快人,晓莲喜欢爽快。
但柳婶一直也不来,大贵那边一直没有动静。晓莲的心一天天沉下去,这段时间他外出了?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是不是相上别人了?我晓得你嫌弃我,切,以为我看得上你?那眼角的褶子能夹死蚊子,我能看上你?晓莲生气,是那种既伤心又愤懑、既委屈又自卑的生气,好看的杏仁眼布满了阴沉沉的乌云。
程晓莲!
清明过后,院子里的桃花红了,香椿树爆出像花一样的新叶,晓莲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打香椿头,突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喜滋滋地喊着她的名字,抬眼瞅瞅院门口,却并没有看见人。
程晓莲!
声音是从院墙头上发出来的,晓莲一抹脸,便看见大贵那张喜笑颜开的脸。他抬抬手,把一盆绿色植物朝程晓莲扬了扬。
你进来呀,晓莲说。晓莲突然就不生气了,眼睛里的乌云被风扫尽了,晴好到一片蔚蓝。大贵警觉地朝屋子里看看。晓莲说,他们都不在家。大贵的头突然不见了,整个人很快从院门口卷了进来,双手捧着一盆绿色植物,茶叶似的叶片间,顶着星星点点的指甲盖大的白花。这是什么?晓莲问。
茉莉花呀,他说,你闻闻,好香,送你了。晓莲便把脸凑过去,贴着它们嗅吸。其实他进院门时,她就嗅到了一股淡雅的香气。是好香,晓莲说。
是吧。大贵嘿嘿地笑,把花放到院子里的石凳上。
哪来的?
嘿嘿,大贵又笑,偷来的。
偷来的?晓莲诧异。
大贵说,马路边的大棚里摆了好多,香气能拽断人的腿。我进去了,知道你会喜欢,想买的,喊了半天没人应答,只有一条小狗在门房里面“汪汪汪”,它问:“哪个?哪个?”晓莲掩了嘴笑。大贵说,没人来收钱,我就抱起一盆走啦。程晓莲问,狗没有咬你?大贵说,那狗在屋里关着,只叫“王八蛋,王八蛋”。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跟她说话,晓莲“咯咯咯”地笑弯了腰。你放心,我下次路过那里看见花主人,会把钱补上。大贵说。大贵走时,晓莲就一直目送着他的腿,一双好看的大长腿迈着轻快又坚实的步子,走过院里的水泥地面,跨过院门,一直朝马路那边迅速移动。
随后的日子里,阳光明晃晃的,晓莲轻快地挪着她向一侧前倾的身子,从客厅到院子,从院子到园子,从园子到厨房。她一点都感觉不到自己行走不便,相反,她觉得她像一只燕子,虽然她的飞翔在别人眼里还是那么滑稽可笑。她灵活地干着能干的活,大声地和邻居说话,甚至和已经读高中的春望打闹。
没过多久,大贵又来了一次,他那辆锈迹斑斑的旧自行车就停在大哥的院门口,后座上还不伦不类地插着红色三角旗。他的头发被风卷乱了,短了一截的裤脚上沾满灰尘,他兴冲冲地走进来说,程晓莲,我带你去西冲花谷看花去。说话时,一只手突然从身后伸过来,一把连花带藤的金银花变戏法似的冒了出来,香掉人的鼻子。
晓莲说,俺不去。金银花的藤蔓已经抓在了手里。
大贵围着晓莲转了一圈,目光像鞭子一样把她抽了一遍。我知道你喜欢花。太阳这么好,风也很暖和,芍药花开了,牡丹花也开了,你为什么只躲在家里?大贵还说,我见过像你一样的女孩子,在服装店里踩电机,哒哒哒哒,一样干得很好。大桥头的超市老板娘,一双腿给车轮轧掉了,人家坐在老板椅上,算盘打得咵咵响,算起账来比小学校的算术老师还要快。我呢,我就喜欢到处跑。大贵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有点难为情地笑了。晓莲也笑,晓莲羡慕大贵有一双好腿脚。
晓莲问,你到处跑都看见什么了呢?
什么都看过啊,看过好多好多人,好多好多山,我骑着自行车去过漠河,大夏天,冰有这么厚!大贵奓开手指比了比。
不会吧?晓莲的眼睛瞪得溜圆。
怎么不会呢?骗你都不是人养的。那里夏天几乎没有黑夜。大贵越说越兴奋,眉眼活泛地跳。我去过西藏,天就在头顶上,一伸手就能摸得着。我还看过一个新疆人在半空中走钢丝,还见过一个大胡子男人,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噌”地一下,就把车从黄河这边飞到黄河那边去了……
走钢丝,晓莲在电视上看过,一根钢丝拉在山谷上,一个穿花裤衩的男人,手中拿了一根杆子,摇摇晃晃地走在钢丝上,好像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那一刻她的心悬在天上,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汽车从黄河这边飞到那边?汽车又不是飞机,晓莲不敢相信,大贵喜眉喜眼的神气又不由得她不信。要是自己有一双好腿脚的话,一定也会到处跑。干吗不到处跑呢?这世上一定有好多好多好去处,有好多好多好看的东西,干吗不到处跑跑呢?晓莲痴痴地看着大贵身后的原野。
晓莲还没有答应大贵跟他一道去西冲花谷,嫂子就从地里回来了。大贵欢天喜地地叫了声“大嫂”,嫂子连头都没有点一下,只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嫂子异常冷淡,大贵待不住,只好骑着他的破车,“哐哐当当”地跑了。晓莲翻了嫂子一眼,噘起了嘴巴。
金银花插在水杯中,茉莉花摆在阳台上。晓莲的目光一天要抚摸它们一百二十四回。有时目光越过院墙,看村头的路口,看路口外的原野,看原野尽头天空中的云朵,想象着自己坐在大贵的自行车后面,一路朝远方飞驰的样子。
从四月到五月,大贵却一直没有再来。晓莲的脚步变得凝滞了,和春望说话的声气也短促焦躁起来。
4
嫂子在客厅里看电视,晓莲挨了过去,找嫂子说话。她希望嫂子主动说柳婶那边的消息,主动说大贵,能问问她愿不愿意嫁。但是嫂子只说电视里的人物好歹,说谁的眼睛不好看,谁的鼻子有点塌。
嫂子你看,那个人像不像大贵?晓莲指着电视机里的一个路人说。嫂子瞪大眼睛看,哪里像?大贵比那人丑。晓莲便噘了嘴,瞥了嫂子一眼,丑就丑点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嫂子终于明白晓莲的心思,她抓着晓莲的手,很认真地看着晓莲,说,以后别理他,这家伙不像是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听说最近把家里的摩托车卖掉去买单反相机,说要照什么风景。嫁给这样的人,以后还怎么过日子?晓莲还想说些什么,但终究不好意思替大贵说话,只是挣脱出自己的手,电视剧却怎么也看不下去了。
这天晚上,嫂子房间里又不合时宜地发出了那种动静。晓莲一下都不能忍受了,她用手推翻了床边的一把椅子。椅子撞击地面的“呱哒”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隔壁房间暧昧讨厌的声音果然戛然而止。
好脾气的晓莲好像进入了更年期,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她拿扫帚打沙发上睡觉的小花猫,骂它整天就晓得睡觉,都不去逮老鼠,她说春望走路的声音太响,说嫂子给她买的新羊绒大衣丑死人。
嫂子本来应该能够觉察到晓莲的变化,或许她觉察到了,但无暇顾及。村庄正面临大张旗鼓地拆迁,人们毫不掩饰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上。锱铢必较的丈量过后,就是找临时居住点,然后就是搬新家,添置新的家具,一家人开始了像模像样的城居生活。
晓莲和大哥他们一起住进宽敞明亮的安置房已经五年了。大贵从此没有再出现在晓莲面前,她甚至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晓莲猜想,一定是自己搬了家,大贵才找不着她了。这些年,柳婶又带过来几个男人,离婚的,丧偶的,也有因为家里以前穷把婚姻耽搁下来的老小伙。这些人中,大哥和嫂子都有相中的,可是晓莲就是相不中,大贵已经住到她心里了。晓莲每天重复前一天的生活,帮嫂子做一点家务,把一日三餐打发掉,闲下来便托着腮帮坐在窗前发呆。夏天依然结冰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西藏的天真的一抬手就能摸到?等到天黑了就上床看电视。唯一变化的就是露台上的花草在悄悄生长,电视剧在持续更新。程晓莲的日子日渐寡淡,了无生趣。这期间她的生活中发生的唯一一件让她激动的事情,就是大贵送她的一束金银花,在露台上生出了新的根芽。
那束金银花藤起初是插在水杯中的,不起眼的小小花瓣里,溢出的香气那么好闻,它用它的香气宣告它的存在。看到那些雪白的花蕾慢慢绽开,又慢慢变黄、凋零,晓莲很有些不舍,她就把那几根藤蔓压到盆土里。不久,它的花全凋零了,叶子卷了、落了,晓莲以为它死了,仍然舍不得拔掉它。后来的某一天,却不经意地发现它又爆出了新绿,竟然活了。奇怪的是,活了几年,它却没有再开花。晓莲觉得这金银花随了她,她也是没有开花的植物。
5
月光明晃晃倾泻下来,罩在露台的几盆植物上。露台和露台上的花草是她生活中的盐。这是大字不识的晓莲说出的最有文化的一句话。
晓莲提了水壶,歪歪倒倒地蹭到露台上,看见她的绿萝和彩叶草挤挤挨挨地生长着,似乎又长出了一截。金银花枝叶郁郁葱葱的,仍然不见花苞。程晓莲的目光投向铁架最上端的茉莉花,那棵养了五年多的茉莉花,今年又打了几十朵花苞,有的花苞已经泛白,香气随时都会从那里袅绕出来。晓莲踮起脚,吃力地举起水壶,这时,干瘦的大哥过来了,他敞开宽大的夹克,拖鞋在脚下“吧嗒吧嗒”地响着。
我来。大哥伸手要接晓莲手中的水壶。晓莲避让开,重心不稳,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她说,你不懂它们,浇少了它们喝不饱,浇多了会把它们淹死。大哥说,那好,你浇,你浇完水我有话跟你说。哥在家是挑大梁的,有着大梁一样的沉稳和肃然。大哥很少跟她说话,晓莲知道一定有什么大事了。晓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哥六年前也这样跟她说过话,那时他们还住在乡村。那场谈话几天后,媒婆柳婶就带过来一个男人叫他们相看,后来又带过来大贵。
晓莲心跳乱了频率,“咚咚咚”,好像有人擂门似的。她慌乱地放下水壶,侧身扭头看着大哥,脸红红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大贵有消息来了吗?
大哥说,你先浇水。晓莲眼睛里跳着两团火,她朝大哥露出洁白的牙齿,撒娇道,有话你就说。
这事得好好跟你商量,还是先浇完水再说。大哥脚上的拖鞋“吧嗒吧嗒”响到了客厅里,停在了沙发边。程晓莲心慌意乱地浇着水。她给茉莉花浇了水,给绿萝和彩叶草浇了水,然后给茉莉花又浇了一遍水,水淋得露台上到处都是。她把水壶撂在露台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就踢踢踏踏地走进客厅了。
嫂子在看电视,大哥在看手机。晓莲半个屁股挨着嫂子坐下,嫂子立即把电视机摁成了静音,把茶几上装满提子的果盒往晓莲这边挪了挪。晓莲瞅了嫂子一眼,又很快地低下了头,羞怯怯的。
晓莲,哥想跟你商量件事。春望马上要毕业了。我希望他回到我们这里工作。大城市好是好,可房子动不动要上百万,我们买不起。
那就叫他回来吧。晓莲的腰一下子塌下去了,仿佛有洪水淘洗了她埋在沙地里的希望。
春望大了,打电话说已经在学校谈了女朋友,我们家这房子有点小了。大哥说话斟词酌句,好像在理一团乱麻,生怕它打了疙瘩。晓莲心里“咯噔”一下,惊慌像烟一样冒出来。她迅速地把屋子扫一眼,房子不小啊。当年回迁安置时,哥嫂为了把她安排在一起好照顾,特意要了最大号的房子,有一百三十多平哩,装饰得姹紫嫣红的,有一种人造的富丽感。晓莲觉得电视剧中的皇后娘娘住的宫殿也不过如此。哥嫂现在是要把她赶出去了吗?晓莲的心紧张得咚咚乱跳。
嫂子说,春望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不了两年就要结婚,他结婚总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晓莲这下总算明白了,哥嫂大概是想晓莲把自己名下的安置房拿出来给春望做婚房。晓莲心里松了一口气,说,我那房子空着也空着,给春望住吧。晓莲的户口不在大哥的户口本上,村庄拆迁时,她也得了一个户头。她和母亲原来居住的两间平房只有四十多平方米,大哥添了钱,给她名下添了一套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在同一栋大楼的另一个单元。晓莲记得她的门牌号是1314。
大哥停了会儿,仿佛有些东西堵住了喉咙口,一时出不来。停了停,大哥才说,晓莲,是这样的,你那房子只有八十几平方米,现在孩子结婚谁不买大房子?况且现在准许生二胎了,八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不够住。我想……我想把你名下那房子卖了,给春望凑几个钱买套大的。
晓莲听懂了,没有理由不答应。
哥,你做主……卖不卖的我不管。晓莲想朝大哥笑笑,但脸皮僵僵的,心里无端地空落起来。
大哥还是早出晚归地在工地上干活,嫂子也不再提这事。日子一如往常,晓莲以为大哥也就那么说说。就在晓莲快要忘记卖房的事时,家里突然来了一对夫妻,六十来岁,男人胖胖的,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女人缩着脖子,嗓子里“呼啦呼啦”的,好像扯着风箱。嫂子把他们让进屋子,那男人把呼呼喘气的女人扶到沙发上坐下。听他们说话,好像嫂子本来就和他们相熟。几句闲话过后,他们便谈起房子,原来是买房的人来了。
晓莲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她听见他们在讨价还价,甚至谈及成交后过户的细节。男人说想去看看户型,如果老婆喜欢,他们就买下来,希望价格上还能让一点。
后来她听到大门“嘎哒”一声开了,又“呱哒”一声关上,室内嘈杂的人声突然都在空气中弥散了。
6
“五一”前,春望回来了。一米八的大小伙,带回来一个小巧的姑娘。晓莲看那女孩子,个头好像还没有她高呢,小脸也像没有长开来。她白皙纤弱得像一根嫩豆芽,小手腕只有锅铲柄粗,手背和额头上凸起细细的青筋。晓莲撇撇嘴,嫂子看着那女孩也直蹙眉。但春望却宣布这女孩是他女朋友。
更让晓莲惊诧的是,嫂子准备好的客房这女孩不住,晚上竟赖在春望的房间里不出来。半夜里,晓莲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扰醒了,她侧耳细听,发现声音不是哥嫂房间里发出的,而是来自春望的房间。那声音像有人在努力吹着气球,大胆而热烈,自由而奔放。晓莲既替他们担忧,又替他们难堪,赶紧用枕巾堵住了耳朵。
这天晚上晓莲做梦了,一个男人不知道从哪里颠颠地跑出来,像舞台上跑龙套的,穿着模糊,长相也模糊,像是大贵,又不像是大贵。那男人的笑,阳光一样照亮了她。
后半夜晓莲没有睡,她把平静无味的前半生捋了一遍,她一直生活在母亲的腋下,然后是哥嫂的腋下。他们爱她,她明白,也很感激。但她却没有像别的女孩那样去读书,不能像小五那样去外面做工。她也没能嫁给大贵那样的男人,没有像兰芬那样一口气生三个孩子。甚至,夜晚她的床上,从来没有闹出过那种让她心慌意乱的动静。晓莲捋着这些时,心田像秋后的草甸,衰草连天,散发着悲哀的凉气。如果日历往回翻也能算数的话,她愿意她的日子过成另外一种样子。
春望小住了两日就带女朋友去黄山旅游了。脸上有红色胎记的男人又来了一次,还是和嫂子讨论房子的事,晓莲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想去看看自己的房子是什么样。如果连它是什么样都不晓得,就这样成了别人的,晓莲心有些不甘。
那男人走后,嫂子也出去了,没有告诉晓莲她要去哪里。晓莲猜想,嫂子大概去替春望寻大房子去了。趁嫂子不在家,程晓莲抓了1314 室的钥匙摇摇晃晃地出了门。晓莲摇出了电梯,晃到了太阳底下,金灿灿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绿化带上,红的紫的粉的黄的,她叫不上名字的花开了一大片,石榴树上红彤彤的,像燃烧的火把,黄莺躲在树枝上“啾啾啾”地唱歌。晓莲的胸腔一下子舒展开来。
没费多大劲,她就走进了电梯,来到了1314 室面前,拿出钥匙费力地打开了自己的家门。灰扑扑的毛坯房,像一个没有洗漱的女人——满脸污垢,披头散发——慵懒地呈现在眼前,阳台裸露着,地面上还有散落的小水泥块,白色的排水管静静地竖立在墙角。晓莲反身把门关上,她要好好看看她的房子。
房子比大哥家的小,但窗户却更敞亮。这里的阳台朝南,跟大哥家的比阳光更足,摆放花草正合适。金银花放到这里,一定会和茉莉花一样,绽放出洁白的花朵来。她看着室内,想象着它打扮好了的样子,怎么想却都和大哥家的一样,一样的木地板,一样的花瓷砖,一样的灶台和吊柜,晓莲不知道还能把它们想象成别的样子。当目光搭乘着想象抚摸到主卧时,和大哥大嫂睡的一样的床边,突然跳出了一张小摇篮。晓莲脸一红,却没有躲避它,仍然看着不存在的摇床继续想象……摇篮里的孩子让她的心突然柔软起来。她闭了眼,静静地体味着那种像蜂蜜一样香甜的柔软。
两天后,程家闹出了大动静,小区里的老太太和小媳妇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老姑娘程晓莲要和她哥嫂单过了。
哟,这女子原来是头白眼狼,她哥嫂待她那么好,还是闹翻了?
她早该出来了,像她原来那样活一辈子,跟没活过有什么两样?
出来单过的日子不好过哩。
没什么大不了的,车到山前自有路。
程晓莲歪歪倒倒地去超市买日用品时,这些话也钻进了她的耳朵里。她装着没听见,她在想,要是大贵愿意带她一道出去疯,她很想看看汽车飞过黄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