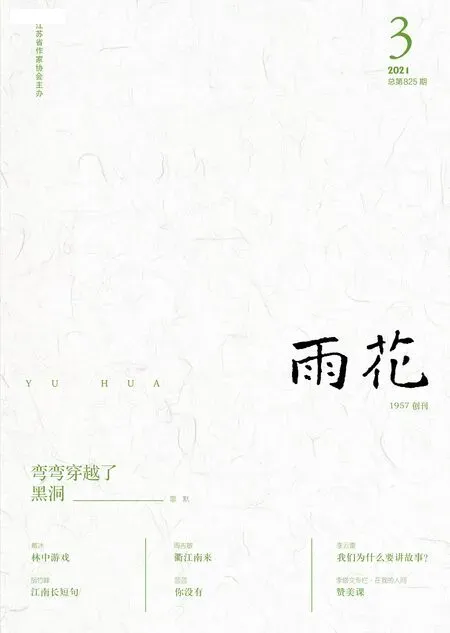赞美课
这天早晨,去学校的路上,他忍不住想要赞美整个世界:沿途的一棵棵枫树,全都在一夜之间变红,像巨大的火炬直插在田野上,又像母亲的心来到了身前,正伴随着他度过越来越寒凉的秋天;仍然是一夜之间,漫无边际的芦苇们也都开出了花,那些芦花,一簇簇被风吹动,却始终低着头,像姑妈,像刚刚死去的语文老师,像世上一切受了苦却不诉苦的人。通往学校的路在芦苇荡里继续向前延伸,因此,他还将在芦苇荡里看见几只正在学走路的白鹤,一只干涸了好几年的泉眼里重新涌出了泉水,所以,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开始回忆自己知道的、所有用来赞美的词,结果,他还是觉得,那些词配不上他在这个早晨经过和经历的一切。
那颗被赞美包围的心,甚至忘记了必然到来的危难——这一年,他十岁,被寄养在一个远离父母的村子里,他所栖身的这户人家,只是父母的远亲,反正他也没有被饿死,如此,在给他一碗饭吃之外,其他的他们也就一概不闻不问了。当然,他一直知道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所以,他完全可以当得起乖巧二字:因为无亲无故,打起架来也没有帮手,在学校里,他便隔三岔五地要挨上一顿打,挨打就挨打了吧,不过是毫不声张地钻进芦苇荡里,奔跑,哭,躺下,在湿漉漉的地上翻来覆去,最后,还是得乖乖站起来,将自己收拾好,再挂着一脸的笑回到寄养的人家里去。是的,对于挨打之后毫不声张的好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但是今天却不同于往常。今天挨的这顿打,几乎令他痛不欲生:他身上穿着一件母亲刚织完就寄来的毛衣,挨打的时候,因为急于挣脱,毛衣上的线头松开了,但他顾不上,只能拖着线头夺路而逃,这样,打他的人便不再追赶他,而是攥紧了线头,再嬉笑着看他跑远,而他,一边狂奔,一边却心疼得喘不过气来:他的确是越跑越远了,可是,他毛衣上的毛线也在被他们拉扯得越来越长,等他终于痛下决心,咬着牙将毛线扯断的时候,他的毛衣,已经缺了半截胳膊了。
所以,在虎口脱险之后的芦苇荡里,他怎能不怀抱着难以消除的怨愤呢?但又别无他法,他只好折断了一根芦苇后,再去折断另一根芦苇。然后,和以往一样,奔跑,哭,躺下,在湿漉漉的地上翻来覆去,无非是这些,让他觉得自己动了起来,陷入了虚妄的、根本不存在的还击,就好像,惟有如此,他才能将怯懦和耻辱一点点从身体里清除干净。可是,越是不停地动起来,他又越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开了一条口子,那些怯懦和耻辱,正像涌向大地的黄昏和夜幕一般涌进那条口子,更何况,还有不同于往日的心疼正在持续和加深——一看见缺了半条胳膊的毛衣,他的心脏便狂跳着像是要离开他的身体,他只好紧紧捂住它,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当然,他知道自己不会死,他知道:自己只是在绝望。
好在,她来了。那时候,天色快要黑定了,隐隐约约地,月亮已经升上了天空,终于,怨愤和怯懦,心疼和羞耻,正如一天终将过去,他将它们全都接受了下来,转而拨开芦苇,踏上回到寄养人家的路。结果,他一转身便看见了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也进了这片芦苇荡的,只怕是已经来了好久,果真如此的话,他在芦苇与芦苇之间的那些行径自然全都被她看见了。一想到这里,他便愈发羞愧难当,吓了一跳之后,他一刻也不停地掉头就跑。见他要跑,她才终于嗯嗯呀呀地叫喊起来,她越叫喊,他越不敢停,可是,她的叫喊声竟然越来越大,直到他下意识地担心自己似乎对她也犯下了一桩什么过错,这过错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这才心惊胆战地止步,一会儿去看她,一会儿又不敢看她。
实际上,他早就认得她。跟他一样,她也三天两头都要挨上一顿打:她是个哑巴,四川人,最早,她是被自己的哥哥带过来的,一开始,兄妹二人在村子中的油坊里做工,后来,油坊垮了,开不下去了,哥哥就跑了,跑掉之前,把她卖给了本地最穷的一户人家做儿媳,因此,她虽说是被卖掉的,却也谈不上是拐卖。据说,她不但是个哑巴,脑子也不太好,做活计的时候免不了笨手笨脚,如此一来,挨婆家的打便成了家常便饭。他其实目睹过一次她挨她丈夫的打,那是个下雨天,她去放牛的时候把牛给丢了,那牛又是借来的,她丈夫气疯了,漫山遍野地呼叫和奔跑,终于找回了牛,接着再找她,她却像是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厄运,不知道躲在哪里,就是不出来。但显然,躲避是没用的,最终,她丈夫从柴火堆里找到了她,拳打脚踢之后,她丈夫的怒气仍然没有消,按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很快,她的脸,她的眼睛和鼻子,全都肿胀了起来,这一切,被远处的他尽收眼底。就在他以为她丈夫快要结束殴打的时候,哪知道,她丈夫竟然拽着她的头发,来到了池塘边,又飞起一脚,将她踢倒在了池塘里。那池塘并不深,淹不死人,然而她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又睁不开,便只好站在齐腰深的淤泥里,怎么也爬不起来。直到很久以后,他还一直记得她站在淤泥里挥着两只手一点点向前挪动的样子。
不仅她婆家的人打她,村子里别的人也打她。谁叫她是个哑巴,脑子还傻呢?有一回,是在割稻子的时节,她挑着一百多斤的稻子回家,一路上,不断有妇女们从她的稻子中抽出几束来放进自己的担子里,她当然未能反抗,只敢讪笑着加快步子往前走,却很快又被妇女们追上,渐渐地,妇女们愈加明目张胆,几近于硬抢,她的稻子越来越少。终于,她忍耐不住,停在原地,嘴巴里“嗯嗯呀呀”地冲她们比划着手势,这一切,都被走在放学路上的他远远看见了。即使是只有十岁的他也能看出来:她与其说是在发怒,不如说是在哀求,因为她的脸上一直都在讨好地笑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继续远远地看见:妇女们没再硬抢她的稻子,却对她动了手,她左躲右闪,又想护住稻子,于是,每一回,当她几乎已经躲过了推搡时,为了那些稻子,她只好又跑回来,趴在稻子上,然后再一次被推搡。
现在,芦苇荡里,她竟然来到了他身边。按理说,他不应该怕她,可是,经年累月的挨打早已让他吓破了胆子,万一,他想,她比自己大那么多,万一自己跑掉了,激怒了她,她也对他动起手来可如何是好呢?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几乎没有一天不暴怒的丈夫。这样,他便在原地站住,一会儿去看她,一会儿又不敢看她。这时候,夜幕真正降临了,但月亮大得很,芦苇荡里明晃晃的。终于,她朝他走近了几步,“嗯嗯呀呀”地比划起了手势。他盯着她,却看不懂她在比划着什么,她便只好变作往日里的她,讪笑,不停地讪笑。最后,她恐怕是明白过来他怎么也不会看懂她的手势了,这才离他更近,急切地伸手,先指了指自己身上那件油腻的毛衣,再去指他的胳膊,紧接着,“嗯嗯呀呀”的声音大起来,她一边含混不清地叫喊着,另一边,手势却变得激烈了,既像是在比划着穿针引线,又像是在威胁着他什么。
也不知道她比划了多久,他总算明白过来,她是在跟他说:她会织毛衣,而且,她自己身上那件油腻的毛衣,跟他缺了半截胳膊的毛衣颜色差不多,也是凑巧,她恰好还有一点毛线,所以,她想让他将毛衣脱下来,交给她,只要一个晚上,她就可以帮他把那半截胳膊补起来。他当然不信,也下定了决心不听她的,可是,芦苇荡之外,远远的地界里,她丈夫大声喊起了她的名字,而且,叫喊声还越来越近,那声音,于他而言,不是别的,是说到就到的灭顶之灾,所以,鬼使神差一般,他竟然乖乖听话,脱下自己的毛衣,递给她,然后发了疯一般跑远了。跑着跑着,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自己可能就此与母亲寄来的毛衣作别,不禁哽咽了起来。等他彻底将她抛在身后,跑出了芦苇荡,再看月光下变得更白的芦花们,还有那些红彤彤的枫树,禁不住恶狠狠地想:早晨,那些被他硬生生回忆起来用来赞美它们的词,他要一个不剩地全都收回来。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第二天晚上,她便给他送来了补好的毛衣。白天里,他已经好多次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他,但是,他们好似两个被圈禁又放弃了逃脱的奴隶,俯首于可能的恐吓,都没敢走向彼此的所在——学校正在新盖几间教室,为了挣上几个钱,村子里腾得出手的人大多都在这里帮工,她和她的丈夫也在帮工,难怪昨天他挨打的时候,她会看见他,而且还追到了芦苇荡里。上课的时候,他不停地向外张望,她走到哪里,他的眼神便跟到哪里,他看着她搬砖和拌石灰,又看着她挑担子和知趣地躲在一边吃午饭,可是,他就是没看见自己的那件毛衣。要命的是,课间的时候,老师递给他一封信,信是母亲写来的,母亲在信里问他,毛衣合不合身。他拿着信,有那么一刹那,他想不管不顾地冲出去,径直去找她,要回自己那件缺了半截胳膊的毛衣,但终究还是没敢。
放学的时候,天又快黑了,跟昨天一样,月亮早早升上了天空,天大的委屈一直跟随着他,他无法推开它,便又在芦苇荡里狂奔不止,那一根根芦苇,抽打着他的脸,生疼生疼。可是,惟有这疼,才能让他原谅自己,到了这时,他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好在,她又来了。而且,她不仅来了,手里还拿着他的那件毛衣,只一眼,他便看得清清楚楚:那件缺了半截胳膊的毛衣,竟然真的被她补上了。他停下了步子,愣怔着,喘息着,对眼前所见难以置信。反倒是她,应该是早早埋伏在这里等了他很久了,要是再耽误,丈夫的拳脚就又要等着她去自投罗网。所以,她并没有多跟他“嗯嗯呀呀”,而是麻利地将毛衣递给他,又笑着指了指毛衣的袖子,意思是,已经补好了。他刚想对她说几句话,还没想好,她却急促地跑开,转瞬之间便从芦苇荡里消失了。
芦苇荡里,那颗被赞美包围的心又回来了——他想赞美一根根芦苇,它们全都像壮士一般挺立,护卫住了他和她的接头之地;还有高高在上的月光,不明不暗,让它们看见彼此,却藏住了她朝向他的奔跑,又藏住了她朝向丈夫的奔跑。一想到她在跑,他也跑起来,一直跑到气都喘不过来,尽管她在跑向自己的丈夫,他在跑回寄养的人家,但他觉得,惟有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他才对得起她,而他仍然要赞美:一棵棵枫树,仍然像巨大的火炬直插在田野上,还有那些芦花,一簇簇被风吹动,却始终低着头,仍然像世上一切受了苦却不诉苦的人。不仅如此,一路上,风平浪静的池塘,让他想起母亲抱着他的时候;突然飞出的磷火,让他想起过年时灶膛里的火苗;还有,就连黑黢黢的竹林,也让他不断想起春天里持续涌出地面的笋尖。而这些远远不够,他仍将迷惑于更多的赞美:为什么,人人都说她是傻的,她却给他送来蜂蜜一般的好?为什么,月光和芦苇荡让她送来了她的好,又体贴地掩住了她的好?也许,它们都是好?既然如此,但凡他看得见的地方,是不是都有他看不见的好?
半夜里,他一直舍不得睡过去,就好像一旦睡着,那些赞美,那些蜂蜜一般的好,就会消失得再无影踪,而他实在舍不得它们。此刻,被褥是单薄和残破的,天气也在急速地转凉,但是,他的体内,他的身外,全都缭绕和充盈着巨大的暖意,他无须再像往日那样瑟缩和咬紧牙关。还有,这暖意,不光让他喜悦,甚至让他想入非非:也许,他和她,这两个在此处挨打和在彼处挨打的人,只要胆大包天,偷偷地,只是偷偷地,他朝她走过去,她再朝他走过来,他和她便也能像旁人一样活着,除了坏,还有好,除了逃避不开的沮丧,更有源源不断的赞美?一定是这样。这时候,夜幕里下起了雨,雨滴轻轻敲打着屋顶,他便在雨声里告诉自己:一定是这样。他一定要将那些好与赞美抓在手中,再牢牢装进自己的口袋。
他说到做到。打第二天起,看上去,他还是那个在拳脚之下忍气吞声的人,可是暗地里,他却变成了一只四处搜寻着她的气味的野狗——冬天里,她家里几乎断粮了,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所以,他每天都要花费好多心思寻找埋伏之地,那埋伏之地,既要不为人知,又要能让自己省下的口粮顺利地交到她手上;春天里,小河涨水,她去油菜地里施肥的路上,脚底下一滑,跌进了河中,幸亏他蹑手蹑脚地跟在她身边,不管不顾地大喊大叫,终于引来了一个好心人将她从河水里捞了上来。一开始,面对他的疯狂,她吓坏了,总是躲着他,而他依然故我,能见她,便要见她,能给她好,便要给她好。渐渐地,她也终于明白过来,在这村子里,惟有他和她才是匹配的,她当然从来没有幻想过任何匹配,可是,要是真正的匹配来了,她只怕也是不忍心推开的吧?就好像两个同时落水的人,除了伸出各自的手去触向对方,满世界,哪里还有第三个人向他们伸出手来呢?所以,并没有过多久,她就不再躲着他,甚至,有点工夫的时候,她也像他一样,躲藏在各种不为人知之处等着他:还是在那片芦苇荡里,她截住了放学后的他,递给他几只已经煮熟了的鹌鹑蛋。芦苇荡里没有石头,他找不到敲碎蛋壳的地方,还是她,一只一只用手轻轻地去捏,蛋壳被捏碎了,一只只蛋却都圆滚如初,她再像捧着宝贝疙瘩一般递给他,看着他吃,他知道,她并没有吃,但她愿意看着他吃。
这样一个她,怎么可能是傻子呢?她当然不是傻子。很快,他就看清了她,她其实是故意想让别人认为她傻——反正是个哑巴,那么,干脆再拿傻瓜当作借口,以此来逃避自己是个哑巴吧。是啊,在旁人眼中,一个傻瓜,总要比一个哑巴更要可怜,那么,莫不如让更可怜的自己罩住一个可怜的自己吧,果然如此的话,在彻底的被轻贱中,她反倒活得更像一个人了?可惜,他只有十岁,无法再往深里想,但是,再往后,一旦她打着手势告诉他说自己的脑子傻,他便立即止住,也胡乱打着手势对她说:你一点都不傻,你不过是想让身边的人放过你,就像你身上那件油腻的毛衣,它不过是让你自己相信,你活该受罪,实际上,你比谁都更爱干净,对不对?——每一回,只要他这么说,她便再也说不出话来,而他却没有停止,继续告诉她:和枫树一样,和芦苇荡一样,她配得上任何赞美。
赞美,这个手势可真难打给她啊。可她竟然非要问清楚,他所说的、经常在身体里横冲直撞的赞美究竟是什么?既然如此,他便下定了决心,从现在开始,他来给她上一堂赞美课,这课堂也不在他处,就在眼前的芦苇荡里。他指引着她,在一眼看不到头的芦苇荡里穿行,再对她说,你看,这些芦苇的根部,看起来平平常常,实际上却是一味中药。从前,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烧了,嗓子痛了,母亲就会挖了芦根回去给他煮水喝。所以现在,他想母亲的时候,就会折一截芦根放在嘴巴里嚼,越嚼,母亲就离他越近;还有那些白色的芦花,你以为它们全都是白色的吗?不,它们其实什么颜色都有,淡青的,微微发红的……每一回,当他辨认清楚了每一种颜色,他便想,待他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又多了一桩可以让自己对他们炫耀起来的本事了;你再看,前面还有一口泉眼,去年彻底干了,今年又活了过来,好多人都没注意到它活了过来,不过这样最好,这样,这口活过来的泉眼就成了他一个人的秘密,如此,他就和他看过的小说主人公一样,也变成了怀揣着秘密却守口如瓶的人了。是的,他指引给她看的这一切,在他的心底里,全都当得起任何赞美。可是,她却越走越慢,终于忍不住,打手势告诉他,在她的四川老家,也有一片看不到头的芦苇荡。所以,她其实害怕眼前的这片芦苇荡,一走进来,她就想家,想她父母还没死的时候。说着说着,她竟然嚎啕大哭了起来,他想上前去劝她,但她却推开手,捂着脸,压低哭声,踉跄着跑出了芦苇荡。
第二堂赞美课到来得实在太晚了一些。上课之前,有好多天,他故意避开芦苇荡,在村子里四处游荡,既磨刀霍霍,又小心翼翼,终于选定了课堂,但是,他却怎么也见不到她了——听人说,她被她丈夫带到邻县的小煤窑里挖煤去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当然失魂落魄,只要放了学,就去她家附近远远地张望一阵子,自然,他一直都没有看见她。大概过了两个月,有天晚上,村子里有人结婚,去镇上请来放映队放了一场电影。他去看电影的时候,又挨了一顿打,所以,电影还没完,他就忍不住伤心,离开了放电影的地方,一个人,在刚刚下过雨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朝前走。突然,他看见了她,她回来了,却不再是他认得的那个她了:她以前就瘦,现在更比以前瘦了许多,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以前,她的脸,她的手,都是那么白,是再脏再油腻的衣服都遮不住的白,而现在,她是那么黑,不是被煤灰暂时盖住了白的黑,而是实实在在的黑,是连月光也照不白的黑。尽管如此,一见到她,他还是忍不住扑了过去,扑上去了,又说不出话来,她却打着手势告诉她,她明天就要再回邻县的小煤窑,现在,她想让他抓紧时间,再给他上一堂赞美课。见他还愣怔着,她便又对他说:虽然她仍然不知道他所说的赞美到底是什么,但是,她也想跟他一样,哪怕远在小煤窑里,身上,心里,都有他所说的赞美。
好吧,那么,就让他们赶紧开始这一堂赞美课吧。说起来,这一堂课的课堂,根本不是什么隐秘的所在,它仅仅只是一本书,对,就是那本《安徒生童话》。满村子的一草一木都可以作证,为了找到一座合适的课堂,他的脚底都磨出了水泡,但是最终,他决定放弃那些隐秘的所在,转而给她好好讲完《安徒生童话》里的每一个故事。只因为,正是这本书,自他寄养之初就一直被他压在枕头底下。它是他的兄弟,让他知道在这世上,在更加广阔的地方,也有挨打、眼泪和四处流浪,却也有相逢、欢乐和迟早都要出现的偿报,比如他和她的亲近,于他便是偿报,便是《安徒生童话》里的故事搬到了他们活命的村子里。也因此,还有什么比这本书更适合当作课堂,还有什么比让她跟他一样读完这本书,无须再借助旁人,仅凭自己就能让自己的心脏被赞美包围,更令他放心呢?
好吧,赶紧开始吧,他拽着她,两个人一起朝前跑,一直跑到了她曾经跌进去的那条小河边,这才坐下,然后,他便开始了——此后多年,他一直记得,并将终生记得,他给她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丑小鸭》。这一晚的月光,比往日里都要亮,亮得像白天,她看他的手势便毫不吃力,再加上,为了这堂课,他几乎茶饭不思,所有可能艰难的手势,他都已经仔细地排练过了,所以,他有十足的把握将那只最后变成天鹅的丑小鸭带到她的眼前来。事实上,她也和他想象的一样,无论他打出什么手势,她全都能看得明白,当他讲到丑小鸭在沼泽地里看见那两只调皮的公雁被猎人开枪打死时,她的身体禁不住颤抖了一下,他刚止住手势,她却催促他赶紧往下讲。然而,天上下起了雨,这场雨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而且,一下起来就再也收不住,一想到她明天早晨就要离开,他便不甘心,非要把故事讲完不可。他骗她,故事很短,他马上就能讲完,紧接着,也不管她同意不同意,冻得瑟瑟发抖的他继续往下讲,只有上天和他自己知道,他是多么想尽快地告诉她,那只丑小鸭,最后不仅变成了一只天鹅,而且,因为吃过的苦,它终生都有一颗赞美和不肯骄傲的心。只是,雨下得更大了,他没办法不停下来,看着她,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最终,还是她站起身来,拽着他,一起跑回了村子里。
第三堂赞美课,是在半个月后。前几天,他在挨打的时候逃进了一片竹林,哪知道,竹林里到处都是蜂窝,在误撞了蜂窝之后,哪怕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野蜂们也没有放过他,他跑到哪里,野蜂们便追到哪里,最后,他的全身上下至少被蜇了几十处。等他跑回寄养的人家,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好半天都没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一连好几天,他躺在床上,几乎奄奄一息,疼痛无休无止,有好多次,他都疑心自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忽远忽近:寄养人家说话的声音,赤脚医生前来出诊的声音,一切都在,一切又都不在,他还听见寄养人家的小孩子跑到了他的床前,但是很快就吓得赶紧跑了出去,也难怪,虽说他看不见自己,却也能猜出来,现在的他,大概和一个满身肿胀的鬼魂差不多。正是在这样的忽远忽近之中,他听见了她的死讯,对,就是她,远在邻县小煤窑里的她。前几天,在小煤窑里,她的丈夫喝多了酒,又追着她打,她开始逃,她的丈夫却一直追到了山岗上,刚一追上,就飞起一脚,将她从山岗上踹了下去,等到有人在山岗底下找到她时,她早已断了气。
而他竟然没有哭,一来是,他的眼睛还在肿胀中,就算泪水再多,也涌不出他的眼眶;二来是,当世界以骇人的模样告诉他,我们的生活到底可以坏到何种地步时,他反倒在闪电般稍纵即逝的震惊与怨愤中长大了。原来,当赞美开始,又或在赞美的尽头,等待着我们的,未见得只有欢乐、相逢和偿报,同样还有死亡、永无相逢和再也说不出话的沉默。但是,他已经作出了一个决定:越是如此,越是要赞美。对,在沉默中,他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要活下去,要赞美,只因为,在你的活下去中,还有她的活下去,在你的赞美之中,还有她从未得到过的赞美。从此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境地,都不要忘了继续上赞美课,无非是,从今以后,他既是讲课的人,也是听课的人。还等什么呢?第三堂赞美课,就从现在开始吧。也许,她还并未走远,而他的双手也刚刚可以动弹,她还能像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一样看得毫不吃力,还等什么呢?开始吧。于是,他缓慢地、轻轻地挪动着左手和右手,让它们破镜重圆,让它们凑在了一起,然后,他开始讲课,这一课,仍然从《丑小鸭》讲起,从上一回中断的地方讲起:“天快要暗的时候,四周才静下来。可是这只可怜的小鸭还不敢站起来。他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敢向四周望一眼,于是他急忙跑出这块沼泽地,拼命地跑,向田野上跑,向牧场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