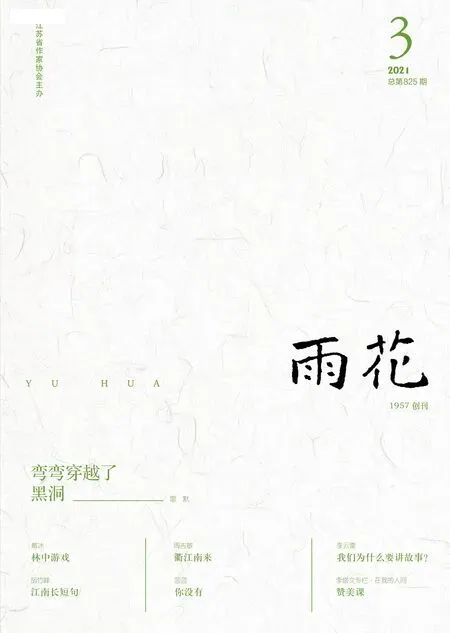你没有
2021-11-12 12:37
雨花 2021年3期
音乐
终于平静了——
独自一人在夜里
听着音乐,犹如项上头颅
被一只手轻轻摘走。
你打败了我。我对音乐说。
并感到有一部分怒火熄灭了。
我是你的奴隶。
前额抵着它的膝盖,我又说。
一种让我慌乱的温柔情感
涌上心头。
我并没有忘记
长久遭受的耻辱,以及
对自己的懊恼。我只是不知不觉
做了它的俘虏。
一位将军曾说:
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士兵听太多音乐,
那样只会让他们变得软弱。
现在,我也屈服了——
鼻涕眼泪抹在我的破袖子上。
我不再咒骂,也不再四处寻找砖头。
我只想抱着一个什么人
为这黑黢黢无边的世界
放声痛哭。
你没有
你没有一个
可以求助的上帝,
也没有一个在半空注视着你的
仁慈的佛菩萨。
有时候你奔向田野,渴望
麦田给你籽粒金黄的思想,
玉米赐予你翠绿的沙沙作响的思想。
沿着麦浪涌向地平线的尽头,
你能看到天边,以及更高处的宇宙。
它们忽然出现,为了使你
在辽阔中看到它们的辽阔,看到
被麦田和青纱帐所表达的秘密和澄明。
难道你不也是其中一个?
和无数株麦子、玉米,无数的人
构成世界的生死寂灭、诞生和轮回——
白杨树把头伸向虚空,
而瀑布从高处跳下,跌碎在大地……
在一个不合拢的梦里,你的疑问
访问了它们——作为一粒种子的
初次上任的女秘书,你又一次
耐心等着春天,以及还没有出现的
某位佛菩萨或上帝。
人只能生活在
人只能生活在目力所及的空间。
顶多,加上想象力抵达的边界。
没有人能例外。
帝王,教授,农夫和海员,
住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并拥有一把椅子、一张书桌
一块土地或者几亩大海。
没有人能例外。
但是你仍然震惊于某些事实:
哲学家在书柜里淋浴
而诗人躺在几个漂亮的病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