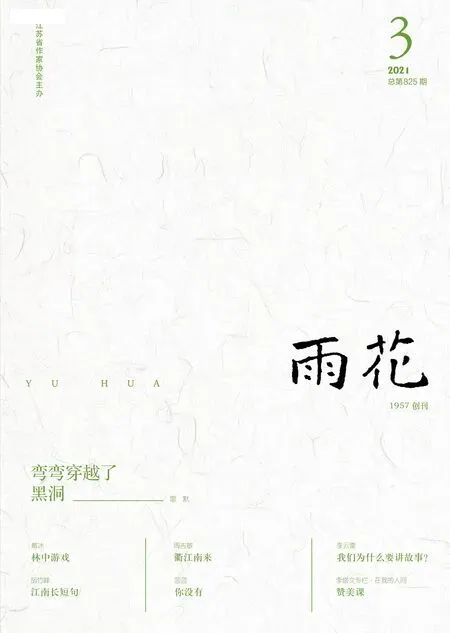我和母亲的战争
1
张小英准备干掉自己。
她一手握菜刀,跳上茶几,架在脖子上,另一手摁住自己后颈,生怕自己从自己手里逃遁。没活法了,我跟你爸去了!她恶狠狠道,我死了,你就满意?
我跨过散乱在客厅里的枕头、椅子,跃起,跳过沙发,准确地落在茶几上。一把夺下张小英的菜刀。
菜刀坠地,声音尖锐刺耳。“死死死,动不动就死去活来的,有意思吗?”
张小英颤巍巍从茶几上下来时,我心里怪难受。
客厅里陷入尴尬的静默。到底是张小英沉不住气:你就不该回来,让我一个人活得清静。我乘胜追击:是哦,我回来干什么呢?我要不回来,就不会被困在这里。张小英说,也不会被逮到派出所去。
被逮这事,我是真冤枉。早上去赶高铁,快要出小区时被人拦住,那里已经设了卡点,工作人员死活不让出,即便我拿着手机订票信息反复解释,对方还是态度强硬,冲我嚷,滚回去,不想死就乖乖待在家里。谁受得了这个态度?我又不是霜打的茄子,瞬间就回了过去,一来二去,推搡起来,也不知道是谁先动手的,警察很快就来了,不由分说就把我铐走。张小英去派出所接我,民警是她的学生,我们也算认识,几年前还铐过我一次。从派出所回来,我们再一次爆发战争,她砸掉餐桌上来不及收的碗筷,要不是我及时出手阻止,她把电视机也砸了。
我现在是真后悔。早知如此,就不该从杭州赶回来。快过年的某天下午,我和安可正打球。那阵子安可迷上羽毛球,她正计划减肥,觉得打羽毛球非常有必要,一下班就揪着我打羽毛球。三十分钟下来,我感觉头有些迷糊。安可停下来喝水,奚落我,你呀,得好好练练了。她灌了一口水,把杯子递给我,你电话响了。我摸了一下裤兜,电话果然在振动。来自张小英的电话让我迟疑。她已经半年多没有跟我联络,上次联络还是她的一个堂哥去世,打电话问我随多少礼。安可起疑,谁呀,半天不接?我斥道,咱妈。安可识趣走开。
通话很潦草。张小英问我在干什么,吃饭了没,最近怎样,身体好不好。然后转入正题:今年回来过年吧!我顿了一下。她说,两年了,你再不来,说不定我哪天死了烂了你都不知。我心中一震,我等下给你打点钱去吧。我有退休金,不缺钱,你回来过个年。她几乎要哭出来。我看了看广场那边低头玩手机的安可,她正用球拍颠球,看我时用空闲的手向我挥了挥,笑得很好看。我说,再说吧,就挂了电话。
安可试探我,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去?我拒绝了。我和张小英一本烂账理不清,安可去了易糟心。何况我还没说要回去过年呢。安可嘟嘴,不让我去,你也得去,你这是不孝,毕竟是生养你的母亲,再大的矛盾,也不至于要老死不相往来,她一个人生活,着实太孤单。她掰正我的身子,你倒是看着我,我们俩要结婚,我不想在一个残缺的家里生活,好吗?我准备好的一堆理由,突然就吐不出来了。
回到暌违近三年的老房子时,还没新冠疫情这回事,商店如期经营,人们如同往常一样生活在自己的轨道上。我们原本计划,我先回老家待一阵,正月初二坐高铁到安徽合肥,安可在那里接我,一起去她家,向她父母摊牌,如果顺利,顶多半年,我们就会结婚。票都订好了。
如果不回来,现在我已经到安徽了。这么想着,我心里更加后悔,是啊,我回来干什么呢?我回来找你吵架的吗?张小英立马顶回来,可不是嘛,你说说自己,回来这么多天,哪件事顺了我的意?但凡是有一件事顺了我的意,也不至于把我往死里逼。可别说了,我说,张小英,谁把你往死里逼?是你把我往死里逼好不好?你要死,你要死早死了,打从我爸去世,您要死要活多少次了?
张小英怔住了,愣愣地看我。
她再一次败在了我的手里。然而我心里一点兴奋的感觉也没有。吵架不是我本意,但当火被点燃,我还是像一枚炸弹一样炸了。
我知道我们之间这种由来已久的战争是该结束了,加上安可渴求的眼神——她是多么希望我和张小英之间的关系能缓和,所以我赶回来了。但回家不到一周,吵了不下五次,不吵架的时候几乎都很尴尬,极难受。眼看就要走,交通突然被封锁,出不去不说,门口还贴了告示牌:“此户有外省返回人员,在家自行隔离期间,请勿上门拜访。”宣告着我和张小英至少十四日内只能待在这个屋子里。
张小英憋了好一阵子的气,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要去捡地上的菜刀。我眼疾手快,迅速蹿去,将菜刀抢在手里。张小英不罢休,抓我的手,死不松开。我无奈松手,张小英得胜那一瞬,刀锋从我的手臂划了过去。突然冒出的鲜血,宣告了暂时的烽火熄灭。刀从张小英手里掉了下去,再次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她抓住我的手:儿子,疼不疼,疼不疼?
你满意了吧?我说,疼不疼关你什么事?那一刻,我心里竟升起一阵幸灾乐祸,伤口处发出的疼痛让我心里爽快,好像因为意外的一刀,心里的憋屈得以释放。我甩开她的手,快步进了书房。
砰——
世界再次陷入静默。
2
冬日寂静,老屋空寥,我常陷入幻听,好像张小英数次走到书房门前,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紧揪我心。但当我凝神屏气,那些声音又消隐而去,好像不曾响起。楼下偶尔传来声响,有人说话,有车经过,寒风使劲地吹着……寂静像一张大网,死死地罩着我们。
不知从多少岁开始,我将书房当作卧室,在狭小空间里,我学习、做恶梦、哭泣,从幼稚长到茁壮,直到结婚前买房,才让它退回书房的功用。漫长岁月里,张小英不止一次推开门,端来开水、牛奶、水果,抢走我的游戏机、零食、课外书。她从不敲门,闯入我的房间是她作为母亲的特权。大约十七岁,我有了第一个女朋友,有天逃课和她窝在书房里,张小英提前下班,听到书房里的声响,愤怒地闯了进来……
电话将我从回忆中拉回,我将声音压到最小,将发生的事情合盘告诉安可。你的性格看起来挺好呀,对我好,对其他人也没发过脾气,为什么和她就相处不下来?安可问我。我说,我不知道,我们都一样,人人都说她好,就是和我吵。我们同时陷入沉默。电话里的电流声让人不安。
天悄然黑下来,厨房传来响动,洗碗,切菜,炒菜,抽油烟机苍白嚎叫……张小英敲门,语气小心地问,你吃不吃?记忆里,这是她第一次敲门。我和安可已从电话转战微信视频,通过网络聊表相思。我慌忙关了视频,开门,张小英站在门外,手在围裙上上下搓着:我做了新菜。我心里叹了口气:吃,我洗个手。到餐桌前,张小英已经把汤给盛上了,先喝汤,她说,土鸡。
我心里有些酸,我们明明才大吵过,现在她却又有些卑微和讨好,为我做饭、盛汤。安可说,你们母子俩,其实都是一个性格,单独看来,都挺好,没什么问题,但两个人只要碰在一起,就是刺猬遇刺猬。她安慰我,她那边去不了就暂时不想了,既然疫情影响,就算回到杭州也没法复工,不如在家里好好待待。要不,把我们的事给妈说说?她提议,她不是还要安排你相亲吗?我没有答应,要是张小英知道安可的存在——我想都不敢想。
我坐下,喝口汤,没说话。本想说点什么的,但一时不知道如何说起,只好再喝一口。汤烫,喉咙一阵炙热。张小英先开口:乡下买来的鸡,味道就是不一样哈。我说,嗯,挺好。话搭上,气氛陡又缓和,战争进入试试探探的谈判。事实上,回家后这一阵子,无一天不是这样,吵一阵,歇一阵,眼看形势向好,转眼烽火又燃,像一场持久的拉锯战,没人真正得胜。
饭毕,我收拾碗筷,张小英迟疑一下,没说什么,移步沙发,打开电视。收拾完毕,我也坐到了沙发上。我犹豫过,但耳边响起安可的话,便坐了过去。电视正停在戏曲频道。什么时候你也看起了这个?我说。张小英说,还不是你爸带的?以前不喜欢,音转来转去,提不上精神,自打你爸走后,你离了家,我竟愈发喜欢起戏曲来,你爸要是在——
她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没往下说。我没接话,这是我们心里的痛。张小英看着我的手:怎么样?疼吗?伤口已经被我用纱布缠住,血早已止住,疼痛感消退了很多。还好,我说,有一点。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处理处理?算了吧,居家隔离不能出门,何况就算去了,医院里人来人往,谁知道会不会遇上携带病毒的人?张小英深以为然。
来来回回聊了阵,张小英突然认真看我,要不,那个谁,老马的女儿,你还是见上一见?我心里不耐烦,这事,回来那晚她首提,我们阔别近三年的争吵由此拉开。
算了吧。
你一走几年,家里什么事儿都是人家帮忙,老马一家,我了解,我和老马就想着,你们年轻人都挺合适,老马也不介意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你,就安排了一下。
什么他不介意?他不介意,我介意。
我说你,就不能听我安排一次?张小英急了。情势大变,我赶紧妥协,打住,打住啊,我可不想再吵。张小英更急,吵吵吵,我还怕你了?是我想吵啊?我就是想着给你安排一下,你至于这样吗?不知道为什么,我压下去的那股气又腾了起来,安排,张凯丽不是你安排的?张小英很快回击,别提凯丽,你没脸提凯丽,凯丽多好的姑娘,被你欺负成什么样?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
不是,张小英,你要搞清楚,我和张凯丽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知道凯丽听话懂事,是你把人欺负出去的。你真是有出息了,把你妈都不放在眼里了。
你又好到哪里去?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就咋咋呼呼说这说那。
你不要我咋咋呼呼说这说那也行,你把凯丽找回来,好好过日子,我什么都依你。
不可能,你就做梦吧。
你这是要我去死。
屋里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炉子上,水壶发出“滋滋滋”的声音。远处,焰火在夜空划出一道道亮光。
一霎那,我感觉自己要疯了,心里有一万只巨兽不断嚎叫、冲突着,随时准备冲出来。我心跳很快,喘着粗气,如果眼前的人不是我母亲,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来。我只得来回踱步,使劲呼吸,直到感觉自己冷静许多,才说,妈,咱不谈死行不行?我爸已经死了。
你还知道你爸死了?你知道你爸怎么死的吗?被你气死的!
我怔住,妈,那是肝癌,晚期,你要搞清楚,不要什么都往我身上推。
不是气你,能患上肝癌?凯丽那么好的姑娘,我和你爸相中的,哪里不好?给你欺负成什么样?
我再一次感到心底里那股火苗燃了起来,凯丽凯丽凯丽,张凯丽死了,别提了行不行?我和张凯丽,我问心无愧,我是打了她,那是她该打,她有错,没法原谅。
凯丽有错?什么错?这么多年了,也不见得说出个什么花来,能有什么错?你还真是能为自己找借口。
我噎住,接不上话,一下泄了气,蔫了,我跟你说不上,反正我问心无愧。我穿上外套,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回来。
张小英在身后气急败坏地问,你去哪,你去哪?你去了就别再回来,永远别回来。
我义无返顾地出了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我,逃离这无休无止的争吵。身后,老旧房门发出沉闷的声音,像极一声暴戾的叹息。
3
张小英突然闯入,把我和小女朋友吓坏了,蜷缩在床,依靠单薄的夏凉被遮蔽尚未脱光的身体。那晚,张小英和我爸对我进行了轮番的政治教育,忍无可忍不必再忍时,我夺门而出,离家出走,无处可去,在网吧里花光了所有钱,在马路边不知去往何处时,被一帮亲戚围住,趁机下台阶回家。现在已不同往日,甩开门,随便一个方向都有无尽的路可走,张小英也不会再像当时那样心急火燎地寻找我。
开门,预想中的霉味并未扑入鼻息。灯光赶走黑暗,眼前陈设和离开时并没多大不同。棉质拖鞋整齐摆放在鞋柜里。坐下,摸一把茶几,沾染少量的灰尘,这一切告诉我,我不在的漫长时光里,张小英定期来此打扫,以确保室内保持干净和整洁。
房子是我和张凯丽的婚房,不大,九十平方米小三居,和老屋同一小区,买时主要考虑照顾家里方便。张凯丽是张小英的同事,深得张小英喜欢。认识她的时候我刚从杭州回到老家,毕业就分手的苦难岁月,被张凯丽一桌一桌的好菜给抚慰了。张小英说,张凯丽是好女孩,我和你爸都喜欢。我心软了,你们喜欢就行。
和张凯丽在此度过快两年,彼时我在市里某行政部门工作,常加班,疏于照顾家庭。一结婚就生娃的计划被我耽搁了。那个暑假,若非领导突然出差,我急匆匆赶回家取备用手机,可能我们还会在此度过后来无数漫长的日子,可能我将永远不知道那个冒充查水表师傅的市演艺团男演员和张凯丽之间的那些事。
事后张凯丽求我原谅,看在张小英和我爸的份上,我忍了。但终究是心里落了根,我们开始争吵,最激烈时,我提刀追了张凯丽半个小区,幸好物业及时制止。我被抓到派出所教育了一顿,张小英带着张凯丽把我从她学生手里领了出来。然后我们离婚,张凯丽从此消失无踪。
离婚没多久,我爸查出肝癌晚期。没半年,走了。从离婚到我爸去世,我和张小英没少吵架,绕不开的,都是张凯丽。她咬定,是我对不起张凯丽,没有家暴,没有提刀狂追,那样的好姑娘是不可能撂下他们二老走的。开始那时,我忍,毕竟张凯丽在他们心中太美好,她情商高,会说话,照顾他们也好。实在忍不住,我顶撞回去,张小英再打回来,你来我往,不消二十句话,我必然败下阵来。
我爸主要靠我照顾,后来病情越来越重,我每天定时给他喂葡萄糖,以防止他晕厥,白天黑夜如此,我身体也每况愈下,情绪越来越差。再吵,就没休止了,四下邻里开始还劝上一劝,后来竟习惯了,好像我们家吵架再正常不过了。我爸倒是每次都想劝,但毕竟重疾缠身,没说上三句话,气已颓了一半。
我爸走时,我和张小英正在为他喝葡萄糖的事吵架。他必须依靠葡萄糖维持清醒,时间长了,整个人面部虚肿,口舌麻木,味觉丧失,吃什么都味同嚼蜡,渐渐对喝葡萄糖开始抵触。那天我正劝他喝糖水,张小英进门,他不愿喝就缓会儿,别逼他行不行?我说,不是逼,再不喝,一会儿就晕了。张小英说,也不见得,现在还清醒,再说了,实在晕过去就注射吧。我心里很难过,每次我爸晕过去都必须依靠注射葡萄糖才能醒来,半醒状态下,他挣扎着,用拳头捶打我,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样子让人心疼。我生起气来,你到底关不关心我爸?晕一次伤害多大你知道不?张小英很快回击,一场吵架就此拉开。我爸看不下去,拼命把杯子里的葡萄糖喝了个底朝天。但我们的争吵并没有结束,从我爸的房间吵到了客厅,我爸劝说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没有了。再回到我爸的房间,人已经没了气,吐出的血呈褐色,被子染了一大片。
那时正值寒冬,离除夕不过两天。丧事那几天,我和张小英几乎没说上一句话,不认识一样。我爸的后事料理完,已经新年。节后上班,我向单位递了一纸辞职信,不告而别,去了杭州。快到杭州时,我在同学群里发消息,说准备回杭州发展,没人理,只收到安可私信:几点到?我接你。
安可早上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对于昨晚又爆发的争吵,安可深为不爽,你这明明是逃避。我说,不然我能怎样?她都说了,我要出了门,永远别再回去。安可说,她是你妈。我说,我还是她儿子呢。安可被噎住,半会儿才说,我觉得,你还是要主动回去,别像个小孩。不回,心烦得很,我说。安可说,冲着我们的未来,你也该回去,听话。我们俩僵住,彼此都有些尴尬,索性挂了电话。
4
漫长的成长岁月里,除了被张小英撞见带女朋友回家那次,后来我也有过几次离家出走。最远的一次,我循着国道走了二十多公里,到附近的一个镇子,找同学。同学悄悄给我家里打了电话,第二天一早,张小英就站在了同学家楼下,塞给了我一些钱,她没有骂我,只是让我玩几天赶紧回家。几天后我回了家,参加张小英为我报名的暑期补习班。那时我爸出差,到某个县的深山里做勘探,整个暑假家里都只有我和张小英。我记得她常在炎热的下午把电风扇搬到近前,转着身子吹风,却不容我靠近,她说这样吹风扇容易湿气重,自己却吹了一整个暑假。
眼下寒冬,张小英只得像那个暑假依赖电风扇一样依赖一台电炉子。我进门时,电炉子还开着,屋里很暖和,张小英不见踪影。我终究选择回到张小英家,我家久无人居,如果我坚持待在那里,得渴死饿死。再说了,安可强烈要求我回到张小英身边,她说得都有些生气了。
家里安静极了,张小英应该是到小区里散步去了。我猫进书房,却无心看书,耳朵时刻关注着屋里的动静,心里不得安稳。到了午后,张小英还没回家,我决定给她打电话,关键时期,我们家又被要求居家隔离,万一给发现了,少不了社区里一顿批评教育,要是出点意外,那可得背点责任。电话拨通,张小英的电话铃声从她的卧室里传来。推门进去,看到张小英躺在床上,睡眼惺忪,脸色苍白,使劲张着嘴,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来,像个哑巴。
我吓了一跳,不由叫道,妈!张小英使劲扭动身子,却不能离开床单哪怕半公分,样子很滑稽,像被渔网困住的鱼。她的喉咙里挤出几个含糊的词,我什么也没听清。我把头贴近张小英的嘴巴,想听清楚她的话,她无力地推了我一下。我脑海里突然想起我爸弥留之际的光景,心里一酸:妈,你咋了?我竟然有些哽咽。张小英这回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
张小英病了,感冒,失声,更要命的是,她发烧了。经我反复确认,体温逼近39℃,浑身酸痛无力,毫无食欲。我心一慌,妈,别急啊,我马上打电话去,别怕,我们马上去医院,没事的,没事的。嘴是这么说,人却慌乱得不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她死死地箍着我的手,当我移动身子,她竟随着我的移动在床上摆了一下身子。我去掰她的手,松开呀。她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使劲挤出一句话,不,不,我不想被人关着。可是,我说,这些症状,和感染症状一模一样,必须去医院。
张小英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只得把她扶起来。我,我不去,她靠在靠背上,不要你管,你要是怕,就别进我屋来。她突然气急败坏的样子,跟每一次我们吵架时的模样别无二致。我说,妈,都这时候了就别孩子气了,生病,就该去医院是不是?张小英突然用几近祈求的眼神看着我,别把我送去,行不行?行不行啊?我杵在床前,过了好一阵子,我说,先给你熬点粥吧。张小英说,给我再来杯热水。
我在家里的备用药箱找到了一些感冒药和退烧药,看着张小英喝粥、吃药,再度睡过去。我心神不宁,忍不住给安可打了电话,她安慰我,感冒发烧都是冬季常见病,如果张小英坚持不去医院,可以先在家里观察观察。刚挂电话,一回头,张小英披着外套正站在卧室门边,她说还是困,让我再倒杯水进屋去。
张小英再度睡去,我百无聊赖之际,便收拾起书房来,在柜顶的盒子里发现了那台老旧的傻瓜相机,是高一那年张小英买给我的。那时我说,要学好拍照,给张小英拍多多的照片,现在细想,拍照学得不怎么样,也未曾给她拍过。相机早已坏了,何况现在已很难买到胶卷。它注定是无用的旧物,却又像一只力大无穷的手,把我反复往记忆里拉。
晚饭我依然熬了粥,加了白菜。张小英自己起床吃的。她的精神好了些,吃了一碗粥,又吃了半个馒头,说还想睡,我又催她吃了些药,便让她去睡了。我熬了半夜,临睡前给她量了一次体温,退烧了,我稍微心安了些,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后来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艳阳里,张小英披着红披风,在油菜花间慢慢走着,远远冲我挥手:儿子,来一张。我举起相机,“咔嚓咔嚓”,随即准备回看,却发现手里拿着的是那台她送的胶片机。我们拍了好多好多,艳阳一直没有落下去,我们说走出油菜花田就回家,但油菜花田太大,始终不能走出来……
然后我突然惊醒,从床上弹起来,先去看张小英。她的被褥很乱,人不在。找到她时,她正弯着腰拆装冷冻饺子的保鲜袋。厨房里弥漫着水汽,燃气灶的火苗发出轻微的“吱吱”声,锅里的水已经煮开。袋子似乎扎得紧了,她正努力用指甲寻找封口的缝隙,最后索性用手一撕,陆续往锅里放饺子。她一共放了十一个冷冻饺子,回头愣了一下,拉开门问我,你醒了?
我说,妈,你怎么起来了?
饿,饿得很。
你叫我啊!
睡得跟个死猪样,我叫你干什么?她转身,要继续往锅里放饺子,我连着你的一起煮?
别了。我找了温度计来,我洗漱完再自己煮,来,量一下体温。
她打开油烟机,厨房里的雾气急速散去。我好了呀,刚量过一次。再量一次。好吧,她似乎笑了一下说,你帮我搅搅锅。
体温已恢复正常,除了身子略微虚弱,张小英并无其他不适,人也食欲大增,十一个饺子吃得一个不剩。然后她满足地把自己移动到沙发上她习惯的那个位置,打开电视机,开始嗑起了瓜子。看到精彩处,噗嗤一笑,半粒儿瓜子仁随着瓜子壳飞到了大理石茶几上。我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拿着餐巾纸去擦,结果张小英不耐烦地冲我说,走开,你挡着我了。我没好气地把纸巾砸进茶几上的小垃圾桶,如果不是她感冒未愈,我非得回击不可。
5
天放晴了,冬日暖阳下,大街空阔,小区寥无行人,远处卡点上,值守人员百无聊赖地晒着太阳。新闻上,全国疫情形势日趋紧张,但眼前的小城里,天地静谧,阳光很暖。
张小英睡午觉了。我搬了椅子,在阳台上躺着晒太阳,玩了会儿手机,和安可打了会儿视频电话,又摆弄起那台废弃的傻瓜相机来,用湿纸巾一点一点地擦拭后,沾满灰尘的老旧相机竟然呈现出崭新的模样。有一刻,它竟像一件艺术品,呈现出某种温暖的气息。我的额头触碰到它,好像它还完好无损,可以瞬间摄取最美好的事物。可惜它已经坏掉了,不然真想试试拍摄效果。
坏都坏了,丢了吧。张小英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床,来到我身后。我给吓了一跳,这不挺好看吗?留着当摆设吧,可惜没地方修了,修好了也没用,买不到胶卷。张小英说,修它干吗?我看现在人们都用手机拍照,多方便啊。我心里一动,从椅子上站起来,来,我给你拍一张。张小英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哦,现在?现在,阳光多好呀。我指着阳台,就到阳台上拍吧。张小英拢着头发,我是不是要梳下头?矫情,我拍了一张,说,再换个姿势。
手机里的张小英很拘谨,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双唇紧闭,不苟言笑的样子。往日飞扬跋扈的张小英不知道哪里去了。
她说,删了吧。
我说,删了干吗?我看挺好。
她说,不好看。
我说,好吧,删。
她突然制止,其实也还好。
我说,我发给你。突然想起来,张小英并没有智能机,她没有微信,只有一个几乎不登陆的QQ。妈,要不我送你部手机吧,可以拍照,可以视频的那种。她一脸诧异,我用那种手机干吗?我又不懂。我说,你好歹是一退休人民教师,干的是教书育人的活,还学不了一个智能手机了?她顿了一下,好吧,不要太贵的。
等待高一入学那年的暑假,我曾追着张小英,从这屋到那屋,从家里到她工作的学校。她吼我,买相机干吗?拍照啊,我说,给你拍多多的照片。买那东西,你又不懂,她说,别费钱。我说,我马上高中啦,相机能有物理、化学难?她定定地看着我,好吧。
我和老马商量了,等过了这疫情,就一起吃顿饭。张小英摆弄着我的手机,我亲自下厨。
不见,我说过了,我不见。我很坚决地回应她。
那你和那个姑娘的事情,总该说说吧?这回,她眼神直直地盯着我,我心里一阵发毛。
楼下传来喧闹声,几个小孩忍不住寂寞,窜到小区里追逐起来。我避开她的眼睛,什么姑娘?
我都听到你们讲电话了,你以为瞒得住我。
我没说话,死死地看着楼下,孩子们正蹲在地上,围在一起商量着什么。张小英喃喃地说,要是你和凯丽好好的,孙子都该上小学——她意识到什么,紧紧闭了嘴。
我不说话,心里数了一下,楼下共七个小孩,他们正谋划着什么。
张小英说,既然有了,抓紧结婚吧,趁我还在,还能帮你们带着。
孩子们四散而去,砰——
鞭炮的声响吓得我浑身一震。我心里一阵烦躁,海浪一般翻涌过来。以往,汹涌的海浪,会冲毁脆弱的防线,一发不可收拾。但那一刻,我定了定神,把目光从楼下移到高空,蓝色天空琥珀一般空阔透明。我心里的海浪慢慢退潮而去。
从张小英手里拿回自己的手机,看到安可一分钟前发来的微信:亲爱的,和妈妈怎么样了呀?我们的事情说了吗?
我看了一眼张小英,她似乎笑了一下,起身离开客厅,走进厨房,佝偻着身子,不知道要开始忙活什么。
我回过神来,在和安可的对话框里打字: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