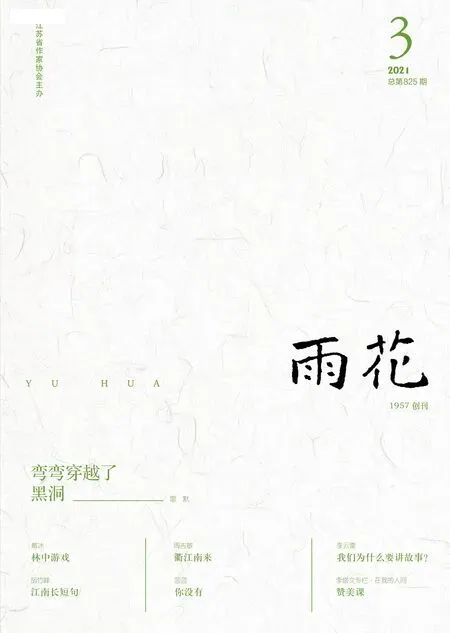要不要做一只弹弓 (外一篇)
樱桃树上的花儿刚谢,就能看到小小的果实了。小得如一个个带尾巴的绿色小蝌蚪,倒挂在那里。看来不只有我关注它,几只肥硕的鸽子也已经到访多次,对其偷觑已久、垂涎三尺。它们不仅天天来,而且还坐在最顶端的枝丫上旁若无人、悠闲自得地晒太阳。
我很气恼。使用了一切伎俩,依然斥不动它们,赶不走它们,于是我心生一念:去做一个弹弓!
有人会问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我儿时是个假小子不成?也的确如此。儿时谁没跳过皮筋,蹦过格子,荡过秋千,射过弹弓?要是没有这些,对我来说那就跟没过过童年一样。
做弹弓是很简单的事,找一个理想的带Y 型叉的树枝,再绑上一个弹力好的宽皮筋,中间再加上一小块可裹住石子的厚布就成了,当然最好是一块皮子,我童年的异性玩伴做弹弓有用卡纸的,也有用帆布的。我自制的弹弓没派上过用场,也没打过人,更没射坏过谁家的玻璃,但至少和男孩子们比试过,能射出不近的距离,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了。
现在,我准备做弹弓,去吓唬那些恬不知耻的鸽子。
其实,原本在这棵樱桃树的位置种过梅子树,果实呈深紫色,无奈却体会不了古人诗词歌韵里的“梅子黄时日日晴”。当年,梅子挂满枝头,来不及采摘就被鸟儿给啄得伤痕累累。这鸟儿也真是的,不紧着一个果子吃,偏偏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一片果实都被它们糟蹋了,被啄出口儿的梅子自然也就让黄蜂们省了事。所以,你若看到饱满硕大的果子而喜出望外时,常常会空欢喜一场,因为等你去摘时,会发现果子的另一侧已经露出大洞来,更残酷的是,你都能直视梅核儿了。这让人很为果实伤心,也为自己的空欢喜委屈。
因为梅子太多,又不能存放,只能做果酱。那一年度假提前回家,本为参加一对德国朋友的婚礼,以为时辰尚早,便把锯掉正生病的梅子树这件事列入了日程。看着轰然倒地的树干虽然很伤感,但上面的累累果实,多得让人欢呼,让人心生欢喜。可见人有时真是见食忘情。平日够不着的树尖,现在触手可及,而且果实也完美得很,于是便兴高采烈地费一下午时间去摘果子,然后又忙着在热锅里做果酱。因去核儿麻烦,就干脆摘了胶皮手套,结果梅子汁把手指染得紫红紫红的,特别是指甲处,留下了洗也洗不掉的蓝色,好像人在地里干了几天农活没洗过手似的。想到用柠檬洗手,但成效甚微。不知婚礼上是否会有人盯住我的手看,觉得与我华丽的服饰很不相配。但也没有办法了。想出了解释的理由后,我开始打扮,一切就绪后就要出发了,这才找来请柬查看婚礼地址,这一看不打紧,却发现把时间弄错了,婚礼的日期是头一天,也就是我们砍梅子树的时候。
白白早回,连个晚集也没赶上。索性再做几瓶梅子酱。
我很奇怪自己当时怎么没想过做弹弓的事,因为那时鸟儿是成群地来的。或许因为那时来的都是可爱的黑炭头麻雀和唱歌好听的乌鸫鸟的缘故,让人舍不得动那个凶狠的念头。
鸽子则不同。鸽子在德国这个地区不是十分受欢迎的鸟类,或许是它们数量太多的缘故,城里的中心——市政厅广场前会聚集不少,行人常朝它们扔面包屑。但它们在教堂塔顶飞来飞去时,可不顾下面的行人和游客,落下几次“炮弹”在人们的肩上甚至头顶也是有的,让人哭笑不得。有一次我在佛罗伦萨的宫殿大门外歇息,眼见着一位太太讲究的遮阳帽上被飞过的鸽子抛了一堆污物,老夫人气得直要扔了那顶款式很不错的帽子。在汉堡有巴洛克拱门的阿尔斯特湖边吃夏日冷饮时,需要十分小心,那些被惯得不得了的鸽子有时会直接落到夏日设在湖边的饭桌上,甚至不知羞耻地进攻高脚杯里的香草冰激凌。或许是它们随处出恭的行为很让人头疼,其次也是因为其他的小鸟儿更多,更灵敏更可爱,也没有攻击性,所以这里的人们对鸽子几乎没有同情心。就像招中国人喜爱的喜鹊,因其名字含吉祥之义而成为吉祥鸟,德国人却视它们为小偷,因为它们常去捣坏小鸟的窝,而且偷鸟蛋。虽然喜鹊也常成双成对地光顾我的花园,吃我的果子,但或许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缘故,我对它们多半充满善意,也绝不会想起去做什么弹弓。
我知道有人把射弹弓当成爱好,还有的地方将它列入体育比赛项目,很有意思。就像踢毽子,本来是游戏,现在也是运动项目了。当然,用德语说,所有的运动都是“玩儿”,也就不奇怪了。
Y 型的树枝我是不缺的,刚刚开过花的白玉兰枝桠绝对是理想的选择。找来一截,比划几下,用花园剪子修一修,就很满意。宽皮筋也不用费力,从商店买来的盛酸黄瓜或者水果的玻璃罐头上卸下来完全可行。这样忙活了一下午,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弹弓妥妥地完工了。
于是就等在了距离樱桃树不远的露台上,身边的椅子上摆着那个刚刚做好的武器。说是看书,眼睛却鬼鬼祟祟地瞟着那棵大树,完全不如鸽子那么光明磊落。正在嘲笑着自己的心虚,就见两只鸽子的倩影掠过,而且如我所愿地落到了正对暖阳的树枝上。
不容分说,我站起身,取了弓,在花坛附近找到了两颗小石子,三步并两步冲到最佳位置,举弓便射。“啪啪”,两声脆响!石子带着弧度漂亮地飞了出去。我等待伟大的胜利。
鸽子没有动,它们依然我行我素地坐在树尖,似乎刚才我在下面的举动与它们无半点关系。
我真是羞愧难当!为我的完美手工,为我的半天等待,为我一厢情愿的进攻。鸽子能说什么?它们会嘲笑我吗?那个连飞都不会的人类!
罢了罢了!这做弹弓打鸽子的设想估计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燕子的故事
燕子来时春未老。
正是五月,燕子又来。已经是第三年了,它们年年春天来这里。
一定是那对情侣燕,呢喃着,尖嘴衔泥,看准了前屋檐下的壁灯,飞来飞去忙着造窝,情状如唐人毛文锡的那句点睛之句:垒巢泥湿时时坠。几日后,白色的老式壁灯上先是一截低矮的围栏,后为半高的围墙,最终连麻线棕毛都用上了,建成了一个与罗马斗兽场一般有观赏价值的燕窝:灰色,半圆,整齐,辉煌。总之对燕子来说几乎是一个重点工程了。
邻居英格丽太太听说我家有燕子,便天天来看。这是好事呢!多年前这里家家门前有燕窝,但人们为了不被打扰和要所谓的整齐干净,第二年就除去了燕窝,使得这里长久以来不再有燕子光顾。英格丽太太说完,叹着气,摇着头。
对面房子里住的福克茨太太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刚出门,她就叫住我,对我说:我知道,你家来小燕子了。她眼睛真好使,两家房子至少隔有三百米呢,她居然看到了我家屋檐下的繁忙景象。
那对燕子就在窝里定居下来。每日,只看到一只燕尾从围墙的边上探出,偶尔也会看到黑脑袋先抬起来,随后是白胸,然后是整个身子。德国这里的家燕可不像我在爱尔兰加油站棚顶见过的那么不怕人,它们一看有人出门就会从窝里飞出去,转一圈然后再飞回来。我相信,这耽误了它不少时辰,把孵出燕宝宝的过程拉长了。这让我目睹了五只雏燕在我家屋顶笨拙练飞的成长过程。待它们翅膀硬了之后,真的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飞走了。这让我很是失落。
第二年,似曾相识燕归来。
燕窝被加高了,如预想的那样,先有五只雏燕的尖尖嘴和肥硕的小身子,齐刷刷的,很可爱。后来,我想它们该如去年的雏燕一般能飞翔了,也会在我家屋顶展翅盘旋了,却在一天早上,在地上发现了毙命的四只小燕,还有一只则在一旁喘气。我不敢贸然去救,遂询问生物学家朋友,无果,无药可医。是晚,窝空燕去。英格丽太太安慰我一番,说或许是鸟类流行病吧。自然界,适者生存。
但是一转眼,燕窝里又有了燕子,而且就在原窝。我诧异,怎么会这么快繁殖呢?这么快就能忘却悲伤?我们不懂动物世界的规矩。由着它们来吧。这次孵蛋成功了,四只雏燕很快长到和父母一般大小,日出而出,日落而归。燕窝那里轮番有燕拥坐,不知是最幼还是最老的,抑或是功劳最大的母燕?直到秋日逼近,它们才陆续飞走。英格丽说,它们该飞走了。
有道是:燕子来时春雨香,燕子去时秋雨凉。
今年是第三年。两只燕子居然不顾疫情,回来了。看来今年的春雨依然香吧。
像回老家那样快活地将壁灯上的巢加高加固之后,它们果真又孵蛋了。跟以往一样,每晚公燕荡秋千似的坐在灯线上,很忠诚地唧啾着,陪伴窝里的母燕。忠诚相伴的燕子也让人类感动。
本以为小燕马上就破壳了呢,也以为窗外不断激烈的叽叽声是雏燕看到父母后在叫食物呢,开门去看时,只见几只燕子在我家屋檐下转圈追赶,显然是两只燕子叫来的援兵。那么敌人呢?紧接着我便看到了地上三个碎了的蛋壳,那么袖珍,那么无助。看来确有外敌入侵!此外我还看到头顶上的燕巢里有白色羽毛在闪烁。不知是否有过搏斗,因为白羽毛只有燕子腹部才有。羽毛为何散落?很像撕打过。太高,不得而知。要不要干预?我又去问了生物学家朋友。朋友说,如果你实在想知道,不妨拿个镜子伸进去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
既然不了解动物世界,我们就最好尊重它。
我正为碎了的蛋壳忧伤时,却意外地发现这两只燕子在转移目标。原来它们放弃了原有的燕窝,打算重新建巢,而且这次的目标是在靠近原窝不远的一盏长条灯后。于是又是每天不知从哪里衔来湿土和草棍甚至麻绳线,辛勤劳作起来。燕子啊,灯体是玻璃的,灯框是金属的,滑溜溜的,沾不住泥啊!这哪里是做窝的地方呢?我不嘲笑你们,是同情你们!虽然我并无信心,但依然全神贯注地关注了它们做窝的过程:它们把尖尖的嘴伸进灯框边缘的缝里,将含着的泥土塞进灯管与灯框之间去,一次又一次,泥土掉了又掉,可它们却锲而不舍,重复地做下去,一连多日。
是的,我错了。人类太小看动物了。燕窝果真做成了,不仅做成了,而且做得跟一件艺术品一样!它造型独特,如同一个精工细作的竹篮筐嵌在长灯的一侧!最为聪慧的是,你从前方望过去,只能看见屋檐下的吸顶长灯,绝对想不到灯的后面会有个燕窝。它藏在灯后,那么巧妙,那么隐蔽。燕子可能知道,无论再来什么动物,都不会轻易发现灯后面的秘密了。这次它们相信自己会成功的。
随后的过程与以往几乎一样,不多久,五只闭眼睛的小毛头从尖尖嘴变成了戴白边儿的圆嘴唇,直至最后羽翼丰满……但是,这次它们没有突然离开,而是在原址的上空练习飞翔。精彩的是每天傍晚,高空上几只燕子快乐地飞来飞去,嬉戏着,打闹着,你啄我一下,我追你一阵,偶尔会有一只飞在最前面的燕子来个突然的俯冲,随在其身后的就跟着模仿,一连几次做同一个动作,就像是最美姿势的飞行训练似的。有时整个白天都没见影儿,晚上却齐刷刷地飞回来了,那时它们又跟刚出壳时那样挤在小窝里,排排坐吃果果似的。因为它们的身子长大了,圆鼓鼓的,所以每晚回窝都会折腾好一阵才能落座,有的得等别的燕子先飞上去转过身,趴好了,才能飞上去,光调整身体姿势就要好半天。后来的攀在管灯边沿,用小爪子紧紧地扣住金属,耐心有秩序地等待前一只燕子把自己安顿好。所以那时唧唧喳喳的声音很大,而且会持续好一阵子,像一群玩疯了的小丫头,快乐地回家来了。更有趣的是,父母燕有固定的位置:灯线上。其实那儿地方很大,但好像晚上那里只留给父母,其他的燕子不去。一天傍晚家人骑车出门,我嘱咐回来时声音轻些,车库门别开到最大,免得惊吓到了窝里的燕子。家人遵旨,小心翼翼地开关门。不过据说,上面的燕子在车库门被打开时居然纹丝不动。看来它们睡着了,怕惊扰它们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了。
我家燕子的故事真可以说具有古希腊悲喜剧的一切特质,不光一波三折,而且还有很多跌宕起伏的元素:意外,夭折,诞生,哺育,入侵,疾病,搏斗,成长,胜利,欢聚……
秋日近了,燕子依然日出而出,日落而归。英格丽太太又来了,问我房檐下的燕子飞走了没有。我说,没有,或许因为有过夭折的缘故,这次延长了滞留时间。“已经快到9月了,再不飞走就太迟了。”英格丽太太很焦急。
它们会飞到哪里去?我真舍不得呢!我说,它们可以就待在这里。
它们得飞到地球的南边去啊,最远能飞到非洲呢,热带地区才有吃的。英格丽太太说。
它们最终还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