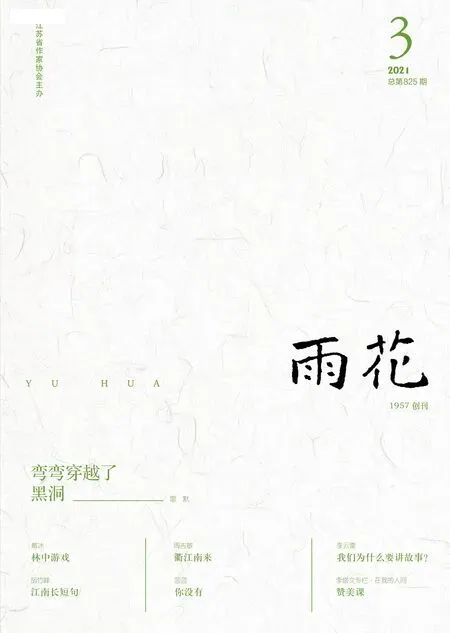陌生之旅
说起来,我对于城市的印象来自于公交车。不知从何时起,公交车便开进了我的日常生活中,让我觉得城市就是由一条条弯曲的公交车线路构成的。在公交车上看城市,它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没有哪种方式比这更富有仪式感:车缓缓而行,玻璃窗外,是轻轻翻过的一栋栋建筑,一个个商铺,一棵棵树木。它们在人的眸子间轻轻地翻,仿佛清泉石上流。
停靠在车窗旁的眼睛紧盯着这座城市。端在脖子上的大脑像一个收割机,记录眼前的一切。那段时间,乘坐公交车成了我的癖好。我想再小的城市也会有远方,远方可能就在家隔壁,公交车转一大圈,又回来了,但是眼睛收获的猎物却不可胜数。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一辆2 路公交车驶入南昌老火车站站台。它在机械地完成了一次吞吐后,迅速离开,带走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开始用他自己的眼光打量起这座城市。
大雨过后,地面尘土的气息被卷向空中,人们呼吸着这种松软而又热烈的气味。阳光有着油画的色彩,展示着诱人的质感,公交车朝着城市的中心驶去。那时候,城门早已拆掉。车由东向西。老福山不是一座山,是一个圆形的街心花园。八一广场高大的革命纪念塔从天空坠入眼帘。展览馆、文联大楼、革命烈士纪念堂、老邮电大楼、江西饭店,垂手站立在长长的街道两旁。
乘公交车去和一座城市相见,要比其他任何的交通工具都更具有抒情性。当然我们也可能因此想到白马或者船。李白应该就是骑着白马去的长安。那一日,拜访对象张丞相正在病中。“哒哒”的马蹄踏着长安的青石路面,马对着长安的天空发出一声深长的嘶鸣。马倦了,诗人李白在马背上也倦了,络绎不绝的马车擦肩而过,他被呛了一鼻子尘土。马已经与现代城市的整体气氛不相匹配。船就显得更滑稽了。公交车名正言顺地成为这个时代马路上最常见的事物,它从一个路口行驶到另一个路口,将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进行置换,如此循环,每一辆公交车都可能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世界就浓缩在一辆公交车中。可是人们并不在意,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就像长安街上,马和马车络绎不绝,居住在长安的人们也没有谁在意。于是公交车就在城市中变得透明。
从南昌的公交车上向外看,一切都是陌生的。游学汴京的张择端,那时也还年轻,相貌也是清瘦的,在马车上,他的目光跟着春天的一缕缕阳光投向汴河边的杨柳,投向船上无数贵妇人的脸庞与胸脯,投向城门楼上的一只乳燕……游人如织,市声都被眼前的繁华滤去了,剩下的是一个存在于光色中的世界。《清明上河图》就从那一刻开始起笔,老树,板桥,茅舍,牛车,农人,河道,桥梁,酒旗,店铺,僧侣,官宦。天高地阔的画面慢慢收拢,最终变成了水泄不通的街市。马车上的景色都是颠簸的。从公交车的车窗向外看,雪白的阳光在地面上有些刺眼。我突然感受到大地是一个很美妙也很伟大的东西,一座座房子立在地上,一株株树立在地上,一个个人立在地上。世界之所以是相通的,就因为地一直是同一块地。我坐在车窗旁看着万物稳稳地立在地上。所有的车都是在地上行驶,这条路和那条路并没有多大区别,它们都属于地的一部分,所有的公交车线路都是一趟车。这仿佛是一个秘密,居然那么容易就被一双外来的眼睛发现了。
但这仅仅是我一瞬间的想法,当我坐上不同线路的公交车,它所通向的地方必定是不同的。每趟车都像是一个志趣相异的人,每一段路都像是一种味道有别的人生。在这个城市中,有些人是你永远也遇不到的,虽然大家使用的是同一个空间,身体一律暴露在阳光下,但你们永远不能相见,交错的空间会让彼此隔离于两个时代。但是对于一个还没来得及被一座城市驯服的人而言,却并不受此限制,他的世界的全部就是他自己。那时候,我还没有固定工作,这里和那里都一样,这种生活状态就像是还并不稳定的地壳。公交车正好让我看到了不同路上的风景。我看到了分布在这座城市中的江河、湖泊,城市周围广袤的原野以及这原野上生长起来的四季,还有各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如此乱窜,我也并不是为了要去哪里,那时候我也没有哪里可去,陌生地,没有亲人和朋友。只是喜欢寻找陌生的感觉,用一场场虚拟的远行来满足一下心中“无穷游”的梦想。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人来说,生命中有太多的正经事要做。这样无聊荒唐的举措无非是白白地浪费光阴,但是我却十分享受光阴被浪费的滋味。那时除了大把的光阴,手上还有什么呢?在我看来,公交车就像是一个风筝,它既可以把我带出去,又可以把我安全地带回来。公交车一直往东,会把我带向大地深处,大地上有华美的词语,有肥沃的文章。心里的天高云淡一旦和自然对应起来,公交车也成了空中的一支羽毛。公交车一直往西,会把人带向幽邃的山林,春山如图画,一声声鸟鸣,摘来王维和孟浩然的诗句。通过公交车,我学会了观看,无论是高深的学问还是长情的生活最初都是从看开始。在公交车上看城市就像看一幅流动的画。你在画外,你是这幅画最初的观众,图像稍纵即逝,下一个路口又捧出新的一幅……
二十多岁的我试图把一切都装进眼睛里。我爬到高高的楼上,目光向下,走进废弃的厂房,目光向外,通过老房子的天窗,目光向上。我的目光是春天的河流,是夏天的繁星,是草原上的骏马,无拘无束。我设法从不同的角度打量面前的这座城市。我想到初入长安的李白,他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四十二个春天。此前的李白,是属于山水的李白,是桃红的李白,是大雪的李白,是床前明月光的李白。而此时的李白将属于这座城市,他是贵妃头顶的白玉,是宫女腰上的白裙,是酒店门前的一扇白墙。在投奔张丞相无着落的日子里,李白肯定也曾骑着马在长安的街上闲逛……
南昌的街道看起来都是新的,和它深厚的底蕴一点都不相匹配,唯独路名老出了厚厚的包浆。建筑和街道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中改造成时代需要的样子,马已经匿迹了,马车也已经退场了,古老的建筑都回归成泥土。路名是这个城市唯一的灵魂,民德路、象山路、渊明北路、阳明路。路是没有声音的,它是真正的隐者,大隐隐于市。它可能被修过了一千次,但是它始终都在那里。一辆公交车缓缓地行驶过来,车到站了。公交车说出了路的名字,这是一百年前的路的名字,被一个十分现代的声音说出来,像一个人的乳名在人群中被说出来。公交车把自己坚硬的身体深深地嵌入这座城市,作为一个移动的公共空间,它每天都只是负责把一些人从这里带向那里。老人孩子女人和醉汉,他们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成为彼此眼中的路人。路人是没有身份的,就像落在地上的树叶和花瓣,并没有谁说出它们各自的名字。公交车也从来不会记住任何一张面孔,它甚至并不清楚要把作为个体的人带向哪里,它只是默默地走着,到一个站台然后就停下来。只有作为个体的人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去菜市场,去理发店,去酒店,去和一个陌生人见面……
深夜,我乘夜班车从单位回到住所。夜色中的公交车是饥饿的,车厢里乘客寥落。灯熄灭了,巨大而深沉的困倦把人拉入幽深的海底,鱼和珊瑚已经睡去。年轻时,梦会带着人飞,就像年轻的张择端,汴京是他的天空,《清明上河图》是一只巨鸟,他坐在鸟的翅膀上,从天的这边飞到那边。在夜车上,突然睁开双眼,发现周围是漆黑的。唯有身体那么透亮,发出那么璀璨的光。
那段时间,公交车像一根隐身的绳子,连接起单位与住所。我在两者之间享用昼与夜带来的快乐,享用喧嚣与孤独浸泡的浪漫感觉,享用简单生活中的丰富皱褶。新公园路口和八一桥两个站台,正如世界的两端,两端之间,构成我生活的外部。我不再像往常一样,喜欢瞎转悠,也不再贪念于观看。我迷恋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我对于公交车失去以往的热情,不再奢望通过它去绘制所谓的城市长卷。我有了另一项爱好,读和写——在这个更加开阔的空间中,我一边奔跑一边张望,隐匿的原野似乎就合在一卷书中。在无光的内部,有无数条春天的河流撕开田野,撕开隐藏的秘密。公交车在这座城市的道路上一如往日地行驶,人们在固定的轨道上一如既往地生活,一个无关的乘客并不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任何影响。公交车经过一家家面包店或者咖啡馆门口,从东湖或者南湖经过,从赣江的任意一座桥上经过,从一个放荡不羁或者温文尔雅的人面前经过。公交车经过时吞吐掉一些人,那些人实现了从此处到彼处的愿望。生活也许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愿望构成,人们每天醒来,想到一天中需要完成的事,然后一件一件地通过努力慢慢实现,这是温暖而有序的人生。公交车在里面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有好几年,我的生活就建立在公交车的基础上。它和我每天喝的水,吃的米饭,睡的床,穿的衣服,还有说的话一样,是生活的基础。在这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有大部分人和我一样,生活中离不开公交车。他们在愿望的实现中离不开公交车。然而,我最终还是离开了。
某年秋天,出版社搬到了江对岸,我也从城市的东边迁徙到西边。赣江穿城而过,我常常习惯性地一个人站在岸边,静静看着白茫茫的江水,遥望对岸的老城。这是永远的赣江,我每回在看着江水时,就觉得这古老的江城,它的童年青年壮年都装在我的眼睛里了,江水的记忆远远超出人类的记忆,它记住了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就像公交车记着所有与它有过接触的乘客,时间隔离的东西太多了,比如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和李白、张择端坐在一起把酒言欢。永远也不能把脚伸到时间之河的另一段去,这是人在时间中的局限。即使同一时空中陌生的个体,他们之间也是相互遮蔽的,个人的经验与记忆都很有限,但是对一辆公交车而言,它接触的可能是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
有一回,公交车把我带到了城郊的青云谱,那儿正在举办一场八大山人的真迹展,那是终点站。最后剩余的七八个人走出车厢,大家互看一眼,都是陌生人,然后就朝着青云谱的大门大步走去。这是一个偏僻而又缺少人气的地方,放在古代就更是偏僻了,水塘和稻田连成一片,天光云影,几株形状各异的树站在田埂上。遗民朱耷就在这里经营着他的剩水残山。公交车转眼就消失了,刚才的乘客立马就成了看展的观众,在某一张画前,大家彼此又遇着了。依然是互看一眼,就分散了。等到看画的眼睛都有些倦了,身子也累了,那些大饱了眼福的观众又站在景区外的站台上翘首以盼着。等公交车再一次出现,车门又一次开了。乘客们走进车厢,陌生人互相看一眼,都埋头玩起了手机。也许,这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陌生人,对于八大山人,他们都有着自己要说的话。可是,在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中,人们最终被与生俱来的谨慎克制了。公交车作为公共空间,在人们看来,它天然具备了某种危险性,这是现代人的认识。近世以来,人类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以想象在遥远的古代,宽阔的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绝望而孤独的内心顿时升起了一种比火焰还要热烈的情绪。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在陌生人面前做出的反应,人们认为,孤独比陌生更可怕。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已与过去大相径庭,世界上最不缺的是人,出门是人,进门是人,低头是人,抬头是人,人来人往,浮生若梦。而公交车亦是虚无的,是照在松林的月光,它是无中的有,虚中的实。一辆公交车在马路上行驶,事实上并不是公交车在行驶,是人在行驶,人们乘坐公交车去往别处。公交车所到之地,就是人所到之地,一些人看见另一些人,他们彼此都是陌生人。人们每天都活在这庞大的陌生中,天空是陌生的,大地是陌生的,周围的环境都是陌生的。公交车就是一万次地把人带到陌生中去,在无数的陌生中寻找着另一个自己。
单位搬迁到赣江西侧,新的住所与单位咫尺之隔,我觉得这一段路用双腿就已经够了。我喜欢用脚去敲击大地,倾听大地在心里的回声。那声音是几万年前发出的,那么真切。那些密集的,交错的脚步声中必定也有另一个自己。可是,凤箫声动,玉屏光转,在层层叠叠的笑语和暗香中,那个人又在哪儿呢?陌生的浪总是把人拍得远远的,你虽然能够真实地感受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应该就在不远之处,但是你看不见。这是你一直处在寂寞与怅然情绪中的最主要的原因。后来,单位附近新盖起了大片楼房,金属和玻璃的反光无端地射进你的眸子。中饭吃过了,你在楼下漫步,大脑有时候突然一闪,想到长安的众诗人们。他们开怀痛饮,马就拴在旁边的一株株杨树下。我一直怀疑自己活在双重时空中,古代和现代经常会因为大脑发生了切换的故障而让我深陷恍惚,此岸和彼岸一时间变得模糊起来。比如,大雨中缓慢而来的公交车,在形貌上,它多么像王勃来南昌和阎公见面时乘坐的那一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