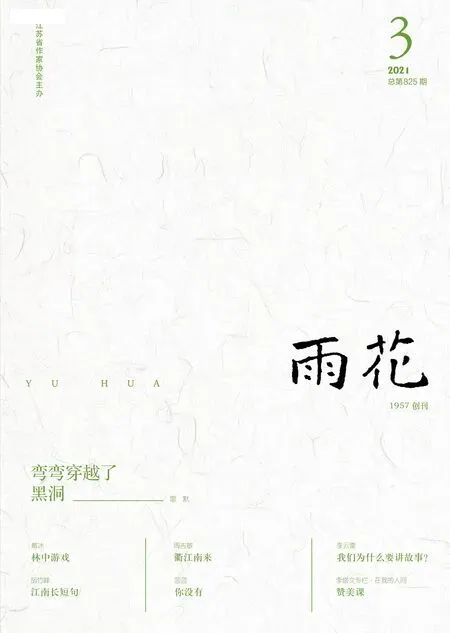衢江南来
一
庚子年江南入秋后的第一场连绵的雨,给衢州这座千年古城添了一抹沧桑的况味。城中,入眼皆是粉墙黛瓦,马头墙一叠又一叠,似未着色的素白卷轴,一幅一幅张挂下来,又恍若是一匹匹白马在飘忽的雨雾中临风而立。马头墙遍地的衢州,有一种古老的灵性。
衢州的徽派风古来有之。古代徽州长期处于浙江西道或江南省的范围内,而浙西又与徽州紧紧相连。明清时期,徽商顺着新安江进入浙江经商,发家后,就在浙江安顿下来,把家乡的房子复制在异乡的土地上。
巧的是,宿地的对面就是徽州会馆的旧址。风雨中,这座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徽州会馆在繁华的县学街上给人独立寒秋的意绪。会馆由在衢的徽商捐资修建,为经商地的徽州坐商与途经的徽州行商服务,也为外出的徽州人提供食宿和资助。徽州会馆是徽商在异乡另一种意义上的家,是徽商文化的一个符号。
随着朱红的大门“吱嘎”一声,我一脚踩进了另一个时空。徽派建筑的朱窗花棂,不用细加描述。会馆有三进两个天井,建有一个戏台。主大厅是一座重檐歇山顶建筑,屋脊正面的“国泰民安” 和背面的“风调雨顺”已斑驳,但在黛青的瓦色中,依然有一种清晰的温度。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时间如流沙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嘶嘶”穿过的声响。
“江南春”——脑海里闪现出这个人名。在哪儿见过呢?哦!是在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撰写的《徽州与衡州:江南城乡的片段记忆》学术论文中。此文对江南春的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论述。“随笔”记录了衢州徽州会馆以及在衢徽商开展的活动。我无意中看过,想不到今天有此际会。
江南春(1788—约1856),自称江子,是徽州府婺源县晓川(今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晓起村)人,出身于婺源木商家庭。此人是个生员,擅长篆刻绘画,医术高明,而且著述颇丰,热衷族内公益事业。曾游历杭州、苏州、江宁、饶州、广州等都会,寓居衢州数年,曾住在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从事木材生意。
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夏天,江南春就住在徽州会馆,歙人王祖,见他一人孤寂,就赠送了数本《聊斋志异》给他。江南春读后感叹:“有异事还须异笔,模蛇神牛鬼,岂虚无君,真戡破人情者,在世山精与野狐之句,喜其叙事详明,笔亦大雅不群,然其事之有无不究也。”有趣的是,江南春嘴上说“不究”,可对《聊斋志异》中提及的事情,还是忍不住作了求证。据说《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颇有“聊斋”之风。
江南春在衢州还参与了徽州会馆“华园冈义冢”的建设始末。道光七年(1827),歙人汪某在衢州城西门外三里的华园冈买了几亩地,打算用来作先人的墓地,后来捐给了徽州会馆。于是知事者商议,谋为义冢,承继古人免尸骸暴露之德行。在衢州的徽商踊跃资助,建厝,停贮客棺,可以祭扫;又建新福庵,供奉地藏王菩萨,中元节后做法事超度死者。后来年久失修,厝屋崩塌,庵堂倾斜。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丙午汪乐山翁毅然集众人谋,于毗连山径之下,续置税若干亩”。这位汪乐山翁是婺源鸿溪人,江南春的外叔祖,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对义冢进行扩充,衢州一带的徽州典商、盐商以及其他徽商积极响应,义冢的建设由此完成。华园冈义冢建成后,江南春受托题额“畅叙幽情”,并为之撰联,曰:“永夕永朝故土人情联太末,好山好水异乡风景胜新安。”此事也收录于“随笔”。
从江南春的“随笔”中得知,徽州会馆的中堂供奉朱熹,左边供奉周宣灵王,右边供奉财神。朱熹出自徽州婺源,为新安理学的鼻祖之一。徽州会馆祀奉徽国文公朱熹,是徽商以儒商自许的标志。供奉财神,是徽商会馆作为商人会馆的特征,而中堂之左的周宣灵王,则是新安江至钱塘江流域最受崇拜的神祇。每逢九月十三日周王的圣诞,要将供奉朱熹的供品,先奉献给周宣灵王;将在会馆演的戏,要先在周宣灵王庙中上演。徽商带着徽州的人文精神行天下,造就了明清徽州商帮的传奇。
我二十多年前去过江南春的家乡晓起村,那里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古朴而又典雅。想着那山那水那人,此刻汇聚于眼前,心上不由也长出一棵花树来。只有心存脉脉温情的人,才会取“江南春”之名。写到此处,江南春的形象也越发清晰了。江南春有才,有情,也有义,亦商亦儒,实不负如此美好的名号。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明清流传于徽州的一句俗语。最初的时候,那些徽商背井离乡东奔西走南来北往,他们走在离家路上或归来途中,或大富大贵,或小商小贩,经历不一样的人生,却感受同样的人生颠簸。
恍惚间,耳边传来一阵锣鼓的喧闹声,唱的是徽戏《单刀会》:“又听得曹营内,大小儿郎闹嚷嚷,我也曾过五关斩六将……”徽剧流水般的曲调里,皖南的风景隐隐约约,一个身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着拍子,嘴巴蠕蠕而动。是江南春吗?
步出会馆,对面就是繁华的街市。衢州街上一定也有徽州菜馆。想起前几日在温州,友人带我去一家开在南站的“徽商菜馆”吃徽州菜。大堂上已坐了三大桌,有光着膀子的,有撸起袖子的,他们高谈阔论,江湖气弥漫。友人说,堂上坐着的大都是在温经商和务工的徽人,从口音就听得出来。我们点了臭鳜鱼、猪血肥肠、拌凉皮、毛豆腐,这些在东海一隅烧出来的一道一道徽菜,是徽人行走天下的人生滋味。
二
都说“不识水亭门,枉为衢州人”。沿着徽州会馆所在的县学街往西,经过两个十字路口,就是水亭门了。迎面而来的是街口左侧一座民居白墙上的一行黑字——“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从清代的徽州会馆到这个展馆不过百余米距离,可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却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越接近展馆,心头就越发紧,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举步沉重。
展馆的前身是衢州市民黄廖氏的故居——罗汉井五号。此地是侵华日军在我国首次以空中投掷的方式实施大规模无差别的鼠疫细菌战的首个细菌投放点,第一批患者中的黄廖氏就在自家这座屋子里死去。
一切都是黑白的,这黑是暗无天日的黑,这白是失血过多的灰白。这些黑白的团块,在我面前幻化成了日本“731”部队派出的播撒细菌的飞机和飞行员、培养细菌的生物盒、细菌实验室、活体解剖、活体实验……这一切好像离我很远,却依然让我毛骨悚然。这种感觉就像一个烙印,表面的伤疤看似好了,一旦触及还是疼痛。这种疼痛沿着神经到达每一个毛孔。
雨,“滴答”,“滴答”,也是时间的声音,也是生命消逝的声音。给我们作讲解的是衢州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吴建平。这位白发苍苍的讲解员低沉有力的声音,穿透时间的墙,把凝固的图片和文字还原成历史的现场。
1940年10月4日上午九时许,一架日本军用飞机从罗汉井五号的天井上空掠过,而后沿着城西罗汉井、柴家巷、水亭街、美俗坊一带,投下大量带有鼠疫细菌的麦粒、小米、棉花、跳蚤、传单等物品。
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见过雪花和雨从天空飘落,当他们看到这些“物品”从天空中伴随着飞机的轰鸣声洒落时,其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附在麦粒、小米、棉花、跳蚤上的鼠疫细菌悄悄侵入人们的肉体。一个月后,露出了魔鬼的真面目。11月12日、13日,柴家巷的居民吴士英、郑冬第,以及罗汉井五号的居民黄廖氏相继发病,头痛、高烧、恶寒、呕吐、出血、腋下淋巴结肿痛,随后于15、16、17日死亡。
在此后的时间里,伴随着侵华日军的长期轰炸以及两次攻陷衢州城,日军在衢州地区先后发动了包括鼠疫、伤寒、炭疽、疟疾等在内的多项细菌战。中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先后在全国二十个省市区发动了三十六次大规模、大区域、大剂量的细菌战,衢州都是其中的主战场之一。战后,衢州地区流行性疾病爆发,累计发病人数达三十余万人,死亡近五万人,成为遭受日军细菌战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黑白照片里藏着的镊子放入铝制卫生盒的声音,黄寥氏生命最后时刻痛苦的呼吸声,此刻都在这座展馆里响起。
步出展厅到回廊上,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雨落在天井里,溅起一朵朵水花。这是一座典型的浙西徽派建筑,坐北朝南,四合院,二层楼,楼层四周设廊,廊外设挑檐。挑檐四周艺术构件雕刻精细,用料上乘。可想而知,从前住在这里的人,生活该是多么和美。
回廊对面的展厅,展出的内容是“抚平烂脚之殇”。不是黑白照片,而是一个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拖着一条或二条像烂树桩一样的腿。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远房亲戚,是我们朋友的爷爷奶奶。似乎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周文清,江山市凤林镇达坝游村人,1942年8月开始烂脚,因救治烂脚,家中一贫如洗;
徐生雨,衢江区廿里镇六都杨村人,1942年6月开始烂脚,2003年9月因全身感染,生命垂危,被迫截肢;
许家燮,衢江区樟潭镇下头村人,1942年6月因感染细菌全身皮肤溃烂;
陈春花,衢江区大洲镇仓洲村人,1942年9月开始烂脚;
……
他们的腿,血的红,肉的红,坏死肉的黑,痂痕的黑,交织在一起,有些老人的脚掌厚达十多厘米,已没有了脚的形状。这些风烛残年的烂脚病人都说:“自从日本鬼子来了,脚就开始烂。”
这些“烂脚老人”顽强地活着,让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所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
烂脚病是炭疽菌所致,一直无特效药,好了又烂,创口无法愈合。一些人受不了折磨就自杀,一些家庭因病返贫,一些人无奈截肢。2014年,我国医学界突破了“烂脚”创面愈合的难题。这一刻,“烂脚老人”已等了六十年之久。
此时突然想起,大概五六年前,我所居住的小区里有一位收废品的老人,七十多岁的样子,两条下肢溃烂,脓血淋漓,脚肿得连鞋子也穿不进去。我经常会看见他坐在楼下的花坛边休息。老人脸色蜡黄,苍蝇在他的烂腿边飞舞,他也不赶,木木地有气无力地坐着。有一次,我招呼他上楼,把囤积的纸板箱送给他。他慢慢地爬上楼,把纸板箱从四楼扔到楼下。现在猜测,这位老人极有可能是丽水、金华、衢州一带的“烂脚病”患者。想到老人家六十多年来日日夜夜忍受的痛苦,我的心都沉到深渊里去了。老人应该回家了吧?应该得到救治了吧?我后悔当时没有整理好纸板箱送到楼下去,后悔没问老人的姓名和籍贯,后悔自己的无知。
八十年前的那个秋日,洒落在这座民居天井里的可不是雨。今天连绵不断的雨仿佛是为了祭奠那段历史。吴建平介绍说,创建“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这个展馆的发起者之一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的首任会长杨大方。
杨大方是日军细菌战的亲历者。1940年,杨大方还只是个8 岁小男孩,父亲在衢州城里修钟表,因为舍不得丢弃生意,没有逃亡。次年3月,父亲和逃到乡下的叔叔都因染上鼠疫去世。杨大方把国恨家仇刻进了骨子里。
杨大方成年后报名参军,成为新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曾于1951年国庆阅兵时驾驶轰炸机飞越北京天安门城楼,随后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回到家乡衢州。
1996年,细菌战调查团来到衢州,杨大方听闻后随即报名参加了调查团。此后,杨大方开启了十年诉讼之路。在长达十年的诉讼中,他一共去了四次日本。“我们起诉的目的并不是想获得多少赔款,是想让日本政府能够直面历史,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真相。尊重历史,以史为鉴!”这是杨大方面对媒体说的一段话。
建一座“衢州细菌战展览馆”,是杨大方实践上面这一段话的又一次行动,他把地址选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罗汉井五号。2005年清明节,由杨大方和原衢州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吴世根共同发起创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正式开馆。这座面积仅三百余平方米的简陋的纪念馆于2014年9月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名录。
吴建平是吴世根的儿子,是杨大方看中的接棒人。
2014年10月4日,八十三岁的杨大方把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会长之位交给五十二岁的吴建平。
2017年2月10日,杨大方突发脑溢血去世。
吴建平现在还是浙江省救治“烂脚老人”的协调人。2015年9月,他开始对接指定医院——浙江衢化医院,协助院长张元海的烧伤科团队,承担起救治“烂脚老人”的使命。至今己收治全省八十七位“烂脚老人”,除七位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上手术台之外,其余八十位经过手术,全部治愈。六年来的操持奔波,让吴建平的一头黑发变成了白发。
“救治‘烂脚老人’是对衢州细菌战受害者最好的纪念,这也是杨老的心愿。”吴建平的声音低沉有力,这种底气来自这片饱受灾难的土地深处,以及刻骨铭心的痛。这种苦难和痛是另一种土壤,是精神之树成长的沃土。
雨一直下着,落在“细菌战死难民众纪念碑”上,落在“衢州细菌战死难者部分名录墙”上。雨水流淌过每个死难者的名字,它们从黑色的大理石中浮现出来,清晰可见。
三
撑着伞走在罗汉井巷子里,人也似一滴雨,落在哪儿都是妥帖的。浙西的粉墙黛瓦不似江南腹地的青砖黛瓦,那么精致妩媚,这是一大片的白与一抹青,似宣纸上落了个“一”字。这种空灵而极简的美,是我喜欢的。
就是有点小装饰,也是用水墨勾出来的花草果实和飞鸟走兽,一般画在门框之上挑檐之下的那一小片白墙或马头墙上,素素朴朴的,让人亲近,一看就明了。有一户人家的后门,做了挑檐以阻挡风雨。门框上面的那一小块粉墙上就用水墨写了“吉星高照”四字,字的上面又画了四盘花果对应——“吉”对橘子,“星”对石榴,“高”对佛手,“照”对桃子。木头门也是落了锁的,是虎头环勾着一把铁锁,留了一条门缝。
在雨巷里,我没有遇见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姑娘,而是遇见了一位妇人,她左手拎着一篮子菜,右手牵着孩子,走进一扇门里去了。这朴素日子里的美好,让我呆立了好几分钟。
透过那道圆拱门,就看见了大街。街上店铺林立,人迹纷沓,那就是水亭街了。
街的东头,耸立着一座塔,就是著名的天王塔了。老衢州人说,先有天王塔,后有衢州城。天王塔为六面七级楼阁式砖塔,建于梁朝天监年间(502—519)。那时的衢州城仅限于府山一带。明弘治《衢州府志》记载:“今龟峰之城(峥嵘山东相连者曰龟峰)亦不知其初建,州人相传,先止土墙而已。”可以想象当时衢州的城郭还是夯土而成的雉墙垛口,隐在莽苍的山峦中。不远处,衢江南来,绕城东去,在城郊旷野中,天王塔高耸入云。塔立好了,人心就定了,一地的生气由此而旺。衢州有民谣唱:“不见天王塔,眼泪滴滴答。”千百年来,天王塔早已成为衢州城的标志,见到塔就快到家了。
水亭街上随处可寻老衢州的印记。叶振兴纸号旧址,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占地约一百五十平方米,前后三间搭两厢二层建筑,呈“回”字形布局。当时叶振兴在上海、杭州也设有纸号,人称“叶半城”。旁边就是仁寿堂药店旧址。店名是取了《论语》中“有仁德而长寿”之意,门墙上的砖雕很精美,“存心济世”四字居中,两边雕的是山水图案。不远处是“王成德医馆”,五个墨绿的字衬着朱红的底,悬在门楣上,爬山虎的叶子沿着木格子门爬上来,中药味隐约可闻。对面“黄师傅捏糖人”的铺子前围了好些个孩子,招牌上就写着“留给童年的美好回忆”。看着孩子们舔着糖人,羡慕之余,不禁感慨童年早已一去不复返。
街尾拐角处有一家叫“邵永丰”的糕饼店。对于地方美食,我总是多看几眼的。这是一家始创于清代的老字号,专门做一种叫麻饼的糕点。麻饼也称胡麻饼,只有二寸左右,小巧得很。史料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麻。胡就是核桃仁,麻就是芝麻。唐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看来这位现实主义诗人不仅诗做得好,麻饼也做得不赖,可以跟京城的“辅兴号”媲美。
据说制作麻饼有上百道工序,大致可分为入饼、上麻、翻麻、入锅四个步骤,其中上麻最有特色。我来得正是时候,做饼师傅正在上麻。竹簟里是脱过皮的白芝麻仁,三十只饼胚随意摆放在上面。师傅把竹簟一圈一圈地旋转,饼胚竟然按着四、五、六,六、五、四的规律排列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等边的六角形。正面上麻后,师傅将手中的竹簟一扬,饼胚整体腾空而起后,又稳稳地落回到竹簟中。一看,个个已在空中翻了个身。然后上另一面的芝麻。上麻的过程,好看是好看,但也最考验功夫,瞬间的技巧,靠的是师傅多年的经验。
衢州人的生活离不开麻饼,从出生到年老,麻饼都会派上用场。孩子满月、百日、周岁,叫添丁饼,结婚叫喜饼,做寿叫寿饼。一饼多用,是人生礼俗中不能少的吉祥小糕点。
麻饼的内馅由黑芝麻、核桃仁、瓜果仁等配置而成,有咸味的,也有甜味的,尝一下,饼皮酥脆,内馅绵香。我各选了一味,当茶点正好。
临近中午,看到巷子口有一家“古铺良食”,还标注着“衢州非物质文化小吃博物馆”,正中下怀,心中产生了“一店吃遍衢州”的错觉。
在临窗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点了衢州双头、乌溪江鱼头、清朝馄饨、鸡子粿、廿八都豆腐。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余下的只能待下回来品尝了。
衢州的清朝馄饨也叫“纸皮馄饨”,不像温州的“长人馄饨”像一朵云一样浮在大碗汤中,而是小而收敛,像小朵的花,刚好用来暖暖胃,打个底。衢州“双头”是兔头和鸭头,是卤制品,经过了反复熬煮,浓汁都进去了,吃的是在骨头边细细挑肉的乐趣。乌溪江鱼头,是包头鱼加豆腐炖汤,豆腐炖老了,韧韧的,而鱼头却很鲜嫩,这就是火候。著名的“衢州三头” 我算是都尝到了。
鸡子馃,我在兰溪就听说了。因为跟李渔有关,不觉“食心”大动。读《闲情偶寄》“饮馔部”可知李大戏剧家是“一生绝三物不食”,这三物就是“葱、蒜、韭”。其文末说:“予待三物有差。蒜则永禁弗食;葱虽弗食,然亦听作调和;韭则禁其终而不禁其始,芽之始发,非特不臭,且具清香,是其孩提之心之未变也。”李渔为啥说葱可以“作调和”呢?据传,李渔一日偶得风寒,妾用小葱和鸡蛋做馃,渔食毕开胃,风寒尽散,对葱的看法遂有所改观。尔后,鸡蛋馃得以流传。
我适才进门的时候就仔细看了店堂内做鸡蛋馃的过程。先擀皮,在皮上摊上一层肉馅,再包上青翠的小葱、豆腐丁等馅料,收口之处尤见功夫,像个小包袱,然后将馃子稍稍压扁放入油锅煎一会儿。接着敲碎鸡蛋,倒入碗中,用筷子轻轻地在馃子上开一个小洞,将搅拌好的鸡蛋顺着筷子倒入馃内,一滴不漏。油煎片刻,金黄喷香的鸡蛋馃就出锅了。趁热吃,皮又薄又脆,内馅冒出的热气带着香气扑鼻而来,入口香嫩鲜滑。这兰溪的食物,现在都成了浙西全域的美食了。
江山廿八都豆腐也是要尝一尝的。豆腐是随处可见的家常菜,但一地有一地的特色,最见一个地方的山水气。廿八都豆腐用陶锅端上来,放在泥炉上炖。这旧日仙霞古道上挑夫的下饭菜,味道还真是不一样,除了嫩,豆气浓,还筋道,不易碎。那稍稍的辣味让味蕾充分绽放,一碗呼噜噜地下来,不觉微汗。热气腾腾中,浙闽崇山峻岭间的廿八都古镇似乎就在眼前。
桌上这一样一样的菜式,皆是人家日常的吃食。一方水土一方人,还有一方食物。
雨还在下着,隔窗看雨吧。同样的雨,在浙西看,跟在浙东、浙南或其他地方看,是不一样的。浙西的雨,落在粉墙黛瓦上,有着日常烟火的和美。这是千百年来风雨磨砺出来的一份安定和沉着。
四
下楼,去看水亭门。
茫茫天雨中,这座老城门稳稳地坐落着,飞檐翘角高高地接着天,雍容中带着飘逸。
斑斑驳驳的老城墙,投射时光,也映射你我。哪一块是唐代的?哪一块是宋代的?哪一块又是明代的呢?我们都还太年轻了,稚嫩的眼光无法看进城墙的深处。
墙基是条石错缝平砌,一共有八层,一米多高。石匠的铁锤还在石头里面“叮叮”响着。上面是砖墙,也是错缝平砌,手指触摸过去是凉的,心里却感觉到烫,是窑火的余温未退去。拱劵大概有五米高,小青砖横砌,像一道青虹,踮起脚,再举起伞也够不着。仰望城楼,雨经过城楼的第一道屋檐、第二道屋檐,经过城垛,擦着城墙“唰唰唰”地落下来,还夹带着风的声音。雨声风声中,老城墙生出一层层的老茧,这是时光的包浆。此刻,雨在我眼中不断放大,似片片雪花飞舞下来,一时竟忘了打伞。
登上城楼,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浩荡的江水,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衢江。江坪上在古代建有卷雪亭,江水从亭下流过。这也是“水亭门”之名的由来。想着衢江水卷着如雪的浪花拥着亭子,那是怎样的景致呀。
徐霞客一定是见过卷雪亭的人。明崇祯九年(1636)九月十九日,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游,主要走水路,在衢州境内经停四日。十月十五日,他一叶轻舟溯游衢江,只见“两岸橘绿枫丹,令人应接不暇”,“橘奴千树,筐筐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他记下了衢江两岸“明艳”的风色。
衢江还是一条黄金水路。作为浙闽赣皖四省重要的商贸口岸,旧日水上千帆竞渡,码头商贾如流,水亭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嗣衍圣公孔端友率支族一路风尘仆仆,护驾南渡,最终定居于宋高宗钦赐的安家之处——衢州。故衢州称为“东南阙里、南孔圣地”。通往码头的城楼,也因水路通向远方,称为航远门,也称朝京门。
当地民间还说:“水亭门,应作水停门,是水只能停在城门外的意思。”民谣也唱:“水亭街,街停水,水亭街上涨大水。”衢州史上水患之重可见一斑。
志书上,衢州水灾屡见不鲜——宋乾道四年(1168)七月,衢州发大水,毁城三百丈,坏禾稼,漂民庐。宋嘉定三年(1210)五月,衢州大水,城圮五分之一,民饥荒……
时局动荡,水运衰退,繁华落幕。1932年,创于清道光年间的衢州当地戏班“叶文锦班”,将全部行头沉没在水亭门外的江中后解散。此事对于一个时代而言,亦别具一番况味。
水亭街只有短短的一百五十五米,东头镇着天王塔,西头守着水亭门,终究抵不住自然的伟力,扛不起朝代的兴衰。
“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衢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衢州军事重镇的地位。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二千四百多年间,这里曾发生过数以百计的战争。“东南有事,此其必争之地。”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衢州城破是侵华日军攻打衢州城。
此时,已是下午三时,风大雨大,雨点像箭镞一样落在江面上。
1942年6月1日,日军攻城,衢州风雨交加,江水暴涨。
《柯城区志》(2005年版,方志出版社出版)“大事记”中“民国31年(1942)”条下记载:“此年5月,连续大雨。6月初,衢江水位67.96 米,超过危险水位2.46 米。大水入城,各地堤堰、堤防冲毁十之八九。时日军侵衢,伤亡人口无法统计。”
因衢江、乌溪江水暴涨,日军在衢州城东、西、北三个方向受阻,于是集中兵力在南面攻城,并使用了毒气弹。6月7日,日军占领衢州城。
我们去大南门。经上营街、天后巷,穿过衣锦坊,沿着护城河而行,再经过和丰门和光远桥……这些残垣断壁,长满野草藤蔓兀立在都市的街头,让人恍惚不知今昔。
到达大南门时,风大雨急。大南门又名礼贤门,在雨中如青铜如黑炭,正大里见沧桑。站在城墙上,我想起八月间随友人去看望原籍瑞安县平阳坑镇吴界山村的百岁抗战老兵吴声远的场景。这位百岁老人正是衢州会战的亲历者。
此时,老人断断续续的声音在风雨中再次响起:
我出生于1921年8月3日,没读过书,家中五兄弟,我最小。二十岁那年11月的一天,我到糖厂绞糖时,被保长吴洪增抓了壮丁。我被编入十六师一营三连。当时,我们使用的是后膛枪,可装五颗子弹。每人另发四颗手榴弹。不久,我们随部队开到衢州。1942年春夏之交,我们与日寇在衢州府激战多日。当时,我们在城里四周挖了洞,用树枝杂草伪装隐蔽,士兵都埋伏在洞里,把枪口伸出,与进犯的日寇作战。日寇有飞机在空中盘旋,常常是三架一齐来,俯冲扫射,我们伏在洞中,戴着掩护草帽,与日寇对峙。我们武器落后,人员伤亡惨重,全师仅剩几十人生还。醒来时,四周都是战友的尸体,我从死尸中爬出来……
城墙的背后就是衢州古城,粉墙黛瓦尽收眼底。城墙下,衣锦坊,百岁坊,北坊门街,车如流,人如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