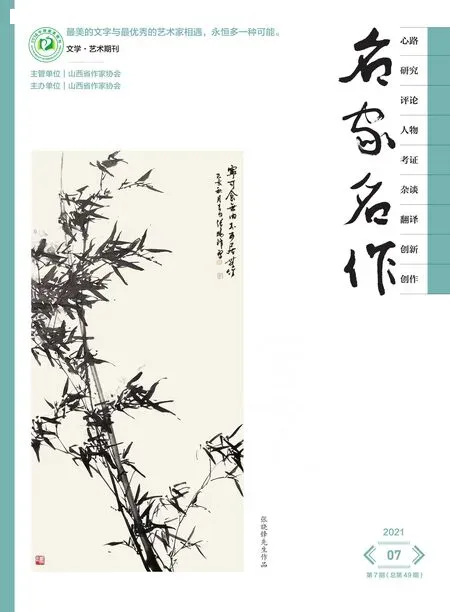苏轼词中的文人风雅
马雪莲
一、风雅概述
“风雅”一词源自《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地方风土歌谣;《颂》是宗庙祭祀之诗歌;《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后世常用“风雅”一词作为高贵典雅的指代。同时,“风雅”一词又为多义词,谓文雅、端庄或高雅。晋陆机《辩亡论上》有言:“风雅则诸葛瑾 、 张承、步骘,以名声光国。”《明史·文苑传四·袁宏道》有言:“(宏道)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本文取其“文雅”之意,以此为着眼点,探析苏轼词中的风雅行为,分析其超然达观思想形成的原因。在深入认识苏轼的同时,也可从中窥见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整体风貌。
宋代文人的风雅生活即是一部美学的辑录。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经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宋人的美学简单清雅,与唐朝的张扬外放不同,与明清的繁华富贵相异,是一种文人的儒雅和风流。
二、苏轼词中的风雅生活
本文对苏轼词中的日常生活进行整理归纳,将其分为酒筵饯别、泛舟之乐、山川游历、四季赏景、佳节醉饮、琴香书茶、安家筑园以及其他风雅活动等8类。通过对苏轼风雅生活的研究,探析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期望对苏轼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
(一)酒筵饯别
苏轼词中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酒筵歌席的场景。友人分别时,设酒席相送,“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一斛珠·洛城春晚》)。友人重逢时,设酒席相庆,“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采桑子·润州多景楼欲孙巨源重逢》)。在席上还有歌儿舞女相伴,“皓齿发清歌,春愁入翠蛾。凄音休怨乱,我已先肠断”(《菩萨蛮·歌妓》)。“共看剥葱纤手,舞凝神”(《南歌子·琥珀装腰佩》)。这些歌姬舞女的出场势必会伴有琵琶、竹笛、笙箫等乐器,因此,在酒席上听乐器演奏,也成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日常,“华堂堆烛泪,长笛吹新水。醉客各西东,应思陈孟公”(《菩萨蛮·述古席上》)。不管是乍然离场还是久别重逢,文人们都免不了要痛饮赋诗,因此,写诗成了酒筵歌席的标配。“杯行到手休辞却,这公道难得。曲水池上,小字更书年月。还对茂林修竹,似永和节”(《劝金船·和元素韵自撰腔命名》),文人们在酒席间玩起曲水流觞,宋代文人的聚会,因此变得别具一格,弥漫着独属于文人的浪漫气息。
苏轼不仅参加这种文人之间的雅集,还参加充满市井气息的洗儿宴,他在《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中写道:“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好友李公择喜得一子,大宴亲朋,苏轼在席间调侃好友说,这件事我本没有功劳,却得到犀钱、玉果这样的洗儿钱,实在是受之有愧,此言引得四座皆笑。苏轼幽默诙谐的形象在此可见一斑。
(二)泛舟之乐
苏轼一生两度出仕杭州,他把杭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写了大量的词赞美此地的山川风物。杭州多湖沼,苏轼最爱西湖,他时常泛舟湖上,醉眠十里风荷,“终须放,船儿去,清香深处住,看伊颜色”(《荷华媚·荷花》)。他曾在湖上听见女子弹筝,曲终欲寻,却不见佳人,“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江神子·江景》)。千年之后,人们荡舟西湖,追寻着这位大文豪的足迹,感受他的风流闲雅。他也曾放舟桐庐江上,欣赏两岸的青山、沙洲的鹭鸟,以及水底的青荇,“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行香子·过七里濑》)。他还在西湖以草荐地,饮酒大醉,不记归路,“携壶藉草亦天真。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
(三)山川游历
苏轼一生多次遭贬,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每到一处,就喜欢游历川泽,遍赏美景。他曾在杭州游风水洞,深觉此间风景都是他写诗作词的题材,“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故应为我发新诗。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临江仙·风水洞作》)。他在赏玩美景时,随缘自适,常常在风景绝佳处醉卧于芳草之中,“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醉落魄·述怀》)。他登上超然台看见千家万户被烟雨笼罩着,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望江南·超然台作》)。他游平山堂,见景物依旧,人已逝去,深刻思念恩师欧阳修,“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西江月·平山堂》)。在这些山川中,开阔了苏轼的视野,增添了他的诗情,同时也寄托了他深沉的感慨。他一生喜欢登山临水,也为他的词中加入了自然清新的笔调。
(四)四季赏景
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富有诗情的文人来说,一年四季都是闲不住的,春夏秋冬,四时各有美景,它们在苏轼笔下变得绚丽多姿。春天百花争艳,他总是早早地去探寻春光的身影,“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夏日,他便去赏那肆意绽放的石榴花,“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贺新郎·夏景》)。哪怕偶尔因政务繁忙,辜负芳华,他也能在秋日得到大自然的眷顾。百花凋零的时节,一枝牡丹却独自为他停留,苏轼在雨中置酒,邀友朋共赏,特意写词记之“闻道城西,长廊古寺,甲第名园。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留连”(《雨中花·今岁花时深院》)。冬天,苏轼忙着踏雪寻梅,煮酒烹茶。“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蹋散芳英落酒卮。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他还把对陶渊明的仰慕和怀念之情,倾注在冰姿玉骨的梅花之中,“使君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江神子·黄昏犹是纤纤雨》)。
(五)佳节醉饮
苏轼词中描写过中秋、重阳、端午、寒食、清明、上元等节日,每逢佳节,必定饮酒大醉。他在中秋节起舞徘徊,醉饮高歌,“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念奴娇·中秋》。他在重阳节沐浴簪菊,虽然两鬓霜华,却爱美之心不减,仍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清爽一些,“浅霜侵绿,发少仍新沐。冠直缝,巾横幅。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黄菊”(《千秋岁·湖州赞暂来徐州重阳作》)。他在端午节用兰叶浸水洗澡,用菖花酿酒而饮,“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他在寒食节新火煮茶,饮酒赋诗,劝慰世人珍惜时光,及时行乐,“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他在密州回忆起钱塘上元佳节的繁华热闹,华灯初上,炉香袅袅,人们出街赏灯听曲,“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蝶恋花·密州上元》)。
苏轼一生历经坎坷,随波浮沉,虽然出生在四川眉山,可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都客居他乡。他曾多次在词中表达这种归而不得的无奈,“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归去来兮》)。他常常借酒消愁,梦见自己又回到儿时的家乡,可梦醒之后依然是羁旅他乡的游子,“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他还幻想自己功成名遂之后要回到故乡,到时一定要饮酒高歌,“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和杨元素》),可惜最后病逝于常州,终究是客死他乡。终其一生,辗转漂泊,天涯游宦,故乡便成了苏轼心中永远的遗憾。每到佳节,万家团聚,他这种思乡之情就变得尤为浓烈。因此,苏轼词中的佳节醉饮大多与思念亲友相关,在家家团圆的日子里,他孤身在外,只能以酒来暂时消解这种惆怅。他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洒脱旷达,哪怕心情郁结,也会随即找到消解之法,让自己以蓬勃的姿态重新投入政务和生活之中。
(六)琴香书茶
琴棋书画,诗茶酒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常态,不管是富贵显达,还是穷困潦倒,文人的骨子里依旧保持着这种高雅的生活习惯。苏轼作为一个诗书画皆工的天才文人,他的生活自然是离不开这份文人间的雅致。
苏轼的词中经常提到茶。他把皇帝御赐的茶拿出来招待友人, “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行香子·茶词》)。宋人喜爱斗茶,并把它作为一种高雅的游戏,苏轼也经常在词中提到斗茶的乐趣,“玉粉旋烹茶乳,金齑新捣橙香”(《十拍子·暮秋》)。他和友人外出郊游时,也要带上茶叶,烹一炉清茶,“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看书犯困时,也要煮上一壶新茶静心安神,“闲卧藤床观社柳,子瞻书困点新茶”。茶几乎充斥在苏轼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茶的钟爱。
宋人不仅爱茶,也极爱香。香文化到宋代已至巅峰,宋人熏香极其盛行,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家家户户皆用香。苏轼的词中经常出现香,“雾帐吹笙香袅袅,霜庭按舞月娟娟”(《浣溪沙·赠楚守田待制小鬟》),“蜡烛半笼金翡翠,更阑。绣被焚香独自眠”(《南乡子·集句》)。
苏轼对古琴也情有独钟,他写道:“嗜琴藏琴论琴事,推崇古琴大雅声”,他还收藏了一把唐代的名琴——雷琴,而且琴技也颇高。他在描写古琴的音色时说:“万籁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并且在曲终归去时,还意犹未尽,“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归去无眠,一夜馀音在耳边”(《减字木兰花·琴》)。
苏轼极爱诗书,他曾说,“寻常行处,题诗千首”(《行香子·冬思》),苏轼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留下墨宝,用文字记录生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时常看书以自娱,“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南乡子·自述》)。甚至被贬到海南,他也随身携带陶渊明和韩愈的书籍,以此作为精神食粮。他还渴望在归隐山林时,仍然有书卷和古琴为伴,“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满江红·忧喜相寻》)。
(七)安家筑园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大起大落,但仍旧超然旷达,随遇而安。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把那里当作是自己的家乡,积极修建房舍,开垦农田,以期自给自足。苏轼谪居黄州时,修建了雪堂,得好友马正卿相助,在东坡开垦荒地,俨然成了一个乡野农夫。他不但不觉得辛苦,反而自得其乐,还为这些乡村风景题诗吟咏,认为此处可以媲美陶渊明的斜川之境,“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他从不以官员自居,而是始终和百姓站在一起,“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他还一直有买田归老之意,“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菩萨蛮》),“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浣溪沙·感旧》)。苏轼在离开黄州时,还殷切地嘱托父老乡亲,要时时替他翻晒打鱼的蓑衣,看护好堂前的细柳,好像他随时都会再回来一样。“好在堂前垂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
(八)其他
苏轼生活中的风雅活动还不止上述这几类,他在坎坷曲折的一生中,把生活过得诗意盎然。他曾在汴京怀远驿和弟弟子由对床夜语,到后来仍旧怀念那段一起读书的美好时光。“对床夜语”之典也反复出现在词中,成为兄弟情深的寄托,“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添华发”(《满江红·怀子由作》)。他还曾折梅寄远,表达思念之情,“折花欲寄岭头人,江南日暮云”(《阮郎归·梅词》)。他在泗州雍熙塔下泡温泉,并对自己进行调侃,“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他在钱塘江上观潮,“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瑞鹧鸪·观潮》),他也曾深情地为亡妻植下三万棵短松,寄托哀思,“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他不只有挥洒翰墨的文人风流,也有千骑出猎的武将风范,“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江城子·密州出猎》)。
三、结语
从这些文雅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更加鲜活的东坡先生形象,他乐观旷达、随遇而安,寄情于山河湖海,托意于草木繁花。在跌宕起伏、屡遭贬谪的一生中,把文人的清雅风骨贯穿其间,超然自适。从苏轼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北宋文人的整体风貌。他们在聚散离合时以酒筵歌席为中心,痛饮高歌;在失意彷徨时,寄情于山水草木,醉眠花下;在身居高位时,恣意疏狂,指点江山;在穷困潦倒时,一卷诗书,半盏清茶,携琴隐于乡野。这是文人的浪漫,也是文人的风骨,给当下浮躁社会里的世人带来一抹风雅和诗意,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