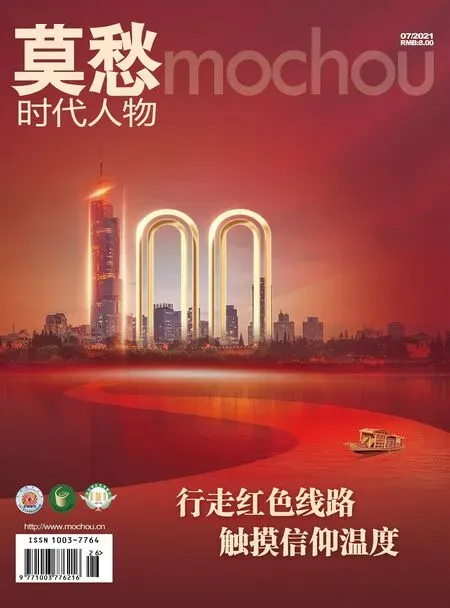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文/乐黛云
抗战初期,我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就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她单身一人,家中却很热闹,常有许多年轻的来访者。母亲不大喜欢她,常在背后指责她走起路来扭得太厉害,有故意卖弄风情之嫌。
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造句和课文之后,给我们讲小说。一本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伯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巅丝姑娘》好得太多,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翻译好在哪里。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还听了《微贱的表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
我们的国文课越上越红火了。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
我连做梦都想扮演四凤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由于演出相当成功,朱老师甚至决定自己来创作一出歌剧。她在课堂上大讲中国京剧如何落后,意大利歌剧如何高超。她终于和贵州农学院一位姓李的讲师合作,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可以称为歌剧的歌剧”。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朱老师家,他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李先生会拉手风琴、会弹钢琴,朱老师构思情节并写歌词。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于是,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每逢李先生过我家门口,母亲总是对父亲悄然一笑。有一次母亲还一直熬到深夜,就为看看李先生究竟回家没有,我也使劲撑着眼皮,但很快就睡着了,到底不知结果如何。
不管怎样,歌剧终于完成,并开始大张旗鼓地排练。朱老师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歌剧中所有的歌,我们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我们年少的记忆。记得演出时,帷幕拉开,就是伯爵登场,他轻快地唱道:“时近黄昏,晚风阵阵,百鸟快归林。荷枪实弹,悄悄静静,沿着山径慢慢行……”他随即开枪,向飞鸟射击。一只被击中的小鸟恰好落在树林深处伯爵夫人的怀里,她于是唱起了凄凉的挽歌:“鸽子呀,你栖息在幽静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飞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些儿阻挡;鸽子呀,你哪知凭空遭祸殃,可怜你竟和我一样,全身战栗,遍体鳞伤,失去自由无力反抗。”正在此时,一位流浪诗人恰好走来,他唱着:“异国里飘零,流亡线上辛酸,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里,痛苦鞭打着我,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讽言。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只能到处飘零。如今,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何处飘零?!”当然,两个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怜,随即坠入情网。
后来,当然是伯爵一枪将诗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杀身亡。
当时,这出“千古悲剧”真使我们心醉神迷!虽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属于漂亮入时的“下江人”,但我们对于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却是十分尽职尽责。记得我当时负责管道具,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我把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和胸罩(当时一般女人不用胸罩)都背着母亲翻了出来。演出当然又是非常成功。露天舞台设在高高的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