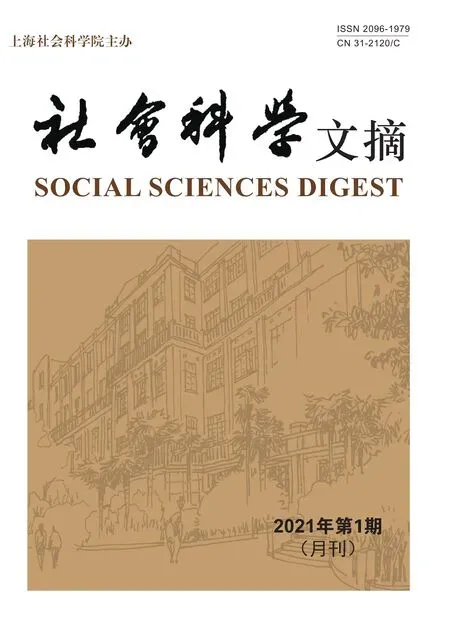作为纪念物的数字移动媒介:德布雷视野下的媒介与遗产传承
中国中小城市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建设和居民的频繁移动,城市遗产保护的议题也随之日渐升温。“遗产热”现象常被解释为新媒介冲击下对地方的应激保护。这种对“遗产热”的解释预设了稳定不变的地方与媒介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变动新世界的对立,将信息的跨地域传播当作媒介的唯一向度。德布雷的媒介学提醒我们留意媒介的时间传承维度,指出媒介在文明传承中的意义。这一审视媒介的新视角和对文明传承的新阐释,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当前城市遗产的另一路径,也提醒学者在文明延续的脉络中重新理解媒介的变革。面对当前智能手机等数字移动媒介日益普及的现实,本文将梳理德布雷对媒介与遗产传承的理解,据此探讨新的媒介状况下遗产传承的变化,并挖掘数字移动媒介在其中的重要意义。
传承文明的媒介
(一)作为媒介的纪念物与城市遗产
在德布雷的媒介学中,媒介是“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是文明发展的前提和文明延续的必要条件,而不只是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再现,或是传统生活的技术优化。这一意义上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之初就早已存在:由骨骼、石头等做成的纪念物是最初的记忆媒介,以其物质象征和抽象符号代替缺席的过去。德布雷强调记忆媒介的物质性,指出物理载体与集体组织在传承中具有与内容符号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组织化的物质载体的中介作用和持续的中介过程,过往的历史及其文化价值才得以固定并持久留存。
本文所讲的城市遗产,便是城市中集合多种历史纪念物的整体。历史建筑凭借建筑实体作为标记工具和储存载体相对持久的特性,在无意中固定城市历史的某些瞬间并将其带到当下。除了建筑上的装饰图案、雕刻文字等抽象符号,建筑材料、建筑样式等也代表着特定时代。这些象征由物理的建筑材料所携带,在时代变迁的痕迹叠加中成为历史纪念物。城市遗产中的节庆仪式或日常习俗等传统活动,同样也在周期性、组织化的反复实践中使某些事件或人物为当前所铭记。可以说,媒介学视野下的历史建筑、习俗仪式等遗产,本身就是文明传承的媒介载体,对遗产的研究便是对记忆媒介的研究、对文明传承的研究。
以历史建筑和传统活动为城市历史的纪念物和记忆媒介,也带来对“地方”的新理解。纪念物以固定或周期反复的土地标记,为其所依附的土地划定特殊意义,构成城市遗产的特殊地方。地方的特殊意义产生于纪念物这一记忆技术及其对集体的延续性集合,而非隔绝于媒介之外的先验存在。媒介作为象征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地方意义的必要构成,而非威胁其稳定安全的洪水猛兽。纪念物作为媒介联系同时代和代际之间的集体关系,而城市遗产的地方意义就存在于这些关系的交织中。由记忆媒介产生的地方并非封闭、稳定的,而一直都处于与外界的开放联系和持续变动之中。
(二)视频圈的即时主义与遗产膨胀
从传承媒介的角度上来看,城市遗产在当前新技术变革中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是信息网络带来的全球化和移动性对稳定封闭本土的冲击,不如说是来自记忆媒介,即文明延续条件的改变。德布雷用“媒介圈”的概念阐述不同主导媒介形成的生态环境:技术革命带来人类社会新的主导媒介,将文明过渡到新的媒介圈,形成新的记忆方式和时代精神。新旧媒介圈之间交错融合,重新组织了社会的不同力量。
从“话语圈”“图文圈”到“视频圈”,人类文明传承的主导媒介从沉重的石头雕刻和反复的神话仪式转向相纸、磁带等。德布雷指出,人们日益面临“传承危机”,并将其归咎于主导媒介的“非物质化”。在以电视等视听媒介主导的视频圈中,轻便的记录载体可以快速广泛散播和复制流通,但也更加脆弱和短寿。信息流通的加速使人们不再主动走向难以移动的石头,在其上雕刻以便记忆。相反,纸张与电子屏幕轻易地将世界实时带到用户面前,载体的移动替代了人的移动,符号信息取代了物质载体的象征性,即时取代了记忆和历史意识。
这种即时主义的时间,是视频圈的时代特征。电视的实时直播以急速的信息套叠消解了碎片事件之间的关系序列和时间深度。一方面,电视是“留住生命的最好仪器”,人们可以利用视频回放,逆转时光流淌的方向。另一方面,信息随时制造事件,也随时代之以新事件,作为“间接实践”、要求延迟与偏移的历史反思不复存在。人们不再花时间记忆,而是被当下的时间所占有。即时可见的图像过度充实,导致以往通过神圣象征物为集体所共同想象、纪念的文化意义,失去了立足之地。
与视频圈的即时主义相对应的,是遗产数量的日益膨胀和人们对遗产的热衷。遗产因记录的便捷而越来越多,同时人们在技术的疾速前进中,又返回对古代文化的热衷,如纪念活动的盛行。德布雷将这种遗产的膨胀与追求归因于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不稳定中对内心精神平衡的保持,而精神平衡的达成依赖于艺术品的“文化遗产效用”:艺术美学被推崇为人类共同信仰的价值观念和联系纽带。对艺术古董、展馆建筑和纪念活动的崇拜和追求,成了集体文化特性的替代黏合剂,人们在艺术品的圣物堆积中进行集体精神疗伤。
然而,这种以艺术品为遗产的复古主义追求,已然渗入了视频圈的时代特征。人们侧重保留了遗产的符号和视觉形式,对包装和衍生品的讲究超过了对遗产本身含义的重视。遗产在体积日益膨胀的同时,其意义也在日渐消沉。人们对遗产的渴望实为时髦的符号消费,遗产从本能记忆变为应用记忆,成为失去背景渊源的粉末。
视频圈下的“遗产热”在延续纪念习惯、追求集体特性的同时,已然改变了遗产的含义。纪念物被认为是可见的、可展示的甚至可被复制流通的物品或商品,其作为传承媒介所中介的历史深度和族群价值退居次位。人们习惯以空间传播的方式来保证文化传承,以消费当下的方式确认集体特性。纪念物作为古老的媒介穿越视频圈,也以视频圈的即时主义和注重视觉展示的新传承观念,延续本土历史和集体特色。
数字移动媒介时代的城市遗产
德布雷的论述并未涉及新近兴起且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数字移动媒介,但其基于传承媒介对遗产的讨论,正为探讨当前更为复杂的媒介圈及城市遗产提供了区别于媒体研究、遗产研究等的新思路,促使我们从遗产传承入手考察数字移动媒介。下文笔者结合当前城市遗产的新状况,梳理数字移动媒介所带来的不同于视频圈的新特征。
(一)纪念物与数字移动媒介:移动设备的地理联系
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的中国,城市遗产几乎已无法与数字移动媒介相隔离。博物馆将藏品进行数字化并在互联网上展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欣赏。数字互动装置被引入历史建筑空间,人们借助线上场景,对城市遗产有了更多维度的身体参与。数字媒介不只将遗产的形态外貌在屏幕上展示,也以其物质设备嵌入用户所在的物理空间,改变人们身处城市遗产时的具身感知,甚至改变遗产的形态,参与建筑和仪式的持续维护和增删修改。
与此同时,城市遗产也影响着数字移动媒介的信息组织和呈现。移动媒介带有地理定位装置,设备所在的地理位置成为其组织逻辑。这种地理逻辑基于特定位置,也涉及该位置上存在的事物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与历史建筑、仪式活动等相关联。手机程序依据用户地理定位周边的历史建筑排布、仪式进程等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增强现实(AR)游戏依据手机摄像头实时“看到”的文物来组织情节。城市遗产作为组织方式影响移动媒介的数字场景,在带入地理逻辑之外也因其象征的时间深度而带入历史的逻辑,改变数字移动媒介的信息架构和用户的操作实践。
作为古老媒介的遗产与新兴数字移动媒介的互动展现出区别于德布雷所述的新形态,现场的互动体验成为到访城市遗产时的重要方面。新旧媒介的相互影响不限于将遗产作为内容的推广包装,或视频圈的符号消费在遗产热潮上的投射,而是两者实体化的相互嵌入,作为各自的物质构成,也作为相互组织的程序、逻辑。新旧媒介在物质设备、组织机构等不同层面的持续变动,共同构成人们动态的时空感知。希尔瓦指出,当数字移动媒介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人们就处于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持续接合的“混合空间”。在遗产的语境中,这种空间正由历史建筑与数字移动媒介等的互动所形成。
当前城市遗产展现出来的“混合空间”和互动体验,得益于数字移动媒介对所处地理位置敏感的特性。一方面,移动媒介作为物质设备,实质改变遗产的地理空间布置,重新组织到访者的所见与所知所感;另一方面,移动媒介可以感知设备所在地点及其文化脉络,并以此作为组织逻辑,指导信息的呈现与数字空间的建构。数字移动媒介不再一味着重于远程传播,而是依据地理脉络而组织实时且实地的信息,展现设备在物理地点中的存在,同时也在与遗产的物质互动中,重新凸显载体的物质实体。
(二)数字移动媒介的记忆:身体存档与算法驱动
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兴数字移动媒介,一方面以其轻便特性延续了视频圈的即时主义,促使不断更新的信息流走向移动中的“我”。然而,手机并未完全取代人的移动,媒介设备反而随人的移动而移动,随人的身体实践而生产符号信息。手机改变了信息的组织方式和人们保存痕迹、记忆事件的方式。
数字移动媒介允许、鼓励用户的记录和分享,使携带手机的普通公众成了记录者,通过手机应用随时生产个人的记录,并在集体中分享。这些记录离不开公众个人的身体参与:身体必须位居某一地方,手指需要触摸屏幕,身体部位的外形或数据也可能出现在记录中。如樊·迪克所说,身体实践成为数字媒介记忆的一部分。当信息向“我”移动时,“我”也在主动生产着记忆,“我”的身体参与记忆的生产。
用户的位置、移动轨迹等种种信息,也时刻为数字移动媒介所感知、记录。人的身体实践,经过手机算法而被转化为数字数据。这些转化可以在用户无意识的情况下持续进行,使下意识的身体动作也被记录在案,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这些记录包裹于算法的暗箱之中,难以为普通用户所操控。加上移动媒介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和记录,多种层次的时空数据形成由机器组织且持续更新的数据库,形成自动化的生活档案。
莱兹琴斯基将数字媒介这种超越人类的话语实践、无法被解构为公众认识的算法特性归纳为一种“物质性”。编程算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本质指导文本内容的形成,形成了数字驱动的过往存档,如今也成为人们回溯过往、指导未来的记载资源,如个人在身体数据的存档中监控健康问题、认识自己,数字地图的街景影像存档服务于城市生活。此时,数字移动媒介脱离人的思想控制又紧随人的身体实践,在与人类话语的区分上形成其独立存在。
数字移动媒介的新记忆方式,将可被记录的事物从权力机构关切的事件,扩展到普通个体的琐碎日常,记录视角也从权力机构的筛选变为多元视角的集合,甚至是维利里奥所说的机器“无目光的视觉”。这种记录一切、随时存储的方式,不同于视频圈中远方事件向被动观众的即时可见和更替,而是在公众自身的身体参与中持续积累数据,经过算法的分析、加工,以可以为人所理解的方式再次呈现不同时间层次。
数字的集体档案记载新近的过往,也成为对新近事件的纪念媒介。数字纪念物与历史建筑、文物、习俗仪式等纪念物和纪念组织并置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并相互呼应,共同构成将当前与过去联系以确认集体特征的文明遗产。
作为纪念物的数字移动媒介:重新浮现的物质性与新传承
数字移动媒介展现出其作为实体存在的重要意义,及其与物质世界的紧密关联。一方面,移动媒介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成为媒介信息生产、呈现的组织逻辑,形成设备与周遭物理空间的随时联系。另一方面,数字媒介因算法的自主运行而呈现脱离人类的自动化,作为与人相区别而又相联系的实体而存在。德布雷曾指出电子视听媒介的物质载体失去了与符号并置的象征意义,数字移动媒介则重新强调其物质性:载体的物理存在和算法组织规定其存储和呈现的符号内容,物理设备在与地理空间、与人的身体的关联中时时提醒人们它的物质性质和形态。
“物质性转向”是近年来人文研究领域涌现的新趋势,学者们从“物”的视角切入关注媒介传播的基础设施、技术系统、实践过程等。德布雷所说的物质,更多侧重于媒介多层次的实体,区别于抽象符号和精神思想,包含载体材料、组织机构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本文所说的数字移动媒介的物质性,同样涉及设备的物理材料和实体化的组织制度。不过,在数字移动媒介中,物质性的重新浮现并非重新恢复不可复制的物理本体,而更多强调媒介设备存在于物理环境的实在及算法脱离于用户意识的独立制度。
凭借重新浮现的物质性,数字移动媒介作为主导媒介组织起新的媒介圈,突出新的痕迹存储方式和对文明的新传承。城市遗产展现出对公众身体参与及互动体验的强调。人们在“混合空间”中体验城市遗产,与过去世界相联系;人类的实践痕迹随时向数据档案转化,持续进行着遗产的再创造。尽管这些参与体验仍不乏娱乐消费的意味,但已不限于对遗产视觉形式的保存和重现。遗产在与数字移动媒介的互动中继续积累当前世界的痕迹,制作新的纪念物和纪念仪式,延续文明活力,也不断确认由众人持续重塑的集体特性。
在这一新的传承状态中,数字移动媒介成为历史纪念物之一,为当前的文明传承提供现在与过往的联系和对遗产的持续创造。数字移动媒介支持参观者与居民以多种方式与城市遗产、与过去相联系;同时移动媒介持续记录公众身体实践与物理环境的数据,使其成为近期事件的档案和纪念媒介。在这些对当前与长期过去、新近过去不同时间的联系中,数字移动媒介成为传承的媒介,成为缺席过去的代表,与历史建筑、仪式习俗等一样构成城市遗产。数字移动媒介也以其持续建构的特性不断对遗产进行改造,更新现在与过往的联系。
对文明传承与遗产的关注为我们打开了考察、理解数字移动媒介的另一视角。媒介既连接这里与那里形成网络,也连接过去与现在形成延续性。数字移动媒介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对信息进行记录和存储,在依据地理逻辑组织信息时也加入地理的历史脉络,成为人们与过往联系的方式,展露出它在人类社会及其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关于遗产议题的热潮也与这一新的媒介圈相关,数字移动媒介的嵌入使得城市遗产并非遥远之物,人们在多种历史纪念物中参与、体验历史。媒介学的视角提醒我们重视媒介在时间维度的传承,也为媒介研究者与遗产研究者共同致力于遗产保护及文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