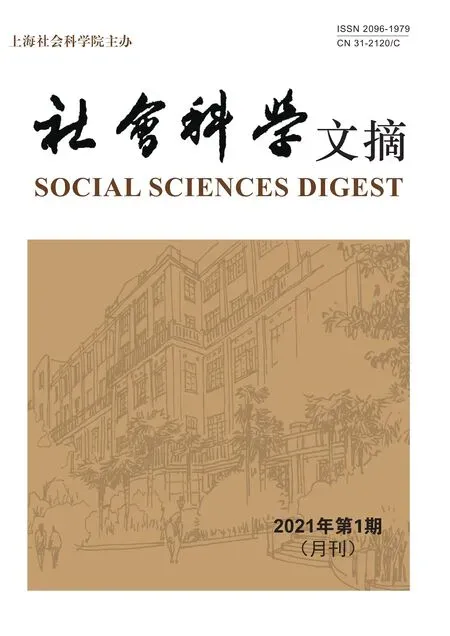《民法典》的四大伦理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民法典,我们可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
《民法典》之底线伦理
民法给人的感觉,主要就是财产法,但翻开《民法典》,笔者首先看到的是“人”,而不是“财产”。民法典的主旋律便是人文关怀。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在人身关系之前,价值重心在“物”。《民法典》总则把这个顺序调过来了,把民法的调整对象规定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人身关系放在了财产关系之前,体现了贵人轻物的价值取向。第二,人格权编独立成编在体系上改变了传统大陆法系“重物轻人”的结构,在价值上确认了人格权在诸种权利中的重要地位,在实践上回应了社会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对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三,在人格权编中,人格尊严的保护问题是最为基本的、重要的、迫切的问题,对自然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回归“人法”本位的《民法典》确认和维护了作为社会的道德底线的人格尊严。应该说,每个社会个体都可以向社会和国家提出必须无条件予以满足的要求,即社会和国家要把人当人看,不能仅仅将其当作工具来使用。这个要求是最根本的,也是不可取消的,因为人格尊严具有压倒一切的道德分量。社会和国家不能拒绝,只能满足并加以保护。这种满足和保护,通过宪法,以基本权利的方式落实下来,通过《民法典》,以人格权利的方式确认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民法典》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人格尊严何以成为《民法典》所确认的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
第一,只有自然人才是尊严的主体。所谓的自然人,是指具有人类生命基因的有生命的个体。也就是说,自然人的确立只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一个由人类基因组所表达的生命形式,二是必须是一个活着的个体。“自然人”的定义界定了尊严主体的范围,既避免了对尊严主体定义过宽之弊,又避免了对尊严主体定义过窄之弊。
第二,自然人的尊严由人“类”的尊严和个体的尊严两个层次构成。(1)所谓“类”的尊严,是人之为人应有的、有别于动物等其他生命形式的形象和存在方式。自然人是凝结了自然进化和人类创造的成果结晶,仿佛是鬼斧神工和人类劳动共同锻造的艺术品,其珍贵程度无可比拟,值得我们肯定和珍惜。(2)所谓个体的尊严是指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传记的作者,这个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传记的唯一作者,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才能超越身体的所与性和偶然性,通过支配身体、财富和精神,彰显出人的自由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尊严是指本人就是人生传记的作者的地位是不可替代和不可动摇的,对这个地位的尊重,是个体尊严的价值来源。
第三,尊严的价值具有内在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三个特征。(1)尊严的价值是内在的,也就是说,尊严本身就是好的。只有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才能成为其他价值的根据,只有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也才能成为衡量其他事物的价值的标准。(2)尊严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有很多,但不一定都具有绝对性,譬如,生命、财产、荣誉等都是可以剥夺的,但尊严却是绝对不能被剥夺的。尊严的绝对性意味着不可限制、不可替代、不可交换。(3)普遍性。人的尊严不是少数人的尊严或统治者的尊严,尊严的荣光落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无论在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方面有何差异,只要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即可以以其人的资格而拥有这样一种地位。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如果要确立一个确定无疑的价值支点,那就是自然人的尊严。
如果上述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民法典》通过人格权编独立成编的结构设计和诸多人格权的确认,无异于画定了社会生活的“人格尊严”的道德底线。
《民法典》之市场伦理
《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既要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的内在道德,又要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所嵌入其中的社会道德。所谓市场经济的内在道德,是指市场交易之所以成为交易的内在道德规定性。没有这种规定性,市场交易就不成其为市场交易,或者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无法实现。所谓外在道德,是指市场经济所嵌入其中的社会道德,这是具体形态的市场社会的道德要求。违背了这种要求,市场交易虽然还是交易,但不是一个好的交易,譬如性交易、毒品交易、武器交易等。《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道德,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风貌。
《民法典》总则编第7条规定了诚信原则,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8条规定了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其中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道德要求,公序良俗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道德要求。
第一,诚信原则是市场的内在道德。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是通过货币和契约的中间环节进行的,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市场经济,而市场交换由于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分离,蕴含了极大的交易风险,要想有效地降低和避免这种交易风险,契约无疑成了人们最理想的选择。可见,市场离不开两种东西,一是货币,一是契约。没有货币和契约的中介,一个跨时空的交易就是不可能的,而货币和契约的本质是一种信用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诚信原则,就没有交易,就没有市场。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构成性规则,是任何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无论是何种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都必须具备的。
第二,公序良俗是市场的外在道德。(1)任何交易都是具体的人在特定时空所发生的具体关系。除了要遵守诚信的内在道德之外,这个交易活动还要遵守交易主体所在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公共秩序。其载体就是习俗。如果说,内在道德是普遍的,那么外在道德就是具体地内在于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2)如果说诚实守信与公序良俗是交易伦理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那么公序与良俗就是目的与规范的关系。所有社会规范都以维护“公序”为共同目的,由此才有了不同社会规范之间的协调和转化。良俗也因此可以沉淀为道德,转化为法律。(3)风俗与善良的形与神的关系。风俗是指长期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风俗的种类及其表现形式繁复多样、良莠不齐,而良俗就是从这些良莠不齐的风俗中,依据社会的道德要求检选而出的。检选风俗之良莠的标准,可以是国家提出和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譬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可以是社会知识精英所提炼和概括出来的具有系统化、逻辑化、体系化的道德规范体系;还可以是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道德常识。
第三,民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就是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有助于凝结价值共识,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民法典。翻开《民法典》,我们也能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共识。这主要体现在《民法典》的立法目的上,即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在公序良俗的入法上,譬如《民法总则》第8条、第10条、第143条都有公序良俗的规定。我们之所以强调公序良俗入法的意义,是因为它体现了《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实质上也内含了特定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特殊的民族伦理。
《民法典》之关怀伦理
翻开《民法典》,我们还能感受到对弱者的悲悯和关怀。第一,民事主体制度中,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定了监护制度;第二,合同编中对格式合同中不利于弱者的免责条款有严格限制,在合同解释存在两种以上可能时,选择其中有利于弱者的那一种规定;第三,婚姻家庭编对妇女、老人和儿童进行特别保护;继承编中规定为无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第四,在侵权责任编里,尤其是关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
在传统观念中,民法是强者的法律,为什么《民法典》会表现出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呢?
第一,“人设”变了。传统民法上的人都是“强而智”的人。他们自利而理性、谨慎而精明、自主而负责。这样的“人设”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关怀。问题是,人是一个脆弱性和坚韧性二重属性的统一体,人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那么有理性,那么有韧性。经验告诉我们,脆弱性贯穿了人生的整个生命周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法作为生活的百科全书,当把眼光从抽象的市场主体转移到现实的生活主体时,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人设”。
第二,平等的诉求变了。传统民法上的主体资格是平等的,权利能力就是这样一个抽象的装置,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差异都抽象掉了,剩下的只是幽灵般的没差别的原子人。传统民法号称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谓的“平等”就是这种抽象人的形式平等。但现实生活中,差异无处不在,在各种差异中,弱者与强者的差异恐怕是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差异。因此,在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平等诉求之外,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平等诉求也应被重视,这是一种实质的平等观。如何差别对待弱者和强者的问题,自然成为“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对弱者的倾斜保护。差别对待就是要对弱者予以倾斜保护。弱者总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者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者缺乏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或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和救济,总之,他们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他们就会陷入被强者欺负的不利地位。因此,法律在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形式进行利益分配时,会对这群人特别予以关照,以保护他们的权益。社会法自然是通过对弱者的倾斜保护来实现社会的平等诉求,民法也不能与这样的价值诉求相悖离,也需要在强弱之间,适当地节制强者的任意,保护弱者的利益。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伦理。
《民法典》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当代社会从强者伦理到弱者伦理的转向。为什么会出现个转向?第一,脆弱性是人类存在的普遍特征。这一特征在现代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诸如世界大战以及大规模流行病之类的惨痛经历中被凸显出来。第二,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强者与弱者的地位是固化的,其中下层的弱者被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伦理学里自然没有地位。而现代社会里,传统的固态社会转向了液态社会,弱者是个流动的标识,每个人在某种特定的关系中都可能处于劣势。这样,弱者脱去了价值的标签,被还原为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伦理学不得不面对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实。第三,风险社会的来临,凸显了人的脆弱性。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在风险面前都可能是弱者;随时都可能成为处于风险中的弱者;每个事件都可能使一个人难以承受其后果。所以,只能以社会依赖与互助的形式来分担这个风险,由此,风险社会的伦理学必然是强调脆弱性和保护弱者的伦理学。
《民法典》之生态伦理
翻开《民法典》,在烟火气之外,我们还能感受到清新的自然气息,由此,《民法典》被称“绿色民法典”。第一,《民法典》总则编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是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第二,《民法典》各分编中,直接涉及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达18条之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物权编中确立了物权的生态边界。二是在合同编中,规定了对合同履行的生态边界。三是侵权责任编以7个条文全面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可见,《民法典》之为“绿色”,实非虚言。
1.透过“绿色民法典”,我们看到的物是什么?近代民法上的“物”是可分割、可支配、可交换的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中国《民法典》上的“物”自然具有这些特征,但我们也看到了“物”的另一个绿色面向:民法上的“物”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资源的一部分。这些作为生态资源一部分的物不但是难以分割的,而且具有经济价值之外的生态价值。由此,从生态共同体的理念出发,一个“绿色的民法典”的物权制度不但要从个人权利保护角度解决“物”的归属、利用问题,也要从生态公共利益的角度顾及生态环境资源的归属、利用问题,从而不但确立手持可分割、可支配、有效用的独立物的私有权人,还要确认那些江河大地、雪山高原、森林草原之类不可分割的生态资源的国家和集体的看护者;一个“绿色的民法典”不但要关注“物”的经济价值,也不能忽略其生态价值。问题是,虽然一个物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但是它们却不能一体得以实现,经济价值的实现往往是以消灭其生态价值为前提的,反之亦然。表现在《民法典》上,就是要整合物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并以此为价值依据,确立财产占有与流转的绿色边界。
2.财产占有与流转的绿色边界在哪里?生态共同体的理念要现实化,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需要通过制度的中介。由于《民法典》涉及人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疑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制度中介。由此,《民法典》不但要保护“物”的经济价值,强调“物”在经济上的有用性,并以此建立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也要保护“物”的生态价值,并因此作出解决这样两种价值冲突的制度安排,包括:对传统民法所有权的绝对性进行必要的限制;确保使用权人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确保我们在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3.透过“绿色民法典”,看到了中国伦理精神的走向。可以说,“绿色民法典”给我们打开了“由近及远”的伦理发展的画卷,使我们看到了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道德经验和知识不断普遍化的进程。这种由于道德应用范围的扩展所引起的伦理形态的变化过程,我们概括为从族群伦理到全球伦理再到生态伦理的过程。按照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的说法,人类起初只是承担对家庭和邻人的义务,往外依次为对社区、对国家和对全人类的义务,还有对后代的义务,再往外推是自然界,包括动物、植物、大地的义务。西尔凡(Richard Sylvan)和普兰伍德(Val Plumwood)十分贴切地用“树的年轮”来指称这个由近及远的演变过程。这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如果用色谱来表达,就是从黄到绿的过程,这也是《民法典》被贴上绿色标签的内在逻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