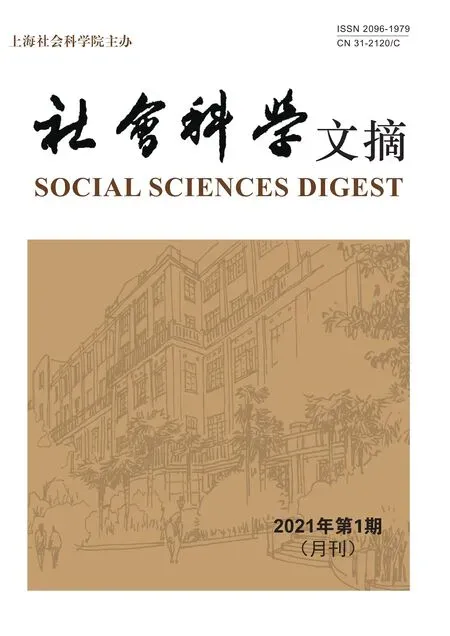论汉学家之于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意义
——以阿瑟·韦利为例
关于中国文化元素对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学界有所关注但未及深入。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曾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重新“发现”誉为“东方文艺复兴”;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领军人物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亦感叹“中国的激励作用并不输于希腊”,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置于与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相并举的崇高地位。如台湾学者林秀玲所言:“英国现代作家和艺术家不仅‘发现’了中国高雅艺术,还将中国艺术吸收进了英国复杂的美学探讨和现代艺术的创作实践之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艺术成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意象派”“漩涡派”等英美现代主义群体除旧布新的重要参照。学界关于罗杰·弗莱等现代主义美学家、埃兹拉·庞德等现代主义诗人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汲取与转化已有所探讨,但对不谙中文的他们接受中国文艺的渠道却语焉不详,汉学家的意义由此浮出水面。如钱兆明所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美学者也注意到这些中国诗人并开始翻译他们的作品。以厄内斯特·费诺罗萨、赫·艾·翟理斯、阿瑟·韦利的作品为媒介,庞德、威廉斯等现代主义诗人得以实现了与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的对话。”本文以20世纪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为中心,探讨其汉学成果作为媒介对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助推作用,由此呈现汉学家对于英美现代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
韦利的汉学研究与现代意识
作为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与汉学家,韦利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日文学—文化的译介和研究。英国汉学的兴起时间较晚,却在19世纪之后名家辈出。韦利继承了英国汉学传统,一方面,不断将中国古代典籍、诗歌与小说等译介至英语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出身剑桥的学者型汉学家,在翻译观念与文本选择上又体现出与传教士或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不同的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的译介更多与西方反思启蒙现代性弊病的美学现代主义运动相互依存,因而视中国文化为助力英美文学艺术突破传统、求新求变的异域资源。
随着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东方文化艺术馆藏品的激增,大英博物馆于1913年成立了“东方图片与绘画分部”。韦利在当年入职博物馆,并在东方学家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指导下开始了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有关中国文学与艺术的翻译与研究。首先是对中国诗歌的出色译介,重要译著有《170首中国诗歌》(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18)、《中国诗文续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1919)、《诗经》(The Book of Songs
,1937)、《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
,1946)等。他的译诗陆续被收入英美各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对中国诗人的传记研究,如《西游记》的节译本《猴子》(Monkey
,1942),《红楼梦》《金瓶梅》《老残游记》等小说部分章节的译介,以及对《太平广记》中多篇志怪小说的翻译。传记研究的代表论著有《白居易的生平及时代》(The Life and Time of Po Chü-I 772-846 A.D.
,1949)、《李白诗作及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701-762 A.D.
,1950)、《18世纪中国诗人袁枚》(Yuan Mei: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1956)等。在艺术领域,韦利的重要论著有《禅宗及其与艺术之关联》(Zen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Art
,1922)、《中国绘画研究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
,1923)等,论文则有《一幅中国画》(“A Chinese Picture”,1917)、《中国艺术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1920-1921)等。此外,他还整理出版了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家人名索引和斯坦因的敦煌绘画书目等著作,翻译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的经典篇目,可说“将一整个文明带入了英国诗歌”。韦利汉学研究的美学现代性追求首先体现在其鲜明的翻译理念上。自1918年起,韦利和翟理斯(Herbert A.Giles)就诗歌翻译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标志着两代汉学家之间观念的碰撞。这场论争以《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
)等刊物为阵地,双方唇枪舌剑达5年之久。两人的分歧表面上主要围绕汉诗英译的准则和策略等,但从深层来看也可视为英国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观念的一次正面交锋。因而,具体到翻译文本的选择上,韦利不喜欢典故繁复、句式佶屈聱牙的诗歌,而喜欢通俗易懂、风格简约的作品。同时,他注重对唐前诗歌的译介,对诗人寒山的译介亦是他的独到贡献。寒山诗歌中蕴含的佛教禅宗哲思带给“二战”后急需重建信仰的英美作家以深刻启迪,诗人因而甚至成为美国“垮掉派文学”的代言人。综上,作为标志着英国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型的关键人物,韦利的翻译理念与实践均体现出鲜明的革新色彩和现代特征。
韦利与英美现代主义者的交游
韦利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学者群体之间,存在着彼此影响、促进的关联性。韦利之所以能顺利开展汉学译介,离不开几大群体的帮助:以G.L.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罗杰·弗莱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以及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和“漩涡派”。
最早引导韦利与中国结缘的是其剑桥导师G.E.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和迪金森。韦利于1907年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时,穆尔的《伦理学大纲》(Principia Ethica
,1903)正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迪金森时任国王学院历史学讲师。穆尔对真理与理性的尊崇、对自由与审美的奉守,启示了整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远离物质主义与市侩哲学,质疑主流话语与官方立场,表现出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对他者文化的尊重态度。迪金森则在八国联军侵华和布尔战争的背景下创作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1901),反转了西方传统中负面的“中国佬”形象,塑造了一位正直聪慧、知识渊博、能言善道的东方智者约翰中国佬,努力在道家的诗意境界中寻找审美化的生存。韦利的弟媳玛格丽特·H.魏理(韦利)回忆道,韦利“接受了由剑桥大学G.E.摩尔和高尔斯华绥·刘易斯·狄金森讲授的那些哲学思想,他们后来都成了阿瑟长期的朋友,并把阿瑟介绍给罗杰·弗莱”。L.P.威尔金森指出,正是迪金森在1907年引起了韦利对中国的注意。另一位促使韦利与中国结缘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当属弗莱。1916年,韦利曾向弗莱征求自己的处女译作《中国诗歌》的出版意见,得到弗莱的热情支持。尽管此书最终只作为私人印刷馈赠给亲友,但多年后,韦利还清晰地回忆道:“这本书完全没有出版的意识,因为我想要同朋友们分享自己阅读中国诗歌的乐趣。对译作感兴趣的人有弗莱、迪金森和L.G.史密斯。弗莱当时对印刷颇有兴趣。他认为诗歌应该被印在波动的线条上,以此来增强节奏感。”1910年,韦利加入“诗人俱乐部”后还结识了庞德、艾略特、叶芝等人。1913—1921年,韦利与庞德、艾略特等人开始每周定期聚会。1917年,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成立。韦利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唐前诗选译》37首和《白居易诗38首》。后者的一部分经庞德推荐,于同年刊登在庞德主编、被誉为“庞德-艾略特运动”之喉舌的《小评论》(Little Review
)上。由于庞德出版译诗的时间更早,韦利在聚会和交谈中常常受益更多。韦利潜心于汉学译介,其成果又通过复杂的交游网络对现代主义者们产生了巨大影响。韦利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诸多成员保持了终身友谊,从剑桥毕业后又长期生活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街区戈登广场,与贝尔夫妇、弗吉尼亚·伍尔夫、凯恩斯等“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核心成员比邻而居。1916年,韦利的首部译作《中国诗歌》即是在弗莱主持的“欧米茄工作室”(Omega Workshops)的会议上由成员讨论是否应该出版的。这部译作赠送的对象包括迪金森、庞德、弗莱、艾略特、罗素、伦纳德·伍尔夫、叶芝、贝尔等人,大多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成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以及“意象派”与“漩涡派”成员。韦利还时常会在朋友聚会时朗读自己的译诗,并被凯恩斯的妻子、俄罗斯芭蕾舞蹈家洛帕科娃戏称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人”。1917年10月,罗素收到韦利的赠书之后,在给韦利的信中盛赞了他的译作,认为正是韦利的翻译让他触摸到“远比西方更令人耳目一新、更精致的中国文化的精髓”。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奥兰多》的致谢中也感谢了韦利给予自己的帮助。
与此同时,从1917年起,韦利的大多数译作还在美国的《小评论》和英国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两种杂志上轮流发表,给热爱中国诗歌的美国诗人带来惊喜。知名诗人弗莱彻、门罗等曾刊文对其译著予以赞扬。而韦利对白居易诗歌的译介,亦成为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创作现代诗歌的典范,并直接影响了其代表作《春天及万物》的遣词造句、思想理念和风格特征。T.S.艾略特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中亦回顾道:“东方文学对诗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翻译实现的。东方诗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影响不可否认;仅以英语诗歌为例,在我们这个时代,由庞德和韦利翻译的诗歌可能被每一位诗歌创作者阅读过。”如此,通过韦利的译介,中国文学—文化深刻影响了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韦利的汉学成果与英美现代主义
如史景迁所言,韦利“以东方的风格为受到严重威胁的生活祈祷祝福,这样的做法非但一点儿也不过时,相反,它们是强大的能量和渊博的学识的产物,它们也是某种信念的产物,这种信念相信有一种价值理念是长久存在的,有一种思想是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因为这理念、这思想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真实的”。韦利的汉学成果对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究竟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思想观念与艺术形式两个层面来看。
从思想观念上来说,韦利对中国道家哲学的重视,对中国诗文所呈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并存境界的赞美,呼应并促进了英美现代主义运动在价值层面的新追求。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欧美社会从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质疑与否定中裂变而出的美学现代性,以反叛科技文明和工具理性的冲动、拒绝平庸的高蹈姿态、崇尚感性与心灵的热情等为标志,通过美学现代主义运动集中爆发了出来。在此条件下,非理性色彩浓厚的东方哲学,如道家思想、佛教禅宗等,成为矫正理性至上之偏颇的异域资源。与启蒙时代的作家与思想家对儒家学说的趋之若鹜形成对比,道家经典在历经数个世纪的冷遇与误解之后,终于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迎来了在西方翻译与研究的辉煌。韦利在《中国艺术哲学》《中国绘画研究概论》《道及其力量——〈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等中不仅阐释了老庄哲学,还进一步将“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概括为中国古典诗歌与视觉艺术最鲜明与共通的特征。他在论及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歌和水墨山水画时,均特别强调了其追求天人合一、“顺物自然”的精神指向。由此而言,韦利的观点有力回应了迪金森和罗素以道家文化崇拜自然、注重生命体悟的特征来对抗“机械的人生观”,将陷入危机的西方人从惯例的、工具化的文明中拯救出来的思想,并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者。
美学现代主义除了从道家、佛教禅宗等观念中汲取滋养以强调感性的回归、天性的舒展,努力将主体从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价值取向之外,还高度强调艺术审美的独立性。“从追求新颖形式到纯粹的审美经验,其中都隐含着一个潜在的观念,那就是对平庸、陈腐和一成不变的现实存在和日常经验的否定。”亦即是说,现代主义者的形式美学追求,是美学现代性追求的自然延伸。这一方面同样在韦利的汉学译介中获得了滋养。
1920—1921年,韦利在弗莱主持的《伯灵顿杂志》上推出了《中国艺术哲学》系列文章,囊括了谢赫、王维、张彦远、郭熙、董其昌等艺术家、艺术理论家的观点和成就,细致梳理了重要的中国艺术理论。1920年10月,韦利重点阐释的是公元6世纪中国南朝画家兼理论家谢赫《画品》中提出的绘画“六法”。“谢赫六法”之首法为“气韵生动”,要求作品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饱含生命的律动感,体现出主客体的交融。这一写意原则不仅成为宋代之后中国文人画的追求目标,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核心。通过对“气韵生动”美学原则的阐发,韦利推崇并强调了“精神”(spirit)在文学艺术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唯有精神方能使世界物象发生变化,如同竖琴演奏者撩拨琴弦一样,通过“精神的运作”以产生“生命的律动”。长期以来,弗莱一直在探索将文学艺术从亦步亦趋模拟现实的僵化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新路,深感“我们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韵律实在是知之太少”。1923年,伍尔夫亦发表了被誉为其有关“现代小说”的美学宣言的长文《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提出小说家要摒弃外部的物质表象,摹写人的灵魂的深度,以抓住生活的本质,表达真正的真实的观点。韦利对中国艺术美学的阐发,为弗莱的现代主义美学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摒弃物质主义的精神主义追求,亦形成了强大的声援。
值得一提的是,弗莱还从谢赫的“气韵生动”中捕捉到了中国艺术美学讲求以简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以唤起生命的律动感的精髓,与西方诗歌与音乐艺术传统中的节奏感结合到一起,发展出了对“韵律”(rhythm)的独到追求,要求无论是语言文字艺术还是视觉艺术中的韵律,都要与人的生命节奏、人的情感变化同构对应,以表达人的心灵的律动。弗莱认为:小说中能唤起审美情感的形式关系即是“大脑状态的韵律变化”。他用“一种穿透整体结构的造型韵律”赞美了自己心爱的画家保罗·塞尚的画作和挚友伍尔夫的小说。在伍尔夫那里,“韵律”一词同样具有相当高的使用频度。由此,我们看到了韦利的汉学译介对现代主义者的美学探索所作的贡献。
概而言之,如钱兆明所指出的:“东方文化中那些吸引英美诗人的因素——历久弥新、丰富多彩的东方文化中的细致、准确、客观、倾心,与自然和谐融洽——这些特点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运动的核心要素。”而在此过程中,韦利及前代汉学家如赫伯特·翟理斯,同时代其他汉学家如劳伦斯·宾扬、厄内斯特·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等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汉学家群体作为跨文化阐释与理解的重要桥梁的贡献尚未得到充分评估的背景下,加强此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