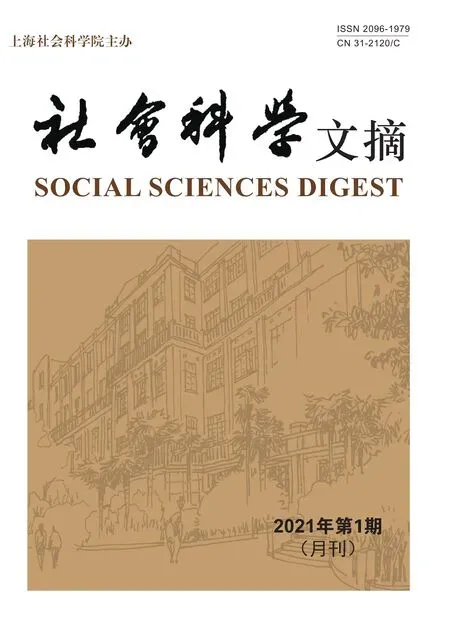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重困境与反思
百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既是中国人思考政治的重要叙事方式,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缩影。可以说,在中国,如何建构、叙述与表达中国政治思想史,早已超越了认识论与知识论等学术问题,既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传统、看待当代以及看待未来的问题,也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看待他者以及如何建构两者关系的问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诞生近百年的时间点,重新梳理与回顾这一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审慎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故事,既是这门分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建构一流的中国政治学的必然要求。
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重困境
1922年春,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正式创建。至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纵观近百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依旧感觉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诞生,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主体意识的追溯和确认。这种对主体意识的追溯和确认,既源于传统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的系统入侵而给精英阶层带来的焦虑感与危机意识,也与一种从历史中发现智慧的历史主义情结息息相关,但这种对主体意识的自我追溯和确认带来的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多重困境。
(一)学科身份困境
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创建之初起,就一直存在着学科身份辨识的问题。这种学科身份的困境,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学术资源、学科边界、学科属性以及学科的概念、内容体系和思想谱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模糊性,也容易引起争议。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贡献甚多的海外学者大多数属于历史学、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同样,中国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的学科来源也是高度多元化的。这其实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学科边界困境;换句话说,这门学科究竟是属于政治学,还是属于历史学,抑或是哲学?此外,在国内教材方面,我们也能窥见这种困境。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其体例往往是传统史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杂糅,这样一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就存在着先天的学科边界模糊的困境。
其次,这种学科身份的困境还体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话语权方面。就内部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几乎成了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中仅次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冷门。此外,在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立项数量在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中是最少的。就外部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外话语权传播机会远远不如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比如在论文发表方面,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群体极少有机会通过国际平台特别是国际期刊扩展自己的学术影响力。
最后,这种学科身份的困境体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方面。就研究主体而言,当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海外学者和大陆学者之间似乎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术共同体。而且,如前所述,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大陆学者的学科来源也是高度多元化的,这种特征虽然能够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多样化,但也加剧了这门学科的身份认同困境。可以说,如何平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各个范式之间的张力,使它们彼此能够融会贯通,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对话,最终使中国政治思想史既具有哲学的思想性、历史学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同时又具有现代政治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建构性,依旧是困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难题。
(二)价值立场困境
中国政治思想史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它自诞生之初就自觉地承担着一种历史使命,这就是为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智识资源,并为现代中国的政治设计与政治追求提供价值支撑。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独特的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困境:即在研究的价值立场上,往往意识形态先行,而学术与知识追求次之,最终导致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
我们只要简要梳理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程,就能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史,跟现代中国的政治追求历程是高度同步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其研究的价值立场是要从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寻找当时盛行的政治思潮的基因。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样“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贯穿该著作始终的主线主要是两条:其一,传统中国的专制政体及其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其二,带有浓重目的论色彩与一元主义倾向的进步史观。至于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其对应的显然是共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学术化。但是,价值立场的争论在这一领域依旧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中;反封建和启蒙的价值主要集中在王权主义学派等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中;至于经学研究范式或者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他们甚至以一种“我注六经”的使命感,主张从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寻找解决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的智慧。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无意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本身,而只是将其当成实现自己文化与政治理想的一个工具。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其直接结果是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知识沉淀与研究水平方面,往往不及政治学、历史学与哲学学科内部的其他分支学科,更与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差距甚远。不宁唯是,这种过于追求政治与实用主义的立场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随意甚至刻意进行加减法,从而忽视或者遗漏掉诸多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资源。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思想史如何把握自身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好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依旧是困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难题。
(三)学科对话困境
首先,政治价值立场限制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内部各范式之间的对话。由于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一直存在着价值立场先行、学术为政治进行注脚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不同范式的对话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方面,对话各方容易因为自我感觉占据道德制高点或掌握了真理话语权而处于一种强势地位,从而限制了对话应有的平等、沟通、交流、妥协、倾听等品质。另一方面,由于对话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与思想争论,而是涉及重大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政治价值争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容易陷入一种质疑动机、立场的状态,甚至上升到“敌我”的高度,从而消解了对话的可能性。
其次,学科话语权、学科语言以及学科概念等限制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跟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对话。在政治学学科内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话语权几乎是最弱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很多开设政治学专业的院校中并非必修课,其学术经典并非学生的必读书,故而,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典籍、核心概念、基本的思想谱系与脉络,很多政治学的研究者是极为生疏的,更不必说与其进行对话。另外,古文文献的阅读困难也使得政治学学科内部其他研究者对这一学科方向往往望而却步。
最后,对传统中国政治的标签化处理限制了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者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可能性。从词根上说,政治是POLIS,就是城邦,它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是由自由、平等的公民对城邦进行治理。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对城邦的治理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公民的事情,是集体的事业。此外,从治理方式上看,城邦或者说政治是一个靠理性言说也就是讲道理来治理的领域,越是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就越远离政治。
如果按照西方“政治”的原初含义,传统中国的政治几乎都是“非政治”的。一方面,从主体上看,政治在中国的语境中,一直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不是“公民的事业”。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概念,这其实已经消解了中西政治思想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因为专制从其本意来说,乃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这与西方政治概念谱系中的理性言说和对话精神相距甚远。
走出困境:如何发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要超越我们前述的三重困境,必须首先重构政治思想史的价值叙事与合法性叙事。这种价值叙事与合法性叙事,既要防止彻底西方化,也要杜绝过分中国化,而是以一种还原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政治思想史的存在价值论。
如果我们从超越古今、中西的角度去重新思考政治的话,可以说,人类之所以需要政治,是因为政治是人类建构秩序最有效的方式,也是维系人类文明最有效的方式。而政治思想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理论化的方式描述这种政治秩序,维系或者改革这种政治秩序,并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蓝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都可以看成是人类尝试建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明的观念表达与叙事,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首先,政治思想是人类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在建构政治秩序的道路上,对政治问题的理性思考而形成的政治智慧。而人类作为地球上特殊的“类存在”,彼此之间一定保持着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彼此之间总是有一些彼此共享或者能够对话的“永恒的观念单元”,而政治思想就是对这些“永恒的观念单元”的政治阐释,政治哲学就是关于这些“永恒的观念单元”的知识追求。在此路径之下,我们可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建构政治秩序的那些共享的观念进行阐释。比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的概念,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思考,卢梭认为强力不构成合法性,甚至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史,从观念上看,与传统中国周朝的“以德辅天”,西汉董仲舒的“天谴论”,以及宋明理学,其实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建构合法性的不同叙事与不同表达,都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概念进行统摄,并为相关的对话与沟通提供空间。
其次,所有的政治思想中都有一定的超越性智慧。政治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即使思想家们思考的是特定时代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隐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普遍主义的智慧。这是因为,人类自身作为“类存在”具有诸多方面的高度同一性,这种“类存在”的同一性,使得他们面临的政治问题同样具有诸多的同一性,甚至具有永恒性。这些问题,构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且永恒的主题,不会因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而消失,只要有政治,这些问题就会存在,故而思想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中的表达也就有了一定的超越性,这些思考在任何时候都能给后人思考他们时代的政治问题带来启示与反思。
最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蕴含着某种正义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诸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善的这样的观念,都是人类建构美好政治生活的尝试,但同时也体现着人类理性的限度。政治总是蕴含着正义,蕴含着某种善,这种正义的观念既构成对以往政治的反思,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也构成对未来政治的期待。因此中西政治思想史在这一层面上,也可以说都是正义观念的历史性表达。此外,在如下意义上,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有对话的空间:政治思想作为人类在面对自身世界时建构秩序的一种最高的理性思考,同时也反映着人类在特定时刻集体理性的限度与高度。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去思考政治思想史叙事的话,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它蕴含着人类思考政治问题的观念单元,体现着人类对正义的价值诉求,表达着人类在特定历史时刻理性的高度与限度,并因为人类面对政治问题的同一性而在普遍主义的意义上获得了对话的可能性与价值支撑;换句话说,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先必定是“政治思想史在中国”,它本身就是人类思想与精神的遗产。
“政治思想史在中国”,这意味着,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发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西方政治思想所无法表达或包容的概念,这些概念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钥匙,是表达中国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思考现代中国未来政治的重要维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先还是要回归学术性与思想性,以现代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对传统中国的这套政治话语体系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之上提升中国人政治思维的复杂性与政治智慧。
“政治思想史在中国”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重新检讨当下某些研究形成的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格式化命题,从而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中西对话以及古今对话提供广泛的、开放的、具有极强包容性的空间。同样,对于百年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存在的西学价值比附的现象,在当下也应该予以警惕。此外,大陆的研究者们如何走出因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的心理困境与价值立场困境,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空间,进行具有国际视野的对话,更是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问题。
“政治思想史在中国”还意味着,我们需要站在人类共同体的角度看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需要以他者可以读懂的方式成为人类政治思想研究的共同遗产,因此它必须走出去。这种“走出去”的战略,包括如何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经典翻译出去,如何与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海外学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典籍中提炼具有普遍主义价值的命题。不宁唯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它要深刻理解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思想谱系,将中国政治思想放在人类思考政治问题、建构政治秩序、实践正义与公平的坐标中,全方位审视它的合理性、局限性以及特殊性,并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捕捉人类在重大时刻何去何从的选择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政治思想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结论
建构立足于中国本位、中国视野与中国价值关怀的政治学,是建构一流的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要求,而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样也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定位。学科身份问题、学科价值立场问题以及学科对话问题,依旧是困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难题。只有重构政治思想史的价值叙事与合法性叙事,既从普遍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政治思想中内含的人类对政治问题思考的诸多同一性,为世界政治中的他者观察与反思其自身的政治提供参考,同时又从特殊主义的视角发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从中窥视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学术与思想的统一、世界视野与中国情怀的统一,最终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既具有哲学的思想性、历史学的严谨性以及学术性,同时又具有现代政治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建构性,才能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焕发永恒的生命力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