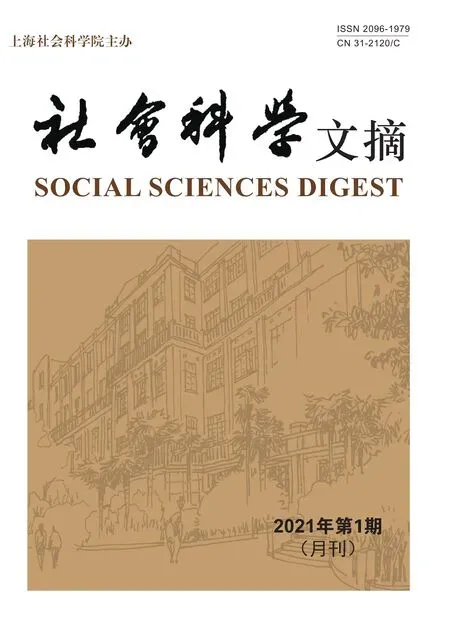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不过,其中“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它们与“原始文化”“史前文化”和“文明”等传统概念之间关系缺乏准确一致说明。有的时候,这些界定与说明之间,逻辑上还互相牴牾。而且,“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三大板块描述用语不一致。“三部曲”是一个文学用语,并不十分适宜用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过程的规律。这类问题的出现是忽略基本科学程序的结果,最终严重影响了该理论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播,有必要加以辨析和澄清。
“古城古国”与“文明”的关系
苏先生这三个历程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使用了“古”字来作定语,但其准确意思很难把握。
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中,他认为:“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同一次讲话中,苏先生又说,最早的“古城古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时期,这“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
第一部分引文是苏先生最初系统提出“三历程”理论时候的经典解释,也是他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最为系统和连贯的解释。以后的解释再无这么系统和连贯过,而且多个解释往往不相一致。
在上述引用的第二部分,苏秉琦明确说明,最早的“古城古国”出现于“文明昌盛的时期”。“古城古国”与“文明”或“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后来他总体上是坚持了下来。虽然,“古城古国”到底是出现于“文明”的哪个时期,不同的场合他说法往往不一。
比如,他在发表于1991年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古城、古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变革的产物,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在这里,至少,“古国”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虽然,“古城”按照文本理解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也就是,“古城”尚未“进入文明时代”。这段话与上引“古城古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文明昌盛的时期”之说法,就“古城古国”与“文明”关系而言,苏先生的认识是退了一大步。
另外,与上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讲话大不一样的是,现在所看到的材料是,与这篇讲话时隔不久,他就将“文明”,至少“文明的曙光”出现的时间放到了红山文化后期,将许多时候与“文明的曙光”紧密联系的“古城古国”的出现提前了1000年左右。我们来看看下述材料:
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宁朝阳发现的这一组红山文化后期的遗物、遗迹群(指坛、庙、冢等——引者),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的解体或开始解体,以及是否传达了文明的曙光或讯息。
比历史悠久、连绵不断更为重要的,当然还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问题。辽西红山文化三种文化遗迹的发现,已拍下考古纪录片。片名未定,拟用“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曙光”。取名意图是:这三种文化遗迹的年代要早于五千年……
按照苏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在“1986年正式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苏先生这种看法之后并未有过根本的改变,有所改变的只是态度越来越肯定,时间越来越提前。
1986年8月4日苏先生再次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说:“……东山嘴村……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牛河梁村……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型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
在1987年发表的《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中,苏秉琦所用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红山文化坛、庙、冢”。
在1989年5月发表的《写在〈中国文明曙光〉放映之前》一文中,他说:“……古史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或仅是一种民族的传说?80年代以来,经过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对此已经出作(原文如此——引者)肯定的答复……”
在1992年的专访《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中,他说:“……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了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米、高17—1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
在1993年发表的《论西辽河古文化——与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一千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
他在1996年接受香港《明报》专访,再次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与大面积宗教活动场所相应的生活聚落,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从红山文化中看到的这种基于社会分工、分化而形成的‘古国’,我归类为‘原生型文明’。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既然“古城古国”是打破“古文化”也即“原始文化”“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标志,那么,这两个以“古”字作为定语的发展阶段,意思就正好是与前一个“古文化”的“古”字所表示的发展阶段相对立的。第一个“古”字是“原始”的意思,后两个“古”字却是“最早”“最初”“第一次”打破“原始”旧时代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意思,第一个与第二个尤其第三个“古”字之间,意思完全相对立。第一个“古”字,是“原始”,是“旧”;第二个和第三个“古”字,是“文明”,是“新”,或至少即将是“文明”,是“新”。不作仔细分析,读者容易将三个“古”字混为一义。
我们的分析更进一步表明,从现有的文本当中,要准确指出苏先生的“古城古国”尤其是“古国”所属时代是十分困难的。从开始的夏家店下层到红山文化后期,“古国”到底是出现在“文明曙光”的时期,还是“文明时代”?本身“成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还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序曲”?其身处“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的“中华文明史”的时期,还是“文明昌盛”的时期?恐怕都是难以确定的。
“古文化”之“古”字语义分析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甚至,“古文化”之“古”,是否就是“原始”的意思,从现在看到的文本中,仍旧无法找到明确解答。比如以下文字:
……现在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目的是对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加以重点研究……
古文化古城古国在这里的特定涵义是什么呢?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
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可以概括为三种文化,属于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
统名红山的理由是:一,红山文化分布面最广,影响最远;二,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等,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苏先生还说,1975年在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就提出要保护“古城古国”,“当时指的主要是历史时期的遗存,而没有同时指出史前文化遗存这一重点;也就是说,没有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古文化”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在1991年12月发表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苏先生还有一种解释:“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原始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
从以上两篇文献的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8个结论。1.“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2.“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3.“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4.“古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5.“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6.“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7.在辽西地区,“古文化”等同于“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8.在中国的古文化当中,“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从以上8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古文化”之“古”其意谓何,关于这一“古”字与“原始”和“史前”的关系,是很难准确指出来的。通过这一“古”字,要想知道“古文化”到底出现于何时段,等同于何时段,至少可以得到6种解释。1.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那个时段。2.等同于“古文化”也即“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时段。3.“主要指原始文化”那个时段。4.等同于“原始文化”时段。5.等同于“史前文化”时段。6.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那个时段。
这6种解释每种都不一致。通过这6种解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6个问题:“古文化”到底是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部分?是“主要指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是等同于“史前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面对这6个问题,恐怕没有人可以从苏先生现存的文本中找到准确解答。
其中,第4、5、6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学术背景是,大家熟悉的“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是并不相等的两个概念,并且,苏先生是清楚知悉的,“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具体来说,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同时,不限于中原、不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在这里,苏先生清清楚楚地强调:“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
上述那段话是1991年年底才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不过,我们恐怕不能假设,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苏先生这样专攻史前考古的泰斗才分辨清楚“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这种常识性的知识。因此,我们唯一可以假定的是,在进行“三历程”理论创新的时候,当他抛弃学术界所常用概念而进行新概念创制时候,并没有进行细致推敲,从而导致了严重纰漏:1.错误地将“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2.因而错误地将“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从而等同于“史前文化”;3.进而错误地将“古城古国”当作了“历史时期”的文化。
“三大板块”之间逻辑关系及描述用语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苏先生理论三大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模式—次生模式—续生模式)这三大板块,一环扣一环,粗粗看去,理论上的结构十分完整。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其板块与板块之间关系与板块名称,仍旧有可以推敲之处。
很清楚,前面两个板块的关系是依次递进关系,后面一个是对前面两个板块的说明关系。在出现时间上,最后一个板块的三种模式甚至可以是同时并进关系。它们都是用来描述同一个中国地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让读者疑惑的是,为何这同一个地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使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词汇来进行描述。三个阶段的“三历程”与“三模式”,中心语“历程”与“模式”,都是普通名词,意思分别是,“经历的过程”和“经历过程的路径”。加上前面作为定语的量词“三”,“三历程”与“三模式”都很好理解,意思分别是,中国地区人类社会演化的“三个经历的过程”“三种经历的路径”。但是,“三部曲”就不一样了,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文学专有名词,作为定语的量词与作为中心语的名词不可分开;并且,像在英文中那样,其本身拥有复数形式,可以使用量词来作为定语,如“One trilogy,two or three trilogies”。“trilogy”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trilogia”,由“tri—(三)”与“logos(故事)”两部分组成,是指在雅典酒神节演出的互相关联的三部悲剧。它现在的主要意思是,三部内容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作品。因而,使用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学专有名词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所经历的三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显然是一种并不恰当的比喻。“三部曲”本义中的三部虽然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不可分开;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即便假定从总体上看,大致有古国—方国—帝国这一演进次序的存在,却并非每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三个依次递进的历程。
此外,“三部曲”是比喻性用法,“历程”和“模式”是用来进行实描的词汇,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词汇,并不适宜拼合在一起,用来描述中国地区同一个人类社会演进的进程。尤其是在苏先生那里,对属于递进关系的密不可分割的两大板块,一个进行实描,一个使用比喻来进行描述,更不适宜。考古学本是一门科学,考古学家语言的使用,准确本是第一要求。在准确性上,比喻的效果显然不如实描,文学的语言显然不如科学的语言。
还有一个不适宜的地方是,“古国”既是三历程的最后一个“历程”,又是“三部曲”的第一部曲,从文本上突然看去,“古国”是从一个领域跳入另外一个领域,从一个实描的科学领域跳入一个比喻的文学领域。这让读者不得不想,这两个“古国”到底是否同一个事物?
“古国”在不同领域语言描述中所处位置,还引起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三历程”加上“三部曲”,关键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六个。但在实际上,其中两个关键进程,使用的描述术语完全是同一个。这加起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到底是五个还是六个?两个“古国”如是同一个,那么,“三历程”与“三部曲”相加,数量上是六个,实质上却是五个。它们如不是同一个,读者又会疑问,为何在不同板块内不同的两个事物却要使用同一个术语或者名字?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无法解答的。
新旧概念关系与科学创新程序问题
苏先生理论创新的概念与传统概念是一种什么关系?苏先生使用了什么程序进行概念创新?这都需要回答。
从总体结构上看,毫无疑问,苏先生的学说构建在摩尔根与恩格斯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演化理论的基础框架之上。并且,它也与新进化论的社会演进基本路径相符。不同的地方在于,苏先生使用了中国材料,尤其是创新的中国术语,来描述古典进化论与新进化论的人类社会演进基本路线。那么,苏先生的创新术语与前人概念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总体上看,他抛弃了学术界熟知的前人概念,创制了自己的概念,但对自己概念与前人概念之间的关系,许多时候并不明确说明;即便偶尔说明了,也十分简略;每次说明还往往并不相同。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其概念与前人概念之间关系,让人难以确切把握。
最为典型的是,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从表面词汇上看去,这一理论的三个历程概念完全是创新,与过往任何理论所指发展阶段绝不相同。苏先生既抛弃了摩尔根等古典进化论者的常用概念,如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如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没有顾及塞维斯弗里德等新进化论者所提供的术语,如游团—部落—酋邦—国家或平等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国家。而且,苏先生对自己创新的这些概念并未进行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定义。在个别场合,苏先生又将自己的术语与学术界十分熟悉广泛使用的概念,如“原始社会(文化)”,如“史前社会(文化)”,如“文明”,如“国家”,对应或者似乎对应起来。这些做法是造成读者理解苏秉琦“三历程”理论十分困难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摩尔根、恩格斯等古典进化论者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进而将原始社会划分为蒙昧社会与野蛮社会,继而将后两者各自进一步划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发展阶段。他们的这种从原始到文明两大板块的基本划分也为新进化论者所接受,不同的是,后者在原始社会演进阶段的划分上往往与古典进化论者不同。苏先生不使用新进化论的概念好理解,在他开始研究文明起源的那个年代,新进化论的学说刚刚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但是,他完全弃恩格斯等人的基本概念于不顾,却让人难以理解。他一心要做的事情,是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做续编,为何却不使用恩格斯的基本概念?有人也许会说,苏先生实质上继承了恩格斯的思想,但在概念上有所创新。问题在于,那些新概念很难认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并未进行过科学意义上的定义。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创新”本是内在要求。但是,科学创新不仅需要科学家持有严谨的研究态度,而且需要遵守严格的研究程序。急于“创新”而忽略甚至省略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所获所谓“新”成果往往并不可靠。
要“创新”,第一程序就是“破旧”。“破旧”然后才能够“创新”,“破旧”是“创新”的第一基础。遗憾的是,我们在苏先生那里看到的“创新”工作,似乎就缺了第一个程序。他并未拆除旧房子,就在旧房子上刷上新房名进行“创新”。甚至,“新房子”的名字,还是使用有点透明的液体书写的,让人隐隐约约还能够看到“旧房子”的名字。“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原始文化”“史前文化”“文明”和“国家”几个“旧”概念,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由于未能通过科学程序破除旧概念,分辨清楚新旧概念之间关系,导致其理论逻辑前后矛盾,让读者无所适从。
结语
当然,尽管有着以上讨论的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仍旧是中国史学界出现过的最为重要的学说之一,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的进展。更不必说,苏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最大功臣之一。对于他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本文论到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考量。苏先生理论的创立处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早期阶段,必然受到了当时的学术条件与学术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苏先生最早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说”是在1985年。30多年来,中国的史前研究,尤其是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程度上,还是在科学方法与科学程序的完善上,都有了巨大的进展。我们应该继承苏秉琦先生的事业,努力完善他的学说中尚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地方,使用更为严格的科学程序与科学方法,创立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同时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社会演进理论,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借用张忠培先生的一个口号,“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时机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