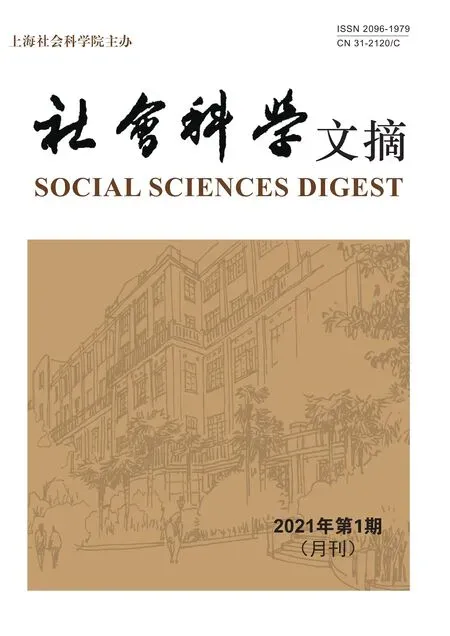超越孤寂:文明进程中的临终关怀及死亡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勾勒的“美好生活”蓝图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表现。梳理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主要议题、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对捍卫生命尊严、推进社会建设、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祉具有启发意义。德国“构型”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对文明进程中“临终孤寂”问题的研究与超越,为本文进行这种具有“中国关切”的理论对话与实践反思,提供了切入点。
作为“构型”问题的临终关怀与死亡
1967年,英国医生桑德斯在伦敦创建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这一事件成为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开端。临终关怀运动从两方面批判与超越临终及死亡的现代悖论:医学进步对死亡的延迟并不必然提升临终者的生命质量;现代临终者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埃利亚斯将死亡与临终模式的演变看作典型的构型研究议题。如果说“构型”体现为不同主体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动态波动,在《临终者的孤寂》中,埃利亚斯对“死亡与临终”问题的关注显现出“生命解放”的价值关怀:揭示人类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构型内隐但清晰可辨的演化趋向,将个体从社会或自我施加的观念蒙蔽中解放出来——“孤寂死去”这种现代生存体验并不是死亡的应然属性,而是文明进程晚近阶段的产物。
文明进程与“孤寂死去”的现代主体生成
(一)现代临终者的孤寂:文明进程的构型生成
埃利亚斯的研究旨趣体现在:以“临终”这一特定生命阶段为切入点,阐明在以“构型演化”为核心的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人格结构的“理性化”衍生的深远后果。在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研究架构中,中世纪具有坐标原点的意义,促使现代西方文明“社会发生”与“心理发生”的条件在这一时期成熟,“现代临终者的孤寂”同样是这一发生机制的产物。
对埃利亚斯来说,“理性”不是人类的天赋,而是个体在社会构型变迁中逐渐摸索出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取向: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克服短期、直接的情感与行为冲动,习惯于从他人对其可能产生的反应及其长远影响出发,约束与调适自己的行为与情感。埃利亚斯指出,当“理性化”成为现代文明的主导趋势,在现代个体的人格结构中凝结后,人类文明的长期性进程被逐渐遗忘。“孤寂死去”本来是文明进程的晚近形式,却被现代主体视为具备“自明性”的社会事实及应然状态,成为现代主体时感痛苦但不得不学会适应的惯常性生命体验。
(二)“个体化”社会与“孤寂死去”的人格结构
“理性化”趋势使现代人罹患情感与行为“无能症”,渐渐荒疏与临终者自如相处的能力,羞于用高度情感性的言辞安慰临终者,往往只是静静伫立。
对埃利亚斯来说,“孤寂死去”是现代社会“个体化”效应的具体表现。任何个体都生活在牵动他人的依赖关系中,是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长链中的一环。埃利亚斯揭示出下述事实:“人类必须孤单死去”的想法在“个体化”意识发展相对较晚的阶段才出现,“当人的自我形象益发尖锐而明确地表现为完全依靠自己而活、不但迥异于他人而且疏离于他人并完全独立于他人而存在的时候,孤单死亡就会成为人类反复出现的体验形式之一”。
(三)仪礼荒疏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属性的侵蚀
临终礼仪有助于临终者确证生命历程的意义,通过突出临终的文化属性超越其自然属性,丧葬仪式有助于临终者通过想象自己死后人们哀悼、纪念与记忆自己的方式来缓解死亡临近时的孤寂恐惧。《临终者的孤寂》的下述忧虑耐人寻味:现代人格的“理性化”及情感荒疏、传统仪礼的荒废已成为遮蔽与隔离死亡及临终者、强化临终者孤寂的重要原因;“而有助于面对生命中一再发生的危机情境,又符合于当今感受与行为标准的新模式,则至今尚未出现”。宗教式微,科学勃兴,理性上位,面对临终与死亡的传统象征仪礼,现代人倍感尴尬,更羞于践行。当死亡临近时,无论是临终者还是其亲属,常常感到手足无措,集体性的价值、规范与伦理的效力消退,面对死亡与临终寻找适当字句与姿态的任务重新落到现代个体身上,这是文明的进程向人类施加的重负。
而在埃利亚斯看来,尽管临终与死亡的“袪魅”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文明”表现,但如果彻底废止临终与死亡仪礼,不但会加剧临终者的孤寂,还会危及现代社会纽带的重塑。
医学:生命延长与死亡的社会属性的张力
(一)医学进步:生命延长与生命意义
埃利亚斯对医学进步既延续生命又拷问生命尊严的双重效应保持警醒。医疗技术关注器官的局部过程,或生命的自然过程,而对这一过程发生于其中的整全的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法国历史学家沃维尔曾对现代医疗场景做过批判性描述:医务人员尽职尽责、忙忙碌碌、疲惫不堪,被当作病案的垂死病人被剥夺好好死去的权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改革顾问葛文德指出,在很多时候,面对死亡,医生做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葛文德认为现实中存在三种医患关系:“家长型”关系强调医生的权威角色,确保病人接受医生认定的最佳治疗方案;在“资讯型”关系中,医生提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列举备选方案,由病人及其家属做出选择;“解释型”关系强调,医生的角色是引导病人及家属在生理的生命延续与整体的生命质量之间确立何者优先。“解释型”医患关系对维护临终者的生命尊严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二)死亡与临终的“去社会化”悖论
医学进步对临终与死亡的自然属性的侧重,使在传统社会陪伴临终者身旁的亲人与家庭在现代社会获得技术维度援助,得以尽可能少、尽可能晚地接触临终者。而对埃利亚斯而言,“现代临终者的孤寂”相当程度上来自亲人及家庭对他们的疏离,无论这种疏离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与现代医学及医疗机构的“解放”效应有关。
埃利亚斯期待有一天,人们彼此的牵绊和随之相互施加的压力与限制能够成为医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与医院能够将关注焦点转向临终者的社会性存在及其作为“整体人”的生命意义。现代临终关怀运动认为,姑息治疗的价值不仅在于放弃对临终者的破坏性治疗,转而利用舒缓性医疗技术减轻临终者的生理痛苦,更体现在它为排遣临终者的孤寂、建构临终者的生命意义提供可能。
这种主张在临终关怀运动强调的“灵性照顾”中得到体现。针对临终者的精神抚慰应当减轻其恐惧、排除其焦虑、缓解其孤独、引导其接受现实。临终关怀机构应当通过“身(体)、心(理)、灵(性)、社(会)”关怀空间的构建,响应临终关怀的理念,将自己塑造成为临终者(末期疾病患者)的心安之处。
在埃利亚斯看来,“现代临终者的孤寂”既是“自然”问题,也是“社会”的成就。伴随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型,给予临终病人以人性化照护、满足其基本欲望与需求、承认其自决权、将临终者作为一个“人”来看待,已成为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与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工作者、临终者亲属及家庭、社区与雇佣单位一道共同塑造着临终者最后的生命历程。只有突破“生理人”及“医学人”的视域,才能为维护临终者作为“整体人”及“社会人”的生命尊严与人生价值提供可能。
构型演化与亲人及家庭的临终关怀回归
(一)代际更替、家庭结构变迁与临终者的孤寂
埃利亚斯强调,个人意义的实现与其在生命经历中成就他人的意义紧密相关,试图在个人生命中寻找它独立于他人所具有的意义,徒劳无功。“孤寂”源于下述恐惧性想象:尽管曾生活于许多他人中,对他人而言,临终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他是否存在,他人也觉得没有差别,他人早已截断与临终者的情感联系。
《临终者的孤寂》为展现构型社会学的“权力”思想提供实例。当人们衰老或病卧床榻时,他们的权力优势渐趋下风;害怕失去权力和自主性,特别是害怕失去对已有事物的控制,是老年人恐惧感的主要来源。传统社会的临终与死亡通常伴随不同世代间的权力转移;而在现代社会,新老世代的权力分配在漫长社会过程中已逐步完成,临终及死亡到来前,两个世代已完成权力转移。
现代个体往往远离故土,外出工作。核心家庭取代联合家庭或扩大家庭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规家庭形态,对渐近暮年的夫妻而言,“空巢”是其基本生存环境。家庭结构变迁为医护结构的发展提供前提。“医护机构与家庭的合作加剧临终者孤寂”的论断,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忽略了埃利亚斯一再强调的下述事实:无论对临终者还是其亲属而言,“临终孤寂”问题都是“不以任何生存单元的个别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构型演化的产物。现代临终者的孤寂并非源于医护机构的介入,恰恰是亲人与家庭的疏离使现代医护机构越来越多承担起原本从属于二者的临终关怀事务。
(二)亲人与家庭在临终关怀中的回归
无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现代人格,还是现代劳动制度,都使工作占据现代人的大部分生命。与医护机构及专业人员在现代临终关怀运动中承担的新角色相比,亲人与家庭在临终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缺位或后退,甚至在死亡到达时才出现。
亲人与家庭的回归对排遣临终者的孤寂、让其感到自己仍被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本文而言,让临终者亲属进入医护机构、成为整体性临终关怀团队的一员,或者在姑息治疗技术支持下让临终者返回家庭,都是实现“回归”的可能途径。安宁疗护机构的实践表明,应通过患者及其家属、医护人员、心理师、社工等人参加的家庭会议保障临终者权益,引导家属站在临终者角度思考,将治疗方案与临终事务的决定权交付临终者。
要想让专业化、人性化的临终关怀服务落到实处,让亲属与家庭回归临终关怀、缓解临终者的孤寂,尚有待国家在法令法规、政策制度方面对临终关怀机构运营、医疗保险体系构建、亲属陪护制度建设等方面给予切实支持。在当代中国,临终关怀事业最重要的建设主体应当是政府。
通向完整的美好生活:作为个人规划与国家事务的临终过程
(一)“向死的自由”与临终及死亡规划
对埃利亚斯而言,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衰老与死亡,而个体走向生命终点的方式,将对其生活与存在的意义产生重要影响。这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死亡哲学存在共鸣。
与对“活”的规划相比,临终与死亡更多地被看作无须筹划的人类宿命。埃利亚斯既为“临终者成为检验医疗技术效力的生理存在”这一可能性而忧虑,也为临终者隔绝于社会、孤寂不堪的困境而烦恼。埃利亚斯提出了“‘后孤寂’时代的临终‘何为’”这一严肃问题。而海德格尔的“向死的自由”启发我们:死亡与临终并不是简单被动地走向生活的终结,而是其组成部分,是现代人必须负责任地做出的自我选择。究其本质,临终不属于医护机构、社会工作机构及临终者亲属,而是临终者的生命本身。与对职业生涯、身心健康、社会保障等个人事务的管理相似,衰老、临终与死亡方式的规划应当成为吉登斯意义上的“自我生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规划应当成为在这些特殊时刻尚未到来时就深思熟虑的自我抉择,治疗方案选择、姑息治疗、安乐死、器官捐赠、设立遗嘱等事务都应当成为个体负责任的自我筹划与自我担当。
(二)塑造美好生活与作为国家事务的临终关怀
作为“人口”治理的技术要素,死亡教育与生命教育已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教育事务,为缓解个体与临终相遇时的恐慌、应对“临终孤寂”提供认知与行为指引。
在现代社会,除去猝死等因素,绝大部分人在去世前会遭受巨大痛苦,而得到临终关怀的人只占很小比例。就塑造“美好生活”而言,临终关怀内含社会福利的特质。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2017年与2019年,国家先后批准77家安宁疗护试点省市与试点单位。2019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印发《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相对于临终者的孤独,以“疾病”为核心的传统健康观对“现代医疗手段在临终者身上不再发挥效力”更加敏感,现有医疗保险体系主要将“疾病治疗”费用纳入支付框架,而舒缓治疗与“疾病优先”原则二者间的矛盾使许多临终关怀服务并未包含在医保报销范围内。2016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选择15个城市启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将临终关怀药物和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已纳入的提高报销比例;鼓励医院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引导家属将患者转到临终关怀病房。
尽管对现代医学进步的社会效应保持警惕,埃利亚斯并不否认临终关怀在技术与社会上的双重属性。完善医疗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引导医疗机构与临终者将关注点由疾病的技术治疗转向舒缓性的临终关怀服务,更为激活临终关怀的社会属性提供制度支撑。就缓解临终者的孤寂而言,亲人与家属的回归至关重要,而临终陪护假期制度不完善已成为阻碍回归的重要制度因素。早在1980年,国家即出台《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但对“劳动者亲属在临终前急需陪护照顾”的事实,并未涉及。2018年11月,宁夏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该条例规定,自2019年起,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子女可享受带薪陪护假。北京市也通过修订《北京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地方条例建立家庭护理假制度,护理期间,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等酌情不予减扣。目前,全国多个省市已建立此项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临终者的“孤寂”。
结语
埃利亚斯从“构型”视角出发对文明进程中的现代临终孤寂开展的研究,对梳理与反思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理念与实践,对建构缓解现代临终孤寂、推进临终关怀服务发展的政策与制度,对塑造中国语境下的“美好生活”带来启示。通过研究,本文形成如下基本研究论断:(1)临终与死亡不是“人口”的异常状态,也不是对“美好生活”的否弃,“好好离去”与“好好生活”一样,是生命历程圆满的基本要素;(2)“美好生活”应当是驱除临终者孤寂的生活,临终关怀有助于临终者安详、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3)临终与死亡不是纯粹的个人事务,还是牵涉到社会伦理、劳动雇佣、社会保障及公共卫生服务的国家事务;(4)国家对临终关怀的适当介入及个体对临终的合理筹划,将为塑造完整的“美好生活”提供必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