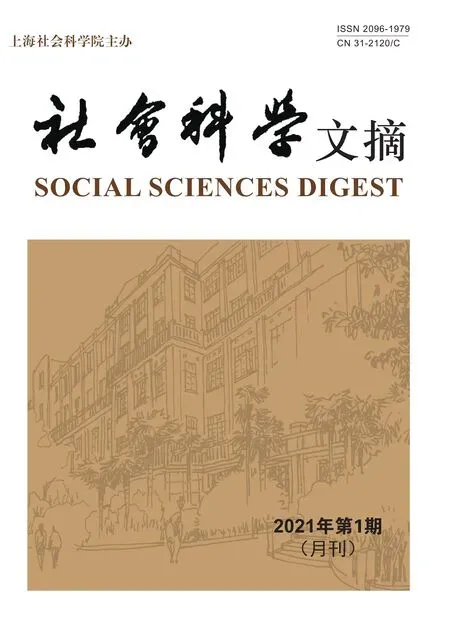重大经济事件视角下的经济学研究创新
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有经济学者曾经总结到:经济学研究应该是学术和思想的统一。这里的学术指科学研究应遵循的规范,是形式上的;思想指创意,是与众不同的新颖思路,是内容上的。
经济学研究者是否自信?在中国的基金行业,基金经理们在推销自己管理的基金时,会强调要建立专业的投资模型,以指导投资操作;并且强调这些模型是毕业于985高校金融工程专业研究生建立的,但是没有告诉投资者的是,他们在管理基金进行投资时,这些模型是弃之不用的。与此对照,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是要依据专业模型进行投资的。
经济学研究意义何在?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世界,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科学依据,但是,对于国内一流期刊重量级论文所得出的结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是否敢于在制定政策时放心大胆地借鉴参考?与我们相对照,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不会充分信任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上的研究结论呢?
历史上三次重大经济危机与宏观经济学理论创新
世界运行的根本规律没有变化,因此经济学研究从亚当·斯密以来,一直是以理性原理为核心逻辑的。但是,现实世界基于规律运行的表现形式则一直在变化之中,需要经济学家去更新认识,与时俱进地发展新的理论。历史上的三次重大经济危机就推动着宏观经济学的变革。
(一)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工程学的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波及全球各地,影响旷日持久,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是产生了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
虽然凯恩斯的理论被视作革命,但是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它仍然有重大缺陷。无论是凯恩斯的追随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没有进行严谨的理论论证;不同之处在于,追随者认同凯恩斯理论的结论,而反对者则全盘否定。凯恩斯理论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差距在于,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市场机制会不起作用,没有从理性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失业和萧条会不断出现。
总的来说,大萧条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凯恩斯在理论上否定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基本结论,罗斯福在政策上也做出与以往不同的积极干预经济的反应。但是他们都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有“思想”没有“学术”。就是说,不管这些理论与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没有从科学规范的角度加以论证,尤其是没有从理性的角度论证。这就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埋下了隐患。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曼昆认为大萧条之后虽然诞生了宏观经济学,但是这个学科缺乏原理,仅仅是宏观经济工程学而已。
(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与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诞生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滞涨席卷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滞涨,从而也未能对此提出有效的干预政策,受其影响的政策当局采取错误的措施反而加剧了滞涨,因此凯恩斯主义受到广泛质疑。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学的“原理”正式诞生。这个原理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理性决策(最优化)被大大强调;其二是理性预期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并起到了核心作用。直到今天,无论是继承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都一致地强调最优化决策和理性预期,以此作为宏观经济学建模的两个基石。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构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不再只是工程学,而是有了原理,只是这个原理与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凯恩斯主义者用这个原理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夯实了基础,使凯恩斯主义的思想从此有了学术支持。相应地,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不再是基础性的,而仅仅是技术性的。新古典主义不再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有问题,而仅仅是在技术层面不认同其市场不完善性的假设。
(三)2008—2009年大衰退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前沿
2008—2009年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引发急剧的经济衰退,并波及全球。这次危机在学术界被称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并再次引发宏观经济学危机。在大衰退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理论已经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它是前述宏观经济学“原理”引入一般均衡和动态过程后的版本。
DSGE理论所做的创新在于,坚持以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所有的经济问题,而不是不同主题适用不同的模型。这个统一的理论综合了如下元素:个体理性选择的出发点、前瞻的跨期动态过程的描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运用,以及不确定性的引入。
DSGE理论从RBC理论发展而来,在大衰退之前已经蓬勃流行,例如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都建立了大型的DSGE模型。尽管如此,它并未能预测并阻止大衰退发生。因此,如同大萧条带来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而滞涨让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危机一样,DSGE理论在大衰退后也受到质疑和诘难,同时连带着经济学的数学化也受到诘难。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DSGE理论的核心思路有什么改变,经济学仍然是在DSGE理论的框架里加入更多的元素,例如将市场的不完全性、个体的异质性、不完全理性和学习行为等纳入到DSGE模型中。
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我国本土经济学研究的创新性质
如果经济学研究有创新的话,这个创新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政策制定产生了实际影响,另一方面是进入了研究生使用的高级程度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卢卡斯等人倡导的理性预期理论和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理论对滞涨是有解释力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的动态不一致性理论也推动了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对政策规则的坚守,从而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他们的理论也都进入了训练博士生经济学研究能力的高级经济学教科书中。但是在我国本土的经济学研究中,从现有发表的成果中看不到符合上述两个标准的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并没有在经济学理论上推动应有的重大创新。我国重大的制度改革往往是先有行动,事后再进行总结。政府历年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则主要依靠相关经济职能部门各自内设的智库进行设计,与经济学学术研究关系甚少。我国学术界也有举办不同层级的评奖活动,所评选出来的理论或者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或者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对经济政策起了建议作用,但是按照曼昆的标准,这些理论大部分只能归类于“经济工程学”,或者叫做“政策学”。它们在根本层面缺乏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逻辑,不能归纳入“原理”之中,因而也更不可能是经济学研究上的创新了。
如果说我们本土的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有思想没学术”的话,那么现在已经过渡到了“有学术”但是欠缺“思想”的阶段,或者说是“学术高于思想”。
这种“思想”的欠缺表现在,我们从国内顶级期刊上读到的论文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上显得高深莫测,但是将它们翻译成文字时却乏善可陈,缺乏故事(即没有思想)。就算是这个学术元素,其中很多也是要打引号的。形象一点说,如果将“有思想没有学术”阶段比喻为肉眼辨别苍蝇和蚊子的话,那么在目前的“学术高于思想”阶段就是利用了实验室高精仪器来进行辨别苍蝇和蚊子。肉眼是否将苍蝇和蚊子分辨开,旁人很容易判断。而操作高精仪器时是否错误,却只有同行才能看出来。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仅仅是辨别苍蝇和蚊子而已,却不必要地利用高精仪器。
本土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接轨国际、思想立足国情
本土经济学研究在学术规范上与国际接轨,在研究内容上立足本国国情,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
(一)学术接轨国际
要让学术与国际接轨,研究人员必须善加利用在研究生阶段接受的系统经济学科研训练,而不是利用自己朴素的逻辑。
例如,即使在本土一流期刊中,有不少文章标榜实证分析,充满了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技巧,但是看不出来作者的专业教育背景是来自经济学专业还是其他专业。当然,更多的文章虽然能看出来经济学专业背景,但是离经济学科研规范仍然有距离。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轻易地创造新的概念却未从学理上论证其必要性和一般性。比如充斥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业绩”一词就不够科学严谨;在同一个“业绩”术语下,不同的文章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新的概念必须有严谨的定义并且能够推广使用从而具有一般性。以自然失业率理论为例,它是弗里德曼提出来的,有明确的严谨的定义,也是用来分析均衡和效率关系的强有力的概念,因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被广为接受,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性概念。
要让学术与国际接轨,还应该清醒地避免直接照搬主流的理论,在学术规范上做出真正的创新。
例如预期形成机制是宏观经济学建模的重要内容,那么是否应该选择理性预期呢?纵向地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里也经历过从静态预期到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再到理性预期的过程。但是,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学建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其说是经济学对现实世界认识的深化,不如说是经济学研究与时俱进的创新。理性预期最终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胜出,并不意味着以前的理论是错的,也不意味着卢卡斯远胜于前人。要知道,在滞涨之前,理性预期毫无必要。这就如同,在卢卡斯之前看病看的是普通的外伤,不需要借助于仪器检测,直接消炎包扎即可。可是在卢卡斯所处的时代,病人的外伤包含着细菌和病毒,必须借助于现代化的仪器来检测。那么,当本土经济学研究采用理性预期方法时,是否思考过,中国目前的经济国情与西方当前的经济环境一致吗?理性预期适合我国吗?
(二)思想立足国情
就思想立足国情而言,无论是选题还是在研究思路设计上,都应该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地方,经济学应该针对这些不同来建模。
第一,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而且,国有企业的动机不是单纯的盈利导向,而是也包含着国家战略和社会责任。于是,很多从经济角度看是非理性的决策,但从政治上看则是理性的。比如中国第一条高铁出现在武广而不是京沪,这与经济利益上的理性相矛盾,但是在政治利益上是理性的。因此,在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行为时,必须对最大化假设进行改造。
第二,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成为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在将政府作用纳入经济模型中时,是将政府作为社会计划者加以分析,还是将其放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中展开研究,需要认真对待。如果作为社会计划者对待,那么政府行为中意识形态动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比重也是影响理论分析的重要因素。
第三,中国经济是发展中经济,经济社会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之中,改革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过程。这种飞跃式的变化完全不同于成熟经济下的边际调整。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强调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这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和线性的,不足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跳跃式的不连续变化。可是本土经济学研究构建了不少看上去高大上的RBC模型和DSGE模型,问题是这些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经济这种处于不断演化和转型的特点。在本土的经济学研究中,更需要采用历史的方法、制度的方法和演化的方法。
去全球化与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学研究创新
经济学研究要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给出深刻的理解。正如大萧条、滞涨和大衰退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和要求一样,目前我们正面临着去全球化的挑战和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环境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地,经济学研究也应该至少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变革和创新:
第一,找到新的方法与技术来分析去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长远影响。新冠疫情冲击和去全球化挑战再次说明我国经济远非成熟静态的经济,再次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并不是连续的边际调整。这表明本土的经济研究绝不能不加改良地沿用过去的方法。成熟的市场经济可以用性质良好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刻画,可以循规蹈矩地找到内点解(interior solution),而与此相反,能够准确刻画中国经济的函数却没有那么好的凹凸性、连续性或者横截面条件,在求解时有可能需要脱离拉格朗日函数、汉密尔顿函数,以其他途径寻求最优解,最终得到的可能是边角解(corner solution);或者根本就没有均衡,研究时需要放弃均衡分析。
第二,供应链受到冲击后的各国政策调整一定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因此仅仅在主流的DSGE模型里计算稳态和均衡至少是不够的,必须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对迈向新的稳态和均衡的过程加以刻画。具体而言,需要刻画主要国家的贸易摩擦和相互制裁。
第三,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对研究思路进行重新设计。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需要分析各种国家力量基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考虑,对中国和国外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分工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供应链的全球分工正处在从“价值导向”的分工体系向“价值观导向”的分工体系转变过程中。各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相互制裁充分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从国内经济的角度看,在假设政府的行为动机时,并不能简单地在社会计划者和公共选择的自利者中选择一个,而是需要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和利益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分析制度环境时,更需要考虑中国特有的人事任命和组织管理特点。对这些复杂因素的分析,必须提出新的建模策略,而目前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通行的方法是不适用的。
第四,相对于实证研究而言,目前更应该在理论研究上投入更多学术资源。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件,从中提炼出规律来。而去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冲击正在进行中,其影响尚未完全展开,因此经济学研究带有预测的性质,那么所需要的是理论建模。遗憾的是国内一流期刊上实证分析的文章不成比例地占领了主要江山。
总之,正如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一样,在去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本土经济研究应该超越现有的通行建模策略和研究范式,针对中国的国情进行理论创新,以正确地解释我们所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