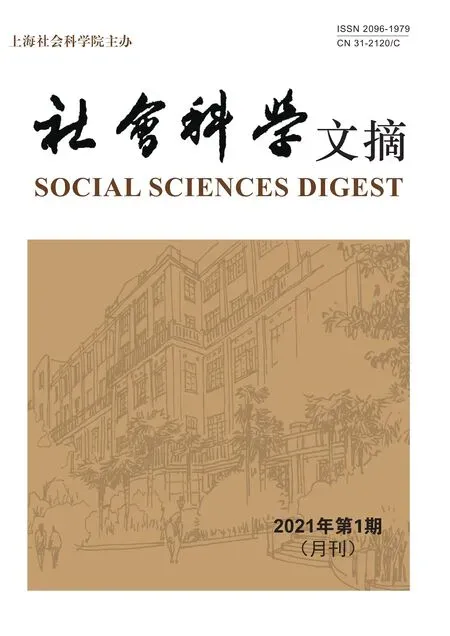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为什么要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问题?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对于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来说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话语是概念的最高形态,它决定着文学理论学术体系的特色,对整个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是思维能力、理论水平、精神风貌的载体,关系到文学理论功能的执行和实际影响力。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不能孤立地进行,须同它的学术体系联系起来,才能获得科学的认知,因为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是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
各种形态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形成多年,在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那么,今天我们为何还要讨论文学理论的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是从现实状况着眼,发现文学理论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上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尤其是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高水平成果不多。
文学理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是它的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和术语是它的话语体系。“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概念以语词的形式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表达思想的内容。一个学科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把语言和思想连接起来,陈述本学科基本的理论内容,构成了表达学科学术体系的话语体系。”所以说,加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
文学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共生关系
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不可分割的。文学理论学术体系是揭示文学本质和规律的成系统的理论与知识,其话语体系则是文学理论和知识的词语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出来。因此,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只有准确、充分地表达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它才是成熟的话语体系。文学理论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它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学科。譬如,关涉文学本质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就同唯物史观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新发现、新见解,必然伴随着新概念和新术语的出现。马克思说:“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任何文学理论话语体系都不是永恒真理的显现,而是在回答和解决当时文学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形成的。当历史进入新的阶段,现实就需要有一个与该阶段相适应、总结该阶段文学基本特征、反映该阶段特有精神的文学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
事实也确实如此。一般说来,文学理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完全是同步的,采用旧的话语体系表达新学术观点的情况很常见,新话语体系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是由文学实践所激发,并且以文学实践为现实基础的。这种“激发”和“基础”,表明它不是要对现实的文学现象作“纯客观”的实证分析,不是仅仅对理论文本作解释学意义上的更新,也不是要将概念或术语作简单的转换或纯逻辑推演,而是要以当下的文学实践为现实基础,以现实存在的文学问题为中心,并且使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升华为概念运动,从而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这样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才会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生命力。
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状况的分析
关于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状况,是一个比较难以下判断的问题,因为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状况十分复杂,其构建的模式和水准也参差不齐。为了直接揭露矛盾,直接透视本质,这里尝试作一下全称性判断的努力。我认为,当下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谓是一锅“夹生饭”。它既没有彻底的“欧美化”,也没有真正的“本土化”,更没有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说,它夹杂了不少国外“新潮”即现代与后现代的术语和方法,可其命题和思维基本上还是“还原式”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注意了对传统文论特色与价值的开掘,可其解释与说明现实文学问题的能力却严重匮乏;它也时常声称自己的研究与话语构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可见不到“指导”的实际成分和实际内容;其教材建设和话语体系多半也是各种话语系统的“大杂烩”,各种名词、术语的“大拼盘”。总之,目前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出现“中不中”“西不西”“马不马”,哪个方面也没说清说透,明显处在“半生不熟”的状态。
这个结论当然是比喻性的,是极而言之的。这个结论并不否认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并不否认某些方面是出现了“术语的革命”的。但是就整体而言,就普遍的状况来说,承认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存在“夹生饭”现象,还是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当前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作用
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和话语没能消化好,是造成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成一锅“夹生饭”的一个原因,那么,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荒疏、漠视和排斥。应该承认,“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比较起来,文学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情况,恐怕比其他学科更严重些。这对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妨害是极其显著的。
从历史上看,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系密切。近些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六神无主,只知拾人牙慧,缺乏自己的创造,就是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与非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区别,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表达,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应用,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是比较起来,弄清楚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显得更为迫切。
一般来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需要主体性,而主体性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其创新性。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需要多方面努力,需要结合本民族文学理论的优秀传统,需要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和发展趋势,需要结合学习国外有益的成果,需要善于提炼出标识性的概念。这样才能说出体现时代进步要求、体现民族思维特点、体现文学创作经验的新术语、新概念、新表述和新范畴,才能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局面。
那么,如何实现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性?我认为,坚持文学理论话语方式的批判性,则是体现其创新本质的关键,也是维护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主体性的首要条件。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处在“多元”的境况中,始终面临着观念与方法的激荡和冲突。在此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倘若丧失了批判功能、辨析功能,也就丢掉了自身应有的锐气和灵魂。有些文学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夹生饭”,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批判性元素造成的。当然,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性,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创新性并非“空中建塔”,也非“推倒重来”,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这里同样存在一个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的问题。严格说来,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并不存在“重建”的问题,有的只是如何进一步“构建”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修养和视野,培养应有的理论历史感,提升参与创造文学理论历史活动的自觉性,对建构未来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十分重要。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为什么需要不断创新?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这是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的辩证法。重视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的作风。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表现在具体研究中就是话语的变革,因为话语的活力就包含在它的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之中。为了认识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的必要性,当我们对目前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分作一下量化分析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的教材和著作,其内容和形式、术语和概念、范畴和方法,至少不少于70%至80%是外来的、引进的,属于我国自己的理论话语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实在少得可怜。
如果我们再作一下质的分析,同样会惊奇地发现,现有的一些文学理论教材和著述,其中许多概念、术语、范畴乃至方法的运用,是相当含混、模糊、曲解或误读的。实现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清晰化,实现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真切性与逻辑性,努力实现对传统文论与外来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恰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地方。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单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建构来说,我们是取得了一些有个性的成绩。但是,面对社会迅猛而独特的发展,面对文学实践活动的复杂多变,面对世界范围内文论话语的竞争比拼,我国文学理论所提出的具有原创意义的话语,还是远远低于文学和社会现实本身所开启的新话语创造的可能性。
当前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存在的问题,且不说中国古代文论,单就西方文论研究而言,我认为对其知识谱系、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在中国实际应用的价值,也认识得不清楚、不彻底,这恐怕是影响我国文学理论原创性话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中的中西汇通,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问题意识”,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有了“问题意识”,又立足现实,才能在理论激荡中站稳脚跟。可是,实际情况却不理想。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缺少的恰恰是“问题意识”。如果这个判断大体能够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创新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依赖依然是严峻而首要的任务。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语境的“多元”,观念的“多元”,使构建统一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确实出现许多不易解决的困难。从宏观上看,各种“新潮”文论涌入及媒介发生革命之后,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的确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种“众声喧哗”不是复调对话或意义增殖的“众声喧哗”,而是无主脑的鹦鹉学舌式的“众声喧哗”,是自说自话、自我消解和耗散式的“众声喧哗”。它不可能有正确的轨道,也没有持续的动力,表演一阵,宣泄一番,就能量式微、偃旗息鼓了。这就是眼下文学理论界沉闷、无语、失声,没有热点,没有焦点,“话语体系”既缺少更新也缺少创造的根本原因。文学理论研究“热点”的缺失,直接导致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产生“无中心”“无聚焦”“无批判”“无建构”的尴尬局面。
改变这种混论、低迷、无力的状态,文学理论界是需要认真反思的。如何反思?除了相信“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外,尊重历史和文论传统,特别是尊重“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则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能否继承和弘扬这个传统,事实上已成检验文学理论发展实绩的一把衡尺,成为提高我国文学理论现有水准的前提条件。
面对困境,有学者采取实用主义做法,主张用文学批评来“替代”文学理论,放弃对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姑且不说这种“替代说”是武断和短视的,单就提出这种意见本身而言,也折射出近些年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在文学阐释能力方面的羸弱和不足。另外,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要创新就应重视其“对话性”。也就是说,要把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探讨、磋商和争鸣在话语层面开展起来,不能把文学理论话语弄成只是在个人的或修辞意义上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真正属于辩证的批判性——即对话性——的文学理论话语已经丢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话语多半是装饰性的、拼凑性的、表演性的“对话”,或者是“假装的对话”,这不能不使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陷入萎缩的泥淖。
加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世界的理性反映,目的是为了达到规律性的认识。文学理论的活动机体只能同相对真理打交道,其话语构建和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弹性和相对性。绝对和武断的做法,在话语体系构建上是不适宜的。文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因此,“可以肯定,科学中有着许多其真理性即使在极遥远的将来也不可怀疑的原理。但是,也同样可以肯定,科学的前沿包含着大量有争议的假说、未经充分检验的事实资料和未经充分论证的理论,这些东西在科学今后的发展中很可能会被证明有误。但这些成分也是科学的不可分割的且富有意义的部分”。我们要理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这个特点。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表达是变动不居的。当陈旧的话语模式或表达方式不能再面对丰富的文本世界和复杂理论现象挑战时,它就应该改变自身的模式或“活法”,或向平行的其他学科看齐,以寻求对象与表达之间的新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一门文学理论分支学科——文学理论语用学——看来是有必要的。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我们不能操一口“纯正”的西方话语来表达中国文学的时代精神,也不能用“地道”的古代文论话语来表达当代中国的文学精神。我们需要面对新的历史方位,创造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属于21世纪的中国化文学理论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