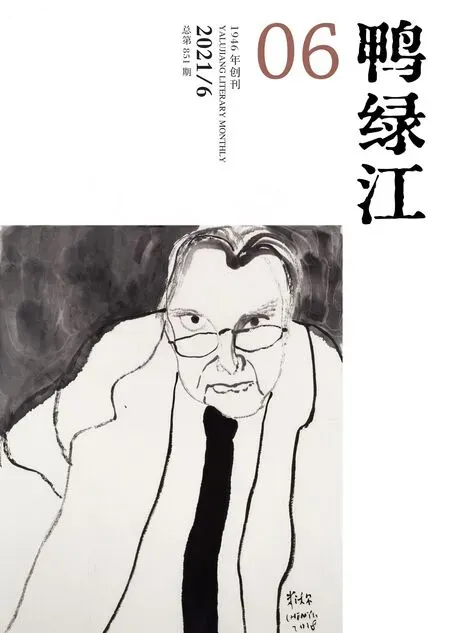疼(短篇)
赵树发
我算是一个资深的痛风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身边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种病。我当时还挺纳闷,我怎么就痛风了呢?后来从正规医院的医生那儿得知,这种病是吃海鲜喝啤酒造成的,进一步的解释是:体内嘌呤过量,尿酸值超标,凝成微小晶粒,阻塞毛细血管,导致局部关节神经疼痛。正所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别看我说得这么轻松,痛风一旦发作,疼起来那真叫要命。我曾经写过一组关于痛风的诗,不妨摘录几句:“痛风的疼,不是要把人疼昏/而是能把昏迷的人疼醒”“曾经的躯壳落荒而去/出窍的灵魂忏悔不跌”“痛风的疼,是疼的制高点/是疼的全部内涵和外延……”这都是我的切身体会,有的朋友说,看了你的文字都疼。我相信每个痛风病人都拥有不下十种治疗的配方,疼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抓住什么都是救命的稻草。我因为犯得比较频,而且年头也不算短,拥有的配方就更多了。一开始我用的是一种注射配方——“6542”配红霉素,一针见效,三针能下地自如行走。但是这种配方来路不明,正规医院的医生甚至觉得不符合医学常识,都不敢给下药。当时,我绝对是因为“有病乱投医”而试用了几次,确实挺灵,但打点滴的时候整个膀子都疼,实在是不敢用了。后来有人推荐我吃一种藏药,叫“二十五味驴血丸”,也挺见效的,但周期太长。我的一个同事推荐给我一种配方:消炎痛两片加维生素B一片。刚开始还行,几次之后就不大灵验了。诗人侯多野推荐我吃痛风舒片搭配饮用降酸茶,我只试了一次,没感觉到有没有效果。后来他又推荐给我一种配方:VB五片加叶酸三片。我买回来一看,药方上明明写的是治疗妇科病的药,气得我直接打电话质问了他,他倒是很平静,说:“你甭管药方上写的什么,那就是治痛风的药,肯定有效。”他好像还很委屈,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但我终究没敢试。在诗人圈里,侯多野是不大靠谱的人,跟我关系还算可以。还有一种药方更邪乎:长白山的黑蚁、神农架的野生灵芝、昆仑山的冬虫夏草、武当山的黄芪——听起来有点像武侠小说。我要是真能找齐这些稀有珍宝,还舍得入口吗?再后来又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土药方,还有水果食疗法、跑步锻炼疗法、泡温泉和外敷疗法……我都试不过来了。其实,治疗痛风最对症的药是秋水仙碱,不过很少有人吃它,正规医院的医生介绍说它的副作用挺大。我现在用的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胶囊,是马爽推荐给我的,据说是一位老中医的家传秘方,真挺神,一粒见效,三粒下去行走自如。
马爽是卖保健品的,就是所谓的直销商。马爽的舅舅是我在企业时候的同事,我调离之后就不怎么联系了。大概十多年前,也就是我刚刚痛风的那个时候,马爽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找到了我,她进门就说:“哥,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在舅舅家见过你,我还要跟你学写诗呢。”我当时一头雾水,怔怔地看着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后来她提到她舅舅的名字,我才礼节性地让了让,但我还是拿捏不准我们究竟见没见过。马爽故意卖这个关子,我估计就是想让我好好打量她,因为她确实挺漂亮的,人也爽快。我说:“你应该跟我叫舅,或者叫叔哇。”马爽说:“咱各是各论,反正你也不比我大多少。”接下来她就开始向我推荐她代理的保健品,滔滔不绝的,绝对受过专业训练,按照她的介绍,那几种保健品好像哪个都能根治我的痛风病。
包括我的老婆在内,没有人奇怪我得了痛风这种病。我自己也挺坦然的,我的饮食习惯和我的生活习惯以及我的做人风格决定了我必须得这种病,不得这种病那才叫奇怪呢。海鲜是我依赖性很强的食品,几天不吃我就会生理失调,以至于我现在出趟远门儿都得带点虾皮或蟹虾酱之类的海产品,以解“内需”之急。我承认,我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忌口,再加上我的应酬颇多,经常推杯换盏,所以痛风难免发作。有那么一次,痛风毫无征兆地发作起来,来势凶猛,势不可挡,疼得我坐卧不安,死去活来的,我甚至都下决心戒酒了。我给我的一些比较知近的朋友群发了一条微信:“这次痛风痛得我痛哭流涕,痛心疾首,痛不欲生,经过痛定思痛我痛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喝酒了!”结果,那几个狐朋狗友看了这条信息后,当天晚上就把我架了出去,灌得我一塌糊涂。
马爽推销给我的保健品,我一口都没吃。保健品既不是药,哪来的药效?不过我还是挺佩服马爽的,她居然能说动我一次一次地掏钱买下这些“不可分类的垃圾”(每次我买完之后都偷偷地送进了垃圾桶)。有一天,马爽又来推销的时候,我调侃说:“我这一年的稿费收入差不多全交给你了。”马爽得意地笑了笑,说:“没有这些保健品你哪来的灵感呀?交给我就对了。”关于痛风,任何一种治疗方式都有一条必备的先决条件,那便是忌口——戒烟限酒,远离含嘌呤高的食物。其实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我还知道痛风只能限制复发,不可能根除。所以,我对任何承诺根治痛风的医生和药品,都毫不犹豫地嗤之以鼻。
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人密切地关注着我的痛风病,这个人就是我的岳母大人。说来也奇怪,我差不多每次痛风发作,我岳母都在现场。确切地说,只要我岳母从农村来到我们家,不超过两天,我的痛风病准犯。这个规律是我老婆发现的,针对痛风的病因和痛风发作的诱因,她研究的领域比我要宽广得多。我知道她私下做了很多调研,对我的衣食住行都做过全面的“考察”,她得出的结论甚至超出了正规医院里的专家的想象。因为看惯了我痛风发作时的疼痛惨状,我老婆可以说已经熟视无睹了。我哼哼呀呀时,她只管负责倒水、拿药,顶多是把我疼得大汗淋漓时湿透了的被褥换洗掉,别的她也确实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岳母对我老婆,也就是她女儿的这种对待患者丈夫的麻木表情很不买账,为此,她们娘俩还吵过嘴。我岳母说:“我来教你怎么伺候病人。”有那么几次,每当我疼痛难忍时,我岳母就倒上半小碗烈性酒,点着火烧一会儿,然后用手蘸着炙热的酒揉搓我脚上肿胀的部位。说实话,这种方法确实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我怎么能忍心让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来为我做这样的服务呢!有一次,我感动得躺在被窝里哭了。我岳母问我怎么了,我说疼。
我和我老婆的老家是一个村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学校。后来又一起考上大学,一起分配到这个城市。我们俩能走到一起并组合成一个家庭,就像我得痛风病一样自然。我岳父早在十多年前就过世了。我岳母平时由我的几个舅哥轮流赡养。我岳母就我老婆这一个闺女,从小就是掌上明珠,所以从我们住进楼房开始,我岳母就盼着能来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我岳母对她女儿的丈夫——我,和我的儿子、她的外孙也喜欢得不得了。只是她每次都是欢天喜地地来,住上几天就不大习惯了。在农村,闷了的时候可以走家串户,东家长西家短的,一天的时间随便就打发掉了。来到城里后,她老人家基本上是一个人憋在屋里,白天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晚上才能看见个人影。所以不到一个月,她老人家就闹着要回去。其实我是欢迎我岳母来的,我不认为我的痛风发作和我岳母来我们家有什么关联。我们现在住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孩子在外地上学,我在外地工作,即使我回到家里,我和我老婆也很少聊天,家里确实缺少一个婆婆妈妈的人。
对了,我忘了说了,我岳母的腿脚也不怎么利索,走道儿一瘸一拐的,上下楼极其不方便。我带她去正规医院看过,检查结果是骨质增生。医生说我岳母年纪太大了,没有住院治疗的价值,就给推荐了一大堆止疼药,主要是双氯灭痛和布洛芬缓释胶囊,疼的时候就顶上几粒。赶上我犯病的时候,我岳母还积极推荐我吃这两种药,说挺管用的。她哪里知道,我们俩得的是不同的病,虽然都是腿脚疼,但她缓解一下就达到了目的,而我得往外排血尿酸。我老婆心情好的时候经常调侃我们,说:“你们两个瘸子,饭好了,赶紧过来吃吧。”
那年冬天,我的痛风病又犯了,同样是在我岳母来我们家的第二天。还是以前的模式:我脚不敢着地,我老婆该上班上班,我岳母伺候我吃饭和吃药。我在家卧床一天之后,单位来电话说有急事,让我过去一趟。我在一个比较富裕的温泉小镇挂职党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应该说工作压力不大,基本上没什么事。这次所谓的急事,是上级来核查农家书屋的落实情况。其实这等事未必需我亲自到场,只是镇里的文化站老站长刚刚退休,换上来的年轻的站长还不熟悉业务,我不去显得不够重视。我穿好衣服,架上双拐就下楼了。我岳母不放心,一直跟到楼梯口,看着我一磴一磴地往下挪。等我挪到我的车跟前时,我岳母在楼上的窗户里探出头喊我,说我的手机落在沙发上了。现在的人好像都患有比痛风还顽疾的“手机综合征”,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它。我跟我岳母说:“你就撂那儿吧,我这就上去拿。”我岳母说:“你别上来了,我这就给你送下去。”我们俩谁都没等对方答话,争着抢着,一个一瘸一拐地下楼,一个拄着双拐一磴一磴地上楼……我们俩在二楼的楼梯口相遇了。我们家住在四楼,这说明我岳母下楼的速度比我上楼的速度快了一些。我接过手机转身就往楼下走,我转身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出来了。我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回头,我能想象到,我岳母应该是爬着上楼的。我知道我岳母上楼后还会在窗户里望着我。我只能强忍着疼痛,假装自如地挪到了车跟前,一直到坐进车里,我都没擦一下我满面的泪水。彼时正值隆冬时节,外面冰天雪地,我的心里却热浪翻腾。我想起了我早年写的一首关于望儿山的诗,其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母亲固执的瞩望/预示了她注定要成为一座山。”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心里是暖的,外面再怎么冷,都是可以忍受的。
前面说了,我在外地工作。其实所谓的外地,距离市区不过六十公里,开车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到镇里去挂职,与其说是工作需要,不如说是我自己争取的。那年省作协有个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市级文联选派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到乡镇挂职,体验生活,采写反映新农村巨大变化的文学作品。我刚好符合条件,在市文联的协调下顺顺当当就批下来了。在选择乡镇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报名现在这个镇了。那个时候我刚刚看完一本莫泊桑的小说《温泉》,让我惊诧的是,莫泊桑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痛风病一说,小说里讲的就是泡温泉可以治疗痛风的故事。我没指望我的痛风病能在我挂职期间治愈,出于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尊重和信任,我倒是想试一试温泉疗法。
马爽在卖我一年多保健品之后,主动放弃了这个行业。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钱挣得差不多了,她毅然决然地退出了直销队伍。我倒是挺欣慰的,一来是我不用再拿钱打水漂了,二来是我不大喜欢马爽干这个,我知道马爽的客户群里,有好几个对她不怀好意。这期间好几家保健品生产企业出事了,被告上了法庭。这期间,还有好几个依赖保健品的养生专家没等拿到退休金就告别人世了。我很庆幸我当初一口都没吃那些来历不明又价格不菲的东西。马爽还是经常来找我,她又开了一个文化传媒公司,干一些商务庆典、企业宣传、文化培训之类的活儿,挺能折腾的。她开始想拉我入股,我没同意,后来又想聘我为顾问,我也没同意。不过我确实帮她不少忙,协调个关系啦,介绍个客户啦,对我来说都是举手之劳。有时候我还亲自操刀,帮她撰写文案,有好几次她要给我报酬,我都谢绝了。马爽说:“哥,这都是你应得的呀,你要不急用钱,就先放我这儿存着,我单独给你开个账户。”那段时间我痛风发作过几次,马爽到处帮我寻医问药,后来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种胶囊,非常神奇,吃上就好。我问她哪儿来的,她不说,问她多少钱她也不说,神秘兮兮的。马爽说:“哥,你下半生离不开我了。”
一般而言,到乡镇挂职锻炼的干部,回去之后都要提拔重用。我身边大多数朋友都是这么认为的,镇里的领导也是这么认为的。报到那天,镇里像模像样地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我在表态发言时照本宣科地说了几句官话,私下里我跟镇里的领导们说,我真不是来镀金的,这绝对不是假话。我说我虽然不是来镀金的,但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热情。事实上,我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力所能及地干着我分内的事。我利用我的资源和人脉,成立了农民剧社,连年举办广场文化活动月,把全镇的业余文化生活搞得风生水起。我拉起的一支演出队伍,上了好几次市级电视晚会,还在省里的比赛拿过奖。我想,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还是认可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来挂职还有一个目的:我想有个合理的、对谁都说得过去的不必经常回家的理由。
来镇里挂职前,我在感情上出了点麻烦。我和我老婆多年前就已经协议离婚。也就是说我老婆已经不是我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了,我岳母也不是我法律意义上的丈母娘了。但是这件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岳母对此毫不知情。我们怎么打、怎么闹都可以,就是不能让老太太知道这事——这是我们当初心照不宣的约定。离婚在城里就像换一种痛风药方一样轻描淡写,但在保守的农村老太太眼里,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如果我岳母真的因为这事有个好歹,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在我和我老婆分居的那段时间里,每当我岳母要来我们家,我老婆都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知道,那段时间我老婆的心里比谁都难受,她曾经私下里哭过好几次,说这叫什么事啊?我妈就我一个闺女,我凭什么不让她来?
我和马爽的事断断续续纠缠了好几年,等我发现她不适合做老婆时,我已经无所适从了。马爽她太执着了,好像做过直销的人都有那个劲儿,以至于后来发展到我走哪儿她跟哪儿的地步。我一再跟她说咱俩不合适,她根本听不进去。她说:“我这一生跟定你了,荣华富贵也好,沿街乞讨也罢,就你了!”她还说:“你要是再回到你那个家,我就登门去找你。”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几年,我搬过一次家,无论是过去三不管的老房子,还是现在戒备森严的高档小区,她都来敲过门。开始的时候,我老婆还问我,她是谁呀?我推脱说是推销保健品的,后来次数多了,这个托词自然就失效了。一般情况下,我回家的时候都是因为我岳母来了,我得装相,我得演戏,这是我不可推卸的义务。可以想象得到,这时候马爽来敲门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儿啊!马爽根据我的车判断我在没在家,后来我不在小区里停车了,她还是来,但日期和时间极不确定,有时候是早晨,有时候是晚上。有一天都后半夜了,她还是在小区里堵住了我。
现在,我只要回到家里,心就慌。半夜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心脏就“突突”地跳;晚上上楼和早上下楼都提心吊胆的,弄得我跟做贼似的。她来敲门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家,有时候没在家。我在家的时候我自己就迎了出去,我不在家的时候我老婆就迎了出去,我岳母偶尔也问:“谁来了?干吗来了?”我老婆就搪塞说:“推销保健品的。”我岳母腿脚不好,自己也懒得走动,所以门外发生了什么事她基本上一无所知,也从来没见过马爽这个人。只有一次,我岳母刚来我们家,马爽也来了。她在楼下喊我,我岳母顺着窗户看见了。我赶紧跑下楼去制止了她。我那天的口才发挥得不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话,平时十头牛都拉不动的她,居然被我说服了。她怏怏地走了之后,我赶紧回到屋里,我岳母居然一点异常也没察觉到。但是,当天晚上,我的痛风就发作了。
我和马爽的事中间漏掉了很多细节,是我故意的。其实我原本不想提到她,也不想把我们的事公之于众。甚至这段纠缠不清的往事我都懒得回忆。那点破事,不但对我影响不好,也会破坏马爽的形象。其实她本质并不坏,只是采取的方式方法太不近人情了。但是,既然故事讲到这儿了,如果不提到她、不提到那段往事真就没法收场。马爽不再纠缠我了,毅然决然地失去了音信,她把电话号码换了,把我的微信也拉黑了。我从一个旧友的口中得知,她现在应聘到外地的一家企业做高管去了。
日子似乎恢复了平静,但是我的痛风还是时常发作。这个时候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马爽,因为只有她有对症的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外地的号码打来的电话,那个区号我非常熟悉,是诗人侯多野所在的城市。接听之后,居然是马爽。马爽在电话里没有寒暄,只是问了一下我的身体状况,然后很平静地说:“哥,你真是个好人。”我赶紧附和说:“你也是好人,咱都是好人。”马爽说:“哥,我一直骗你来着,那个痛风药根本不是什么老中医的祖传秘方,就是一种普通的西药,叫‘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以前我都是从药店里买的,然后分包装一下。”我当时差点气乐了,她蒙骗我这么多年的所谓灵丹妙药,原来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我在电话里没有纠结这个事,随口问了下她的近况,马爽支开了,说了两句祝福的话之后就挂了。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什么,我马上拨通了侯多野的电话,刚一接通,侯多野就说:“马爽在我这儿帮我打理广告公司呢。”我当时就急了,对着电话就吼了起来:“你他妈的算什么朋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这算什么?金屋藏娇吗?你有钱是吧?有钱就牛×呀……”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侯多野用他那浓重的地方口音跟我说:“其实我现在也不想告诉你,马爽她快不行了,你要是有心就过来看看她吧。”侯多野没等我再说什么,迅速把电话挂断了。我顿时感觉急火攻心,疲惫地仰躺在沙发上,目光呆滞,宛若僵尸。
那天我劝走马爽之后,我和我老婆一夜无语。第二天早上,我老婆让我自己做出选择,要么我走,要么老太太走。我说:“我们俩谁都不能走。老太太刚来,有什么理由让她老人家走?我呢,已经下不了地儿了,往哪儿走啊?”我老婆没再言语,头也不回地上班走了。傍晚的时候,我三舅哥开车来把我岳母接走了。我试探着问了问理由,我三舅哥说家里的农活儿缺少帮手。我当时差点儿从床上掉下来:那叫什么破理由啊?!家里的农活儿缺少帮手,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能帮什么忙?也难怪,我三舅哥他就是一个农村的大老粗,哪有城里人那么多鬼心眼儿。我老婆下班回到家,我看出了她一肚子的委屈。我假装怯生生地责怪她说:“你把老太太弄走了,谁来伺候我?”我老婆说了一句极具文学天分的话,她说:“疼在你的腿上,总比疼在她老人家心里好。”
关于痛风的故事到现在已经讲完了。我还想再啰唆几句。我老婆说痛风确实跟吃海鲜喝啤酒有关,但也和“被惊吓”有关。我当然不相信了。我还专门去正规医院问过医生,医生说这也不符合医学常识啊。但是我老婆坚持说,那些呆板的医生只知道医学常识,根本不了解生活事实。
——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