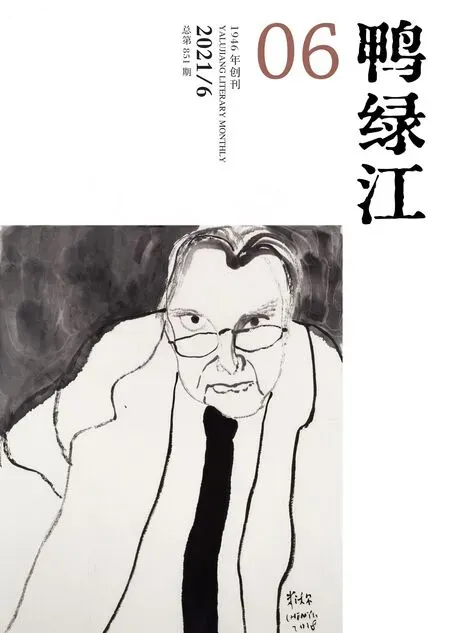节日(短篇)
万 胜
今天是第八天,她最担心的事情如期过去了,自己的身体总是经得住考验。很早,她就在院子里晒了一大桶水。桶是红色的,齐腰高,满满的一大桶水到了中午就会被阳光晒得温热。早上的空气很好,甜丝丝的清爽,像含在嘴里的薄荷糖。昨天夜里她还担心如果阴天下雨了该怎么办。半夜里她便醒了很多次,悄悄地把窗帘扒开一条缝隙察看天气。漫天的星星让她放心了,但是她还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大清早就哗哗啦啦地下起雨来,把她急得不行,赶紧找出大铝锅,放到火上烧水。这时她发现院子里开满了叫不出名字的花,每一朵都有汤碗那么大,各种颜色,说不出的妖艳。她在梦里想,这些就是丈夫种的吗?她记得自己跟丈夫央求过,在院子里种些花,把那架葡萄砍了。那架葡萄每年倒是都结果,但每年都生病,结出来的果又小又软,还不等你去稀罕就烂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丈夫就是舍不得砍。有一天,丈夫从外面挖了一大堆藕回来。她高兴了,她最爱吃藕。把藕切成片,用开水烫一下,再放到冷水里过一遍,拿出来后拌上糖醋盐和香油,清香爽口。丈夫知道她这爱好,时不时地买些藕回来给她吃。但这次丈夫没急着做菜,蹲在院子里对那些藕挑挑选选,挑出两根壮实整齐的耦放在一边,然后到墙根把冬天渍酸菜用的大水缸搬了出来,用水冲干净,又拎上铁锹和铁桶出门,挖了一桶黄土回来铺到水缸里。她就在旁边看着,到后来她才懂了,丈夫是要在水缸里给她种荷花。果然,丈夫把挑选出来的两根藕埋到缸底的黄土里,然后开始往水缸里注水,水把黄土都淹没了才住手。丈夫是个喜欢沉默的人,就算是为她做了再多也不愿意说出一句讨好的话。但是她懂。她有时候想,自己要是不懂该多好呢,就不会生出愧疚感。
不知内情的人会觉得院子中央放着一口大水缸很突兀。因为院子并不大,前后走不出十步,左右也走不出十步,况且还有一架葡萄。院子的地都是用红砖铺的,铺得很好看。丈夫竟能用一块块方砖铺出螺旋式的斜纹来,水缸正好放在螺旋纹路的中间,好像在铺设地面时就预先设计好的。丈夫每天都用水把院子的地面冲刷得干干净净,把砖的红色洗得像红地毯一样鲜亮。她在家从来都是打着赤脚的,甚至会整个身子躺在地上。整个夏天她都很迷恋那种凉丝丝的感觉,有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是一条蛇。丈夫说过她的身子很软、很凉也很滑。
没过多长时间,第一枝荷花就从水面上探出了头,像一支精致的小毛笔。接着第二枝、第三枝也都跟着钻出来。来串门的人都恍然大悟,哦!还真不错啊!所有人都知道丈夫非常宠她,也都嫉妒他们能如此恩爱。但没有一个人能够钻进她的心里去问一问:“你爱你的丈夫吗?”
“不爱。这是真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是个好人,他对我好。”
“就这么简单?”
“不,这不简单。”
太阳升得越高,仿佛离人越近,让人越来越燥热。大红桶的内壁上生出了一层小气泡。她轻轻地敲一下红桶,那些气泡就脱离了内壁,扶摇直上。水在升温,用手试着还是有一点凉。她有点着急了,尽管时间还早着呢。需要准备的事情还很多,洗澡仅仅是第一步,但没有这第一步,后面的许多步都没办法进行。她回到屋子里,把所有的洗浴用品都拿了出来,放到一个木架上,排列有序。燥热的空气让她的皮肤上溢出一层细细的汗珠,脸蛋儿也镀上一层热红。她对自己说再等一等,耐心一点,想一想这份耐心的付出是值得的就好了。为了不让阳光把自己晒黑,她躲进葡萄架下,坐在一只木板凳上。原本有一只蜻蜓在葡萄架下飞来飞去,见她来了就飞了出去,歇在荷花骨朵上。荷花骨朵像个小巧玲珑的饺子,绿中透着粉红,要不了多久就会绽开。另外一只更小的花骨朵很霸道地穿透了一片不大的荷叶。她想一定是因为缸口太小了,它只好穿透荷叶让自己探出头来。它总得出头吧!她突然就觉得有点忧伤,觉得那缸里的荷花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还有点像自己。她环顾着这个不大的院落,高高的围墙和房屋,让她只能仰头看天上飞过的鸟和飘过的云彩。当然谁也没有不让她走出去,她是自由的。为了不让她受累,一结婚丈夫就让她辞了原来的工作,一心在家享福。这也是她同意的。丈夫说宁可自己累点儿,也不愿意让她过早地被生活的担子和工作的压力折磨成老太婆。对于他的这些话她从来都不反驳,他想怎么做她都同意,即使她在心里很反感,也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她觉得作为妻子,她能为他做的太少,她的心中始终对他存在着愧疚感。
两个相爱的人结婚了,会是什么样子呢?类似这样的问题她不知问过自己多少遍。
其实她是在说:“如果我和他结婚,而不是跟现在的丈夫结婚,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天天都像过节一样呢?”
她一想到他的时候,浑身就那么一热,一股悸动从心底往外扩散。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种味道起初是从他的微笑中传递出来的。她从认识他那天起就知道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后来她调皮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爱笑了。”他说为什么?她说:“你的笑里有只钩子,一笑就会把人勾住。”他捏着她的小鼻子说:“对,你就是被我勾住的。”她把头靠在他的胸脯上,说:“既然你都勾住了我,就不允许你再冲别人笑。”他说他只有这一把钩子。
她发现如果死心塌地地爱上一个人的时候,说的玩笑话都是真的,都能拨开皮肉见到骨头。但是这份爱来得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相见她都像块大力胶一样黏在他身上不肯撒手的原因。
可毕竟是晚了。他说:“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我很清醒。”她说,“我什么都不求,只求在想见到你的时候就能见到你。”
他沉默着。他一以沉默的姿态面对她,她的心就不踏实了。所以她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他是对的,需要冷静,能够这样已经该知足了。
又是那么久没见面了。真想啊!这句叹息悄悄地就触碰到了埋藏在心底不敢示人的那种幸福,她仿佛是在跟自己撒娇,连叹息都分泌着甜蜜的味道。那只蜻蜓被她幸福的叹息惊到,飞离了荷花,停在大红桶的沿儿上。她赶紧去用手试水的温度,差一点被小木凳绊倒,心里笑话自己怎么就按捺不住了呢。
她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站在日光下。身子白得刺眼,有些地方血管的脉络清晰可见。她的皮肤仿佛比别人的薄很多。他有一天对着她的身体想到了一句诗:“揭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她红着脸说:“我没你说的那么好。”他不说话,用手轻轻地在她的皮肤上摩娑,细细的,痒痒的。她想笑,但不敢,好像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她想不明白他那双从废墟里扒出六个孩子的手怎么会柔软得像缎子一样。她仔细端详过他的手,被瓦砾伤害的疤痕还在,让她心疼不已。“当时一定很疼吧?”她问。他说:“当时看着那些孩子只觉得心很疼。”他的手抚摸着她的肌肤,他的认真劲仿佛是在做一项情愿付出一生的精力来完成的事业。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很莽撞,急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男孩。不管怎样,都让她陶醉,让她幸福。让她觉得和他在一起很踏实,真就是世界末日突然来了,她都不会害怕的那种踏实。爱情真好!
“你说什么?”
有一次她和他在一起时,情不自禁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爱情真好。”她羞赧地笑着,眼神温顺地伏在他的胸膛上。
他竟然叹了一口气。胸腹起伏了一下,使她的眼神像蜻蜓一样飞离,落在他的眼睫毛上。
“你怎么了?为什么叹气?”
“我们已经过了谈情说爱的年龄。”他说。
这是他唯一让她感到不安的地方。他总是那么冷静地对待她的感情。她的情绪就像是坐在火上的水壶,每当壶里的水就要翻滚时,他就会添些冷水进去。这应该是一个成熟男人应该有的那种理智吧。成熟的男人让人着迷,尤其是他那让你捉摸不透的内心世界,就像一棵粗壮的大树,当你抱着他的时候,他的敦厚和坚挺让你无限依赖,你却无法知道他埋在地下的根系有多庞杂,扎得有多深。其实女人真正想要的并不多,也就是那份敦厚和坚挺。
水掠过肌肤,凉丝丝的。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还是令她浑身的皮肤一紧,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就在这时,大门被人敲响。为了安全,在脱衣服之前她把大门反锁了。她赶紧用浴巾把自己的身子包裹住,冲着大门问:“谁呀?”“是我。”丈夫在外面回答。她心里纳闷,丈夫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呢?
丈夫进来只淡淡地问了句:“你要洗澡吗?”
“是。”她的心里突然就有一点慌乱,“天太热了,我冲个凉。”
丈夫没再说什么,独自走进屋里。
刚才的心境被搅乱了,她一个人站在红桶旁边不知所措。这很正常啊。她在心里替自己找理由。天气闷热,洗个澡是应该的。丈夫怎么会怀疑呢?可是,他今天的态度有点不对劲儿。她的心上长满了又细又长的触角,那些触角能感知到别人身上最微弱的变化。不但丈夫说过她于敏感,就连他也说过。女人都这样的,女人的感性有时候让男人觉得不可理喻。所以女人的爱不需要理由,只要爱了就不想退路,不计后果,越是阻挡越是执拗。至少她是这样的。扯远了。她心里生出一点点委屈,对丈夫说:“你怎么了?”丈夫躺在床上没回答。她又问了一句:“你怎么了今天?”丈夫说:“没事,需要搓后背的时候叫我。”
她听出丈夫的话语有冷漠的成分。她有点生气了。她一生气就觉得埋在心里的那份愧疚减轻了。有时候她甚至想,如果丈夫对她不好,像别的夫妻那样经常吵架,她就心安理得了。在她最想他的时候,她会毫无来由地发火,逼丈夫就范。可是丈夫从来都忍着她,让着她,让她的无名火烧不起来。过后她就觉得自己太荒唐,太不像话,于是那份愧疚感就更强烈。她觉得自己应该对丈夫更好才对,也想过干脆断了和他来往的念头,老老实实地做人家的老婆。可是这由不得她,没过一分钟她就又开始想他了。那种欲望比什么都强烈。
她把水浇到自己身上。水顺着雪白的肌肤快速地流淌下去,每个毛孔都被唤醒了。如果不是身体每个月都要例行公事地含蓄那么几天。她每天是离不开和水亲近的。隔一天不洗澡就会觉得浑身痒痒,皮肤干渴得像沙漠一样。每个毛孔好像都被脏东西填满了,想一想都觉得难受。
“女人就是水。”他说,“水一开始都是最纯净的,一旦被污染了就不纯净了。”
“我呢?”她问。
他说:“你很纯很纯,纯得我不忍去碰,怕自己把你给污染了。”
她回忆着他的话,心底又开始分泌幸福了。她把毛巾裹在手上,用力地搓,皮肤被搓得通红。毕竟一个星期没这么彻底地洗澡了,她不能允许有一点点脏东西残留在自己的身体上。她要让自己的身体清纯得像泉水,干净得像月光。还要淡淡的香,她希望他闭上眼睛就能够有种走进花园的感觉,这个花园里只有一种花,那就是她。
把沐浴露的泡沫都用水冲干净了,红桶里还有好多水。她把准备好的香水滴进桶里几滴,然后把自己装进了红桶里,水刚好漫到桶沿上。她就那样静静地等着水里的香味渗进皮肤里。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回忆着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为她的身体而陶醉的样子,还有她感受到他怀抱的那种温暖。她闭着眼睛,细细地呼吸,已经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清香了。突然感觉到自己的鼻尖儿痒痒的。微微张开眼睛,她看见那只蜻蜓安安稳稳地停在上面,她心里好笑。那种笑显然没有掩藏住,蜻蜓从容地抖动翅膀飞走了。她的眼神一直跟着它,它飞得很缓慢,好像是在有意识地牵引她的目光,把她的目光牵引到那朵荷花上。她突然笑了。因为缸里的荷花和桶里的她简直太像了,都那样静静地等待着开放。也许荷花也在观察她呢,真有意思!她这样一想,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她决定从红桶里出来,进行下一个程序。
丈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是睡着了。她裹着浴巾走进来,坐在梳妆台前端详自己。今天该怎么打扮自己呢?她回忆他是怎么说的。女人真正的美不是装饰出来的。他说的有道理。她从来都找不出理由来怀疑他的话。但是大多女人的自信是靠化妆树立起来的。女人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这是个悖论吗?他说浓妆的女人很腻,很俗气,就像一块肥肉。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男人离不开肥肉,但他是不喜欢的。他喜欢轻描淡写,喜欢含蓄,喜欢安静,喜欢淡雅。她在没认识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打扮自己。他做了一个比方,化了妆的女人好比是成熟的旅游区,人为设置了很多假山假水,让人扫兴;不化妆的女人好比是未经开发的自然风光,浑然天成的美才真正让人流连忘返,即便是有些遗憾也是美的。所以,每次她和他见面时都尽量保持自然本色,顶多涂一些润唇膏。她怕自己在他的眼里成了一块肥肉,她怕他会厌倦她。听很多女人都说,男人厌倦女人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稍不留神就发生了。而且这种厌倦是必然结果。她怕这种必然发生在她身上。她从来没有想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她该怎么接受。她不敢想,所以就始终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就只能处处小心着自己不要做出让他感到厌烦的事情。她是在按照他的理想塑造自己,她甚至想自己来到世间这一回,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他。
其实穿什么衣服她早就已经选好了。那条素雅的裙子两天前她就洗好熨平了,像个宝贝一样挂在衣橱里。之所以选择那条裙子是因为那条裙子是他给她买的唯一一件情人节礼物。他说这条裙子很多人都在穿,但是没有人能比她穿着更合适、更美了。这条裙子不应该是买来的,而应该是长在她身体上的一部分。她答应他,只有在最重要的节日才穿它。精心打扮的过程中仿佛他一直在她的身边做指导,这是一个让她无比幸福的过程。只要他喜欢,就是她的幸福。她跟镜子的里自己说悄悄话,无意中却看到镜子里的丈夫并没有睡着,而是很专注地看着自己。她的心怦地一响,赶紧让眼睛离开了镜子。
“你,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试探着问丈夫。
丈夫沉重地叹口气:“我头有点疼。”
“感冒了吗?”她回头问。
“大概是吧。”丈夫翻了个身,把后背留给了她。她犹豫了片刻,起身向丈夫走过去,坐到床边,用手去摸丈夫的额头。的确有点烫。
“吃药了吗?”
“在单位吃过了。”
“我给你揉揉吧。”
丈夫转过身子,平躺着,闭上眼等着她的手。她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所剩时间不多了。她两只手在丈夫的太阳穴上轻轻地揉,频率很慢,时间却过得很快。丈夫今天比她还要耐心。换在平时,丈夫就会说:“你歇一歇吧,我一会儿就好了。”可今天他始终闭着眼睛,就是不说话,仿佛有意跟她较劲。
“好点了吗?”她问。心里想如果他说好了,她就可以离开了。丈夫不答话。
“我给你倒杯开水吧,喝点热水就好了。”她想到了脱身的办法,起身去找杯子和暖水瓶。
丈夫突然说:“我难受。”
她端着热水回来,心里的愧疚感深重了。强迫自己坐下来,再次把手放到了他的额头上。
时间由太阳引领着急匆匆地走。她越来越急躁了,手上也毛草起来。丈夫始终不为所动。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对丈夫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丈夫的眼珠在眼皮下痛苦地转动着。她知道丈夫不希望她这个时候离开他,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这个节日她都准备了好些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她的欲望不断膨胀,她的心已经无法装得下了。她必须去,义无反顾,死心塌地。
她不等丈夫做任何表态,快速而慌乱地从衣橱里拿出胸罩、内衣、袜子、裙子,一件一件往自己身上套,来不及照镜子就跑到门口穿上了高跟凉鞋,把挎包拎在手里。这个时候她想她应该对丈夫说些什么。他是个好人,虽然她不爱他,但是他对她的爱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她的内疚感让她的脚步突然变得很沉重,但只要跨出了这扇门,她就会觉得轻松一些。她就会想人活这一辈子不能委屈了自己。
她在推开门的那一刻,回头对丈夫说:“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买回来。”
丈夫睁开了眼睛,眼泪含在里面说:“他都死去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忘不了吗?”
她惊愕了。许久,身子软下来,虚脱地靠在门框上。她咬着嘴唇,眼泪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
“为什么每次你都要这样提醒我呢?”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