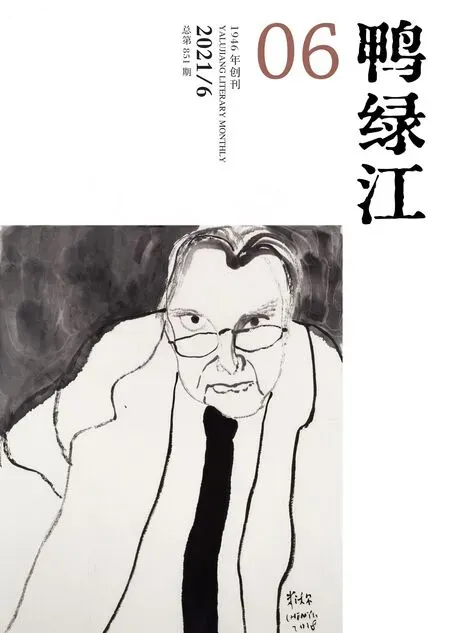古柏芬芳(短篇)
杨家强
林寻顶着小轻雪孤身进山寻大清庵。已是初春,绵软的雪絮微微有些粘,落到身上就不肯离开。林寻披着一身轻雪穿过稀疏错落的农舍,走到最后一户人家门口时,天突然暗了下来。
林寻不由得看了看腕上的老手表。泛黄的表盘上时针指向两点,分针与秒针刚好在十二点重叠,林寻的心一颤。多年来,她从不在这个时间看表,因为母亲就是这个时辰走的,在老街昏暗的小屋里,母亲从枯瘦的手腕上吃力地脱下手表,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把那块表戴在林寻细嫩的胳膊上就咽气了。林寻从未见过父亲,小时候每问起父亲,母亲总是低下头看着腕上的手表沉默不语,为此,她会数日得不到母亲的理会。林寻时常听到有人背地里议论她是“婊子养的”,她以为自己的父亲是块手表,所以人们才这么说。后来,林寻渐渐懂事了,就不再问母亲了。
林寻停住脚步,她有些纳闷儿,才两点,天就这样暗了?不由得抬头张望。是山,两座陡立对峙的山峰挡住了光。
林寻不经意地向院子里瞟了一眼,透过低矮的石头院墙,有个小男孩抱着一捆干草,蹒跚地朝院子东边的那头黑驴走去,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儿隐在干草的缝隙间,一颤一颤的,似在抽泣。男孩的头顶和身上落满了雪,看样子,在外面待的时间挺久了。男孩儿的头发有些长,有的盖着耳轮,有的向外翘着,上面落满了雪,也像一捆干草。他见到林寻,紧走了几步把草扔到驴旁边,便匆忙往屋子里跑,边跑边往院外看,嘴里不停地喊“爷”。驴没有急着吃草,扬起脖子呜啊呜啊地叫了起来,两个粗大的鼻孔往外喷着热气。这时,从低矮简陋的老石头房子里走出一位驼背的老男人,他吃力地直了直身子,勉强抬起头朝院外张望。林寻犹豫了一下,进了院子。
林寻上前问老男人大清庵在哪儿?老男人摇摇头:“大清庵?”林寻说:“康熙年间的老尼姑庵。”老男人依然摇头:“尼姑庵?”林寻进一步询问,就是尼姑住的寺庙。老男人说:“庙啊,黑桦谷里有座庙。”林寻急忙问:“咋走?”老男人指着眼前两座山峰中间的谷口说:“这是谷门儿,往里走,一直往里走,走出黑桦林,在深谷的阳坡上,庙里有两棵很粗的老柏树,见着老柏树就是了。”两人说话时,小男孩扯着老男人的衣角一直盯着林寻,眼睛水汪汪的,确是刚哭过的样子。老男人把一双大手捂在小男孩的脸上:“山宝儿,看这脸冻的,快跟爷回屋子里吧。别再抱草了,草都快把驴埋上了。它吃不了,都踩白瞎了。”山宝儿像受了莫大的委屈,撇撇嘴,眼泪噼里啪啦就掉下来。老男人赶紧说:“抱吧抱吧。抱累了就回屋子里。”又自言自语道:“还是驴好,一把干草就能养住。人咋就留不住呢。挺好的一个媳妇,咋说走就走了呢?好好的一个家,说散就散了,让人一点儿盼头都没了。”老男人说着话,把男孩头顶的雪轻轻抹掉,抚摸着他的头顶安慰道:“山宝儿,别哭了,你妈去城里给山宝儿挣钱去了,过些天就跟你爸一起回来了。”
林寻走出院子,突然回过头,老男人已回到屋子里,院子里只剩下小男孩还站在原地看着她。见她回头,小男孩赶紧躲到草垛边,眼睛依然水汪汪地盯着林寻。林寻猛一转身,急着向山里走去。
林寻沿着山溪边隐约可见的山路,只身走进幽暗的山阴里。山溪的落差大,冰面尚未完全融化,溪流挤在毫无规则的冰洞下急促地向下游涌去。哗哗的山溪像城市拥挤的车流,繁华喧嚣。林寻想到了离家出走的女人。哪个女人不爱繁华呢?可繁华过后又怎样?林寻是经历过繁华的人,渐渐地她厌倦了,腻烦了,诸事缠绕成一个大大的死结时,她走出了家门,除了那块老手表,她把一切抛在了身后。
早年,林寻独自进山写生,在山林里迷了路,刚好遇到在林子里采野茶的妙然师父。林寻跟着妙然师父走出山林已是傍晚,妙然师父留林寻在青岩庵住下。青岩庵不大,隐藏在半山腰,只有妙然师父一人居住。林寻因钟情山中景致便一住数日。临别,二人均有些不舍,妙然师父嘱咐林寻,烦心时来住住也好。林寻因琐事缠身,一去多年再未回来。
林寻这次能决绝地了断一切,与潜意识里一直向往青岩庵不无关系。妙然师父见了林寻,平静地说:“就知你迟早会来。”令林寻想不到的是,而今的青岩庵香火极旺,香客繁杂,青岩庵也不再是妙然师父一人居住,又增加了好几位居士、尼姑常年居此,这让林寻感到有些不适。妙然师父了知林寻一心想寻个清静处独居,便告诉林寻,她的同门师姐妙本师父在大清庵已圆寂数日,因大清庵太过冷清落魄,至今无人愿去,如林寻不怕孤寂可去那儿久住。林寻自然求之不得,她第二天一大早便告别妙然师父,只身前往大清庵。
据妙然师父讲,大清庵是清康熙年间一位将军为其女厨出家所建。民国年间重修,改名资福寺。因正殿前曾有“佛堂神阁”的老匾,当地人俗称“佛堂庙”。难怪无人知道大清庵呢,它早已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但林寻却喜欢称它最初的名字“大清庵”,有来头,有渊源。林寻一心想找这样一处无人的地方独居。
山路呈缓坡向上,而旁边的溪水却一直是向下流淌着的。林寻走得有些口渴,她蹲在山溪边,伸出双手探到冰洞下,捧起水喝了一口,清冽微甜,果真是好水,她一连喝了好几口。林寻站起身,边抖着手上的水珠,边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溪流,自言自语道,漂得越远就越混浊。林寻总觉得山外的水像浸着油,有一种说不出的腻味儿。
林寻无意间又看到了那个小男孩。他站在自家大门口,面对着林寻这边,不知道在干吗。林寻一扭脸,快步往前走去。林寻想到了将军的那个女厨。能让将军为她修庙,想必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林寻清楚,其实越是非同寻常的人就越有纠缠不清的困扰,尤其女人。
林寻走出峡谷的阴影来到半山腰,隐约闻到一股清香,她有些纳闷,这是哪儿来的奇异香气,以往从未闻到过。疑惑间,她寻着香气,终于看到寺院里两棵老柏树的树冠。林寻疾步来到寺院的半圆形石拱门前。石拱门洞口有一扇厚重的木头门,门半开着。林寻侧着身子用肩头把门顶开,走进仅供一人出入的石门洞,她跑到老柏树下,伸出双手抱了几次也没有抱住,又试着抱另一棵,依然抱不住。这两棵老柏树,像两座陡立的山峰直指天空,林寻惊叹,这老树恐怕上千年了吧?难怪有奇香呢。两棵老柏树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红石桌,石桌周围有三个石凳,看着像是缺少一个席位。林寻不知道原本就这样摆放,还是年久缺失了一个。石桌的北面有五间正殿,应为早年的大清庵,现已残破不堪。正殿的背后是直插云霄的陡峰,陡峰呈半弧形走势,紧紧围拢着寺院。山峰的末端是深不见底的断崖。整个寺院只有石拱门这唯一一处通道。林寻暗叹,藏在深山里的大清庵果真不凡。这里清幽、寂静、独立,虽有渊源却鲜为人知,既有天险为屏障又有寺庙这个特殊身份为庇护,清静无扰,正是她心底所求。林寻顿时有了踏实的归宿感。她喃喃自语:“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了。”
正殿的前面有两栋偏殿,东西各四间。唯东边紧靠北的两间看着较为完好,很明显是修缮过的,该是妙本师父的住处。林寻走进去,外间有锅灶和几件简单的厨具,对着门的南墙脚有一个大青石水槽,石槽前放着两只水桶。石槽边放着一垛白菜和一堆土豆。北墙角放着两个粮袋,有多半袋子米和少半袋子面。里间有土炕,房内微微有些暖气,并无一丝寒意。林寻把后背上的行李卸下放到炕上。随后,她来到正殿前,抖落身上的轻雪,整理好衣裳走进正殿。正殿里供奉的是一尊与真人大小相仿的老青石佛像,佛像的左手从腕间断掉没了手掌,右手臂从肩胛处彻底断掉了。佛像的面目已被毁得模糊不清了,林寻辨不出是哪位神佛。看来,当年这深山里也未免劫难。好在佛像的身形尚存,终究是受了数百年香火的老石佛,沧桑厚重,让人顿生敬畏。
林寻虽不是出家的佛门弟子,但对古佛、老寺院充满了虔敬。她双手合十敬香跪拜:“此生就侍奉你了。”这时,林寻忽觉一点冰凉的东西落入后脖颈。她抬起头,见是细碎的雪粒从漏顶的残瓦洞飘下。
傍晚,林寻早早把石门洞的老木头门关好,又抱起门后的大木棒,将门从里边顶严,仿佛把整个世界都关在了门外。
第二天早起,林寻去附近的林子里拾柴。她背着一捆干木棒回到石拱门时,见有个小男孩正坐在石门墩儿上打着盹儿。她脱口叫道:“山宝儿。”山宝儿忙站起来,怯怯地蹭到林寻近前,从裤兜里掏出一只黝黑锃亮的大冻梨放到她手中。林寻拿着梨呆立着,有些不知所措。山宝儿从裤兜里又掏出一只冻梨,双手捧到嘴边,使劲儿啃了一口:“好吃,真好吃。”看一眼林寻,又啃了一口:“解渴,真解渴。”林寻犹豫着将冻梨送到嘴边,她眼睛看着山宝儿,轻轻咬了一口,黝黑的冻梨上露出月牙儿般雪白的果肉儿:“嗯,酸甜解渴。”山宝儿突然兴奋起来,他像鸡啄米似的夸张地啃起冻梨来,眨眼间他就把手里的冻梨啃得只剩下一个小核了。看着山宝儿那无法言说的开心劲儿,林寻有些措手不及。山宝儿扔掉梨核,把身上带的另外四个冻梨全放到石门墩儿上,蹦蹦跳跳地跑下山去。林寻肩上背着柴,手里托着只咬了一口的冻梨,站在石门口,眼盯着山宝儿歪歪斜斜的背影变得越来越小,直到眼前一片模糊,她才想起把压在肩上的那捆木棒卸下。
林寻跑到高坡上,双手搭在眉宇间向山谷里张望。她看到山宝儿已走进最深的谷底,大概是累了,他走得慢慢腾腾的,边走边不时地回头看看。
林寻跑下山坡,避着山宝儿的视线来到谷底。她偷偷尾随在山宝儿后面,直到看见山宝儿到了自家大门口,她才急忙返回。
林寻从附近的溪流中找到一处天然的小石潭,这里阳光充足,石潭里的冰已化净。林寻每天拎着水桶去下面的山谷里打水。这天,她打水时无意中竟打上来一条泥鳅鱼。她连忙把水倒回石潭。水花平静后,林寻发现,泥鳅鱼并没有慌忙隐遁,依然在石潭里悠闲地游来游去,它青幽的身子在清澈的水里充满了灵性。林寻忽然生起画画的念头,她不记得自己多久没画画了,她曾经那么如痴如醉地迷恋高古水墨。
林寻出神地注视着小石潭里的景象。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翠绿的水草间有这么多的泥鳅在闲游,可她在这儿打了许多次水竟没发现。这时,她看到了水中的自己,一个清秀简洁的布衣女人,与那个披着一头长发背着画夹满世界疯跑的女孩子判若两人。她不由得摸了摸头顶,那一头令人羡慕的长发也被她丢得干干净净。她不记得已经多久没有打量过自己了。
站久了,林寻的腿有些麻,她向旁边挪了挪脚窝儿。这一挪动,她看到水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倒影,一个站在她身后的小男孩。林寻没有回头,她对着水面轻轻唤道:“山宝儿?”山宝儿凑上前来。林寻揽住山宝儿:“真是山宝儿,你啥时来的?”山宝儿说:“来半天了。”林寻说:“咋不叫我。”山宝儿说:“怕把鱼吓跑了。你看了老半天,咋还不下手抓鱼呀?泥鳅鱼最难抓,我抓过好几回,它都从手心里溜跑了。我妈最会抓泥鳅鱼,抓上来就直接给我烧着吃,泥鳅鱼用干树枝一烧,能烧出一层黄油,真香啊。”山宝儿的眼睛亮亮的,红润的小舌头不停地舔着干瘪的嘴唇,满脸的幸福。大概是在寺院待久了,林寻下意识地合拢双手,但随即又分开了。双手再次合拢时,轻轻扣在山宝儿的脸蛋儿上:“哦,你有点开心了,你看上去好多了,真棒,你真棒。”
林寻重新打好一桶水,低头看了看,除了几片嫩绿的水草叶儿漂在水面,其余啥也没有。林寻提起水桶说:“山宝儿,咋又来了?爷奶知道吗?”山宝儿摇摇头。林寻说:“回家吧,山宝儿,别让你爷奶惦记。”
林寻拎着水桶一口气走到石槽前,把水倒进石槽里。她用手背儿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身子靠着墙歇了一阵子,才拎着空水桶去打水。走出石拱门洞,她看到门口的石墩上放着五个黏豆包。她轻轻喊了声山宝儿,又向四周看了看,未见山宝儿的影子。林寻放下空水桶,把黏豆包拿进房里。
林寻回到石拱门前,见山宝儿从不远处的杂木林子里出来了。他怀里抱着一小捆干树枝来到林寻近前。林寻接过干柴,让山宝儿坐在石头门墩儿上歇歇。林寻说:“山宝儿,妈妈在冬天经常进山拾柴?”山宝儿眼睛看着远处的林子点点头。林寻又说:“妈妈拾柴累了喜欢吃冻梨解渴?”山宝儿又点点头:“妈妈临走的前一天还带着冻梨去山上拾柴,那天她拾的柴最多。”山宝儿用力地展开双臂,“拾了老大老大的一捆柴。妈妈说,我家的老房子处处漏风,一时也离不开柴火。”林寻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山宝儿,歇够了就回家吧。出来久了爷奶会着急的。”
“我帮你拎水。”山宝儿突然起身,抢过林寻手里的水桶向谷下跑去。林寻追到山溪边,山宝儿已打满一桶水,双手拎着水桶摇摇晃晃地往回走。林寻忙接过水桶问:“山宝儿,几岁了,这么有劲儿。”山宝儿说:“九岁了。”林寻又问:“上学了?”山宝儿说:“上学了,刚上一年级。”林寻说:“九岁才上一年级?”山宝儿说:“我家附近的村小学黄了,合并到另一个村小学去上学,离家远,没有伴儿,妈妈怕我走不动,晚上两年。”
林寻拎着水桶走到上坡时,感到没有拎前一桶水时腿脚利索了。因为坡度大不能歇脚,她走得越来越吃力,脑门上的汗珠很快就下来了。山宝儿见状,及时上前帮着她把水抬到坡上。林寻把水倒进石槽里,放下水桶说:“山宝儿,我看看你的手。”山宝儿向后退了退,把手缩进袖子里说:“我帮你把水槽打满吧,我有劲儿,我爷腰有摔伤,都是我帮他抬水。”林寻说:“不打了,水放久了走味,每天都打新水好喝。”林寻向前凑了凑说:“山宝儿把手伸出来。”林寻把山宝儿的双手从袖子里拉出来。山宝儿的手背红肿得像包子似的,上面裂着血糊糊的冻口。林寻说:“疼吧。”山宝儿说:“冻着不知道疼,等天一暖和才钻心的难受。”
第二天,没等天亮,林寻就下山去了谷堡镇的药店。她先买了冻疮膏,又买了些简单的生活物品。回到村子,太阳已经落山。林寻喜欢在两头不见日头时穿过村子,以免被人注意。其实她的顾虑有些多余,村子里除了过年有些生机,现在全是老人和孩子,根本没人注意她。
林寻从村口走到山宝儿家门前,一个人也未碰到。林寻数了数,这个叫“石佛堂”的小村子一共才二十几户人家。都是依山而建的老式土木房子,随着山的走势,稀稀拉拉延伸到山宝儿家就终止了。山宝儿家的房子最老,窗户是黑洞洞的木头格子的,林寻在老电影里见过。
林寻推开山宝儿家的木栏栅门,穿过院子来到房门口儿,她拍了拍老木头门:“山宝儿,山宝儿在家吗?”山宝儿应声打开门,林寻哈腰进了屋子。灶房里,山宝儿和爷爷正忙着做饭。里屋的炕头上坐着位老女人,是山宝儿的奶奶。林寻从口袋里掏出冻疮膏放到老女人身边,告诉她如何给山宝儿上冻疮膏。老女人伸开双手,摸了几次才摸到冻疮膏,眼睛不知看着何处说:“谢谢你,谢谢你好心人。”林寻问:“您的眼睛……”老女人说:“白内障,好几年了,起初还能看个模糊的影儿,现在啥也看不着了。”林寻起身出了屋子,快步朝大门口走去。她听到身后山宝儿的爷爷在屋子里喊:“山宝儿,山宝儿,灶膛里的火蹿出来了,快帮爷凑进去。”林寻回过头,见山宝儿刚出前门口又跑回屋子里。
许多时光,林寻都是独自在老柏树下度过的。她特喜欢老柏的香气,吸着这股香气,她感觉自己的身子越来越轻,仿佛随着香气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老柏树上时常有各种小鸟聚集,来得最多的是山喜鹊。偶尔也有松鼠在上面跳来跳去。起初,怕惊跑它们,林寻不敢抬头看。后来,林寻试着慢慢抬起头,发现它们并不怕她,有意思的是,在她抬头看它们时,它们也会低头朝下看她。
有一天,林寻发现老柏树上有个仅拇指粗的灰白枯枝,枯枝上落满了山喜鹊,它们翘着长长的尾巴不停地叫着。而那么细的枯枝竟硬挺挺的纹丝不动。她忽然想起了古书上记载的木舍利。她从墙角搬来简易的木头梯子,爬到树丫上,费了挺大劲才把那根长长的枯木枝锯下。这根枯木枝像骨头一样,沉甸甸的,坚硬无比,果真和古书上描述的木舍利特征相符。她把木舍利拿到房内锯成一百零八个小段,顿时满屋清香。
林寻把锯末收集起来做了一个香袋,夜深失眠时,放到鼻孔下,闻着闻着便入睡了。林寻稍得空闲便拿着锯下的一小截老柏木舍利在青石槽上荡来荡去地磨圆儿,有时,一天磨成一个圆珠,有时几天也磨不圆一个,她以这种方式打发时间。磨圆的过程中,她能时时闻到老柏木的清香。但哪怕是磨得再投入,若山宝儿来,她也会立即停下。山宝儿总是跃跃欲试,都被她制止住了:“小孩子不要碰这个。”
一晃儿,山宝儿好多天没来了,林寻就一连磨出了好几颗圆珠子。这天,林寻磨成一颗圆珠才发现,山宝儿不知啥时已站在了身后。“山宝儿,山宝儿你啥时来的?山宝儿你总是不声不响地等我发现你。咋不叫我一声呢?”山宝儿低着头,心事重重的样子。“山宝儿,你老背着手干啥?让我看看手好了没有?”林寻转到山宝儿背后,见山宝儿反背着的双手拿着两张题单。林寻拿开题单,看了看山宝儿的手背儿:“哦,消多了,慢慢就好了。”山宝儿依然不吭声。林寻看了一眼山宝儿手里的题单:“哦,开学了,今天是星期天,怪不得好多天没来了。遇到难题了?拿来我看看。”林寻认认真真把语文数学两张题单看完:“你做得全对,干吗还愁眉苦脸的?”山宝儿一下一下地咬着嘴唇,就是不说话。林寻说:“山宝儿你别哭,我来帮你,你别哭,我什么都能帮你。”山宝儿终于支支吾吾地说:“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爷不会写字,我奶识字可……”林寻沉默了好一会儿,在学生“申山宝”的家长栏里签上了“林云”。她告诉山宝儿,以后老师再问,就说妈妈叫林云。
此后,山宝儿每个星期天都会拿着作业来找林寻。林寻总是认真看完每道题后,把错误的教山宝儿纠正过来,再在家长栏里签上“林云”。
春天,黑桦谷里开得最早的花是野杏花。林寻不喜欢看粉红的野杏花,觉得太艳,刺眼。她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房内,往黑桦树皮上抄写佛经,林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野杏花开过,山地上的小野花也陆续开放了。先是紫地丁,它紧贴着地面,刚一冒头就开花,矮矮的身子顶着一串串紫花,在山野的各个角落都能见到。而此时的青草才刚刚泛绿。这天,山宝儿双手捧着一大把紫地丁来到林寻近前。林寻说:“山宝儿,以后别采了,养不活的,还是让它长在山坡上好。”山宝儿说:“放水瓶子里能开一个星期,下星期我再采新的。”林寻说:“山宝儿你别采了,我想看花,到山坡上看就是了,水瓶子里的花无根,总比不得野地里的花有生机,打动人。”山宝儿说:“各有各的好,我妈说,有花的屋子才像个人家。我妈年年春天都带我采野花放到屋子里……”
到了下个星期天,山宝儿果然又采了新花。不过这次采的不是紫地丁,而是换了鸢尾。林寻不忍看水瓶子里如紫蝴蝶般的鸢尾花一天天枯萎,终于重新拿起了画笔。令她想不到的是,搁笔多年,她竟比原来画得绝妙了,她甚至怀疑不是自己画的,这是她此前从不敢奢望的画境,她发现自己在不经意间竟脱胎换骨了。犹豫了一下,她最终还是一把火把画烧掉了。
端午节的前一天,林寻去林子里采野桑葚。她在每棵桑葚树上都采一些。有紫的,有红的,还有白的……有酸的,有甜的,还有酸甜的……端午节一大早,林寻就端着满满一盆各种味儿的桑葚,来到老柏树下。她把盆放到石桌上,然后坐在石凳上看下面山谷里的溪流、草丛、野花、野树。此时,草木嫩绿的叶子尚未完全展开,看上去舒朗灵动,而最活跃的是跃动在草木间的各种飞鸟。
坐久了,林寻觉得身上有些凉。她从树荫里移开身子,坐到了日光下。这时,她听到石门洞的木头门似乎响了一下。她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走到石拱门口,打开虚掩着的木头门,探出身子向外看了看,什么也没看见。她抬头看看天,一丝风也没有,老柏树上有两只松鼠在相互追逐。她向远处村子的方向看了看,山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她想到端午节,人们都会在家中过节,山宝儿也得和爷奶在家过节。端午节学生放三天假,反正还有两天呢。
林寻回到石桌前,看了一眼盆里的桑葚。有些已经变得不那么新鲜了。这些桑葚全都挤到一起,恐怕放不到明天就全得烂掉。她去房里取出一个空盆,而后,小心翼翼地把好的桑葚挑到空盆里,再把有些变软的桑葚扔掉。林寻挑得极仔细,却一个也没舍得吃。这时,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停止挑选桑葚。直到山宝儿来到她身边挡住眼前的日光,她才微微仰起脸:“山宝儿,你来了。”山宝儿把满满一小筐桑葚放到石桌上:“吃吧吃吧。甜得齁嗓子。”林寻看了一眼山宝儿。他满脸的汗珠,干裂的嘴唇里露出白白的牙齿,无一丝桑葚的汁液。林寻说:“山宝儿,你还没吃,咋能知道它有多甜呢?”山宝儿说:“我妈以前带我采过,在大山里边,老远了,这棵树的桑葚最甜,我知道。”
林寻和山宝儿一个一个地吃着桑葚,说着话。山宝儿说,下学期他就升二年级了。再开学,现在这个村小学也保不住了,都要合并到乡中心小学,村小学都得被卖掉。以后,去乡中心小学上学,离家就更远了。林寻问,那么远的路,你怎么去上学呢?山宝儿摇着头说,不知道。
林寻和山宝儿不知不觉地就把石桌上的桑葚全吃光了。林寻说:“山宝儿,你采的桑葚真甜,甜得我嗓子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山宝儿说:“你的牙都被桑葚给甜紫了。”林寻说:“山宝儿,你不光牙,你的脸蛋儿、鼻子还有你的手全变成紫色的了。哦,我看看你的手,现在彻底好了。以后别再冻着了。”
太阳落山了,林寻说:“山宝儿,我送你回家吧。”山宝儿说:“我自己敢回家。”说着,他一路小跑消失在山谷里。林寻只好像每次那样,偷偷地紧跟在山宝儿后面,直到亲眼看着山宝儿进了自家大门她才返回。
这天早上,林寻把最后一颗老柏木舍利珠磨圆。然后,她在佛堂前用烛火把纳鞋底的老锥子尖烧红,一个一个地把木舍利珠烫出小孔,再用线把木舍利珠穿好,又从头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一百〇八颗。她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子,却未戴在自己身上。
林寻双手捧着精心磨制的一百〇八颗佛珠,轻轻挂在了老青石佛像上。她慢慢走到老柏树下,她的脸紧贴着老香柏,抱了好一阵子。而后,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石拱门。
山宝儿作业本上的“林云”那两个字,林寻早已教山宝儿写会了,连笔体也和林寻的一模一样。但山宝儿和往常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大清庵。他每次来都会把灶膛填满干柴,烧上半天。院子里林寻原来备下的干柴越烧越少,他就去附近的林子里拾干柴。山宝儿的时常光顾,让这个深山沟里原本荒凉孤寂的寺庙,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儿。他坚信,林云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可是,一场罕见的大雨把大清庵的正殿偏殿全浇倒了,林云也没有回来。只有山宝儿还在如山的废墟上忙着搬砖头瓦片,他要建一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