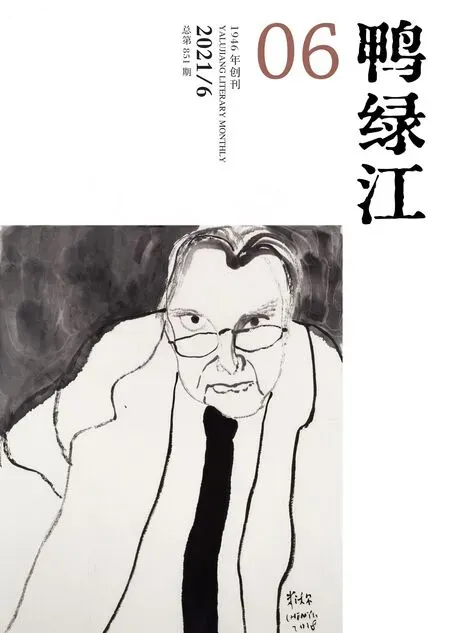童少六记(短篇)
王怀宇
很多人在童少时代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灰色记忆,灰色记忆从来不会是什么美丽相约,也不会是什么幸运会见,更不可能是什么惊奇艳遇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灰色记忆只能是无法逃避的尴尬邂逅。
丁小眼睛
当我还在母腹中孕育的时候,身为五棵树乡村中学语文教师的父亲意外地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这个意外,不仅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们全家所有人的命运。
父亲是个文学青年,姐姐出生后的某一天,乡村语文老师出身的父亲一觉醒来,突然就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一本正经地跟母亲说,他想当鲁迅。
这种事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就是个玩笑。可是在父亲这里就不是什么玩笑了。父亲可不是说着玩的,他一向是个做人做事都非常认真的人。而可怕也就可怕在父亲的认真上。父亲要是不认真也就没事了,我现在也许就不会生活得这么沉重了,我也许会生活得非常随意。
认真的父亲果然行动起来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头悬梁,锥刺股,三年以后,三十二岁、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即将又有一个儿子的我亲爱的农民父亲竟然真的奇迹般地考上了大学。一直想当鲁迅、心怀文学大梦的父亲报的专业也当然是中文系。父亲肯定以为自己又向鲁迅迈进了一步,我敢肯定,他一度是非常兴奋的。母亲的妊娠反应和老中医的把脉都证明父亲就要拥有一个儿子了,本来就兴奋的父亲再加上意外地考上了大学,可谓双喜临门。
父亲是乐颠颠地从五棵树村奔向省城的,我一定是隔着母亲的肚皮看见不甘平庸的父亲一蹿一蹿离去的背影,否则我现在不会有这么深刻而牢固的印象……
一心想要儿子的父亲并没有因为儿子就要降生而停止他前进的脚步。父亲临走时非常潇洒地扔给了母亲一句话:“我儿子生下来就叫丁文学吧!”父亲走得就像那个传说中的李太白,口中同样念念有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那时,除了就要降生的我,父亲还有个三岁的女儿在恋恋不舍地张望他那渐渐消逝在五棵树村村头的背影……你试着想想,我的父亲该是个多么有理想、多么有志向的文学青年啊!为了实现文学梦想,他不仅要告别妻子,还要告别女儿,更要告别就要出世的儿子丁文学。
用现在人的话说,父亲好像真的有点儿不靠谱啊。
但母亲说,也有羡慕父亲的人,那个人就是父亲的同事——同为五棵树乡村语文教师的邻居郑大眼镜。郑大眼镜当时的生活境况和父亲差不太多,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四岁,另一个一岁。但郑大眼镜的父母身体都不好,家庭负担太重了,导致学习比父亲还要好一些的郑大眼镜无法实现上大学的梦想。
送父亲上学的饯行酒上,喝高了的郑大眼镜还在不断地祝福并遗憾着,不断动情地说:“真心为你高兴啊,终于可以飞出去了……不过,我的梦想只能靠我的两个儿子帮着去实现了……” 郑大眼镜给两个儿子起名叫郑大龙和郑二龙,骨子里就是希望有一天他的两个儿子都能成功,最好变成两条腾空而起的飞天大龙。
父亲在外地上学最初的那两年,身为乡村小学教师的母亲同时拉扯着我和姐姐两个撒不开手的小孩子。母亲每天还要上班,还有一个班级的学生,要付出多少辛苦就可想而知了。我虽然当时不太记事,但还是听大人们经常说起我那些见不得人的灰色事件:
我从小就死要面子,在学校的托儿所里,我从不像别的小孩子那样让母亲袒胸露乳当众喂奶,得到没有人的地方才行。母亲经常利用课间休息给我喂奶,每次匆匆跑来,都会让我逼到没有人能看见的角落里。否则我是坚决不吃奶的。
有一天中午人多,母亲没办法,就把我抱到学校空无一人的大操场去喂奶。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大操场上的安静,就每天都要求去大操场上吃奶。
一向讲原则的母亲却尊重了我的个性。为了给我顺利喂奶,年轻漂亮的母亲已经顾不上她原本最该顾及的尊严了。母亲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风吹雨打太阳晒。骄阳下,寒风处,阵雨中,雪花里……
春夏秋天还好说,最难受的是冬天。母亲温暖的怀里每次都会灌满凛冽的寒风。我肯定,母亲晚年的风湿病与当年为我哺乳有直接关系。
一个端庄少妇在空旷的乡村学校的操场上解开衣襟为一个男孩哺乳,肯定曾经是五棵树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我以为旁边没有人看见,我吃得很神秘,也很专注。但我没想到,哺乳的母亲让全校的师生们都远远地望见了。那时我太小,我还不知道教室里、食堂里、树林后到处都可能有一双双贪婪的眼睛……
另一件灰色事件就是我曾经有一个非常难听的外号——丁小眼睛。我小时候很胖,眼睛就被挤压得又细又小。我爱吃肉,尤其爱吃肥肉,我叫它白肉。
那时,乡村的菜碗里基本看不见肉。母亲所在的乡村小学食堂除了过年那几天能见到肉外,平时只有炖豆角的时候才偶尔能见到一两片肥肥的咸腊肉。老师们舍不得吃,就夹着肥肉逗试我:
“丁小眼睛来了吗?”
“丁小眼睛来了。”
“丁小眼睛在哪儿呢?”
“丁小眼睛在这儿呢。”
“谁是丁小眼睛啊?”
“我是丁小眼睛。”
“丁小眼睛啥样的?”
“丁小眼睛这样的……”
他们明明早就看到我了,但每次都有这么多废话。我生怕失去机会,竟然总是每问必答。每次,我都是一边拎起小眼皮儿,一边向那个手中挥舞着肥肉的人跑过去……
死要面子的我,总是无法抗拒一片肉的诱惑。
一阵哄笑之后,肥肉最终被放进了我的小嘴儿里。吃到了肥肉,我就红着小脸飞快地扑向母亲,有时还是忍不住要哭,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就迅速地趴在母亲的腿上,偷偷抺掉几滴不争气的眼泪……
我还时常从接下来的午睡中惊醒过来,把小脑袋蒙在被子里小声啜泣。有一次,正在我委屈地小声哭时被跑回来取围巾的母亲发现了,母亲跑过来不断地安慰我说:“别往心里去,那是大人们逗你玩呢。”我并不完全相信母亲的话,最后,暗自神伤的我还边抽泣边毫无底气地小声问了母亲:“妈妈,我的眼睛真的很小很小吗?妈妈,我是不是很给你丢脸啊……”
其实,那个年代的大人们又何尝不馋肥肉吃呢?只是因为他们不舍得吃,才把肥肉给了我这小孩子。“丁小眼睛”,只不过是人家把好吃的让给我之前,我得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人家把好吃的肥肉给我吃了,我总得让人家心理平衡吧?我总得让人家乐呵一下吧?只是当时大人们并不知道,对于死要面子的我来说,那代价可以说是过于大了。
直到有一天,我已经来到平安县城了,母亲带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在电影正式开演前一个加映的新闻纪录片里,我偶然看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方,我终于对自己的小眼睛有了最初的释怀。我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很响亮的幼稚童声:“妈妈,你快看呀,那个人的眼睛比我的还小啊,竟然也能做成那么大的官呢!他也给他的妈妈争光了呢……”
当然,我这些见不得人的糗事更多的是大人们后来讲给我的,其实我记事算早的,我记事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夸张了。
乡村小画家
似乎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是我的“死对头”。我这个天才的乡村小画家就毁在了父亲的手上。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我是先遭遇了捧杀,然后又遭遇了棒杀。
我在三岁的时候就喜欢画画了。当时,我那已经三十多岁还不甘平庸的父亲正在外地的一所大学求学,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留守在五棵树村,寄居在外祖父家。
外祖父是个大大咧咧的热心人。他宠爱外孙子超过了亲孙子。正是因为有个与众不同的外祖父,我才从来没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我在外祖父家生活得心安理得、自由自在,俨然一个作威作福的小皇帝。我想干啥就能干上啥,画画一不小心就成了我的最爱。鸡鸭猫狗,猪马牛羊,我几乎是见啥画啥,而且画啥像啥。
念过私塾的外祖父是村里的文化人,见外孙子有如此本领,脸上的神情就更加慈祥。乐不可支的外祖父有空就领着我在整个村庄走家串户地表演画画,那可真是一场不知疲倦、兴致勃勃的终日游荡啊。我又是那样配合和乖巧,外祖父指向奔走的狗,我就画鲜活的狗;外祖父指向跃上窗台的猫,我就画灵动的猫。外祖父让我画啥我就画啥。那时的我还会背很多句唐诗宋词呢,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类的古语,都是不经意间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在外祖父眼中,那时的我一定是神笔马良或者是天才仲永。
五棵树的乡亲们那时还没学会嫉妒和恨,他们都对我投以羡慕的眼光,我和外祖父当然非常受用。正在我乐此不疲地在乡村走家串户地画画,沉浸在“乡村小画家”的称号中时,在外求学的父亲毕业回来了,说要带着母亲、弟弟和我进驻平安县。那时五棵树的乡村人视平安县为天堂,谁也没有理由放弃进城的好机会。
捧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看上去更有文化的父亲并没有忽视我的画画天赋,在去平安县的路上,他还在跟母亲说,平安县有文化馆,文化馆里有教画画的好老师。
父亲没有食言,不久,他就找到了平安县文化馆美术辅导部的李主任。
李主任比父亲年长几岁,毕业于一所大学的美术系,论起来竟和父亲是大学校友。老同学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父子,李主任还慷慨地送给了我三支又粗又黑的专业素描笔。临走时,李主任摸着我的脑袋说,这孩子能行,好好学吧,又加送给我一本厚厚的精装大书——《鸟的基本画法》。
过分热情的老同学显然让父亲受宠若惊,素描笔和工具书更是让父亲如获至宝。当天晚上,父亲把睡眠都弄丢了,竟然熬夜亲自为我列好了学习计划。
接下来就是那场噩梦般的棒杀了。
按照父亲制订的学习计划,开始时我每天要画完一只鸟。我每天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在父亲急赤白脸的指挥下勉强完成任务。
父亲一向干啥事都认真,这次更不会例外。只要我画画,他就不再急着去上班了,总是一丝不苟地站在后面监督着我。我几乎每画一笔,他都要认真点评一番。画好了还行,一旦哪笔画得不对了,我就要挨训;画得再离谱点儿,就得挨骂;如果画错了,就要挨踢。从那以后,我的每天好像都变得漫长了,年少的我过早地拥有了那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延续,不知不觉中,我发现画画已经不再是我的美好爱好了,好像越来越变成了痛苦的负担。
几个月后,按学习计划,我每天必须画好两只鸟了,就更得经常被训被骂被踢了……渐渐地,我对画画竟产生了恐惧心理,常常暗自后悔:当初自己为啥要有这种爱好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我打心眼儿里越来越不爱画画了,可死要面子的父亲哪会同意?他还急着去向老同学李主任汇报教学成果呢。
每次我流露出想放弃的意思,一顿训骂都是难免的,有时还要挨上几大脚。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坚决不画了。我决定,无论父亲怎么骂,怎么打,我一定要挺住!我想,只要挺过了这一次,以后就彻底解放了,彻底自由了,一定不会再因为画画这件事挨骂挨打了。
那天父亲怎么骂的我,怎么打的我,我都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最后他实在骂不动了,也实在踢不动了,竟然首次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前不论我怎么淘气,父亲可是从来不打我脸的。
最后,父亲气得说不出话了,好像也打不动了,才浑身颤抖着用嘴在我的大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把嘴角都咯出血了。父亲是一边擦着嘴角的血迹一边最后训骂了我,父亲最后的骂声空洞而无奈。
可以说,是父亲的异常严厉导致我最后选择了放弃画画。那个天才乡村小画家终于生生地被他父亲给扼杀在摇篮里了。那年,我刚刚七岁。曾经那么热爱画画的我不敢再热爱了,我摆脱画画就像摆脱掉了一场巨大的噩梦……
一天下午,外祖父从五棵树乡下来平安县看我。我还没放学,见外孙子心切的外祖父就早早地来到小学校园里。当时校园里正办着全校小学生画展,有些驼背的外祖父就背着手满操场转悠着,边等我放学边看画展。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哪张是他外孙子丁文学画的呢?他居然一直没有看到我的名字,难道是外孙子改名了?可是从没听说外孙子改名啊?放学后黄昏的校园里,在我没认出外祖父之前,我先看见了一位满脸失望的老人。之后我才发现那位满脸失望的老人竟然是我的外祖父,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困惑、最失望的外祖父,外祖父在拥抱我之前的那一脸茫然若失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这些年,我并不觉得父亲怎么对不住天生喜欢画画的我,我倒觉得父亲更对不住的人,应该是我那慈祥、善良的外祖父。我不敢去深究父亲到底对不起谁,怕父亲重新让我学画画。直到多年以后,我仍不敢提及跟画画有关的事。
小城孩子王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是我家那一片儿有名的孩子王了。很多同龄的孩子都“司令、司令”地叫我。邻居大力最不好管理,是个典型的好战分子,那也只能死心踏地做我的副官。因为我除了有人缘、有威信,还有一手小绝活儿——除了弹弓做得好,我还会做烟火枪。出自我手的烟火枪不仅好使,而且好看。身边的弟兄们几乎人手一把烟火枪,差不多都是我亲手武装起来的。
因为我会制造精美的烟火枪,手工费永远是一节车链子,所以我过早早地拥有了两把十二节车链子的烟火枪。“司令”的威风更表现在具体装备上。在那群孩子中,同时拥有两支烟火枪,而且是两支超大超长的十二节车链子的烟火枪,绝对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的孩子们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平原游击队》,尤其喜欢电影里使用双枪的传奇战斗英雄李向阳。我那十二节车链子的“双枪”一定能让孩子们时刻联想到智勇双全的李向阳。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整个平安县都很少看见自行车。谁家会有二十四节车链子呢?就算有,谁又肯把它们都用于做车链子枪呢?现在想想,那都是个非常独特的奢侈现象。
一般情况下,做一支烟火枪至少需要五节车链子。孩子们手上终于攒足了五节车链子还是做不成,因为还要交出一节作为我的手工费。这样,他们就得攒足六节车链子才能来找我,否则他们就只能尝试着自己去做了。孩子们当中也确实有实在等不及了自己动手的,李大平和二宝子等都这样尝试过。对于这些,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我心里太有底了。
自己动手做枪的孩子们好像没有谁因此而高兴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看上去总算完成了,但总是存在两个致命问题:一是不好看,二是不好使。由于车链子少,枪栓必然要短一些。加上选择的皮筋弹性稍稍弱一点儿,各个部件细节稍稍粗一点儿,总体安装技术再稍稍差一点儿……尤其是撞针的制作问题,更得细心一点儿,不能磨得太尖,又不能磨得太钝,关键是弧度和角度的把握必须极其精确,一点儿不到位都不行。这些“一点儿”凑到一起,枪肯定就要出大问题了。有时,自认为大功告成的孩子兴奋地把枪举过头顶,一连勾了好几下,枪却一直勾不响。该响时不响,哪还配得上叫枪呢?气性大的孩子立马就会把自己辛辛苦苦做成的枪摔在地上,甚至还要狠狠地踹上几脚。
而我用五节车链子做成的烟火枪却总能一勾就响,这就是孩子们宁愿送给我一节车链子也来找我做枪的根本原因。五节车链子的烟火枪响是响了,但它不可能响得那么透亮、那么潇洒。就算我做得再精致,它也终究没法和我那十二节车链子的烟火枪相提并论。十二节车链子的烟火枪毕竟枪栓足够长、冲击力足够大,每次勾动扳机都会随之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脆响。在孩子们的眼中,“司令”那十二节车链子的烟火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烟火枪啊!
印象中,平安县的孩子们一直在竭力搜寻更多的车链子,一直在梦想着手里的烟火枪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响……
后来,光听响声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了,烟火枪就发展成了火药枪。
所谓的火药枪,现在来看就非常简陋了。无非是在枪头套上一个车闸管,再将其焊牢。火药枪可以装上黑火药和铁沙子,不再是从前那“摆设有余,威力不足”的烟火枪了,火药枪喷射出的铁沙子多且密,比弹弓的威力还要大。火药枪才更有枪的味道,不仅能让人听到响声,还拥有巨大的杀伤力。一把这样的“枪”拿在手上,该是多么有威慑力、多么风光啊!那一度是整个平安县所有男孩子对“枪”的终极梦想。
自从有人利用自行车的车闸管制造火药枪,平安县里为数不多的自行车的车闸管几乎一夜之间就被孩子们偷光了。大人们防不胜防,新买的自行车五天之内就会残缺不全,所以那时大人们骑的自行车基本上没有车闸。街上时常发生自行车撞车事件,与大量车闸管被孩子们用于做火药枪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了,没有人会指责对方为啥不刹车,都是说:“你为啥不往那边拐呢?”接下来,就会听到这样的争吵声:“你没长眼睛啊?咋不往右拐呀?你扬了二怔的!”另一个则骂道:“你才没长眼睛呢!咋不往左拐哪?你傻了吧唧的!”曾有那么一段时期,平安县总的感觉就是:刹不住车。
一天,我招集小伙伴们来帮我家垫院子。但那天下午收工后发生了一件蹊跷事:我放在自家窗台上那两支十二节车链子的火药枪竟然不翼而飞了!光天化日之下,司令那么扎眼的两支大枪同时不见了,这在当时无疑一件惊天大案!
垫院子时,枪就放在自家的窗台上,没有外人来呀,怎么会丢呢?
全力破案!我认为我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边说“谁也不好使!我就不信邪”边招呼大家:“马上给我全体集合!”
一起干活儿的小伙伴们便掘地三尺地找起火药枪来……孩子们无望地把整个院子翻了一遍又一遍……一个个累得汗流满面,精疲力竭,也没见到那两把大枪。我认为,包括那个贼在内,也在假模假式地寻找。
有人怀疑是不是丢在运土的路上了,我就带着所有人去后岗子的路上撒大网式地反复寻找……仍然无果。
最后,我不得不用上排除法。一个一个过筛子,很快确定了最可疑的一个人,大家都怀疑是满脸通红的李大平干的。
严刑拷打,李大平却坚决不承认。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孩子们无形中也在模仿成年人,斗争也是十分残酷的。
我的副手大力用手术刀割破了大平的后背,那已经是孩子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可大平还是不承认自己偷了火药枪。
大力有一天又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反标,跑来向我汇报,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写我是小孩头头。毫无疑问,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大力还是怀疑是李大平干的……
还有一天,我们自制的火药也湿透了,是谁给浇上水或是给尿上尿了呢?又是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又有人怀疑是李大平干的……
那时我们还小,只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还远远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直到后来上了初中,学了物理和化学,我才知道火药第二天早上为什么湿透了,那一定是露水惹的祸。
后来也知道了当年厕所反标的谜底,那是大力自己写上去的,大力为的是镇压一直不服他的李大平。那是我考上大学后伙伴们为我送行的晚上,孩子们头一次喝多了白酒,酒后的大力自己揭开了困扰孩子们好多年的未解之谜。
但是一直没人再提那两把火药枪的事,火药枪到底是谁偷去了呢?这仍然是我少年时代最大的悬案……
转嫁梦想
我相信,不会有太多像我这么倒霉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是个文学青年,也就决定了我文学青年的命运。
文章开头的时候不是说过吗?我亲爱的农民父亲奇迹般地考上了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父亲真的又向鲁迅迈进一步了吗?
大家笨想都能想到父亲的悲惨结局。通过上大学见到更大的世面之后,父亲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班里那么多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门望族的同学,才华远远在他之上,也没有一个能成为鲁迅。怎么办呢?梦已上身,是挥之不去的。渐渐地,父亲把梦想恋恋不舍地转移到自己儿子身上来。于是,我苦难的日子来临了,父亲对我的要求越来越严厉。我这命可真苦啊!
那时我还不知道,当年父亲之所以风风火火地大学毕业回来,又急三火四地将我们全家搬进平安县,是因为他心里正怀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他根本不想让我画画,他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那当鲁迅的文学梦想,大有传说中的愚公那“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执着架势。
已经读初中的我本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理科天才,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时代,学生们对文科生是多么不屑啊!可身为文学青年的父亲却命令我非学文科不可,以后目标必须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否则跟我断绝父子关系……父亲的武断还导致我和初中时最志同道合的几个理科同学过早地分道扬镳了。
那时父亲是平安县戏剧创作室的小头头,每天哼哼呀呀地写地方戏唱段。有时拿不准了,就以考考我为借口,让我帮着押押韵。回答好了说我还真能蒙一阵,回答不好就要挨一顿臭训。
叛逆期的我有时也抓住机会回击父亲。当时知识分子家庭并不宽裕,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梦想当鲁迅的父亲却每年都要订上几本国内大刊,除了《剧本》月刊之外,还有《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当时名气较大的小说月刊。有时我真的想不明白,省下那些钱能买多少个面包和麻花啊!
有一天放学回来,本来因为摸底考试成绩不理想要挨骂的,可我意外地逃过了一劫。当父亲问我考得咋样时,我竟先说了句当天学到的陶渊明的名句:“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年有所亏。”父亲笑了,说我学以致用,好样的。见父亲高兴,我并没见好就收,突然发现父亲正在看《小说月报》,我就又半开玩笑地说:“天天写地方戏能有啥出息?要写就写小说,得争取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你口气可真大呀!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小说月报》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吗?咱们平安县这么多年真没听说谁在那儿登过作品呢!”父亲都要急眼了,骂我跟他抬杠子。
我当然不会示弱,又指着旁边《青年文学》的头题封面人物作品《摇滚青年》说:“你看人家刘毅然,那才是个好作家。”
父亲无语了,竟要举手打我,见势不妙,我只好溜之大吉。
而我根本就没有父亲的恒心与毅力,真不是努力学习那块料,我喜欢跟学习无关的任何事物。父亲是专门用来学习的,我是专门用来不学习的。我喜欢打冲锋仗,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喜欢抓山雀、挖鼠洞、种各种树、造各种玩具枪,用东北话说,我是属蝲蝲蛄的,样样通,样样松。(蝲蝲蛄啥样,父亲骂我时有过多次描述:蝲蝲蛄会飞、会叫、会游水、会跑,还会挖洞,但飞不高、叫不响、游不动、跑不快,洞也挖不深,总之都不咋样……)无论是小鸡小鸭,还是小猫小狗,只要是动物,我都喜欢。我天天看我种在庭院里的花草,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还能看小半天。父亲骂我:“你不看,它们照长不误的。”而我却一直认为我的目光对花草们很重要。我还喜欢天文、地理、外星人、UFO等事物,直到现在,我最爱看的电视节目还是《动物世界》和纪录频道,此外,只看体育赛事。
大学中文系毕业、乡村语文教师出身的父亲实在难缠,他对我的学习要求总是远远高于我现有的实际水平。我的考试成绩总是达不到他的期望值。在那个高考是唯一出路的年代,我面对着“分是命根”的严厉父亲,更多的时候,我无法斗智,更无从斗勇,接受训斥和拳脚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这个问题上受到父亲的伤害和摧残,直到上大学以后,远离了父亲的视线,伤害和摧残才得以减轻。但是,我已于无形之中被父亲引向了文学之路。我每天在东北师大中文系的大楼里学习文学理论,看中外名著,课余时间再去听讲座、搞诗会……
可以说,本来爱好理科的我是被父亲逼上文学之路的,在这条路上,我并不比被逼上梁山的林教头轻松多少。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当作家和上不上大学中文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有这种认识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蹲级包子
有“蹲级包子”这样经历的人不会太多,但是我有。现在看来这是经历,是故事,但是在当时可不是,那时简直是事故。毫不夸张地说,这绝对曾经是我少年时代头顶上最不光彩、最黑暗浓重的一块乌云,尤其是对我这种虚荣心很强的人来说。
20世纪80年代,不仅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就是从普通初中考入重点高中,中考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尤其对我们这些县城的孩子和县城以下的乡村孩子来说,考上与考不上,就是人生一次重大的转折。打个比方说,中考就像一场比分僵持不下的足球比赛中一个决定胜负的点球。
那年,我没有考上平安县的重点高中——平安一中,这粒生死攸关的点球就这样被我紧张而颤抖地罚失了。
开始时,学校说我考上了,第一次通知还有我,班主任胡老师亲自到我家,兴奋无比地通知我下午就到学校去开会。我被一直兴奋无比的胡老师弄得更加兴奋无比,吃过午饭我早早地就跑到学校去了。距开会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呢,我就兴奋无比地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转悠。以前没注意,学校竟是这般亲切——单杠、双杠、篮球场、足球场都像在和我打着招呼……操场也显得比从前大了许多,并显示出向我张开怀抱的样子。
我还激动地听完了关校长热情洋溢的祝贺讲话。记得关校长最后说:“考上了县一中,就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校门,父母没白供你们一回呀,会为你们高兴的,也会因你们而自豪的。我的同学们,祝你们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的青年才俊们,我期待着你们所有人在三年后都金榜题名,都传来令人振奋的佳音……”
因为平安一中的高考升学率一度达到95%以上,听了关校长的一席话,我兴奋异常。我还下意识地想到了我们班上的尖子生王龙飞,连学习那么好的王龙飞都没考上,而我却考上了,真是不容易啊,真是幸运啊!记得那天我只会兴奋,不会思考,只会憧憬,不会回顾,更没有时间去细想王龙飞的处境和感受。
可是没想到,后来平安县教育局出台了一个土政策,明确规定外语和政治加起来不足160分的减去10分,倒霉的我两科加起来正好不足160分,这样我的总分被减去10分之后就比录取线低了1分。所以,第二次被通知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中就没有我了。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出局了。我至今都认为那一定是平安县教育局某个当权者的阴谋,他可能为了某个关系的孩子能考上,谋害了我这个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当然,这只是我自己想的,因为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
对我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一度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考试之前并没说哪科加上哪科不够多少分要减去多少分啊!再说,我是被我父亲立志要考大学中文系的呀……
然而,我的抗议无效。我的声音再大也没有用,因为我不过是个中学生而已。对于平安县教育局来说,我的嘴实在是太小了。我想也许我父亲的能嘴大一些,可他没敢对平安县教育局说出半个“不”字,而是一遍又一遍恶狠狠地大骂着我:“完犊子……”
其实,考不考上重点高中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无所谓。我并不觉得考上了就如何好,我当时真没啥太大的理想,也不爱学习,要能永远不上学,在家领着一群孩子,在平安县当孩子王玩才好呢。只是老天爷呀,你可让我咋过我那望子成龙的父亲这一关啊。
平安一中在平安县所有的居民心目中都是神圣无比的。真的就如关校长讲的那样,考上了平安一中,就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大学校门。平安县本来没有什么风景,平安一中上学和放学的学生俨然平安县最美丽的一道风景。人们议论着这里有谁谁家的儿子或女儿,谁谁家的儿子或女儿肯定能考上某某名牌大学……那是更美丽的景外之景。
那群佼佼者中没有我不要紧。要紧的是没有我父亲的儿子!
一向好强的父亲就像被所有人捉到了短处,于是,公共场合抬不起头的父亲回到家里就会对我表达出十足的愤怒。“给我回读!”
老爸怎么打的我,我已经吓忘了。我不知道疼痛,只知道耻辱,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见不得人的事。我怎么也沦为人们常说的“蹲级包子”了呢?
因为我都会了,回读一年相对轻松,只是白白浪费了我一年的青春。
老天爷真的跟我过不去啊,太令人意外了!第二次中考,一向名列前茅的我竟然又只差了一分。这不能不让我迷信人们的说法,考场、赛场、战场都是出怪事的地方!这不,这次就怪到我头上了!没想到会是我的最强项数学出了问题,事情真的就坏在我的天才数学上了!那是我最拿手的鸡兔同笼问题,题目是:小鸡和兔子共20只,一共有50只脚,问:小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
正确答案应该是最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设小鸡数为X,兔子数为Y,列出二元一次方程式为:X+Y=20;2X+4Y=50……最后X=15,Y=5。
而我的算法则全凭想象:假设小鸡和兔子都能听懂人话,先喊抬起一只脚,50-20=30;再喊抬起一只脚,30-20=10,这时小鸡都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四条腿的兔子还有两只脚在顽强地站立着。所以,兔子有10÷2=5只,小鸡有20-5=15只。其实我还能做得更简单,就是直接下令让小鸡和兔子同时抬起两只脚,小鸡便直接坐地下了,只剩下兔子用两条腿站着。所以,50只脚减去20对脚,剩下的10只脚就都是兔子的了,再除以2,就是5只兔子。我的结果是对的,但根本没用上标准答案规定的步骤。判卷老师以为我的结果肯定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15分的题就给了我0分。
这一次,我父亲为了他的儿子,终于厚着脸皮求了他的校长同学。我终归没有逃脱掉耻辱,我还是以走后门的方式来到了平安一中。
大耳刮子
虽然我相对顺利地通过了高考,但是在我高考过程中却有一段并不愉快的小插曲。
上午刚考完语文,题虽然很难,但确实能考出点儿真正水平。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最高水平,用上了所有的积累,每道题都答得非常用心非常较劲。中午回到家时,我处于一种飘飘然的状态,正好姐姐也放假回来了,我就眉飞色舞地和姐姐说起了语文考试题:考试题出得有没有水平,得看答题人能不能用上劲,今年这语文题出得真有水平……正在我向姐姐穷显摆时,父亲也下班回来了。父亲一听我答得不错,就兴致勃勃地帮我估起分来。父亲毕竟是当过乡村语文教师的人,估分也是相当有经验的。可是估来估去,发现我的语文成绩顶多能得75分,父亲的脸都变形了。父亲竟怒不可遏地骂了我一句:“娘了个蛋!满分120分的语文只能得75分还考个屁大学呀!你还瞎叫唤个啥呀?”说着一挥手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大耳刮子……
“可是我已经尽力了呀!我发挥出我的水平了,我有啥办法啊。”我捂着热辣辣的脸和父亲对抗着。
姐姐也感到意外,吓得躲到里屋去了。
母亲及时赶来,和父亲喊了起来:“孩子还没考完呢,哪有这个时候打孩子的?”
我气得中午饭都没吃,在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才肯去继续参加下午的考试……
没想到,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以总分469分、全班第五的好成绩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
最后,我的语文得了74分,竟然是全年级的第二高分。因为那年的语文题实在偏难,能及格就是优秀学生了。只是我一向出色的数学没有考好,本应拿到高分,却拿了90分的平均分。还是因为我嘚瑟,有道大题省略了应有的具体步骤而没有拿到每步的得分点。
父亲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歉意,当天晚上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饭后还一脸笑容地给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两只白天鹅叼着一根树枝,一只乌龟紧咬着树枝,在高远的蓝天上进行着一次美妙的飞行……地上目击的人群一片惊叹,都说这太有创意了,一定是聪明的白天鹅想出的好办法,那只笨乌龟可真有福气啊。而实际上这是乌龟的主意,乌龟想上天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听到人们对天鹅的高度赞扬,乌龟这个急呀……最后,乌龟终于忍不住了,可它那“我”字还没说完,就悲惨地摔向了大地……父亲说,就算乌龟当时不说,人们早晚也会知道真相的。
一个语文拿了全年级第二高分的人却蹊跷地挨了一记响亮的大耳刮子,我一直搞不清楚,这是我的不幸还是父亲的不幸?但我能肯定的是:我仍然是父亲心中那只不够成熟、不够稳重的叫唤雀儿。否则,就算我们当时估出再低的分数,父亲也会认为那是一个高手应该得到的分数。就算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他的手也不会有高高举起来打向我脸的理由……
但还是谢天谢地呀!我总算考上大学了呀,我终于可以远离父亲,不再承受父亲的严厉管教了……
少年时代的灰色记忆还有很多:我还有多次无足轻重的死亡经历,比如野外洗澡弱水,死里逃生后又被开除出少年先锋队;比如少年时代被喜欢恶作剧的邻居小春子电击昏迷,险些一命呜呼;再比如第一次游向大海时,死要面子往前冲,最后无力游回岸边;再比如和表弟手拉手滑向家乡嫩江口的无底深渊,后被意外搭救;等等,等等。我童少时代经历过的凶险事件这么多,但唯有那个中午的大耳刮子成了我日后的心结,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一晃儿,我大学毕业了。父亲的梦竟然真的上了我的身,我竟真的写起了小说。先是在省内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但初学乍练的我写得并不十分理想,多半是出于编辑对年轻作者的鼓励。后来,我又在全国大刊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突然有一天,儿时无意中挖苦父亲的话蹦了出来:我的作品能不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呢?这件事竟真的一度成了我内心深处无法张扬的一个结。于是我开始梦想自己的作品能在《小说月报》上露面,我就更加努力地写呀写……我知道我更主要是想报复一下父亲。
有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信笺,看完信后我才知道,原来《小说月报》就是这个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呀。
信的内容简直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竟然是一封征求意见信。写得、确切地说是印得十分简单,大致意思就是,《小说月报》编辑相中了我发表在一个市级小刊上的短篇小说,问我是否同意转载。
这还用问吗?这可是我自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好事啊!我怎么会不同意呢?我还兴奋地绕道来到父亲住的小区,我把那封小信拿出来认真展开给父亲看。就那么几个字,父亲竟然看了好半天。最后,父亲用极其羡慕的目光盯住了我,激动地说:“那就抓紧同意吧,马上去回信说同意啊,真的会有这么好的事儿……”
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没想到这梦想实现得也像做梦一样啊!最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感到我对父亲有了胜算,那是在我和父亲英勇对抗多年后取得的一场伟大胜利。虽然这场胜利来得极其偶然,但还是能缓解我多年来一直渴求复仇的病根儿,就像真的有人为我讨回了那记响亮无比的大耳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