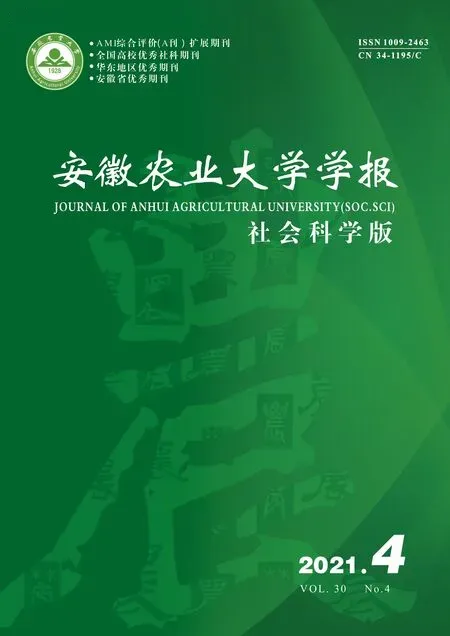论“斛兵塘”“量兵塘”“站塘”与魏晋屯田*
俞海燕,汪 清
(1.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2.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汉末魏晋时期江淮地区曾经是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而处于其中的合肥是重要的战略重镇,至今仍保留有众多其时的文化遗址。在合肥市屯溪路与宁国路交汇处东南侧合肥工业大学南校区校园内有一口塘, 2002年合肥市人民政府在塘的西北角立了一块石碑,说明了塘的名称及其成因:“斛兵塘,又称站塘、量兵塘。东汉末年,曹操为统一天下,亲率大军南下,攻打孙权,途中在合肥安营扎寨。曹军号称八十万,但无准数。为清点人马,曹操令人在此挖一大土坑,命士兵排队走进去站满,如此反复计算出人数。当曹操率军南下后,此坑废置,渐成一水塘,后人据此称斛兵塘。”但并没有说明碑文内容的根据,其中透露的信息也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有必要予以考证。
一、斛兵塘碑文存在失实之处
根据碑文,斛兵塘开挖的时间似乎是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碑文中所说“东汉末年,曹操为统一天下,亲率大军南下,攻打孙权……曹军号称八十万……”应是指《资治通鉴》所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是时,曹操遗(孙)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但实际上曹操大军南下的路线与合肥毫不相干。《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曹操)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刘)备……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民多死者,乃引军还”。《资治通鉴》亦有记载,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南击刘表”,但大军未到,荆州牧刘表已病故,依附刘表的刘备只得率部转移,“备将其众去,过襄阳,比到当阳……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后赤壁大战爆发,曹军死伤大半,大败退回北方。由此可知,赤壁之战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曹操与合肥没有产生交集,碑文所云与史实相矛盾,因此不能断定斛兵塘开挖时间是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
根据碑文,斛兵塘开挖的用途是曹操为了“清点人马”。如此费时费力地挖掘一口大工程量的池塘去清点人马,显然不合事理逻辑,并不科学,也谈不上是智慧之举。碑文撰写者由“斛兵塘”“量兵塘”“站塘”望文生义,以塘为斛,以兵马为谷粮,像以斛量谷粮一样以塘来量兵马,所以叫“斛兵塘”“量兵塘”;因“士兵排队走进去站满,如此反复计算出人数”,所以叫做“站塘”。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应叫“站兵塘”而不应叫“站塘”。
二、斛兵塘是曹魏屯田的水利遗址
其实,斛兵塘应是在赤壁之战后开挖的水利设施,其用途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赤壁之战后,曹操势力遭到了重创,再无力统一全国,因此被迫收缩战线。其西线与刘备等势力对垒于上邽、天水一带,其东线与孙权等势力对峙于合肥所在的江淮地区,进入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合肥及其周边地区就成了曹魏与孙吴对峙的最前线。为了配合这种战略大调整,就地解决军粮问题,曹操在与孙吴对峙的前线地区广泛推行屯田,以战养战。建安十四年(209)“春三月,(曹操)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建安十四年即赤壁之战后的次年,曹操吸取赤壁之战中其军队“不习水战”的教训,建立“水军”,并且亲率大军抵达合肥。曹操采取了多项措施巩固江淮地区统治:政治上加强地方政权组织建设,“置扬州郡县长吏”;经济上通过屯田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在合肥及邻近的周边地区掀起了一个屯田的高潮。由上可以得知:其一,赤壁之战后曹操鉴于实力,被迫收缩战线,其东线即合肥所在的江淮一带,与东吴形成了对峙的态势。其二,因为长期对峙,大量军队长期固定驻扎在前线地区,军粮就成了重要的问题,而从别处调拨军粮会有许多风险,后来的邓艾就曾经说明军粮转运过程中费时费力的弊端:“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如果就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屯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好形式,而水稻单产量高,江淮一带的气候和水资源条件适宜于水稻的种植,故种植水稻是较佳的选择。其三,种植水稻对水利条件要求很高,因此要种植水稻必须兴修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故曹操在扩大利用已有的水利工程如“开芍陂”等的同时,还兴建新的水利工程,斛兵塘应是在这次大规模推行屯田后挖掘的水利工程。故斛兵塘应是建安十四年(209)以后开挖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设施。公元209年,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合肥及周边地区迅速地掀起屯田种植水稻的高潮,是因为在此之前已有相当的基础条件。《三国志》载:“刘馥,字元颖,沛国相人也……太祖(曹操)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刘馥单马走合肥,设扬州治于合肥,合肥成为曹魏扬州的政治中心。《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建安五年(200)。本来扬州所属有庐江、丹阳、会稽、吴郡、豫章、九江等郡,但此时扬州的大部分尤其是江南地区为孙吴等势力控制,刘馥只能经营合肥所在的扬州江北等地区,通过兴修水利、广泛屯田发展农业生产。虽然刘馥采用的屯田类型为民屯,但为曹操赤壁之战后在这一地区进一步大规模屯田奠定了基础。
三、“斛兵塘”“量兵塘”名称的来历与屯田相关
屯田是官府把士兵或平民组织起来,实行军事化管理,从事农业生产的形式。这不同于郡县制下编户齐民的私有制的农业生产方式。西汉文帝时已存在零星小规模徙民于边陲农垦的现象,这是较早的民屯萌芽。汉武帝时,内修政治,外拓疆土,在新开拓的西北和北部边陲等广大地区,从内地迁徙去了大量的人口实行屯田,这是民屯。后来又发展到军队士兵“且耕且守”,即一边就地从事农业生产一边戍边的情况,因此有了军屯。故屯田根据劳动主体不同就有了民屯和军屯之分,不过两汉时期尚未在全国普遍推行屯田,但汉代屯田的管理机构、组织系统、经营方式等为三国时期曹魏普遍屯田提供了历史经验,后来曹操在许下推广屯田时有云:“‘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屯田,所在积谷。”可见曹魏屯田是受到汉代屯田启发的。
三国时期,魏、蜀、吴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全面推行屯田制度。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其后进入长期战乱时期,因此出现了以下情况:其一,很多地主逃亡或死亡,大量原来地主所私有的土地成了无主荒地,于是官府按照“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的原则,使这些无主荒地名义上成为官府所有。正如时人司马朗所言:“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官田”“公田”就是这些无主荒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其二,战乱导致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走上逃亡之路,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整个社会出现了大饥荒,甚至严重到“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悲惨状况。粮食问题也决定了汉末以来兴起的各路军阀势力的生死存亡,军阀因缺粮不战自败,“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军阀有粮则存,无粮则亡,解决军粮问题就成了各路军阀的当务之急。要解决军粮问题,就要恢复农业生产,大量无主荒地和脱离土地的流民劳动力的存在,为恢复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条件,而屯田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适合的方式。许多军阀割据势力为了生存,不得不实行屯田,把大量的流民劳动力用军事手段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如中平末年(189)徐州牧陶谦就在所辖州境内屯田;兴平二年(195),幽州的公孙瓒“开置屯田”。曹操主持的屯田最有典型意义。建安元年 (196),曹操在许下大规模地实行屯田。后来曹操的势力扩张到哪里,就把屯田推广到哪里。曹操正是通过屯田措施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解决了军粮问题,为曹魏政权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所以曹操在中原军阀混战中一枝独秀,脱颖而出,得以完成对北方的统一。王仲荦评价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许多重要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算曹操的在内地推行屯田政策了。”
赤壁之战后,江淮地区成为曹魏与孙吴对峙的前线,合肥成为军事重镇,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巩固在合肥的统治,曹魏在包括合肥在内的江淮地区大规模推行屯田。曹魏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类型。军屯以士兵屯田,“且田且守”,一边进行农业生产,一边履行军事职责。江淮地区的军屯主要种植水稻,士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到前线作战,“春惟知耕,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军屯按军队编制管理,最基层的单位叫做“屯”或“营”,也有称“屯营”的。每屯六十人,屯田的士兵被称为“屯兵”,因为在田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所以又叫“田兵”“田卒”;因为屯田兵是佃种官府土地,所以又称为“佃兵”。汉末三国时期,粮食等物品用升和斛等容器去盛装,升和斛等还被作为容量单位。如曹操令,“其收田租亩四升”,国家对私有土地征收“田租”,每亩征收定额实物田租粮食四升,可证升是法定的容量单位。同样,斛也是当时法定的容量单位,如兴平元年(194),“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建安元年(196),“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等。由于屯田兵生产的粮食用“斛”来盛装计量,故屯田兵可以被称为“斛兵”,这是从借代意义上产生的名称。“斛兵塘”则是屯田士兵兴建的用来蓄水的池塘。军屯的士兵主要种植粮食,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粮兵”,而“粮”是现在使用的简体字,繁体写作“糧”,由于“糧”与“量”读音相同,字形有部分相似,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糧兵塘”就被误写作“量兵塘”。 “量兵塘”与“斛兵塘”一样,也是从借代意义上产生的名称。今人望文生义,加上联想到了“斛”这种量器,不认真考究,因此就有了2002年合肥市人民政府的碑文解释。
四、屯田促进了曹魏政治经济发展
曹魏的屯田意义重大。首先,曹魏实行民屯使因战乱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得以重新回到土地上,避免了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苦。屯田民虽然因佃种国有土地受到了沉重的剥削,但在曹魏政权的庇护下,有了有利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保障了相对安定的生活。曹魏政权可以从屯田民那里获得大量田租,缓解了粮食危机,为曹魏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其次,军屯使军队自己就地进行农业生产,以战养战,既避免了从其他地区运输军粮长途跋涉、消耗人力物力的弊端,同时还减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正因为曹操“州郡例置屯田,所在积谷”,所以“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进而可以胜兵南顾。其三,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江淮地区为了种植水稻,需要兴修陂塘等水利工程。建安五年,刘馥“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拉开了江淮地区兴修水利的序幕,其后相关记载不断。魏文帝时,郑浑“迁阳平、沛二郡太守……于萧、相二县界,兴陂堨,开稻田”。正始三年(242)三月,“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正始四年(243),司马懿“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另外还有史书没有记载的许多陂塘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一般可以灌溉数百顷、数千顷农田,有的甚至可以灌溉上万顷农田。只有屯田这种集体组织,才能有条件组织大量民力,兴修陂塘等相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较难进行水利工程建设的。这些陂塘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自然的雨水不会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与否而降或停,陂塘在降雨充沛时蓄水,待农业生产需水而又不降雨时,根据需要开启陂塘闸门自动流淌到农田中,既利用了自然,又节省了人力。史载,“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可见战国时期江淮地区就使用了陂塘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农田灌溉的陂塘水利技术以及其他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经济中心由中原南移。陂塘水利技术“既有防洪的功能,又有蓄水的效用,可以利用江河水盛之时蓄水以备旱灾。且启闭由人,大小任意,视农田需要而定……较之单纯依赖自然水源的利用,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也大大提高了对自然水资源的利用率和人工控制水利的能力,对农业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四,有利于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由于大量兴修陂塘,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史载江淮地区的屯田,基本是种植水稻。建安五年,刘馥“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邓艾“行陈、蔡已东至寿春……许昌左右水稻田……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寿春、淮南、淮北等地的屯田也种植水稻,产量常三倍于其他屯田。
五、屯田制废除与“站塘”来历蠡测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事业,被称为“本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表现为土地所有制,通常表现为封建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私有土地所有制两种形态,而且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其土地所有权都属于封建国家所有,属于国有土地所有制性质。屯田民政治地位低下,被军事性地控制在土地上,不得改行、迁徙,成为隶属于封建国家的依附农民;经济上被剥削,要把土地上生产的超过一半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官府,有时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杂役。因此屯田制度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虽然在战乱时期屯田有着许多积极意义,但也有很多消极影响,一旦进入和平年代,屯田就不为时代所需要了。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曾想统一全国,但都没有实现。后来曹魏政权被司马氏所控制,在司马氏正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前的263年灭了蜀,灭蜀的第二年废除了民屯制度。咸熙元年(264),“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曹魏民屯有一套独立的管理系统,军事特征明显:屯田民有一套独立的不属于州郡户籍系统的屯田民籍;其基层组织与军屯一样,也叫“屯”,军屯每屯六十人,但民屯每屯五十人,设屯司马一人,屯之上设屯田都尉或称典农都尉,简称都尉,与县令长平级;又在其之上设典农校尉,或称典农中郎将,简称典农,与郡太守平级。263年,随着蜀的灭亡,西部战事解除。而东吴此时也沦落不堪,难与魏国较量,原先的对峙局面基本已不存在。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废除了民屯管理系统,主管屯田的典农相应地变为郡太守,都尉变成了县令长。将原来属于国有土地的民屯土地分授给屯田民,或者说让他们自行占有,国家予以承认,这些土地名义上就由国家所有变成了屯田民私有,屯田民变为郡县管辖下的编户齐民。同时这也是对屯田国有的土地被官僚地主所侵蚀、侵占变为私有的既成事实的承认。譬如何晏曾经“共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曲田数百顷”。一次性就侵占国家屯田土地数百顷,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司马师兄弟“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这些原来的国有性质的土地就转化为地主的私有土地,大量的国有土地流失。另一方面,封建官府还将屯田上的劳动力屯田民用于赏赐,如《晋书·外戚·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再加上屯田民受到了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没有积极性,大量地逃亡,甚至起义,所以劳动力越来越少,屯田因此失去了必要的条件——一定量的国有土地和劳动力。所以咸熙元年(264)罢屯田官,废除民屯,使屯田民成为郡县统领下的编户齐民拥占有一份土地并向国家缴纳赋税。另外,伴随着民屯的废除,原先的军屯逐渐民屯化。原先的军屯改变经营方式,通过租佃的方式租种国有土地,由传统的“且田且守”“出战入耕”的“带甲之士”的军屯演变为租佃型军屯。由于战事渐少,军事越来越淡化,农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一部分士兵已演变成了专门从事屯田的“佃兵”,实际和以前的民屯屯田民无异,只是仅有军籍而已。如晋武帝泰始五年(268),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把所领戍守襄阳的兵士一分为二,一半专门屯田,一半专门戍守,“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史书所载类似例子还很多。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平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结束了自东汉末以来的战乱分裂局面。正是在灭吴的大好形势下,晋武帝希望“辑兵静役,与人休息”,决定“罢州郡兵”,大量裁军,军屯的士兵卸甲归田,成了郡县的编户齐民。虽然我们没有见到明确的废除军屯的史料,但事实上在此后晋武帝时期基本不见了军屯的记载。就在平吴的280年,西晋颁布占田令。《晋书·食货志》载占田令的主要内容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也就是说,一般平民占田,男子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即一夫一妻可以占田百亩为私有,超过这个限额就是违法。官吏按照官品的高低相应占有不同数额的土地,最高五十顷、最低十顷为私有,超过相应的限额即为违法。尽管官吏可以拥有的私有土地广大,毕竟有个上限,不能无限制地占有土地,占田令为限制大地主私有土地所有制的膨胀提供了法律根据。
占田令把私有土地命名为“占田”。封建社会承认土地私有,有完全的处置权,可以买卖。国家把这些土地登记在私人名下,这是对土地私有在法律上的承认,因此私有土地就叫“名田”。汉代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哀帝颁布了限民“名田”的法令。《汉书·哀帝纪》载:“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其下颜师古引曹魏时人如淳解释曰:“名田国中者,自其所食国中也,既得租税,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顷。”所以“名田”等同于“私田”。汉武帝不准有市籍的商人“名田以便农”,唐人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商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故“名田”又可称为“占田”,东汉以后的人将《史记》《汉书》的“名田”都称为“占田”。及至魏晋时期私人占有国有屯田后,国有土地就成了私有土地,称为“占田”。“占”的基本含义就是私有。随着屯田私有化变为“占田”,其土地上附属的水利设施等也成为私有,故池塘就叫“占塘”。斛兵塘所在的屯田土地为私人所占后,原来的斛兵塘就变为了“占塘”,意为私人所有之塘。但由于历史的变迁,“占”的私有含义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因为读音相近的缘故发生了讹传,原来的“占”变成了“站”,“占塘”演变为今天合肥工业大学斛兵塘碑文的“站塘”。无独有偶,在今合肥市瑶海区有一个“站塘村”,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此处存疑,有俟于贤者方家。
综上,可以证明斛兵塘是赤壁之战后曹魏屯田所兴建的水利设施而不是为了“清点人马”所挖的“土坑”。从“斛兵塘”到“占塘”名称的演变,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屯田制度的兴衰变化,也折射了此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