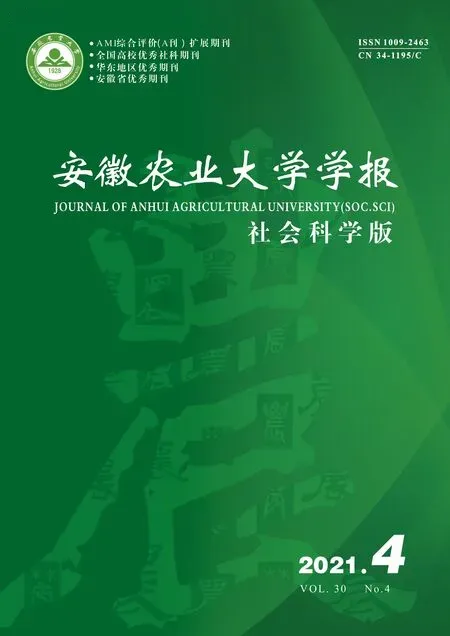论欧阳修之清泉雅致*
何婵娟
(广西教育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在滁州作《醉翁亭记》,文成之后,天下传诵。朱弁《曲洧旧闻》言道:“《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醉翁亭记》自诞生至今,千年时光里,一再被传诵,成为古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欧阳修庆历五年因张甥案贬滁州时,时年39岁。正当壮年的他以“醉翁”自嘲,怡情山水之间,以消解仕途之不顺。《醉翁亭记》从滁州山水一层层写来,重点归到太守心态的述写上。在山与水的描绘之中,突出了“讓泉”:“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讓泉也。”醉翁亭“翼然临于泉上”。在文章中,“泉”是风景中灵动之笔。不仅如此,文章第三段写道:“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此处,“泉”化为“酒”,入欧阳修之品题,与豁达、洒脱的醉翁形象和谐融为一体。
此文之外,“泉”多次出现在欧阳修笔下。在其作品中“泉”这一物象共出现了四十多次,这些诗文体现了欧公之雅趣与风范。
一、泉的呈现场景
(一)优美的山水
欧阳修喜好山水,每到一地,多出游,对履经之地的山水不吝歌颂。欧阳修笔下的山水画卷中,不乏潺湲的泉水、清澈的小溪。
明道元年(1032),欧阳修在洛阳为西京留守推官,春天与杨子聪、张谷、陈经等人游龙门,这次游玩很尽兴。他们“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间,登山上方,路穷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楼,听八节滩,晚泛舟,傍山足夷犹而下,赋诗饮酒,暮已归”。这次游玩,欧阳修作了《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其《伊川独游》咏道:“东郊渐微绿,驱马忻独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远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诗歌雅致清新,“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响”既从视觉上写了晴朗天气下盛开的梅花,又从听觉上突出了泉声之响朗,从而突出了环境之清幽美丽。
《和丁宝臣游甘泉寺》一诗作于景祐四年(1037),欧阳修时为夷陵县令,丁宝臣为峡州军事判官。此诗记录两人游玩甘泉寺情景。诗中描写甘泉:“空余一派寒岩侧,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岂解惜清泉,蛮俗那知为胜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中评论道:“夷陵县治下临峡,江名绿萝溪。自此上泝,即上牢关,皆山水清绝处。”欧诗慨叹泉水不被当地人怜惜,似有所寓托。
《幽谷晚饮》是欧阳修初到滁州时所作,“山势抱幽谷,谷泉含山泓。旁生嘉树林,上有好鸟鸣。鸟语谷中静,树凉泉影清。”可见,在欧阳修山水诗中,凡是有泉之处,他必特意描绘。
(二)雅致的生活环境
欧阳修日常生活雅致清放。蔡絛《西清诗话》曰:“欧公守滁阳,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谢某者杂植花卉其间。谢以状问名品,公即书纸尾云:‘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其清放如此。”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了欧阳修知扬州时作平山堂:“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
《幽谷泉》作于庆历六年(1046),诗歌描绘了幽俗泉旁优美的环境:“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溉稻满春畴,鸣渠绕茅屋。生长饮泉甘,荫泉栽美木。潺湲无春冬,日夜响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惯逢朱毂。顾我应可怪,每来听不足。”泉旁环境幽雅宁静,百姓生活怡然自适,俨然世外桃源。欧阳修很喜欢此地清幽雅致的环境,喜欢听此处的泉声。他在《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阳》其二中言道:“三年永阳谪,幽谷最来频。谷口两三家,山泉为四邻。但闻山泉声,岂识山意春?春至换群物,花开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颍之滨。人去山自绿,春归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种花勤。”离开了滁州,他依然对此地念念不忘。
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转兵部尚书、知青州。其雅致之风,至老而不衰。《游石子涧》:“席间风起闻天籁,雨后山光入酒杯。泉落断崖舂壑响,花藏深崦过春开。”他仍如年轻时那般,选择环境雅致优美的地方举办宴席,边喝酒,边赏风景,边听泉声,快乐悠哉!
(三)欢乐的聚会
欧阳修热情好客, 陆鎣言道:“欧阳公文章政事,衣被天下,喜奖后进。足迹所至,多山水游宴之乐。”
在夷陵期间,政事余暇,欧阳修常与判官丁宝臣、推官朱处仁诗酒漫游。《蝦蟆碚》一诗作于景祐四年(1037)。《夷陵州志·卷二》记载:“蝦蟆碚,在州西六十余里,江之右有石如蝦蟆,其大数丈,石上出泉。”蝦蟆碚泉水水质较佳,欧阳修与友人来此煮水烹茶:“石溜吐阴崖,泉声满空谷。能邀弄泉客,系舸留岩腹。阴精分月窟,水味标茶录。共约试春芽,枪旗几时绿。”诗中的“春芽”“枪旗”都是指茶叶,《大观茶论》中言:“茶枪乃条之始萌者……茶旗乃叶之方敷者。”朋友们一起品茶论道,其乐融融。庆历元年(1041),他写给梅圣俞的《忆山示圣俞》诗中高度称赞蝦蟆碚:“蝦蟆喷水帘,甘液胜饮酎。”
在滁州时,“州南百步许,有山曰丰山,山势一面高峰,三面竹岭,山下一径,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尽,遂得幽谷。引泉为池,作亭其上,号丰乐亭。州之西南曰琅琊山,岩谷深远,有溪自两峰夹流而下,曰酿泉。公自号醉翁,作醉翁亭于泉上,每暇日,或独游,或携宾客觞咏于二亭,滁人望公若神仙焉”。
欧阳修在诗歌中反复回忆滁州游宴。他在《送谢中舍二首》其一中概述了这段往事:“滁南幽谷抱山斜,我凿清泉子种花。故事已传遗老说,世人今作画图夸。金闺引籍子方壮,白发盈簪我可嗟。试问弦歌为县政,何如罇俎乐无涯。”皇祐元年(1049)伏日,徐无逸、焦千之二人游西湖,欧阳修因身体不佳,未往。所作《伏日赠徐焦二生》一诗回顾了滁州任上之快乐悠游:“清泉白石对斟酌,岩花野鸟为交朋。崎岖磵谷穷上下,追逐猿狖争超腾。酒美宾佳足自负,饮酣气横犹骄矜。”
泉是自然界中一道优美的风景,在欧阳修的山水游宴中,凡是有泉之地,多引发他反复思念。
二、泉的媒介作用
在欧阳修笔下,“泉”不仅与优美的山水、雅致的环境以及欢乐的聚会相联系,“泉”还有着特殊的功用,起到多方的媒介衔接作用。
(一)泉与酒
“酿酒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酒既是一种物质饮料,又具有一种精神文化价值,它从一产生起,就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升,为酿酒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使市民阶层急速壮大,他们对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酒也有了更大的社会需求。
欧阳修诗文中多次表达对酒的喜爱。 “在欧阳修存世的860余首诗歌中,涉及酒的有309首,比例为35.7%,高于李、杜、白三家。比例之高折射出欧阳修日常生活中饮酒之频繁”。在欧阳修诗文中,“泉”有时酿为酒,入口而甘,如《醉翁亭记》中“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 何焯《义门读书记》引《泊宅编》云:“东坡书此文,改‘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按倒转则句响,亦本《月令》‘水泉必香也’。”这可能是欧阳修对“泉”特别钟情的原因之一。
《圣俞会饮》一诗作于庆历元年(1041):“洛阳旧友一时散,千年会合无二三。京师旱久尘土热,忽值晚雨凉纤纤。滑公井泉酿最美,赤泥印酒新开缄。”诗中以美酒衬托友情,突出了滑州井泉所酿酒之美味。日常生活中,“泉”可酿美酒,自然让欧阳修对“泉”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愫。
(二)泉与茶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两宋时期中国的茶区继续扩大,制茶技术进一步改进,贡茶和御茶精益求精,饮茶之风更加普及,斗茶之风盛行,塞外的茶马交易和茶叶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宋人一般在酒后饮茶。其一是茶能解酒,“遣兴成诗,烹茶解酒”,其二是“酒后饮茶可以增加聚会的时间,将欢乐的时光留住并延长”。
欧阳修是饮茶爱好者,作有近二十首茶诗。好茶需好水,欧阳修对水相当考究,曾撰《大明水记》点评天下之水,辨别陆羽《茶经》记载之谬。在欧阳修的茶诗中,“泉”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尝新茶呈圣俞》一诗作于嘉祐三年(1058),当时福州知州蔡襄寄北苑新茶给他。蔡襄为北宋著名茶人,曾任福建路转运使,先后知福州、泉州等地。他在“大龙团”茶的基础上改良生产出贡茶“小龙团”。北苑茶为极品茶,“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得到好友馈赠的贵重之茶,欧阳修喜不自禁,待客以新茶:“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远从天涯。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泉是烹茶之佳水,刘源长《茶史》曰:“山泉独能发诸茗颜色滋味。”又曰:“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水也。”欧阳修待客人时,选择好天气,备好甘甜的泉水、洁净的器皿、慢悠悠地品茗论茶,颇具闲雅之致。欧阳修仕宦各地,对甘泉比较留心,这也与其爱好饮茶有关。
不仅自己待客讲究水之品味,送礼时也特意叮咛对方用好水冲泡茶叶。《送龙茶与许道人》中言道:“我有龙团古苍璧,九龙泉深一百尺。凭君汲井试烹之,不是人间香味色。”“茶之品,莫重于龙凤团。凡二十余饼重一觔,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缕金其上,其贵重如此。”送朋友如此好茶,当然要特意叮嘱汲取九龙泉的好水。
欧阳修尝自陈:“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在他的这一爱好中,“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泉与琴
欧阳修喜好音乐,是江西琴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歌入弦,并以琴会友,形成了一个艺术群体。道人李景仙、潘道士,琴僧知白、义海,文人苏轼、梅尧臣、刘敞、沈遵是其琴友”。早在景祐年间,欧阳修即从好友孙道滋学琴:“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他对琴的爱好至老不衰。晚年自号“六一居士”,自喜有“琴”。
《醉翁亭记》天下闻名,太常博士沈遵慕名而往滁州实地勘察游玩,“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作《醉翁吟》一调”。 嘉祐元年(1056),沈遵遇到欧阳修,特为其弹奏。欧阳修感慨而作诗《赠沈遵》,又为其作辞《醉翁吟》。嘉祐二年再作《赠沈博士歌》。沈遵一曲,拨动了欧阳修的心弦,让他重温了滁州醉翁记忆:“醉翁吟,以我名,我初闻之喜且惊。宫声三叠何泠泠,酒行暂止四座倾。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翁欢不待丝与竹,把酒终日听泉声。有时醉倒枕溪石,青山白云为枕屏。”诗中,欧阳修一再回顾滁州泉水动听的声音。泉声即乐声,友人将其写入琴中,勾起了他无限的回忆。他在《忆滁州幽谷》中一再咏叹:“谁与援琴亲写取,夜泉声在翠微中。”嘉祐二年(1057),沈遵通判建州,欧阳修在《赠沈博士歌》中再次表达了他对滁州山泉的眷念:“自言爱此万仞水,谓是太古之遗音。泉淙石乱到不平,指下呜咽悲人心。时时弄余声,言语软滑如春禽。”欧阳修如此眷恋滁州山水,跟滁州讓泉、幽泉等发出的天籁之音有密切关系,不仅仅是“泉香而酒洌”勾起的思念。“泉”如同一道纽带,将自然界与欧阳修的心灵世界连接起来。
欧阳修自己也常携古琴出游,谱泉声入琴。《游琅琊山》作于庆历六年(1046)滁州任上。“使君厌骑从,车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长松得高荫,盘石堪醉眠。止乐听山鸟,携琴写幽泉。爱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牵。”不仅在滁州,他携琴写曲,早在夷陵时期,即有此举:“飞帆洞庭入白浪,堕泪三峡听流泉。援琴写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穷山间。”作为北宋文人琴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可谓擅取以“泉”为代表的自然界之音。《醉翁吟》后经苏轼作词,成为江西谱的代表作,流传并影响至今。
三、林泉雅致与文学书写
(一)林泉雅致
中国士人很早就与山水结缘,孔子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中国的诗歌,以山水清音为佳赏。于文人而言,“山水清音最写不尽的一个意象,便是山泉之美。清泉汩汩,诗心千年浸润;林泉高致,词人代代向往”。
北宋著名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言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山林之乐、林泉高致,寄寓着历代文人之理想。魏晋时期,山水诗兴起,魏晋士人借山水诗寄托他们归隐山林、与自然山川为侣的思想以反抗现实政治。唐代士人发现了各地山水之美,他们中不少人游历广泛,高山大川、瀑布清泉、田野园林,在他们笔下都有精彩的呈现。唐人的山水诗,寄寓了他们蓬勃的朝气和进取的热情。由于新儒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禅宗的影响等因素,宋代士人侧重心性修养的内省。宋代“文艺随着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而变化,追求静、幽、淡、雅,内心细腻感受的精致表达,向着超尘脱俗、忘却物我的方向发展”。欧阳修是宋中叶文坛翘楚,他学问渊深,诗文取径广泛。其山水诗文既学习前代文人技法,又注重创新出奇,凸显宋人风范。
林泉雅致素为欧公喜好,他尝自言:“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在北宋士人眼中,山与水密不可分。郭熙曰:“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众水之中,“泉”以其清甘可口、清音泠耳又备得欧阳修喜爱。“泉”在他笔下,有着生动的书写。
(二)泉的书写
欧阳修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了泉的声音、味道、意境与形态,他最喜欢表现泉的声音,在与泉意象相关的诗文作品中,写泉声的占了一半。
欧阳修年轻时就喜欢啸傲泉石、隐逸渔樵的生活。作于明道元年(1032)的《伊川独游》曰:“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远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作于同年的《二室道》说得更直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贬谪夷陵时,欧阳修生活寂寞,他对夷陵山中的泉声颇为眷恋。“林枯松鳞皴,山老石脊瘦。断径履颓崖,孤泉听清溜。”滁州丰乐亭附近的泉更让他流连忘返,《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阳》其一曰:“山气无四时,幽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鸣,野艳笑而傞。宾欢正喧哗,翁醉已岌峩。”泉水泠然之音,既让欧阳修得到了美妙的音乐享受,又消解了他仕途之不快而达到自适之境。“翁欢不待丝与竹,把酒终日听泉声。有时醉倒枕溪石,青山白云为枕屏。”在听泉之际,欧阳修既充分享受这份林泉雅趣,又能得到新的启示,获得新的动力。他在景祐四年(1037)所作的《下牢溪》中言道:“隔谷闻溪声,寻溪度横岭。清流涵白石,静见千峰影。岩花无时歇,翠柏郁何整。安能恋潺湲,俯仰弄云景。”林泉虽好,但不能过于迷恋,深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他还有众多理想要付诸行动。
前文所述,欧阳修好茶,喜欢用甘甜的泉水来烹茶,因此他很关心泉水的味道。《普明院避暑》曰:“选胜避炎郁,林泉清可佳。拂琴惊水鸟,代麈折山花。就简刻筠粉,浮瓯烹露芽。归鞍微带雨,不惜角巾斜。”他和梅尧臣、谢绛、尹洙等人选择林泉清佳的洛阳普明院避暑,众人一起弹琴、赋诗、烹茶,宋代文人的雅致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泡茶定要好泉水,“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揀择客亦嘉。”泉影响着欧阳修的地域观念,在他眼中,有甘泉的地方才是理想的居住地,“泉甘土肥兮鸟兽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寿而丰”。
清泠美妙的泉声能安抚诗人躁动的心灵,启示其反躬自省;甘甜美味的泉水能满足作者的口腹之欲,增加朋友相聚的快乐。潺湲的溪泉又为大自然增添了灵动的风景。《陪府中诸官游城南》:“一雨郊圻迥,新秋榆枣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声喧。”诗歌动静协宜,溪水流淌的原野,更让人喜欢。《和子履游泗上雍家园》中道:“苍云蔽天竹色净,暖日扑地花气繁。飞泉来从远岭背,林下曲折寒波翻。”因为飞泉,整个园子的景观变化多端,雍家深得造园之道。
欧阳修喜欢游宴之乐,《醉翁亭记》中描写的“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的热闹场景让他非常陶醉。但他具博爱精神,面对自然万物时,他更愿意安静:“泉落断崖舂壑响,花藏深崦过春开。麏麚禽鸟莫惊顾,太守不将车骑来。”他生怕打扰这些山间的动物精灵。有时听着泉声,他仿佛与万物融为一体:“是时新雨余,众壑鸣春泉……野鸟窥我醉,溪云为我眠。日暮山风来,吹我还醒然。”这些与泉相关的诗文充分展现了欧阳修的林泉雅致,寄寓了他涤尽尘缨、忘却物我、归返自然的情趣与人生理想。
(三)唱和与影响
自庆历始,欧阳修即以文章独步天下。叶梦得《避暑录话》曰:“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洪本健指出:“庆历初入主文坛的欧阳修,在此后的岁月中更加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盟主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从政、交游和创作上。”欧阳修不仅深刻影响了他所处的北宋文坛,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耒《上曾子固龙图书》曰:“欧阳公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之豪杰,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正如洪本健指出的那样,交游酬唱是欧阳修文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朱弁《风月堂诗话》记载:“欧公居颍上,申公吕晦叔作太守,聚星堂燕集,赋诗分韵,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刘原父得‘风’字,魏广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无逸得‘寒’字。……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从此记载来看,欧阳修主持的日常宴会已成为北宋文坛之盛会。在欧阳修与其朋友、门生交游酬唱的作品中,“泉”有时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话题。
欧阳修在滁州建丰乐亭、凿清泉,作《醉翁亭记》,一时成为文坛佳话。其朋友、门生或唱和或寄题,非常热闹。梅尧臣在《寄题滁州醉翁亭》中言道:“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使君爱泉清,每来泉上醉。醉缨濯潺湲,醉吟异憔悴。日暮使君归,野老纷纷至。但留山鸟啼,与伴松间吹。”可见,作为欧阳修的知己与诗友,梅尧臣非常了解他内心的所思所感。梅尧臣另作有《和永叔琅琊山六咏》等诗,表现了同样的情感。庆历新政时与欧阳修同为“四谏”之一的蔡襄在《寄题滁州丰乐亭》中赞道:“君为滁上守,乘闲务幽寻。群从留山阿,美望穷前林。良醼追佳赏,高亭旷遐临。烟云无定姿,水石唯清音。静见鱼鸟适,遥闻鸡犬深。”赞颂友人治理之功,同时表达思念之情。刘攽在《题欧阳永叔新凿幽谷泉》中赞曰:“公有高世材,此山共森峙。公有济物心,此泉共清泚。泉始居地中,隐塞未如此。今为万丈流,近自一勺始。”朋友们围绕着“泉”这一共同的物象,或鼓励或赞扬欧公在滁州之政。曾巩庆历元年(1041)入太学时,即得欧阳修赞赏,成为其得意门生。曾巩有《奉和滁州九咏九首》。其中《游琅琊山》描写了琅琊山之泉:“长淮水未绿,深坞花已开。远闻山中泉,隐若冰谷摧。”其《幽谷晚歌》再次描绘了此处优美的环境:“爱此谷中泉,声响远已播。槎横势逾急,雨点绿新破。旁生竹相围,竦竦碧千个。”。
在欧阳修及其友人的歌咏之下,滁州山水享誉当世。葛立方《韵语阳秋》曰:“滁之山水,得欧文而愈光;欧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薛时雨《重建醉翁亭碑》曰:“醉翁当宋全盛治滁,不三年,滁之山水遂托于醉翁而气象始发。”欧阳修与“泉”有关的文学唱和与创作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坛,更影响了滁州等地的地域文化。杨士琦在《重建醉翁亭记》中言道:“滁人岁时谒拜二贤,退而歌咏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亲见公之乐乎此也,而又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
文学影响之外,欧阳修与泉有关的以酒、茶、琴为代表的日常喜好,也影响了北宋的休闲文化。潘立勇《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与美学转向》一文论述宋代休闲文化兴起之因:“商业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的形成,人本追求的凸显,使宋代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近世特征,从而导致休闲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已更多地把自己的审美追求同金石文玩、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花木品赏、诗酒茶食等闲适生活联系起来。在宋人的这些休闲方式之中,欧阳修是积极的践行者,其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欧阳修是北宋三朝重臣、文坛盟主、学界领袖,其一举一动均受世人关注。其丰富多样的休闲方式、雅致的醉翁情味、豁达超然的精神深刻影响了宋代士人。
于上所论,“泉”是欧阳修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物象,它仿佛醉翁世界的一把钥匙,深入进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欧公之作品与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