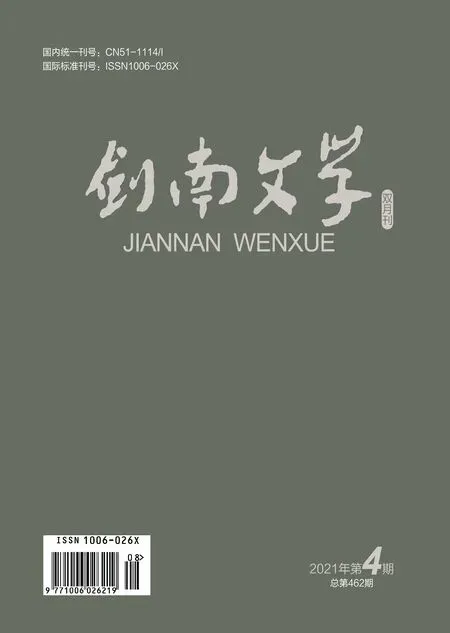风吹塞影淡烟云
——马平小说新作《塞影记》的家园叙事
□曹雪萌
《塞影记》 的小说文本始终围绕“家”这一核心语义拓展。作家返归历史现场,以“我”误入一处叫鸿祯塞的地方采访写作为线索,借访谈形式,将主人公雷高汉的生命历程呈现,以书写四川、铭刻历史的使命感构筑鸿祯塞宏大场域,借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命运述说家园得失与重建。在叙事中着意挖掘雷高汉命运悲剧,在爱与善的指向中,呈现百年家园与人生意蕴。
一、家园的寻得与皈依——生存与爱欲的“饱饭”
“‘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对于孤儿雷高汉而言,“家”是极其模糊、极难建构的存在,脱离了血缘纽带的关照,他就是可悲的无根之萍。因为雷高汉的坚韧与善良,作者将鸿祯塞设置为主人公雷高汉的诗意家园,这一与他毫无血缘链接的居地接纳了他,并逐渐成为他寄托生命历程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作者设置了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来体现小人物于大环境中的生存困局与惊险,如修暗道时面临死亡的恐惧、被当作抢亲傀儡时的无助、担任水官时的虚空等,用笔简练却生动翔实,语言朴实内藏机锋,作家将现代社会卑微“打工人”的典型形象刻画清晰。文论家提姆·克雷斯韦尔曾指出:“当人们以命名的方式赋予空间以意义之时,空间就变成了地方。人们通过身体在日常空间中的流动来确认地方,从而与之建立起情感联系,这可以理解为本土认同得以生发的基础。”作家着意发掘与凸显的正是人物历经生存苦煎后的身份认同与情感皈依,赋予主人公以活泼积极的生活态度,使其拥有巴蜀人民所禀赋的坚韧、实干、豁达、勇敢特性,着力冲决苦难,顽强扎根于包氏家族群体之中,逐渐寻得“饱饭”的生理满足,并找到情爱的寄托,获得个体身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重与劳动的价值。鸿祯塞,成为主人公雷高汉承载生存与欲望的多重慰藉,也成为承载作家对四川人民“劲草”般生命活力的关注空间。
作家笔下的家园供给雷高汉以生存的“饱饭”。在乡土中国,苦难的肇始便是饥饿,正如哲学家马斯洛所言:“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就是对生存的需求。一个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会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求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者掩盖其他的需求。”在小说中,作者“无意”且精心刻画饥饿对于主人公的意义:“饱饭”是养父母为雷高汉作的小名,也是雷高汉儿时生活中唯一的甜梦;当他进驻包家,隔三岔五能吃上大笼里的蒸肉便是极大的生存满足;在饥寒交迫的年月,“指望今年能吃上一顿饱饭”也成为雷高汉们最大的企盼;而当雷高汉问及虞婉芬的小名时,作者的语言建构则极尽幽默与反讽,凸显乡人对“饥饿”的原始理解与“饱饭”的诗兴追求:“雷高汉分不清小婉和小碗。小碗,怎么吃得了饱饭。”
在家园空间中,作者一方面呈现着饥饿的粗野面目,再现百姓在愚昧时代对“饱饭”的生存欲望,对艰辛苦难生活进行有力的书写;另一方面则歌咏乡人于苦难中前行的生命强力,由饥饿所串联起的乡村善义,在小说中显得弥足珍贵:“雷家收留了我,我就姓雷了”,正是对养父母赐予食物的感恩与孝义,成为小说主人公进驻包家的前提;拿到修护暗道工程的报酬,他也不忘旧恩,仍以名为“饱饭”的谦卑小辈自居,将土地分给饥饿的乡人;面对困难年月的饥寒交迫,毫不犹豫潜进暗道,冒出偷粮救助虞婉芬的念头。这都是发自内心的善、义换得更多的良报:罗红玉给他蒸馒头,丁继业为虞婉芬送米……这些人物的聚合都成为作者家园意识的承载,爱与善的意义融汇使主人公与读者均体会到家之“饱饭”的重要与温暖。当小说情节行至末尾,作者则令雷高汉中气十足地向鸿祯塞高吼着“饱饭”一词,这也是作者情感的喧泄喷薄,饥饿——无数次的“饱饭”,以善、义与不屈不挠的乡土文化信仰,从而一次次召唤着家园的生命与根魂。
家园同样也是牵动人爱欲情感的敏锐神经,当“饱饭”的生理需求得以缓解,作者帮助雷高汉从饥饿中走出,伴随而来的却是情感的跌宕,另一种痛楚叠跃至他与翠香们的情爱纠葛之上,作者借此转向需求的更深一层——关爱与欲望的书写。
一条暗道让他黑了几年,一块小镜子让他焐了几年,一折戏又让他苦了几年,结果却是入了那苦戏,恐怕出不来了。
家园中曾经寄托情感的爱人均离散于历史长河,作者借一个个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填补着主人公的命运空虚。在刻录伤痕之余,作家也相应在小说中构建着爱欲之外女性的爱与暖,这是抚慰情感欲求的双手,也是在苦难岁月中支撑存活于家园的毅力与精神依靠:主人公的第一任妻子包松月死在新婚夜,留下的镜子却成为他倾吐心绪的对象;梅云娥被包家强夺、内斗致死,却把一曲《翠香记》与雷家血脉传承至今;自诩为“过了一水衣裳”(意再嫁)的翠香则舍命学习,以生命成全“富农”雷高汉的识字愿望;虞婉芬则用其水性与柔情掩住雷高汉女儿的秘密,用一方手帕延续了梅云娥的爱恨情愁。
在各色女性情感象征的关照下,雷高汉不自觉进入《翠香记》的场域,上演跌宕起伏的情爱风波:
雷高汉浑身一振。他站在戏台中央,而戏台在鸿祯塞中央。那会儿,他才是鸿祯塞的主角。
“翠香”们作为配角,或泼辣或温顺,或独立或保守,均在雷高汉“平凡的世界”中书写着爱的不凡、生的伟岸。在家园,或曰雷高汉孤独的人生戏台之上,女性以爱与奉献、美与高尚,上演着“识字大课”,着力填补雷高汉的归属与爱的缺位,小说呈现着另一种家园人民的至真、温煦情感。
小说开篇以叶芝的诗歌为序幕,简笔勾勒了雷高汉爱情传奇戏台上的一唱三叹:
爱怎样逝去
又怎样步上了群山
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
流逝的爱情、重新被关照的情爱,都潜隐在时空的繁星之中,作者也将“我”的麻木婚姻生活藏掩于行文,老人对爱的信与诚、依恋与不舍与“我”对爱情的不屑甚至是虚伪在两组人物的对照之中愈加鲜明,有着反讽的意味。
“人类在世界的角落,家的意象反映了亲密、孤独、热情的意象。我们在家屋之中,家屋也在我们之中,家屋在我们之内。我们诗意地建构家屋,家屋也灵性地建构我们。”作家马平三次探访四川武胜县宝箴塞的采风体验,使其得以真切置身于庞大场域,与家园空间进行互动与对话,从而体验它的威严与神秘,进而有力地彰显表现,呈现出小说的诗意。小说字里行间扩散着农人对抗饥饿、爱欲的勃勃生气以及坚忍、义理、纯朴忠厚的巴蜀血液滚滚流淌。小说巧妙地将鸿祯塞这一森严冷冰的防御要地,构筑出有温度的“家”的形态。
二、家园的失落与重建——历史与现实糅合的叙事策略
小说主人公雷高汉的身世不断被冷落,又一再被关照,鸿祯塞这一“家”空间也在马平小说的架构中经历着失落又重建、生活无序而又有常的曲折传奇。繁盛背后则是无尽的悲凉,作者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发展造成的传统的损毁、家园的没落,浓厚的家园意识使得作家借文字唱出一曲动人的生死挽歌。
包氏家族的明争暗斗、历史长河中的大小征战、金钱社会的商业冲击、亲人的逐渐别离,均逐渐溃散着雷高汉悉心建构起的“家”。曾经极具归属感的港湾如今已成为资本家与慈善家谋构的商业别墅群,当年寄居的鸿祯塞如今涣为空旷的“玻璃屋”。没有了家园的宏阔场域,老人身处的透明景观形同福柯的“圆形监狱”,以凝视的方式解构着雷高汉的精神堡垒,将老人如今居住在此的困窘、孤独、念旧与恐惧的心绪完全外放:“一百零七岁的人生,收拢在一个玻璃护卫的逼仄空间,以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以分针或秒针的脚步,向近在眼前的终点走着,让我听到了生命的滴答声。”与此同时,玻璃屋与屋中安放的暗红皮箱,则潜藏着他与鸿祯塞的百年隐秘,他的话语被压抑于玻璃屋、被淹没于时间长河中,衰老、沉默、千篇一律、日复一日,精神家园如同暗道般就此失落,因而雷高汉道出“这儿曾经是我的家,现在是我的店”的哀叹。
独特的生活场域是构成一部好长篇的基本空间,没有这个空间,你施展拳脚的地方就会局促,逼仄。所幸作者终不愿舍弃这一家园,也不愿在逼仄的现实暗道中展开宏大的历史传奇。马平在访谈中坦言:“鸿祯塞不只是一个堡垒,但对雷高汉来说,它也绝不是一个牢笼。我能够说的是,雷高汉不能一直待在一条暗道里,一直走不出来。”原本的空间不复存在,家园的外观虽则改变,但《塞影记》承载的历史意蕴与人物张力却渐趋永恒。作者设置雷高汉以敞开的姿态面对“我”的采访,打开记忆的箱匣,将曾经的激荡岁月一一掇拾,以自身的零碎体验、情绪感受拼接起完整的充满“善义”的人生,重新寻找自己的“家”与“根”,建构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身处玻璃屋的他不再是被凝视的对象,反而是透明的全景式建筑使得旁观者“我”更好地渗入主人公的历史语境,隔绝掉当下的纷杂家常,成为与雷高汉交流取材的完美空间。作者帮助雷高汉在记忆中重新开掘精神的庇佑所:他追溯修建密道时与死神的擦肩,讲述他未曾谋面的新娘,叙说寻得亲生女儿时的哑言,串联他与鸿祯塞充满伤痕又常有温暖疗愈的一生。
“罗列日常生活不是目的,罗列历史事件不是目的,二者怎么糅合在一起就是个问题。”小说中,现在的个体(雷高汉)与过去的文化客体(鸿祯塞)相遇,作者以“书中书”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有机融合糅合,构成“生命战胜历史劫掠”的叙事模式,在记忆的重新翻检中架构小说《塞影记》的独特魅力。两条“暗道”交织始终,小说双数章节为雷高汉的口述历史,重返他生活、生存的历史现场,勾勒出他于鸿祯塞生活的真实全貌;单数章节为作者“我”与雷高汉的当下对话,“我”一边倾听雷老经历用作故事素材,一边写作名为《塞影记》的小说,让雷老等人即时品评。两条线索趋近、交融,汇合于穹顶,钩沉出鸿祯塞浩大、恢宏的生活风貌与雷高汉坚韧、不屈的苦难岁月。作家将小说生命与现实人生有机融合,文章贯穿着雷高汉本人对小说文本的价值判断与历史评价:或认为暗道过程描述过于简单,或对人物说话的语气不满,或对人物形象有所质疑,从而使得家园的构筑更具现实感与在场感。作为听众的作者(“我”)与作为读者的讲述者(雷高汉)构成复杂的对话语境,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交叠,老汉“真实可信”的口述历史与史料纠错,加之“我”的田野调查与“身临其境”,作品在阅读性文本与书写性文本中游刃有余,使得鸿祯塞完整、宏大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有效填补小说的真实性的空白,切近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贴近人性的温情与历史的真意。
“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 通过作者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这一“故事得放进一定的场所中去编织”。鸿祯塞便是马平为编织故事提供的场所与家园空间。风吹塞影淡云烟,王朝垮台、日本侵华、大炼钢铁、划分成分、识字运动、互助小组……政治的风云变幻、时代的跌宕起伏都在小说的时间长河中流过,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当下的界限被作者模糊,它们是鸿祯塞的年轮影迹,也是雷高汉所处家园的云淡风轻。经由历史的沉淀与主人公记忆的留存,以“小说”这一“精神家园”的构建形式长潜于文字之间,其价值则会被追忆与留念,正如小说腰封所印:“百岁老人雷高汉,一直活在鸿祯塞的影子里。”
玻璃屋、喜鹊窝、天井、田庐、秋千等,它们与旧址拉开了时空的距离,却依然无法剥离宏大的家园之影,成为作者铺设的提示性线索,帮助作家“我”在雷高汉老人叙述回忆之余进行细节的探寻与补充。暗道、戏台、望哨楼、黑松林、水库等,链接生死、承载情爱、见证忠义、铭刻悲情,均是精神家园构建的重要地标与符号。在23 万余字的小说篇幅中呈现百年中国的秘史传奇,作者在小说线索、章节结构等叙事策略上努力:“我在鸿祯塞进进出出,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大门、不分暗道,进进出出若干回。”
三、“这一经典(小说)永不过时”
《塞影记》是多重“中间文学”的有机结合。它不仅汇聚严肃文学的纯粹性与通俗文学的故事性,也兼有大河小说的宏阔、现实主义小说的内核。卡尔维诺曾言:“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塞影记》并非沉浸于恢宏壮大的历史现场,家园场域自觉承担了戏台的角色,作家以“我”的身份成为老人穿梭于现在与过去,从个人切入时代、从家园透视历史。在人生舞台亮相之余,也促成着“子故事”向生活与历史的逼近,众星捧月般共同助推主角雷高汉的形塑:“我这条老不死的命,是那么多人拿长长短短的命换来的。他们一齐在我身上活到了今天。”
《塞影记》感人的关键在于,作者构筑了典型家园空间下的典型人物形象——雷高汉。他是家园的卑微构建者,因“饱饭”之需而积极进驻家园,寻觅着人性的爱与暖;他亦是家园的坚强守护者,面对风云激荡与家园失落,他不离不弃,始终脚踏鸿祯塞的泥土,留驻家园的灵魂。
尽管光线暗淡,他也能认出大衣是黑色的。他还能认出,那一片打开的月光,是女人的肌肤。他牵起了那一片黑色,包住了那一片月光。然后,他抱住了那一轮热乎乎的月亮……月亮热乎乎地出来了。下面戏台上响起了锣鼓,一声比一声嘹亮。
五条命没了,那一场丧事却办得匆忙而潦草。孩子被土匪丢下了旱井,因为旱井太深,所以,天还没亮就有人往里面倒泥土。那两个该死的家丁一大早就被抬走了。梅云娥不能像汪碧鸾一样埋进祖坟那风水宝地,当天就装棺抬了出去,埋在了黑松林。
作者讲究诗兴的语言,让读者于亲切中探得陌生的新趣,于遣词的质地中读出历史与现实。作者借“我”之口断言:“我写的这个人,一文不名。他说他做了一辈子无用功,并且,他已经没有未来……尽管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但我已经可以断定,即使我的作品过时了,他这个人也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