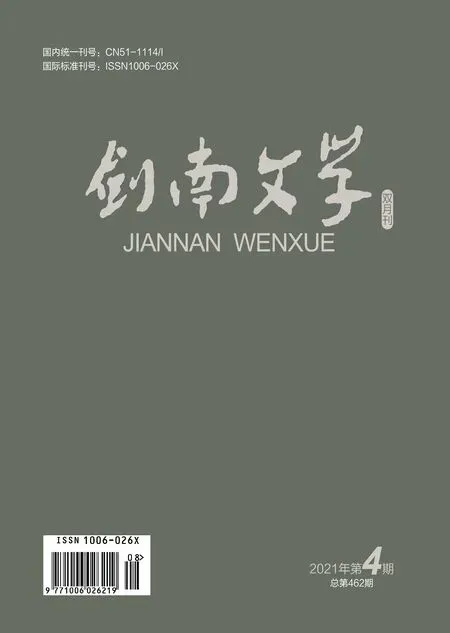虚掩之门
□马青虹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下定决心要写这篇小说了,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因为它仅仅停留在了一扇孤独的门的构建之上,为此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整,我尝试将这扇门构建得独一无二,但终究还是没有找到足够支撑起我动笔的点。
时隔一个月以后,我第二次尝试着把这扇门安装到我的文本当中,但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当中,我的整个文本如同一堵没有空隙的墙,没有丝毫地方可以安装这扇门。于是我在写完三千字以后便停了下来,直到两个月后我遇见了一位朋友,他主动请缨,想要成为我故事中的主角。为了避免透露出他的真实信息,以至于给他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我只好用第三人称“他”来替代他原本略显尴尬的名字。
我还能清晰地复原出当时的场景:我正穿着睡衣坐在(准确地说是半躺在)沙发上,将卡尔维诺的书籍从第一章的末尾直接跳到了该书最后一章阅读,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后记》比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都要长。由于天气的原因,我并没有处在静下来读书的状态,但是强烈的阅读愿望又迫使我拿起了这本书。我的眼睛几乎是半睁着快速地从书页上扫过,正当读到小男爵柯希莫写好那份名字长得吓人的权利声明的时候,静躺在米色茶几塑料垫上的手机响了。
“有没有兴趣写一个小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素材,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他的言语之中透露着在夏季的燥热中突然收到降温的天气预报的那种期待和兴奋,尽管他已经竭力隐藏了他的情绪,以便他能条理清晰地讲述事情经过,但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喝酒可以,写这些没兴趣。”我把一桶冷水倾倒在他的头顶。
“我前段时间病了……”他把他的不适症状一一讲述以期能打动我。
“病了就去看医生呗。”我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他,然后挂了电话。
我躺在沙发上闭着眼试图回到先前昏昏欲睡的状态,但是经他这么一闹,我的瞌睡像是被中断的写作状态一般,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再续接上。越是想睡越是睡不着,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我冬天的草原上点起了一把火,我一开始只想用极小的力气吹灭它,但是它却借着风势蔓延开来,直到我再也没有办法轻易将之扑灭。
“在干啥?”我回拨了他的电话,带着歉意问,并直言刚才自己的状态有些差。
“没干啥。”我们将先前的语气互换了。
“出来喝酒。”
“不来。”
“那算了。”
挂了电话后,我又试图邀约其他几个人,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都没有办法即刻与我靠近碰杯。这样的失落使我愈加清晰地感觉到了那团已经蔓延整个山头的火势。家里的另外几个人要么上班去了,要么同他人约好逛街看电影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显得格外冷落和空荡,这种冷落和空荡刚好为火势的蔓延提供了足够的客观条件。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将音响的声音开到最大,将一杯茶叶泡了五六次,泡第四次已经没有了茶味,因为懒得换茶叶我每次在新倒进开水以后就必须得盖好茶杯摇晃几下,以榨干茶叶中仅存的那一点点味道。
科恩的声音是下午的一束光,照在摆放在书架第二层左边的《不朽》之上。这本书已经买了快两个月了,随它一起入住的还有诸多名家,大都是国外的,其中一部分我是在客厅的沙发上伴着下午沉重的倦意翻阅完的。
我转动椅子伸手将它取下,封面上印着黄色的英文手写体的书名和那个素未谋面的老熟人的名字,笔画摆放杂乱但极具有艺术感,左下方是一只没有主人或者忘记了主人的油画高跟鞋。或许是昆德拉的情人的,抑或是书中某个女性角色遗失在此的。
这一刻,我之前积郁已久的烦闷得到了少许开示。越是将注意力放在书中,就越发地意识到能够关注灵魂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现实生活已经足以抽取绝大部分人的精力让我们无暇他顾。而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文学显得愈发弥足珍贵,昆德拉显得愈发“不朽”——甚至所有关于灵魂的事业及其从业者都不朽了。这当中也包括我自己,平日里不时显现的卑劣、自私和心胸狭隘,从未显得那么容易被原谅。
为了庆祝,我决定出门走走。临走之前,我是说换好衣服准备出门之时,我又折身回去把杯子里失去味道的茶叶倒掉,连同一些像茶叶一样被人为加工保留下味道的那些旧事。
我顺着河堤行走,不时看向那些顶着广告的小摊车,广告上印着艳丽的宣传图案和千篇一律的文案,通常是冰粉、土豆等小吃,市井至极。但每每看到那些摊贩和与之讨价还价的顾客的时候,却又显得那么脱俗。他们都不是作家,甚至在这些年里可能一本书籍都不曾阅读,但他们是鲜活的,似乎永远没有灰尘能落到他们的灵魂之上。
过了两座桥,桥下的河水浑如生活一般,并且死寂,只有岸边流动的人群能够证明它还活着,还有源源不断的细小的水流为它注入活力。不知不觉已经沿着河堤走了半个多小时,我决定向山靠拢,一路漫无目的,或许是惯性或许是缘分,我来到了山脚下的烧烤街。
街对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农贸市场,卖菜卖水果,也卖衣服和零件钟表等杂物。从靠山一边的丁字路口开始,整齐地排列着四五家烧烤摊,餐桌一律摆放在靠马路一边的广场上。
经常与朋友们去的一家在最外边,门口有两棵女贞树,每年春末夏初坐在树下总免不了被它们的落花弄出一身颜色。我在客人最少最不常去的一家选了一个最不显眼的角落坐下。我确实没饿,只是想坐一坐,便只要了一盘花生毛豆和两瓶冰冻啤酒。
我刚将杯中啤酒一饮而尽的时候,忽然听到邻座的玩笑。没有刻意听也没听全,但是当中一个关键词引起了我的注意——征服。我想起前两天同一个编辑朋友聊天的结论:“征服是为了被征服,吃是为了被吃,爱是为了被爱,占有是为了被占有,我们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世界也向我们证明自己的存在。”乍听之下有些绕口,甚至看起来有点哲学意味,但若是你知道我们聊天的过程便决然是另一种感受。
话题起源于牛——称赞一个人厉害,随后引至吃草,又由草牵扯到吃和征服的问题,进而得到了最后的结论。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省略掉当中一些带着双关语气的玩笑。这是一次经典的对话,毫无疑问。
正当我走神的时候,我忽然瞥见了一个身影,同时他也心有所感似地一下就看见了最角落里的我。
你不是不喝酒吗?我们相视一笑。
要你管,老子想喝就喝。不过,你怎么跑这边来了?他说着就自己拖了一个凳子坐下来。
不想碰到你,你呢?
我也是,不想碰到你。他递过一支烟又自己点了一支才说道。
所以……哎……算了,吃点啥?我左手撑着下巴,右手大拇指顶着下颌食指和中指将烟嘴送到嘴边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看到他,我的内心便没有办法像之前那般平静,他身上有令我不安的因素。
我生病了。
你啥时候正常过?我看了一眼他,开玩笑道。
我真的生病了。
记得吃药。我再次打趣他。
这一次他没有再试图让我相信他的话语,只有一层浅薄的夜色在他的脸上结网,丝毫没有平日里的温度,脸色也迅速变得憔悴,像一棵在烈日暴晒下迅速枯萎的栀子花。
怎么回事?我意识到了事情比我想的要复杂和严重,便不再打趣他。
自从我明显地感觉到了近期身体的不适,我便开始了长期的失眠,且随着失眠时间的叠加,我的健康也随着睡眠的遗失而被蚕食着。我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身体总是越来越不听使唤,思维也间歇性地停滞在某一时刻。
剩下的情况你自己看吧。他带着一丝无奈的语气道。
看?我怎么看?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老板,来一杯樱花贴。他侧身朝着烧烤店的吧台喊道。
樱花贴?啥玩意?他这一通操作让我有些蒙了。
好的,是你喝还是他喝?老板端着一个托盘,高脚杯里盛着三分之一的浅蓝色液体,疑似鸡尾酒。随着老板走动,那浅蓝色的液体不停地朝着玻璃杯壁拍击,像是一层又一层的海浪正涌向一个由玉石构成的海岸。
他喝。他半靠在桌子上指着我说。
老板把他手里的樱花贴放在桌子上便转身又去忙活了。虽然几乎没有客人,但是老板似乎从来没有停歇过,玻璃杯里的海浪稍微消停了一些,但是仍旧被月亮的吸力牵动着不停晃动。他从托盘里拿过一根细针,在自己的手指上扎了一下,一滴鲜红的血液从他中指的指头上浸出。他将这滴血挤到杯子里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中的液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换了三次颜色,最后成了一杯白水,而先前的晃动也在颜色变化的过程中消失不见,仿佛它从来不曾摇动过一般。
喝吧。他把杯子推到我面前。
我干嘛要喝?你不会是得了艾滋吧?
别磨叽,我没得艾滋,也不会害你,我不知道怎么给你讲得清楚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因为它就像这杯樱花贴一样不可思议,它会帮助你看到我所经历的一切。
你确定它没毒?我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了相信他,将这杯来历不明的液体喝了下去。还没来得及辨识它的味道,我便感到一阵晕眩。随后我迷迷糊糊地进到了一个满是大雾的地方,可视距离不过是十来米,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的布景完全是我们所在的城市,只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雾。刚准备迈动步子,我就看见刚才让我喝下那杯不明液体的家伙了。但他似乎看不见我。这就是他所经历的吗?我自言自语。
我看见他在十字路口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面无表情的他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在斑马线前站立着。许是来往的人轮换太快,许是人们都只顾着低头玩手机或者是心有所思,总之没有一个人发现他站在那里从没动过。随后我感到手被人碰了一下,我就变成了他。
为了避免视角过于混乱导致整个故事看起来毫无头绪,我只能用他来替代变成他的我,他所经历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我,不,应该是他——他几乎就要看清楚那个穿着黑色布衣的死亡使者了,使者面无表情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躺在床上,使者就立在床边;他坐在沙发上,使者就站在电视机前;他走在街上,使者就一直在他前面退着走。“他完全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等我被空中掉落的云团砸中而不幸身亡,或者等待我在一场惊恐的睡梦中张着大嘴再也无法吐出下一口气。”他跟朋友这样说道。
大大小小的医院、各式各样的医生都看过了,却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种治疗方案。都是将他的身体在各种医疗器械上摆弄半天后一脸不解地摇摇头说没问题,连一副药剂都不开。最后还是在一个老中医那里得来一副治疗失眠的药方,他一五一十地照着药方抓来药煎好,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小瓶把瓶中的药引倒入药水中服下。当夜他便稳稳地睡了一觉,梦中他安稳地躺在一个土墙院子里,死神在墙外站了一会儿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第二天,他先是突发奇想地筑起了四道不规则的墙体,将自己团团围住。墙体总能善解人意地跟随他,他走到哪里,墙体便移动到哪里。四道墙体如同一个带着排斥功能的能量环一般,将他和周遭的一切隔出三尺的真空地带。他自己则隐居在墙内,如同一个隐喻一般行走在由人潮拼凑成的讲述日常生活的庸俗小说之中。
墙体隔绝了他大部分的天性,诸如群居、繁衍以及贪婪。他不再喜欢扎堆到马路边一只被耗子咬死的猫的尸体旁边看热闹,不再热衷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肉体,不再需要无休止的参加劳动来获得一些于他的生存毫无益处的东西。只是对于自身之外的事物的好奇心仍旧无法彻底根除,他仍旧免不了偶尔踮起脚尖或者干脆跳起来看一看那个令他重心偏移的个体究竟是什么。不时也有一些人试图攀爬这些移动的墙体,想看看里面究竟关着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唯一能不经过他允许就肆无忌惮地探望他的只有太阳和月亮了,星星的光芒是隔着更远距离跳动的烛光,过于遥远也过于微弱,无法真正地触及这一个离奇的索居者。太阳把他的影子扣在墙上,除非用一架相机延时拍摄,否则没人会注意到他的影子其实是缓慢移动着的。月亮把他的影子抠出得要少些,一条更加轻薄的灰色纱巾软耷耷地搭在墙体粗糙的斑点之上。光越强烈的时候他的影子就被抠得更多、更重,这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更加轻巧,多余的重量便由抠出的影子承担了,总的重量并没有变化,只是他被一分为二了。
刚开始他还热衷于在太阳最强烈的时候出门游荡,这时候的行人并不太多,而他也刚好可以把多余的重量甩给自己的影子,能够更加轻便地行走。直到夏至日那天以后,他便再也不想出现在强光之中。那日早上还能稀稀拉拉看见的云朵很快便如水中漂浮的泡沫一般被上帝用手从湛蓝的天空中捞了出去。从视觉上来看,太阳比平日里大了一倍,他的影子前所未有的浑厚,一个比他自己大了好几倍的健硕的黑人,看不清嘴脸,看不见真实的肌肉纹理,但是毫无生气的影子却在此时竟如要从墙里走出来一般。他感觉到自己重量的遗失,他感觉到自己几乎就快同秋日掉落的蝉翼一般,双脚离地飘起来。
这样的状态是极其不妙的。他立刻在心里告知自己。但是,直到太阳下山他的影子渐渐消失,他的脑袋才接收到这一信号。他在心跳加速的后怕中有了一个恐怖的假设和担忧——假以时日他的影子定然会偷走他的所有重量,从墙上走出来,成为一个新的更加强壮的活生生的人。那他自己呢?他会飘起来,越过这四面墙体然后招来死神?或者他甚至可能会变成影子,被死死地拽在自己影子的脚底,扣在自己亲手所筑的墙体上?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都是一把刀子要插入自己的身体,选择插入前胸或者后背,无论哪个方向都是疼痛且致命的。此后他便开始刻意地躲避起光来。
他成功地避开了所有的光,但没日没夜地待在房间里躲避影子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难受。他下楼不是,不下楼也不是。
他像戈壁滩上一株独居的骆驼刺一样没日没夜地忍受着时间,忍受着孤独肆意在他的身体里游荡。他在这些时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枯萎着,同他一起远离光的盆栽便是最好的见证者。
终于,他受不了了,他想下楼走走或者寻找一点能让他感受到自己还活着的事情来做。他把手用力砸在坐垫上,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一只被寂寞笼子关押已久的野兽决定走出铁笼。那只野兽用它黑色的爪子在他的心里反复抓着,他也把自己的手弯曲成爪子的形状抓在自己的胸口上。
他在屋里来回地快速踱步,从厨房到阳台,从厕所到卧室,再从厨房用力踩着地板走向阳台。最后他还是决定下楼走走。洗漱干净,换好衣服,他把一把大黑伞撑开,上面的灰尘厚度证实了他有很久没有用过这把伞。他斜着向外来回撑伞,借此抖掉大部分的灰尘,然后又拿来一条帕子抽打一番,才算打理干净。
伞把上细小的缝隙总爱咬他的头发,还没走出门口,他的头发便被扯掉了好几撮。他翻出一顶灰色的鸭舌帽戴好又取下:不戴帽子吧,他可能会在回来之前被扯光头发,带上吧,天热又碍事。就当帮自己理发了吧,反正也有好几个月没有出门理过发了。他最终还是决定把这顶帽子重新放回衣柜左下角的抽屉里。
快走到大门口时,他远远地看着那对铁门。原装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露出一块块暗红色的铁锈,那些凹陷的坑洞像门被影子偷走的部分。但是他又不想如屋子里的花瓣一样枯萎,只得狠下心再次迈步来到门口。
走到门口时,他的内心又开始犹豫起来。他像一座恐怖的雕像一般立在屋檐下光与暗的交汇处许久,再次面对一把刀子是插前胸还是后背的问题,是选择枯萎还是面对自己变成影子。如若不出门,枯萎是必然的,出门的话被影子替代变成影子也是一种可能。
他决定先探出一只脚试试,一只脚,一只穿着白色板鞋的脚试探性地踏进阳光中。踏出去的脚和尚未行动的这一只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感受。谨慎起见,他又抬起头看了看远处的天空,低头时的双下巴被减掉了一个,灰扑扑密集的云层给了他心理上的安慰。
他撑着黑伞推开门走在被淘金者挖得面目全非的河道旁。翻过墙体时,迎面吹来的风将伞上剩余的灰尘一点点剥离,将他连日来的阴郁和枯萎之态也一同吹落。他如同一座被时间侵蚀已久又突然遭遇爆破的雕像,疲惫的表层岩石开始一块块地剥落,露出崭新的鼻尖,整个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
影子并不曾出现。他大步地走了起来,清清楚楚的风,完完整整的身体,身上披着的沉重的疲惫和内心揣着的惊恐和忧惧都在他大步的行走中洒落一地。
一个樱桃一般的声音从墙外传来。他始终没想明白这无比柔软的声音为何却有那么巨大的能量,隔着四道墙体还能如一记重拳一般令他重心偏移。他原本的好奇心早已被墙体隔绝干净。但是此刻,一颗种子比春天夜里的竹笋生长得还要迅速,他在摇晃中似乎感受到了久违的异香。或许正是这香味迷了他的眼,也迷了他的心。现在生长的是一种新的没有根茎的好奇,和之前的完全不同。
他踮起脚尖朝着墙外看去,除了那些由于遗传或者是富裕生活给予了极高营养而比墙体还高的人之外,他没能看到一半或者一个完整的头顶。当初筑墙的迫切心情导致他忘记给墙体设计一个合适的高度——这墙体还要高出他半个头——以便于他能够像一个有着特殊的偷窥癖好的人一般观察墙体外的一切人和事。
他望着头顶的墙沿,粗糙的工事像遗留下的草纸一样参差的毛边将他的心思硌得生疼。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他首先找来一袋子石灰倒入用完了油的胶桶之中,然后一点一点地加入清水和粘胶,搅拌、加水、搅拌,直到桶内的物质呈稀泥状。他用石灰将墙体粉刷了一遍,将墙体的边缘抚熨平整。
正当他不停修复墙体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个人绝不会是我,那么,这就一定是一个梦境了。
我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正立身在青石城的河堤边。
从河堤回家,停住电瓶车,我就火急火燎地从后备箱里取出前两天买的一本加缪和一本散文选,下车,取书,开门,放书(准确地说是扔在沙发上),一气呵成,直到拿了纸坐在马桶上才感觉到热和累。其实早在河堤上和H散步时我的腹部便发出疼痛的信号,我意识到我需要通过排泄来缓解身体的不适和H 吐给我的一大堆垃圾。之所以说是垃圾,是因为我觉得H 所说的东西毫无意义。一路上我的眼睛都在寻找一个可以方便的地方,可是没有一个地方适合我在那样的情形下做私密的事情。期间,H 似乎发现了我的东张西望,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她我需要排掉身体里的垃圾和她塞给我的毫无意义的话语。即便要表达我也不能把后一种说出来,虽然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她也不可能因为我这样说就停止和我的来往。出于对她的尊重当然也出于我作为直立行走动物的自尊和私密,我只告诉她我在看风景。无可厚非,看风景是一个值得相信的理由,说到底卫生间也是一种风景。在这座小城,所有的建筑都有些独特的民族风味,如果把卫生间改成住房,相信也是有很多人会愿意去住的,至少我很乐意住,前提是不要太贵,最好免费。
慢慢地脱下身上的亚麻布格子衫,所有人都应该相信这是我买的最划算的一件衣服,不光价格不错,而且和我的体型还有肤色都很搭配,外面其实还可以套上一件黑色外套,如果天气再凉一点的话。现在这个鬼天气,我打死也不愿意穿多一点,所以当我排泄完事时,我便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物,躺到了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