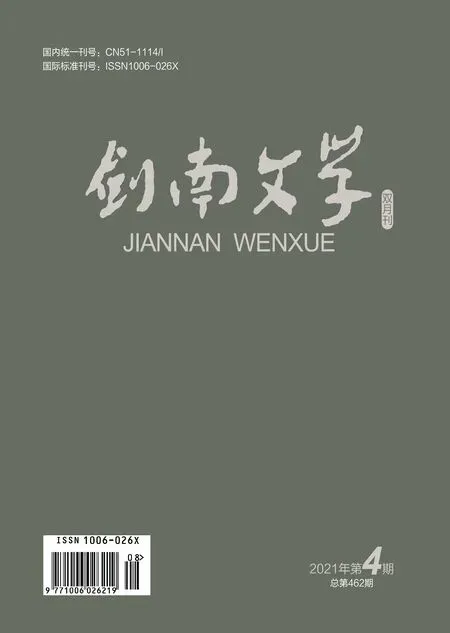往开阔处去到世界中去
——关于中篇小说《白鹤已然入云端》创作后的一些思考
□羌人六
关于文学,贾平凹有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他说,把文学比作一条瀑布,我们这些写作者,每个人都是端着碗在瀑布下面接水的人,有的人接的多一点,有的人接的少一点。写作者同时也是读者。作为读者,我相信世界上一切文学经典,都是巴别塔坠落的碎片,原本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如果,把这些碎片似的文学著作连在一起,就能连出一条文学的璀璨星河。写作近二十年,我创作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已有一百多万字。虽说写作仍在持续状态,但我深深明了这些从瀑布下面接到碗里的“水”,在思想、艺术形式、语言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锻炼”。写作,只是为了在文坛混个脸熟凑凑热闹吗?写作,只是为了挣稿费养家糊口吗?写作,只是为了在某个小圈子抛头露面吗?写作,只是所谓的自娱自乐或者自我安慰吗?当然不是的。
曹禺二十三岁写出《雷雨》,张爱玲二十三岁已经完成《金锁记》,肖洛霍夫二十三岁已经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前两部。作家王跃文先生曾当面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国画》,是他三十二三岁写出来的。今年,我三十四岁,时常扪心自问:你写出了什么?你能让人记住的作品是什么?我的那些作品,也许不过是些还没有经过风雨锤炼的精神花朵,也只是花朵,还谈不上果实。基于这样的自知之明,我常常害怕参加各种文学聚会活动,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我清楚的是,文学创作,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不是一群人的狂欢。文学作品,并非取决数量,而是质量。文学,比的不是写作速度,而是写作态度;文学,要求的是慢,而不是快。几年前,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有天傍晚去超市买烟,掏出手机付钱的时候,明显感到收银员的眼睛鲨鱼般快速地朝我的方向挪了过来,落在我的手机上,然后,他用一种略带好奇的口吻问我:你用的苹果手机什么牌子?我当时没反应过来。说实话,我可能会记住某个作家的某些作品,某一段话,甚至其中的标点符号,但真不知道我如影随形的手机属于苹果的哪个牌子。对我来说,手机就是用来联络的工具,我不知道收银员为什么会那样问。为了避免尴尬,付过钱我便匆匆离开。记得那天晚上,适逢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地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我有幸去了现场。颁奖结束从博物馆出来,我忽然想起那位收银员,想起他耐人寻味的目光,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过用了四年多的苹果手机在他眼里,看上去可能已经像一件出土的文物。似乎,我落伍了,像博物馆里呼吸岁月的文物,因为活得太慢,忘记了生长的时间。我落伍了吗?我觉得未必。久经岁月的文物,不也是因为活得慢,才因此显得珍贵吗?在我眼底,慢,是一种宝贵稀缺的品质。有一年到九寨沟,一个作家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段真实故事,说是有个外国小伙独自跑到九寨沟研究那里的金丝猴部落,为了赢得金丝猴的信任,他在栖息地旁边定居下来,与金丝猴朝夕相伴,平时,也基本不到县城闲逛,因为金丝猴对人的气味特别敏感。他就那样离群索居、风餐露宿待了两三年,最终,他写出一部关于金丝猴研究的专著,一举成为国际知名动物保护专家。我想,如果不是出于慢,出于耐心,出于专注和执着,这个外国人是取不了“真经”的。
“它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就要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诗人里尔克曾如此感叹。一度,我对自己的写作感到不满、沮丧,我不止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也渴望自己能写出相对成熟的文学作品。但写好作品,又似乎太难,进步也慢。一个人身体发育走向成熟只要十到二十几年时间,而读书写作,是精神上走向成熟的长途跋涉,是一辈子的事,需要一生的付出、坚持。湘西民歌里有句歌词,“冷水泡茶慢慢浓”,就是用冷水泡茶,听着有些舍近求远,其实,据说,冷水泡茶的效果一点也不差,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茶的本色、茶的清香、茶的营养就会慢慢渗透出来。慢,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属性和应该秉持的态度。一个写作者,应该成为一个慢人,成为纸上孜孜不倦、勇于求索的攀登者,锲而不舍久于其道。慢工,才能出细活。文学,是关乎灵魂的事业,也是关乎人的事业。作家麦家有段话我印象深刻,他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关注人是文学的本分,关注语言是作家的本分。
“2004 年秋天,初次离开出生地,走出大山,到四十多公里之外江油中学读书。其间,我偶然写了一首题为《归宿》抒发思乡之情的小诗,后来,这首诗被年轻的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诵。很幸运,处女作就这样被我的语文老师口头发表。选择文学,既是跋涉,也是不断后退不断向内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变得孤僻、胆怯、自卑,但与此同时,那个粗糙的我也在变得细腻、宁静、丰富。文学,让我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去路。这些年,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我在多文体的变奏中辗转、摸索,这些作品,是生命穿过岁月留下的脚印、记号,当我往回走,它们就会变成路标,让我看见回家的路。”这是我几年前写过的一段“创作感言”,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初衷”,我有意识地创作了大量关于出生地(“断裂带”系列)的文学作品。很多作家都是如此,身体或许早已离开家乡,置换了生存意义的背景与空间,精神却一直在原地徘徊。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不断的阅读和写作,我渐渐洞悉到某种“局限”,怀疑和厌倦也在这种“局限”的脚后跟上变得理所当然。“要打出真铁,要锻造出吼声!”这是爱尔兰诗人希尼的诗句,大概也是写作者必然的一种“野心”。我渴望写出更为开阔、厚重、丰富、多元的优秀文学作品。基于此,我也主动开始“蜕变”,开始尝试自己新的“冒险”。这种“冒险”始于2019 年,那一年,我决定少写甚至不再写“断裂带”;那一年,我开始动笔写以我媳妇老家(绵阳市盐亭县)人事为背景和题材的系列中短篇小说。截至目前,我已写了五部中篇一个短篇,十余万字,中篇小说《白鹤已然入云端》亦是其中之一。媳妇老家属于丘陵地带,我将这些作品暂时命名为“丘陵系列”小说。“向生活取经”,是我那时的一种姿态,通过这些充满“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我真正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丰富、拓展了个人的写作视野。
小说是艺术,是第二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或许有两个重要的元素和特征,一是地域色彩,二是作品自在的意义或价值。《白鹤已然入云端》这篇小说便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完成的。我期望以一种动态的、细节的叙事语言,引领读者顺着故事的墙根走向当下,走向广阔的现实和斑斓的人性,最终,走向对人的命运的思索和关注。
“往开阔处去,到世界中去。”如今这句话与我如影随形,时常浮现脑际。回头看,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白鹤已然入云端》等这一系列丘陵题材小说的写作尝试,让我挣脱了曾经的束缚与局限。小说是表达现实、回应现实的强有力武器,然而,毫无疑问,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缺陷是明显的。“往开阔处去,到世界中去。”在我看来,不仅仅指向当下的现实,指向未来,其实也涉及我关注到的历史、文明、自然、传统、现状……
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编织一个不存在的世界,让读者看到人的存在的各个隐秘的层面,把人的未来、现在和过去连在一起,唤醒生命中日益麻木枯萎的激情、信念和对真善美的渴望,在我看来,正是小说的魅力和存在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