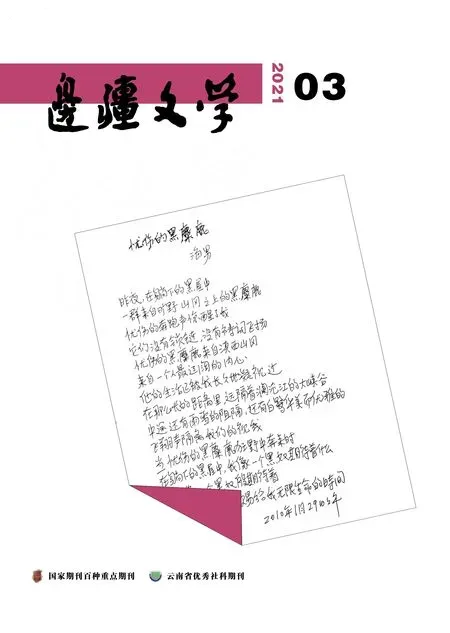刘洋希的诗
刘洋希
做面包的人
面包“咳吱”一声挺起肚子
把周遭的空气吸入腹中
表面仍写满大地的质朴
那是小麦啊!
支撑一场场风雨盛大的抒情
谦卑的庄稼,把头深深埋进心里
“让我进去。”我向面包祈求
面包没有回答
“让我进去,学习你的质朴。”
面包只是继续吸着空气膨胀
“我和你一样,是这片土地的孩子。”
面包放慢吸食空气的速度
最终在烤箱“叮——”的一声中
掩藏了大地的叹息
被一只面包拒出体外
触摸它的手
竟一时也如面包壳般皱纹满布
吃面包的人
我们都是吃面包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朋友
不吃你就会饿死。
我们一直很饿,直到
手里握住一块面包
第一口狠狠地咬,生怕它不翼而飞食不知味。
第二口细细地尝,确保它已属于你称赞美味。
第三口慢慢地嚼,觉得它不过如此味同嚼蜡。
然后,机械地吃完整块必须吃完的面包
上路,却是寻找新的面包
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继续寻找
我们都是吃面包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朋友
吃完了,生命就结束了。
我想
我剪头发
因为不想留长发了
我休学
因为不想去学校了
我闭眼
因为不想睁着了
我阅读
因为不想被麻痹了
我写作
因为不想枯竭了
我用此方法
回答了所有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因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除了想做这些事
我什么都没想
仙人掌
一株沙漠里的仙人掌
身上长满敏感的刺
后来沙漠消失了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搬进了水泥钢筋里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住进了花盆里
我的刺、我的敏感
被剪掉大半
直到有一天沙尘席卷城市
我摔倒在地上
心安理得地躺进了沙里
圆滑?
怎么才能不得罪左右
我在床上平躺
空气中侧卧
倒过来也一样
为了学会处事圆滑
我在夜里辗转反侧
春城
昆明的冷是随机的、突然的
窗外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囚禁在这一片寒冷中
飞也飞不出去了
这大概就是春城吧
一座迷惑,和囚禁了春天的城
蚊子
一只很瘦很瘦的蚊子
晃晃悠悠的路过面前
我的眼睛,像交警
死死盯着这只“疲劳驾驶员”
它已经无力吸血
“可它万一传播疾病?”
“万一在我身上享用了最后的晚餐?”
“万一……”
这该死的生物!
下一秒,它死在我的指缝中
没有一点血迹的尸体被水流冲走
我无法对想象中合理的威胁
抱有侥幸的同情
我有罪,并且纵容
审判官是谁?
怨恨
10:39 看了我一眼
我看着它。突然
10:40 问:
“为什么不是我?”
10:38 问:
“为什么不是我?”
10:39 问:
“为什么是我?”
它们的疑问中生出无端的怨恨
也许无端之问
滋生了许多无端之恨
梦
嘿,你还记得昨晚的梦吗?
哪怕再新鲜
它也已锈迹斑斑
做梦的卡吕普索
不可避免的和每一个梦,在梦里缠绵。
当厄俄斯顺着光的海浪
放下一只只船
梦便一个个起身离开,远行……
这些故事
永远美丽,永远锈迹斑斑
距离
注视太阳的眼睛
无法测出未来的距离
——一切已成历史
它无法让我们避免陌生
也不能制造熟悉
每颗原子都渴望一场爆炸
抛出叛逆的星星
打破轨道
一次飞向太阳
一次飞向眼睛
使者
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
而人间需要月亮关怀的人,却很多很多
于是月亮想了个办法——
孕育出无数的星星
去照亮每个需要微光的人
不要因为一时见不到星星,就怀疑月亮
也不要因为天气阴郁,就斥责星星
乌云再厚,也有消散之时
偶尔风
也需要一点你的帮助
商品
我喜欢商品
喜欢它们不属于我的优雅
喜欢它们“弄坏了要赔”的高傲
喜欢它们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挑逗,和
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疏离
喜欢它们的“非我”
我对它的报复和爱
在于永远把它视为一件商品
漏电
手机放在床头,漏电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
电去哪儿了呢?
我的梦里
雷电交加
诗的节骨眼
哎,我的心
还在留恋莎士比亚的风雨
梦
还在向往雪莱的春天
目光
还在追寻普希金诗歌的贵族气
……
现世呢?我坐在现世的节骨眼上,倾听
现实,现实的咳嗽
城市,城市的呻吟
雨水,雨水的哭泣
我的语言呢?
它站在,诗的节骨眼上
我要憎恶,憎恶现世虚妄
我更要深爱,爱当下,一切
我爱的诗人,
他们也是深爱,深爱
那时代的枯荣
也是在谱曲——
用那时代的歌喉歌唱
危险
我突然觉得
诗,是一种危险品
它入侵我的眼睛
攻占我的大脑
可患者,我
却从来不顾“吸烟有害健康”
重量
世间所有的白
都不如扎在母亲头上的银针耀眼
那一根根的,好重好重
母亲病了,半夜咳嗽着
裹挟着风沙的磨砺,一道道划开我的梦
那一声声的,好重好重
她救下一窝流浪猫,三只中
两只长得很好,有一只……
就在那晚,她咳嗽的那晚
一个小幽灵挠了一下我的鼻尖,酸酸的、冰凉的
那个小生命走了,
走得好轻好轻
巧合?
脚步,寻着鼓点
走进我的凌晨一点
谁在敲鼓?
是我,是我
我说。
是我吗?
我问。
你忘了,是我啊
我说。
不会忘了
我说。
那便晚安,明天见!
我说。
我得把我们的船推向黎明
我说。
好吧,谢谢你
我说。
不用谢
我说。
多么巧啊,我的心脏在我体内安静跳着
是它在敲鼓。
童话
光明,也曾驱散影子
尽管影子,对它抒情
没有光,影子如何生存?
没有影子,光如何证明?
哦,我忘了。它
不需要证明
白天,影子栖居在我体内
黄昏烧成一只熟透的虾子
影子一步步走出。
“兴许它是黄昏猎人?”
越来越多的影子走进黑夜
直到整个夜晚都是影子
我躺在影子怀里
听它说光明的故事
牛奶盒
箱子里,一只只整齐排列的牛奶盒
挺着快要临产的肚子
站在手术室外,等候
我取出一盒饱满的牛奶
用吸管在她的腹部戳开一个洞
奶水汩汩流出
瓶子在挤压间歇大口吸进救命的氧气
发出痛苦的呜咽
直到最后一滴牛奶落进另一个不属于她的肚子
牛奶盒枯槁的身体
宛如一个干瘦的老妇
艰难地用跛足,支撑在桌子上
再也吸不进一口气
我看着桌上的她,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