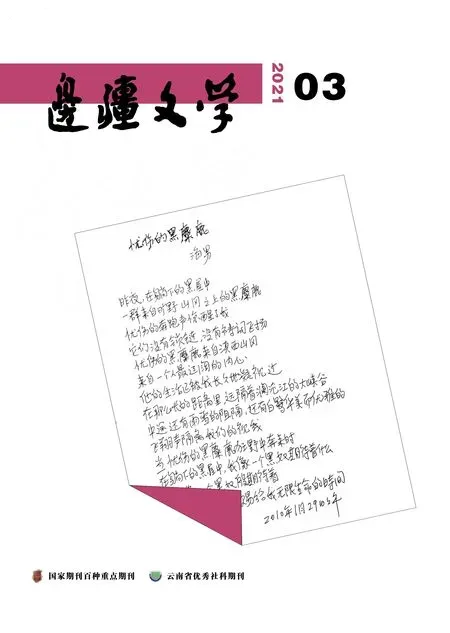孤鸿短篇小说
徐一洛
1
8 岁那年,一场高烧将伶牙俐齿的冯秋水变成了一个哑巴。她的母亲跟一个挑货郎跑了。父亲成日不归家,回来了也是烂醉如泥,动辄骂咧挥拳。她和奶奶相依为命,她们只当他是死了。
冯秋水习惯低头走路,避免看到那些复杂的眼神和上下翕动的嘴。这一天,她低着头,行色匆匆,经过一片草丛时,一道奇异的光射中了她。她好奇地蹲下身,扒开草丛,意外地看到一堆零散的钱币,躺在没被踏过的野草里。她望了望四周,空无一人,她慌忙起身,准备继续前行,但双脚无论如何也挪不动了。钱是捡的,不是偷的,她拼命安慰自己。她一把将一堆钱币抓进衣兜里,几枚硬币从她手中蹦了出来,她迅速拾起,又开始奔跑,将草丛远远地抛在身后。回到家,她瘫倒在床上。平静后,她开始数钱,每一角、每一分都被她反反复复数了许多次。10 元4 角。这是活了近15年的冯秋水最大的一笔财富。她在狂喜与惶恐之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她有许多梦想,买一把上好的木梳,两块香喷喷的肥皂,买一条碎花裙子,一顶遮阳的大檐帽,还想给奶奶买一副眼镜,一双棉鞋……这15年来,她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是快乐,当她握紧手中那一把钱时,她尝到了金钱带给她的喜悦,只有把钱花出去,她的快乐才能变现。
第二天,天刚亮,冯秋水就到了供销社门口,门没开,她就站在那里等,像是过了一天,营业员才来,打开链子锁。她低着头,跟了进去。手在口袋里紧攥着钱,不安地四处张望。柜台上方挂着的一条蓝色健美裤,像一只钩子,迅速将她勾住了,她的双眼再也无法挪开。她看了看营业员,用手指着那条裤子。营业员极不耐烦,慢吞吞地取了裤子。她伸出手,在裤子上抚摩了一下,又迅即缩回来,飞快地偷望了一眼营业员,随即将双手放到健美裤上,尽情地将整条裤子细细地摸了个遍。突然,她沉默了7年的嘴咧开笑了,露出一口冰雪般的牙齿。她摸出零碎的钱币,小心地摊在柜台上,营业员瞟了瞟她,从一摞零钱里数出9 角钱找给她。这是最后一条健美裤,蓝色的,虽然她想要的是黑色的,穿上也有点大,但她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关键是这是一条健美裤,她终于拥有了一条健美裤,这就够了。
这一天是冯秋水15 岁的生日,她穿上心爱的健美裤,挺着胸,满心富足地走在马泉镇的街道上。
看,来了个女流氓。一个中年妇女惊奇地叫道。
没想到这个哑巴也这么风骚。一个年轻男人的眼睛黏在健美裤包裹的臀部,又停留到腰部以下的三角地带,再也收不回来。
裤裆里那点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这跟脱了裤子有啥区别?
真是丢人呐,丢丑卖国!
不过还真是好看哩。
听说健美裤很贵,她哪来那么多钱买?
……
冯秋水心中充盈着欢喜,这些杂音统统都被她隔绝开来。她蹦跳着回到家,奶奶一见到她的健美裤,脸色大变,转身去找剪子。她扭头便跑。她像魔怔了一样,健美裤时刻不离身,就连睡觉也要穿着。拥有健美裤的她是快活的,一向被人遗忘的她乍然成了众人眼中的焦点,他们嘲弄她,嫉妒她,也羡慕她。整个镇上穿健美裤的只有她一人。很快,年轻的女人们纷纷蠢蠢欲动,向自己的丈夫或母亲要求买健美裤,遭到拒绝后,她们以绝食或分房睡来抗争,为此,镇上的男人和女人们对冯秋水深恶痛绝,并一致将矛头对准了她。村里的妇女青香一手拿砧板一手拿菜刀,在冯秋水家门口边剁边骂,骂她不要脸,骂她贱货和婊子,骂她故意穿得风骚想勾引男人……一盆盆恶毒的脏水肆意泼向15 岁的冯秋水,她将大门拴好,又用桌子抵得死死的,试图将那些腌臜的东西阻隔在门外。门关严了,他们又往她的窗户里吐唾沫、扔砖头,她家唯一的一口铁锅被一块飞来的大石头砸穿了一个洞。奶奶枯坐在柴房里,面无表情,半晌不语。冯秋水不声不响地进到厨房,用一口土陶甑开始烧水、做饭。
冯秋水不明白老天为什么单单把她变成一个哑巴,而不是一个聋子和瞎子,她白天穿健美裤,背后总会有一长串指指戳戳,晚上穿健美裤,从暗处会飞来一口突如其来的浓痰。一天清早,她打开门,赫然见大门上挂着一只肮脏的破鞋子。
从那以后,冯秋水只敢深夜出门。她意想不到,那一晚,黑夜向她睁开了一双邪恶的眼睛。
夜黑得像一团浓墨。冯秋水心事重重地走在下马河边。奶奶说她年纪不小了,该嫁人了,可是谁会要一个哑巴呢?河滩上摇曳着一个长长的影子,她踏着自己的清影,艰难前行。突然,另一道影子同她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又迅速分开。她的心一紧,她抑制住想回头的欲念,加快了步履,那道陌生的影子亦步亦趋,她开始狂奔起来,在河滩上留下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脚印。不料,她被一棵枯树绊倒了,随即,一个瘦弱的身躯扑了上来……
莫想跑!一张稚气的脸,咄咄逼人地问她:你是不是捡到了我的10 块4 毛钱?
冯秋水挣扎着坐起,望着眼前的少年,隐约记起他是邻村的祁二木,又望了望她毫发无伤的身体,吁了一口气,瘫坐在河滩上。
不等她回答,祁二木又将一张5 角纸币举到她面前,正色道:我在所有的钱上都做了记号,这五角钱上我画了一个乌龟。
冯秋水纳闷了,剩余的9 角零钱明明装在健美裤里,怎么会跑到他手里去?
其他的钱呢?
冯秋水从健美裤里摸出4 角钱递给他。祁二木接过,又问:怎么才这么一点?
冯秋水指了指身上的健美裤。
祁二木起初不解,很快明白了。他恼怒地问:你把我买喇叭裤的钱买了健美裤?
冯秋水点了点头。
祁二木生气地钳住她骨瘦如柴的肩膀,眼里喷出了火。
冯秋水自觉理亏,将头埋到了胸口。她注意到,他的左手食指上有一道疤,像一只眼睛。
祁二木突然抓住她的健美裤说:把我的喇叭裤还给我!
冯秋水吓愣了,只见祁二木疯狂地拉扯着她的健美裤,她极力挣扎,又踢又打,却奈何不住急红了眼的祁二木。
眼看她的健美裤即将被剥下来,冯秋水将赤裸裸地呈现在下马河边,河滩上忽然出现了第三道影子。这道影子狠狠地踹了祁二木一脚。
2
冯秋水紧咬着双唇,怒视着麻子爬了半张脸的祁万金,恨不能将他咬碎。
正是这个跛脚男人,在祁二木脱她的健美裤时,一瘸一拐地跳出来,假装救她,待祁二木离开后,却真正脱下了她的健美裤,试图将他肮脏的东西塞进她的身体里,她激烈反抗,照着他的跛足死命地跺下去,才得以逃脱。
正是这个麻脸男人,一回到村里就大肆宣扬她冯秋水被祁二木强奸了,导致祁二木被派出所的人带走。没有人会相信祁二木只是想抢她的健美裤,只有她相信,偏偏她不能开口说话,所有的话,都被祁万金说了,他的腿跑得慢,嘴却跑得飞快。冯秋水的丑事从下河乡跑到了马泉镇,又跑到了方圆几百里的人耳中,跑到了田间地头,茶余饭后,有好事者特地绕道去她屋里看这个被奸污的不洁女人,看看她是不是长得像狐狸精。男人和女人用不可名状的眼神,意味深长地从她的胸前打量到臀后,似乎想从她身体里挖出点什么秘密。
正是这个麻脸的跛脚男人,第二天就带了一包白糖、一斤猪肉来冯秋水家提亲。冯秋水不住地摇头,乞求奶奶不要将自己送入这只恶狼口中,奶奶握着冯秋水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水啊,认命吧……奶奶进到厨房,坐在土灶前,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冯秋水将白糖和猪肉扔到祁万金身上,那块晦暗的猪肉从祁万金头上耷拉到他黝黑的脸上,竟十分搭调,活像一张肿胀的猪脸。冯秋水看到这一幕,吃吃地笑了,笑得祁万金发怵。他讨了个没趣,捡起散落的白糖,又将手指放到嘴里舔了舔,临走前,他凑近冯秋水,将舔过白糖的舌头在她面颊上舔了一圈,又拍了拍她的臀部,才满意地离开。
冯秋水踉跄到厨房,舀了许多瓢水洗脸,洗出一脸苦涩的泪水。
冯秋水虽哑,却不傻,她跟着镇上健全的孩子一起读完了小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她想继续念初中,奶奶却拿不出钱来供她念书。
她恨这个跛脚麻脸男人,她怀疑他居心叵测,一直预谋奸污她,她记起深夜外出时,总感觉有一道暗影缠绕着她。
成亲的头一晚,冯秋水穿过荒凉的站台,来到下马河边。她站在湍急的河流里,浑浊的河水一遍遍冲刷着她的健美裤。健美裤一步步向河中央走去。一只灰狗在河滩狂吠着,冯秋水转过身,同那只瘦骨嶙峋的老狗四目相对。它瘸了一条腿,她是个哑巴,他们都是被遗弃、被遗忘的。冯秋水在水里倒退着,每退一步,灰狗都会呜咽一声,这叫声令冯秋水感到温暖,这世间留恋她的,竟是一条跛足的狗。明天,她将被一个龌龊的男人糟蹋,而她容不下身上有半只虱子。
一根光滑的树枝漂到了她身边,她截住树枝,在水面划起了道道涟漪,那些涟漪在月光下舞蹈。她眼前浮现出祁二木那张惊恐的脸,祁万金那张淫笑的脸也跳了出来,龇牙咧嘴的,随时准备将舌头伸向她。她望着下马河上空的流云,凄惶地笑着,缓缓将健美裤褪到大腿边,闭上眼,横下心,将那根尖利的树枝捅进了自己的草丛……
一股殷红的血浮上水面,又顺水漂走。她立在痛楚的下马河里,目送着她溺死在下马河里的青春渐行渐远。这一天之后的冯秋水,将不再做一个沉默的哑巴。
3
光秃秃的火车站,一趟趟列车呼啸而过。当最后一趟列车驶过时,夜幕便开始降临,黑夜用黑暗,缝了一把刀子。
冯秋水扯下红盖头,从红嫁衣内取出一把刀,寒光一闪。这把刀是她出嫁前夜,奶奶亲手交给她的,冯秋水万万没料到,拾了一辈子垃圾的奶奶,竟藏了这样一件宝贝。这把刀有三个锋利的刀刃,扭曲成一个尖锐的刀头;刀柄由和田玉、大红酸枝木、猛犸象牙以及银板构成;刀鞘是白铜质地,鞘首是椭圆形,比鞘体稍宽,看似一块盾牌,鞘身正面雕龙反面画凤,龙凤呈祥,龙与凤之间镶嵌着几枚绿松石。冯秋水一见到它便爱不释手,这是她从奶奶家带来的两件嫁妆之一。她为这把刀取名为“孤鸿”。
另一件嫁妆是一只缺了口的瓷碗,这只碗陪伴她近八年,是母亲留给她的唯一纪念。她将碗倒扣着,取出孤鸿,开始在碗底磨刀。嗞,嗞,呲,嘶……
祁万金龟缩在门边,试探着推门,又畏缩不前。冯秋水兀自磨着刀,刺耳的声响吓跑了门外槐树上的几只乌鸦,它们发出凄厉的叫声。
两柄红烛被孤鸿削成了四截,磨砺过的锋刀横在冯秋水身旁的枕头上,床中心,躺着一个豁口的瓷碗,碗中盛了满满一碗清水。冯秋水放心地睡去。深夜,冯秋水忽然感觉呼吸困难,她下意识地去摸手边的孤鸿,却摸到一个毛茸茸的人头。那只碗没了踪影,床铺也是干的。祁万金压到了她身上,将臭烘烘的嘴拱了上来。冯秋水四处摸索那把刀,但只是徒劳。祁万金虽瘸了一条腿,双手却孔武有力,他钳制住拼命抵抗的冯秋水,费力地扒下她的健美裤,健美裤扒到膝盖处时,冯秋水无力地放弃了抵抗,像一具尸体一般,直挺挺地躺着,任由他摆布。他的坚硬靠近她时,卒然疲软了,无力地耷拉着。祁万金沮丧地从她身上爬下来,冯秋水笑了,起初是嗤笑,继而是轻轻的冷笑,又转成幸福的狂笑,笑得浑身颤抖,笑得眼泪濡湿了枕头。那笑声自身体深处发出来,刺破这寂静而惨白的夜空。
祁万金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冯秋水起身,进到厨房,倒了一盆温水,一遍遍擦拭身体,她狠狠地揉搓着被那个无能的男人触碰的每一寸肌肤,搓得又红又痛。正准备穿上健美裤时,祁万金撞开了门。他夺过她的健美裤,操起一把剪刀,泄愤似的疯狂剪了起来,健美裤变成了一块块碎布条,一阵大风吹来,碎布条飞得七零八落。冯秋水穿着一条花裤衩,静静地看着,等他剪完,她走到他面前,抓起他唯一的一只酒杯,掷在地上,酒杯碎成了几瓣。不等祁万金反应过来,她就不声不响地走进卧室。祁万金青筋暴起,跟了进来,将未剪完的健美裤遗骸摔到她身上。冯秋水的身体一抖,仍安静地将床铺抻得平平整整,又背对着祁万金躺下。祁万金忍受不了她的漠视,粗鲁地拉起她,她用冷冷的眼神回应他,那眼里结着寒冰。
祁万金的耳光扇到了她倔强的脸上,拳头挥到了她直挺的背部,瘸腿踢到了她穿过健美裤的臀部,他痛得龇牙咧嘴,又换了一条好腿,将所有的愤怒倾泻到她身上。聒噪的夜骤然安静了下来,祁万金的怒气倏忽熄了火,他的一条瘸腿停在了半空,一双小眼睛惊恐地瞪着:一把闪着幽光的孤鸿抵到了他裆部。
冯秋水胜利地笑了。
每次被祁万金蹂躏,冯秋水都会将自己冲洗许多遍。清洁干净后,她就开始磨刀。好事的邻居们茶余饭后时常议论,那个哑巴女人天天磨刀,一磨就是一晚上。
4
这一夜,注定不平静。
祁万金一只好腿刚迈进门槛,另一只瘸腿却无论如何也迈不动了。一把孤鸿抵在了他的瘸腿上。冯秋水的眼睛里闪烁着火焰,那火焰能将祁万金化为灰烬。
祁万金骂骂咧咧道:“你穿什么都能看得到的健美裤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你是不是希望被那个小卵蛋强奸?”冯秋水不语,只回应他一个轻蔑的眼神,便转身,砰地关上房门。祁万金死命地踹门,准备将这个女人狠狠修理一顿,瘸腿猝然发作了,又痒又痛,他扭曲着脸爬到椅子上,开始喝酒,酒能麻痹他的神经,也能缓解瘸腿的疼痛。大半瓶烧酒下肚,他醉醺醺的,无力再碰冯秋水,便倒在床上早早睡去。半梦半醒时,祁万金惊觉一个黑影坐在他床头,不声不响地看着他。他以为是梦,揉揉眼睛,见冯秋水坐在他床头,手里提着一把奇怪的刀,正用诡异的眼神盯着他。祁万金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当晚小便失了禁。不久,他开始出现幻觉,有时是哑巴女人将一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有时是她砍断了他的瘸腿,有时又切掉了他的命根子。他拼命酗酒,只有醉在酒里,他才能跑赢冯秋水的利刃。
那天,风似刀子一般,割到脸上、身上,冯秋水在冷冰冰的床上卧了一夜,隔壁祁万金的房间离奇地悄无声息。冯秋水有些讶异,却也懒于起身,她独守这难得的清静,睡了个好觉。第二日,她在下马河边见到了那个气若游丝的男人。原来,祁万金喝得烂醉,找不回家的路,他鬼使神差地来到下马河边,河水结了冰,被酒精炙灼的他,抚摸着凉爽的冰,像是抱着一个通体温软的小媳妇,他惬意地抚摸着,一脸笑意地沉沉睡去。清晨,早起的村民发现,他的身体一半在冰面,一半浸在解冻的河水里。两个村民将死狗一样的祁万金拖回了家,拖到冯秋水面前。冯秋水面无表情地探了探他的鼻息,又端来一盆热水,泼在他身上,祁万金的身体抽动了一下,吐出几注黄水,冯秋水将一杯温水灌进他嘴里,他才渐渐有了人色。
两天后,祁万金彻底苏醒过来,但他的下半身却无法苏醒了,他那根不争气的玩意儿再也没有知觉。他的双腿在冰水中泡变了形,镇上的医生说要截肢,祁万金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自那天起,他拒绝吃东西,每日歪在一把破旧的藤椅上,两眼发直,一心等死。冯秋水尽心竭力地伺候祁万金,给他喂水、喂食,按摩双腿,他却毫无反应,像个木乃伊,听凭她摆布,他的全身都哑了。一天,冯秋水给他喂饭时,祁万金直直地盯着她,忽然抬起右手指着她身上的健美裤,冯秋水不解,他的手始终指着那条健美裤,直到咽气。
冯秋水穿着健美裤为祁万金送终,她自始至终没流一滴眼泪。镇上所有的男女都指责她铁石心肠,薄情寡义,一个爱管闲事的妇女指着她的鼻子骂她克夫,并朝她身上啐了一口。冯秋水面不改色地取出一块绣花手绢,将那口痰擦拭干净,又进到幽暗的屋内,将更多的唾沫关在门外。
当天晚上,有村民说,那个哑巴是假哑,她会唱歌,唱了一整夜。
5
冯秋水一夜之间成了寡妇。她的窗户上陡然出现了许多双眼睛,那些眼睛分秒都在追随着她,从客厅到厨房,从卧室到茅房。有时她感觉门外有一双眼睛窥视着她,她不声不响地迅速打开门,一个男人来不及躲藏,被她当头泼过来的水淋了个稳当。她左手扶着脸盆,右手叉在腰上,笑盈盈地看着男人狼狈的模样。
一次,冯秋水发现,她晒在外面的健美裤上沾有不明的黏稠的液体,她瞬间明白了这是什么,当场呕吐起来。她将那条健美裤不停地洗,洗了十几次仍觉得不干净,她边搓裤子边哭,眼泪将拧干的裤子又打湿了。这是祁万金死后,她第一次落泪。
她将洗得发白的健美裤,剪成一截截布条,又用打好的面糊,将布条一条条黏在窗户上,屋子变得密不透风,窗外那些眼睛再也占不到她的一丝便宜了。
有几只苍蝇习惯叮在她门上、窗边。冯秋水一听到苍蝇来了,便开始在碗底磨刀,每一下都磨得触目惊心,磨得那些男人胯下一凛。待苍蝇们离开后,她收起孤鸿,露出胜利的微笑。
祁万金走了,冯秋水头上的虱子也神奇地和他一起走了。冯秋水开始留起了长辫子,深夜,她拖着齐腰的辫子,来到雾气蒸腾的下马河畔。她褪下健美裤,裸露着身体,缓缓走进冰凉的河水里。她闭上双眼,将自己全然交给河流。河水冲刷着她洁白的身躯,她纵情歌唱,歌声随流水一起荡漾。
那一年,健美裤已经不流行了,冯秋水仍执着地穿健美裤,将一头长发烫成了大波浪,配了蝙蝠衫和呢子大衣,还描了眉,画了眼,神色淡然地上集市买菜、逛街。健美裤耀武扬威地直挺着,将那些男男女女异样的目光甩到身后,又用她十公分的高跟鞋将流言蜚语碾碎。
有时她也会穿一身亲手缝制的旗袍。旗袍在村民眼中是稀罕物,他们都觉得很美,又觉得大逆不道,露胳膊现腿的,分明是想诱惑男人。而且,哪有女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镇上的女人们嫉妒她的美和她的衣服,拼命想将她拉入她们的行伍,和她们一样穿得大红大绿或者灰不溜秋。冯秋水偏不,她我行我素地在旗袍和健美裤之间轮换,丝毫不顾忌什么。村民说,那个哑巴女人是妖精变的,想勾引马泉镇所有的男人。
冯秋水时常沿着铁轨前行,谁也不知道她要去到哪里。站台废弃了,栏杆锈迹斑斑,再也没有煤车经过了,哪知老灰狗也不知去了哪里,偶尔呼啦啦飞过一群麻雀,发出沙哑的叫声。她哼着谁也听不懂的歌,铁轨上的火车同她一起唱歌。
上马山上,漫山遍野的孤独里,她赤着脚,在草地上奔跑,累了,便躺倒在草坪上,沐浴着阳光,心无挂碍地睡一个长长的觉。梦里,没有虱子,没有苍蝇,只有奶奶那慈祥的笑。出嫁的第二年,奶奶便去世了,剩她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同世界无声地对话,亦对抗。
她爬上门前的那棵老桑树,坐在树上思念奶奶,她幻想奶奶会变成一个洁白的蚕茧,又破茧而出,飞到她面前。
她生得越来越出挑了,却是一只无法近身的刺猬,男人们都只能将眼睛黏在她的背影里,偷扫着她丰满的胸和微翘的臀,意淫和她交配。后来,那些男人们被家里的婆娘揪着耳朵拖回家,婆娘们冲着冯秋水的背影吐唾沫,骂她贱货、骚货、婊子。
她从铁轨旁采来不知名的野花,插在祁万金存下来的酒瓶里,满室便开始旖旎芬芳。她打着赤脚,散开一头长发,在一个人的房间自在地跳着舞,跳得香汗淋漓。再也不用伺候那个醉汉了,再也不用心惊胆战了,当年那个15岁的青涩少女,那个隐忍、屈辱的少女,已经死了,死在了自己的孤鸿刀下。如今的她,不必顾忌他人莫名的目光,不必在意恶毒的流言。她在风中恣意地舞着,她就是一阵风。
冯秋水晚上不再磨刀了,她开始咿咿呀呀地唱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歌声里带着欢欣,也含着凄婉。村民路过时,都惋惜地说,那个哑巴女人疯了。
6
门外有轻微的响动,那响声凝滞住,像八年前流经的乌云。冯秋水起初磨了几下孤鸿,随后又停了下来,她听得出,门外不是苍蝇,而是一只壁虎。她头一次为门外的人主动打开了门。
门一开,冯秋水见到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祁二木。她想起来了,一晃8年过去了,他应该是被放出来了。
祁二木迟迟不敢进门,他呆呆地望着迎接他的那把精致的刀。冯秋水笑了,露出两颗兔牙,她收起孤鸿,并将他拉进门里,反手关上了大门。
冯秋水背对着他,准备给他倒水。祁二木痴望着她的背影,她穿着一条紧身的健美裤,浑圆的臀部,轻轻地晃着。祁二木忽然冲到她身后,一把抱住她。冯秋水的身体一颤,任由他抱紧。他紧紧地箍着她,她的呼吸开始急促。她低下头,在他长了眼睛的左手食指上咬了一口。抱着她的手松开了,冯秋水转过身,立在他面前。
她靠近他,将食指划过他的嘴唇,凉的。她又扳过他的脸,那张脸有些粗糙,喘着粗气。冯秋水低下头,将同样冰凉的嘴唇贴了上去。那是她的初吻,也是祁二木的初吻。祁万金掳走了她的身体,却夺不走她的吻。祁二木的身体剧烈颤抖着,他听到了牙齿磕碰在一起的声响。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冯秋水却脱去自己的上衣,并将柔软的手伸进他的衣服里。当她的手接触到他的囚衣时,他高涨的情欲骤然冷却下来。
他轻轻地推开冯秋水,将一堆零散的钱,一股脑儿地塞到她手里。冯秋水用惊异的眼神看着他,他嗫嚅着,说:对,对不起,对不起……
除了这三个字,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冯秋水读懂了他的心,她又何尝不是对不起他呢!她任由他将钱塞进她的棉袄里。她转过身,用陪伴她十几年的一只碗给他倒水。他喝下一碗温水后,身体顿时暖了许多。
祁二木语无伦次地说,八年前我真的不是想害你,我去砍柴、卸煤,辛辛苦苦攒了一条喇叭裤的钱,却弄丢了。冯秋水一怔,用苍白的手揪紧了健美裤。祁二木又说,这八年里,我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头,也在车间里自己缝制过一条喇叭裤,可是,我始终没有真正穿过一条喇叭裤……
冯秋水坐在他对面,静静地看着他。他大着胆子回望冯秋水。冯秋水开始脱自己的健美裤,又用迷离的眼神注视着他。她的身体在他脑海里出现过千万次,却一次也没有真真正正地看过。她即将褪下健美裤时,他按住她的手,将头靠在她胸口,微微闭上双眼,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又仿佛重返故乡。许久,他又蹲下身,抚摸着那条健美裤,将脸贴在上面,一遍遍地亲它,吻它,吮它。他跪在地上,将头埋在她的两腿间,无声地流着泪,他的眼泪越来越多,身体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冯秋水抚摸他的头,像抚摸一个孩子一般,突然,她现出一个动人的笑,祁二木扬起脸,虔诚地看着她,竟看痴了。那张脸妩媚中带着妖娆,是他平生见过的最美的脸。
他的身体微微地抽搐了一下,一股鲜血从他身上缓缓流了出来。祁二木望着天上的白云,它们飘在一起,很快又散开了,像一团灰。他幸福地笑了,身体渐渐软了下去。他终于抵达了故乡。冯秋水手中的孤鸿跌落地上。冯秋水抱着他,坐在血泊里,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歌,唱了一整夜。
冯秋水将一块绣着梅花的手绢盖到了他脸上。鲜血沁到手绢上,手绢上的梅花,开得更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