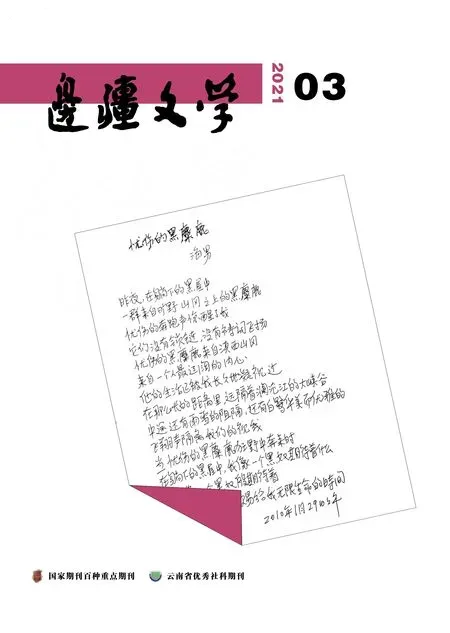背后的秘密散文
加拉巫沙(彝族)
一
一条古道要这么走,那是历史的事情。
世居于沿路和附近崇山里的人们是否得到过它的庇佑,不好说,可能有,也可能无。毕竟,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太厚重,一时说不清、道不明。
古道被废弃后,新的公路从另一端开山架桥,豪迈着,激昂着,甩将过来,但一穿越高寒的海棠古镇,就折了方向往竹玛垭口逃去。这是古道山民的绝望,海棠以上更高海拔的村寨更加静默,只是人心从未孤寂和荒芜。
生活是满地的世俗。讨生活,还得往古道旁的高耸爬升,向着比海棠更高的寨子进发。
重峦叠嶂,林箐茂密,七弯八绕,攀到极致,早前跟着山麓压抑的目光突然没了遮挡,辽阔开去,这便是哺尔儒诺了,彝意为麂獐跃动的原始杉林,汉语则直率些,唤作平坝,真的名副其实。瞭望的此刻,再憋屈的事都该放下。你瞧,大山垂下头颅,让位给高原,还有啥事愁啊愁的!地理开阔之际,心境跟不上,胸襟还有啥用?若真的苦逼,吼两嗓子,淌一通泪,仄仄的人生甬道便一马平川。
不要以为气魄的大山都是尖锐的。
雄浑的山间有一湾一湾的褶皱,肥沃的台地纵横在湾里,鸡鸣和炊烟便成了日常。步步抬升的汉彝村庄啊,各有其名,自居其所,鲜有混杂。但彝人懒得琐碎,索性把攀爬向山顶的沿村,以及顶上的平坝统称哺尔儒诺。
从北方出发的古道犹如长长的绳索,盘绕在山脚一隅,要越过横亘的高山,没有捷径,必须隐没于感觉往空中一节节抬升的幽深峡谷,才能达到高地的缓坡。这秘境之路是彝汉交界的清溪峡,老百姓唤作深沟。自秦汉以降,兵家必争,烽火狼烟,其战略地位,可见一斑。作为商道,它同样跟历代王朝的经济命脉一起搏动,是古南方丝绸之路挺进横断山脉的第一峡。
尽是乡野的地名,人们却烂熟于胸。谁一旦开口,上至耄耋老者、下及光屁股幼童,皆可娓娓道来。
大树李子晒经关
白马抬头望河南
河南站,吃杆烟
八里平英到大湾
一进深沟五洞桥
平坝窑厂双马槽
尖茶陡坡到海棠
……
像彝人的指路经,连接川滇的古道由成都往南,过雅安的汉源,一程程把路引向大凉山的北大门甘洛县,经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后,再穿滇越境,延伸到跳肚皮舞的古印度。
古道,戎马倥偬,商贸频繁。历史的呐喊、弑杀、赌博、嫖妓,以及荣耀与颓废,跟深山人家有多少关联呢?往历史深处膜拜,乃汉人和彝人的最爱,两相比较,后者更甚,胡乱吹嘘,雪白的豆腐竟能挤出殷红的鲜血。他们喝着转转酒,扒拉的尽是古道与家支的兴衰往事,仿佛亲力亲为过这一切。坐轿的政客、骑马的商贾、步行的兵士和落魄的旅人,要哪类往来于古道,与其先祖如何交集,全凭不烂之舌随意翻卷。或许,马帮托运的盐块和布匹,半道遇劫,而抢匪恰是其祖上;又或许,某先祖到深沟的酒坊打酒,与夜宿的武官对饮,获赠过一炳战斧;再或许,八竿子打不到一撇,杜撰出好汉的传奇……不尽假想,仅是或许。这么一条交织着官、军、商和文的古道,在彝人的观念里,却终究是一条英雄的道。尚武的山地民族,行侠仗义,漠然生死,哪管你其他那么多的道道?
哺尔儒诺的汉民钦佩啊,彝人兄弟最能吹,看哪天,说出的大话戳破了天!是的,在彝人的语境里,土音浓郁的汉语活蹦乱跳,即便讲母语,也是点缀而已。汉人问:你咋晓得么多事?
彝人回击,“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还不是你们教的。
倘若反击的是缺牙老妪,拖腔拉调,把“不出门”的“不”字兜半天,才抛出,场面既风趣又滑稽。深山里的彝家,老老少少,语言混杂得花花绿绿。
杂居的现实,埋伏着所有可能的发生。
但是,千百年来,汉彝间可能的爱情与婚姻被却彝人盯死看牢,见光便死。
纵使打开所有尘封的记忆,还没有哪个家支与汉人结缔联姻,相反,听闻的多是被剿灭的惨无人道的案例,杀鸡给猴看嘛!他们担心,旧制的民族内婚、等级内婚的规矩遭到践踏,有悖于从先祖手里沿袭下来的传统。
彝人推崇血统的纯粹,戒律约束着每一颗“红杏出墙”的心。诸恶莫作,自净其身。为吓唬被荷尔蒙催情的青年,有则谎言经久不衰,说与他族的女子交往,等你死亡火葬的那天,下面的两颗睾丸会“轰轰”爆炸,一世英名,弃若敝履。彝人还拿动物比拟,称自己是绵羊,小尾巴晃来荡去,关键时候,遮盖了屁股上的羞;他人是趾高气昂的山羊,小尾巴翘上天,不知害臊!谎言和比拟都是彝人夜郎自大、自以为是的告诫,难道人家的儿女非你莫娶、没你不嫁?
内部的秘密不可能守住,还是像风一样吹遍了崇山。
二
生老病死,人间烟火,汉彝之间彼此宽心的襄助和扶植多了,冷漠的心慢慢融化,生的除了友谊外,偷偷摸摸的爱恋竟悄然萌发。
三娃就害过相思病。那是山顶一位卖鸡蛋的叫乌嘎嫫的女孩,汉语不怎么流利,羞答答的,说话时脸彤红。好几次,三娃都买下她的鸡蛋,最后一次,还端了一碗米凉粉送她。从此,那女孩不再出现,只在想象中和梦境里向他微笑。
等晚荞收入粮瓮,彝族年在孩子们的喧嚷声中来到了彝寨。
到了傍晚,母亲在家门口扯着嗓子喊,木尕惹,快回来喂年猪。这一喊,孩子们的梦才叮叮当当地破碎,他日,只好等着远村的同龄人嘲讽:小杂种!自己的年都不过,还彝人呢?孩子除了戏耍时想赢得面子之外,真正的念想是肉。然而,年年岁岁的节庆,深山彝人杀只鸡,一来祭祀祖灵,二来糊弄小孩,彝族年就敷衍着过了。
相当庞杂的声音在不同的远山激荡,归结为一个观点:哺尔儒诺的彝人呀,最爱舔汉民胡须。形象地讲,汉人吃肉丝肉片的炒菜,粘在胡子上的油星无需去擦,谄媚之流会给你舔舐干净!言下之意,那里的彝人阿谀曲从、遗弃自我、不敬重祖训、不遵循传统。
恶毒的言论,有人赞,有人驳,也有人和稀泥。任凭唾沫横飞,累的依然是自己,终究不去争论了。
眼看,春节还剩半月,哺尔儒诺的彝人突然忙活起来。数日内,年猪的叫声此起彼伏,喜庆像糖果甜蜜了一湾湾的彝寨。冬天里没有花开花香,但老中小三代人的笑脸便是寒冬最鲜艳的花朵、最馥郁的芳香。
正是检阅一户之主交际能力的关键时日,谁会轻言放弃这美妙的人生体验呢?受邀者,不都是结拜过的孩子干爹干妈、患难之交的挚友、情投意合却不敢声张的恋人?日子铺排得满满当当,一时想收,难啊!他们送来的汤圆粉、碗儿糖、爆米花、干牛肉,以及烧酒悉数收下,待归去,用木棍儿穿了长条的猪肉,予以馈赠。
一来二去,差不多分完了全部猪肉。
翌日,母亲早早起床,煮一锅沸腾的汤圆。苦于稀罕,刚才揉粉时掺杂了磨好的玉米细面,但孩子的贪吃劲儿没减下来,一颗颗地数着,往死里撑。过会儿,腆着滚圆的肚皮飞也似的炫耀去了,好像汤圆才是家庭外交的成功标配。
那些天,汉彝亲密无间,里里外外的蜿蜒小径上熙来攘往。估摸着,三娃也加入了宾客的队列,行走在山野,身后晃荡着长长的猪肉。
在起云飘雾的天气里,古老的传说会神气活现,两三根猪肉悬垂着,闪闪地飞,就是不见人。无疑,这又是远年传开的“阿俄”——小神子作怪了,不知偷了谁家的猪肉,也不知偷来送给哪家?过几日,总有人家惊呼,要么缺了肉,要么增了肉,说得有板有眼。可三娃始终没有遇见,心想,怕个毬呀!朝着无影腿左左右右砍几刀,肉不就落地了?
灵异的怪事,说得多了,心头生虚。于是,遍一切地使用新招,送人的猪肉往热水里浸泡,洗掉血迹,妖魔便无奈了。认知的统一,没人刻意去指使,但深居大山的汉彝山民淳朴着、简单着、迷信着,衍生出新的一方礼俗。
赶集,那是乡人对古道最好的怀念。
起初,不会有很多人,天亮就出发。当地土语讲的“马驼子”前只有几匹牲口,但可以想象成千军万马的商队。不靠谱的想象,乃深山人最得意的浪漫。驮物的牲口要走斜斜的坡,上蹿下跳,马、驴和骡吃不住,也无法体味古道沧桑、厚重、陶然的精道劲儿。从平坝到海棠,两个多小时的脚力,跟着古道慢悠悠地行进。半道上,定有其他村寨的牲口不断汇入,俨然成了一个完整的队列。牲口间一旦陌生,便亢奋无比,烈性的相互撕咬、尥蹶子,不打一场,决不罢休;温顺的同样劲爆,见不得一泡尿、一坨粪,能嗅出骚气和臊气,负荷如轻,奔去母系的队列龇牙咧嘴,愚蠢的脑袋里,兽性大作的想法实在太多,举止粗暴,恬不知耻。这时候,马驼子英明唉,三五人赶几匹,把牲口心痒痒、硬生生地隔开,鞭长莫及了吧!
一路谈笑,话题偏不了古道的是是非非和起起落落。
“深沟开发了,娃儿子些就有前途咯!”
“那么多有钱人,咋一个都干不起?”
“可惜这条古道了。”
倔强的努嘴,日怪,你们还信那几爷子?
翻过前面的坡,路开始往下,可以像鸟一样俯瞰整个海棠古镇。
曾经的军事要塞,风行的庙林古城,皆因雄关漫道的衰落而破败,已经显不出丁点的庄严、肃穆和华贵了。相反,房屋陈旧,设施破烂,影调灰暗,它像一名正在老去的英雄,刀光剑影后,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暮年里,消遣着时光。
归隐的过往,活在一代代乡人的记忆里。于此,老朽的海棠依旧是心目中的那抹亮色,历史的遗风,如山岚缥缥缈缈。
男人去了,深夜一定会挨骂,婆娘的愤怒些许有理。昨晚交代的事,咋忘了呢?叫买醋,拿出来的却是酱油;木梳子变了戏法,弄成塑料的了;木尕惹的鞋码太小,脚后跟再硬塞也枉然……反正,没有一件事情是办妥的。最让女人气恼的是,男人满街找人喝酒,血亲的、姻亲的、干亲家的、狐朋狗友的,碰面便守不住口袋,少则打半斤白酒,多则抬几件啤酒,晕乎乎的醉了。说大话的他们哪还管牵去的牲口的死活,害得拴在电杆上的马、骡或驴不情愿地翻着嘴皮,拱自己的粪便。女人去了,苦荞、燕麦、土鸡、猪仔、蜂蜜等售卖的钱,恰当地派上用场。很多时候,家庭是按针一样细的心眼来筹划收支的。人的体面,暗示的往往是她们的持家之道。紧要的是,牲口不会遭罪,回家的路有多远,它们就放多远的响亮的连环屁。
古道的荣光来自每个年度的庙会。
四乡八岭的彝人来了,可他们不是信徒,来这里权当看稀奇、凑热闹、会亲友、做买卖;说不准,还能幽会到年轻时候的恋人,倾诉一番儿女衷肠。
高潮时刻终于来临。舞狮耍龙的队伍走在前列,后面跟着轿夫,抬着的菩萨颤颤巍巍的,担心摔落下来。古镇的路不宽也不长,吹吹打打间,绕了几圈,盼着菩萨被抬进了庙宇,人的洪流才跟着决裂,泄洪似的不见了。看客满足了眼睛,心里的渴求则一堆堆地敞开,街沿的餐馆里,市场的空地上,山坡的松林处,各自找乐子去耶。
文化的衍生是有趣的。彝语里本没有“庙会”的词汇,彝人取颠颠的动作译成“卜启”,意为抬菩萨,煞是形象。至于深奥之道,因文化本源的差异,管不着了。但娱乐的那一面却让彝人痴迷,辛劳之苦,寡淡之味,平庸之累,统统嘻嘻哈哈翻过,精神又振振地提起劲来。人,不就活一口气?劲儿没了,气还上得来?
待黄昏,过足身体和心灵之瘾的彝人,从海棠四散,可能在星月下,抑或于风雨中,行色匆匆。
古道夜归人啊!
三
日子有趣无趣地过,山人添岁,光阴增年。
寒冬霸气,浸淫整个哺尔儒诺的时间要延至来年的三四月。风没有少刮,天地间的冷,不是窸窸窣窣的雪,而是呜呜的风。雪累得停歇了,风的动静更寒,一阵紧过一阵。生活的技巧从不偏袒哪村哪寨,但除了一样的圈养牲畜、修缮农具和缝补衣裳外,汉人的寨子可多几门赚钱的活路,烧土酒,腌猪肉,开门市,可以忙碌到来年。
天时、地利的拙劣,皆因人和的机智翻转,冠以“海棠”二字的土酒和腊肉齐齐叫响,当真是崇山之运、乡人之福。
彝人呢,甭管年岁跑得再快或再慢,永远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能耐的,卖些粮食和家禽家畜;不济的,大白芸豆总能卖个好价钱,自个儿乐活。钱多钱少,只要荞麦和绵羊不愁、元根和萝卜足够、兰花烟能散给客人,日子就顺得起劲。
不酿酒,不等于不打酒。烈酒穿喉,一醉,自己就是天,天就是自己!
家里腌制的腊肉,再穷,气不会短,怎么拿去兜售?更何况,早在春节前,不是送得差不多了?除非,宰杀两三头年猪!感觉上,变卖五谷和牲畜,乃辛劳之回馈,心头踏实;若从别人手里买来加工成产品,既一万个羡慕,又一万个不情愿,矛盾得不知往哪里躲?于是,在两难的境地里,他们索性不屑地坚韧着、粗犷着,悠悠然,过着老日子。
欣喜的是,年轻的彝儿彝女与汉人朋友商议着赚钱的门道了。
可惜,没有人来咨询三娃。他憎恨自己,为什么不多赶几场集后才送凉粉给乌嘎嫫?那不又可以多看她几次?土酒生意如此紧俏,女孩的父亲为啥不到山下租房酿酒呢?如果来,他会嚷着家父传授真经,说不准她会像他一样,守着门店,将散装土酒和腊肉卖到纵横八百里的大小凉山。
痴恋,忧虑,诘问……三娃心知肚明,统统没用,还不如一个屁。彝人设置的那堵墙,变化莫测,无形又有形,巨长、巨高、巨厚,怎么也翻不过去。
又一场雪,没完没了。
此时,牛皮风箱拉风啊,呼呼的,管口对着熊熊的火炉。无须吆喝,锻打和修补农具的会来;无所事事的也裹着用羊毛捻制的“瓦拉”前来围观;小孩更是欢天喜地挤在人前闹热:仿佛是观赏一场娱乐大戏,硬邦邦的铁块如何经受千锤百炼,变身锄头、二锤、砍刀、匕首或剪羊毛的两撇叉子。
火炉驱散着空气的阴冷,暖和人。遥远的太阳晃得再亮,也显得虚情假意。当然,长盛不衰的话题胜似火炉,滚烫男人的心,赤裸的荤段子,说得咯吱咯吱地笑,从不顾忌少儿不宜。村里的几个寡妇被许配数次,名义上最先得到的是汉人铁匠,师徒都有份,语言贿赂,彝人精到哩。分给小孩时,当真了的就急眼,惹哭一场鼻子,边骂粗话边跑人。皑皑的雪地上,脚印,深深浅浅。
三娃是以徒儿的身份来到彝寨的。其实,借口而已。此番前来,还不是因为乌嘎嫫住在这个寨子里,好久没有她的音讯了嗳!粗俗的笑谈中,三娃一直抿着嘴笑,脑子里映画着女孩娇俏的面容。他倒是希望像许配寡妇一样,把乌嘎嫫许配给他。两块高温的铁,在锤子的反复击打下合二为一,先火红,后紫黑,涅槃成人们想要的农具。三娃多想变成火炉里的铁,拥抱着女子,将身体和灵魂融为一体。然而,三娃明白,彝人用的是另一种无形的大锤,将越过“楚河汉界”的爱情生生地砸散了、阻断了、灭迹了。
看着已读小学的木尕惹走向人群,三娃立马来了精神,拉着他走向空旷的雪地。一打探,朝思暮想的乌嘎嫫已在半月前的一场雪里出嫁,嫁到了远山的一个寨子里。话音刚落,忧伤自起,不是三娃迷乱,而是天地怜悯。你看,雪连着天地,粒粒落,线线飘,纷纷扰,犹如他的心境。
向现实低头!三娃有无本事,都只能这样。
心神不宁的青年吐纳着寒气和满腔的怨气,蹦出来的话,像是被牙齿锯断了。
“肯定跟……炸弹一样,炸它个……死翘翘。”
木尕惹吓得拉住三娃问:“哥,你要炸啥子?”
“不是正在修公路吗?”
“是啊!”
“每个寨子都接通了,你们的女娃儿要逃婚,跟人家跑了,会把老规矩炸个稀烂。”
木尕惹懵懵懂懂,无法将公路与炸弹接拢,傻着笑。三娃用手机搜索了一些照片,指着说,以后你娶模特儿当婆娘,好好轰那个老规矩。
骄傲的是,时代作出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抉择,沿历史纵深和退隐的古道将变成宽敞的公路,那段还遗存着一窝窝马蹄印的清溪峡被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公路大老远叉向更高的深山。古道人家的笑是得意的,精准扶贫好啊,白线一样的公路,将串联村村寨寨——整个哺尔儒诺——还能说闭塞和僻远吗?告别,是为重逢天下;“废弃”,是为被天下瞩目。
极目远眺是不可能的。目光里只见雪花乱象,可以遐想的是,从海棠借道而来的公路正往深山古道翻越,向沟和临渊的边坡,铁质的护栏跟着走,波浪似的,闪闪锃亮。只可惜,遐想中的路被积雪覆盖了,被冰凌冻结了。但又想想,严冬还未尽,春天不是已经在候场了吗?
古道的一前一后,竟是累加的两千多年,之前,让古道这样走,乃治边的需要;之后,令公路也这样走,则民生的福祉。前后之开路,揭开的皆为历史的一篇章节,名字都叫“伟大”或“壮举”。三娃想说的是,路全部修通后,沉寂的古道还会哑然么?深山人家的秩序不会打烂么?现代之风劲吹,一股股猛烈着来,又猛烈着去,只怕古道的遗风猝不及防,也防不胜防。
至于开发,也许从遮天蔽日的清溪峡着手,朝北或向南,牲口的商队铃声叮当,驮的货物虽鼓鼓囊囊,却轻巧,装着草料,表演呢。穿着古装的马驼子象征性地跟着,紧要的是高歌由地名编串的古谣。公路上,汽车正一辆辆驶来驶去,旅游者在一面小旗的指引下拍东拍西,异常兴奋。届时,彝人的那堵墙可能这村那寨的,无形中斑驳、塌陷,最终夷为平地,化为乌有。
对未来,谁都可以猜想,但又无法猜准和看透。未来,如果预测准确,那也不叫未来。未来之美,美在一切的不确切和可变化。
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