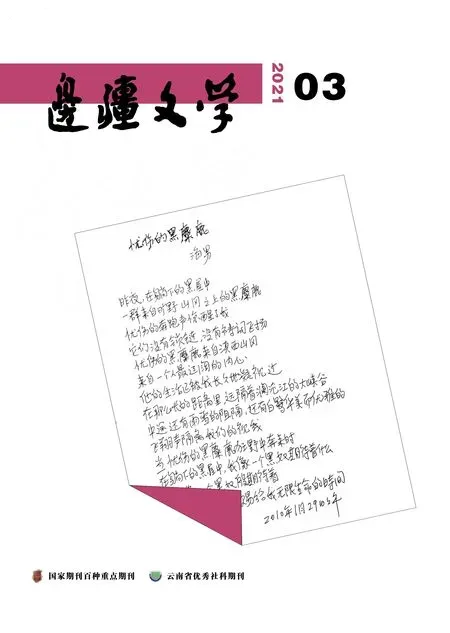蚁窝短篇小说
吴娱
蚁窝
那时候竟没有偷拿一根骨头。
地上全是蚂蚁窝,大大小小丘陵似的。一个个土包。
和周围大片的墓地经由长短秘密通道连接在一起,阿元想象着密遮天际的蚂蚁排着队热热闹闹去新建的墓地领餐。新来的,温热带着营养,算是和大家见过面,打过招呼了。通过一只蚂蚁,一堆认识了隔壁同样是一堆分不清胳膊和腿的散骨和灰。
下车的时候,阿元踩上一个不太大的蚂蚁窝。表哥叫阿元快跑,那里的蚂蚁个个大得吓人,会咬人的。表哥说起几年前去过的地方。
“忘了为什么会去那地方?蚂蚁啦,毒蛇啊,四处是,潮湿又热。”
阿元想起表哥前两年提起过打死一条毒蛇的事,表哥说那时候也没想什么,就想拼了命打烂那颗蛇头。后来呢?
表哥侧头点了一支烟,不说话了。
表哥在前面走,阿元在后面跟着,有些吃力。阿元知道表哥不想来这地方,更不想看墓地里埋的人。表哥不喜欢外公。
见过蚁后么?阿元一边小跑着跟住表哥,一边浏览四围墓碑上的照片。
“那些家伙躲在很深的地方呢。”
阿元觉得表哥不是在说蚁后。
那时候怎么忘了偷拿一根骨头呢?
“什么?”表哥停下来,看了看阿元,又往前走,“恶心!”
阿元不说话了。
两个人走到外公墓前才又说起话。
花和外公喜欢的糕点。
“全是孝敬蚂蚁的。”表哥说。
墓碑上下爬了蚂蚁,不多。
阿元掸一掸墓碑上的灰。外公打过你么?阿元不看表哥。
“他啊,爱听戏。”表哥转过身,让阿元一个人坐在外公墓前,自己跑到远一些的地方抽烟去了。
阿元挨个说起家里的人和一些近况,越看墓碑上的照片越不像外公,人死了长相也会跟着变吧?像活着一样,三岁会变,十二岁会变,十八岁阿元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外公已经八十多了。一只大头蚂蚁爬上外公的脸,阿元抬一抬手,又放下,只觉得自己的脸痒起来。
忽然旋起的风,把蚂蚁吹到哪去了?阿元抬头看一旁的柏树,大概掉进某片树叶的梦里了。
阿元又想起蚁后。问一问外公,捅毁一个蚁窝究竟算不算做了坏事。照片里的外公笑了。
那时候阿元捡起一根树枝,往外公的墓地周围乱捅了几下。
能偷一点灰也好啊。
阿元往远处看看,一整片,墓碑靠着墓碑,碑上的照片都是同一个尺寸,有些黑白有些彩,笑着的多,也有严肃的,张大嘴的只有一张,看起来像个歌唱家。墓地规整和平坦,不像蚁窝,起伏歪扭。
新来的很容易分辨,墓碑两边的塑料花开得爽朗。阿元想把那些花全拿走,种满一座荒山,说不定成了旅游胜地,死人的塑料花。阿元想象着,坐飞机从那座假花插满的石头山上经过,没有衰败的时候。蚁窝会有消亡的时候么?
表哥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阿元身边,墓碑上印出两个人的脸。
“一会儿去哪呢?”表哥问阿元。
阿元还在那座石头山上,变成一只山羊、一只蝴蝶,慢慢也就不需要吃和喝,那些都是假的啊。
外公从那间屋子里出来的时候,阿元看着矩形大盘子里的碎骨和灰,他们哭什么呢?都是假的吧?哪有什么外公!
偷拿一颗牙齿也是好的啊。
“外公早就没牙了。”
阿元和表哥在外公墓前大笑个不停。
阿元看着墓碑上三个人的脸,陷进一团黑里,又浮起来。
“走吧。”表哥拉起阿元的手,站起来的时候顿了顿,阿元以为表哥想和外公说点什么。
车还在刚刚停的地方,蚁窝也在,大大小小围满十几个。我想看看蚁后,阿元说。
表哥捡来一根粗些的树枝,捅了捅蚁窝。算了吧。
车里很热,表哥抽烟的时候,阿元就盘腿坐在进出墓园的公路中间。有什么东西摇洒游漂,经过阿元的眼睛,十几米外的公路上,像是有一排透明的东西起伏滚旋着来回走,阿元站起身,什么也没有,再坐下,兴许是一群透明的蚂蚁。外公也在里面吧。远处传来鞭炮的声音。新来的。阿元转过身,这地方草不好,但树长得很好,向天里去。一棵最高的,已经枯死了。
“喂,快起来,坐上蚁窝了!”表哥在对面大声喊着。
阿元这才发现,蚂蚁一粒粒爬上他的腿,整整齐齐排着队。
有人死了嘛,总会长出新的蚁窝。
阿元想带这些蚂蚁去外公的墓里偷拿一根骨头。
外公死太久了,墓里大概什么也没有了。
黑猫
“那只黑猫死了。”
阿元想起黑猫的时候,母亲正在隔壁房间里跳舞。那首《茉莉花》来回放了十几遍: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起初阿元似是闻见了茉莉的味道,眼前的云也像花瓣开合,慢慢地,阿元就忘了那朵茉莉花。耳朵里只剩一个中年女人不够清澈的嗓音,哪里像什么茉莉花。
“那只黑猫死——了——”
阿元故意拖了长音,音调也提高一些,母亲还是听不见。阿元想象母亲手里那把鸡冠色的扇子,从右耳边滑下去,小腹前收起来,再打开,果真像一朵花。只是开合得过快,一下就过了许多个花期。母亲跳舞时动作十分不协调,阿元总笑话她像个机器人,手腕轻巧转不过来,脖颈和肩膀也都僵直的。“一朵茉莉花,又香又白——”阿元忘了后面的歌词,就闭上眼睛等待着女人微微走音的答案。
黑猫死在阿元每天路过的巷路边,歪斜着身子,一半铺在草地里,另一半伸出来横在水泥路上,那是一条走不通的小巷,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它的死。
不知怎么阿元在心里责怪起那个女人。
阿元是在深草丛里第一次遇见那个上了些年纪的女人。那时她正半蹲弯着腰,背对阿元哗啦啦往草地里泼倒些分不清物种搅缠在一起的内脏,阿元吓了一跳,像是那女人剖了自己肚子,还转身对着阿元呵呵傻笑。
等她再拿出冰冻很久的鱼啊虾啊,阿元才明白,她是在喂猫。
“总也活不长久啊。”
女人笑过便又背对阿元,不知道这话是说面前的猫还是身后的人。
为什么不让那只黑猫先吃一些呢?
往后阿元常见到她,一边喂猫一边和猫说话。她大概听不见什么声音,从不理会阿元的攀谈,只一个劲地重复“活不长久”之类。阿元知道野外的猫活不长久,可她总念叨这句话,让阿元不大高兴。
阿元常常想,也该从家里带些猫粮来,可每天到了清晨,这思虑就从脑袋里溶化了。
“人人夸——”
隔壁的音乐停了,母亲大概又在琢磨哪个记不熟的动作。母亲近来总梦见考试,清早就一边嚼着早餐一边告诉阿元,昨天晚上是数学,前一天是地理,答案放在眼前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抄好。阿元知道母亲是在担心跳舞的事。
早说过,你记不住的。
阿元又想起母亲那只握住扇子的手,僵硬得像是再用些力,就会咔嚓断成节,真像那只死了的黑猫。
“怎么死的?”
原来母亲早就听见阿元嚷嚷黑猫的事。
那天,阿元见女人走了,才钻进草丛里看猫。阿元喜欢看猫吃食的样子,猫的牙齿和虎一样,不是用来咀嚼食物的,只撕扯成片,然后吞咽。那群和猫抢食的飞虫,阿元凑了很近才看清,是蜜蜂。谁说蜜蜂不能吃鱼呢?一只蜜蜂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在花与花之间充当了繁殖器,花也不知道,蜜蜂是自己身上一个重要的器官。阿元盯着那些蜜蜂,除人以外的动物,沉浸在生存里,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也不知道什么是活着。果真么。阿元正想得出神,耳边忽然贴过一蓬女人的头发,阿元又被喂猫的女人吓了一跳。
真奇怪,目前为止,阿元也只记得女人脸上那道扎眼的红。
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又绕回来,站在阿元身边,也不理阿元,只对着猫说,多吃些啊。
可是,活不长久啊。阿元接了一句。
心里升起一阵厌烦,“那又为什么天天喂它们,为什么还要吃呢!” 阿元冲女人大声起来,反正也听不见。女人往后退了一步。
阿元再不理女人,转身就走,经过巷口时,往里看了一眼。
那只黑猫正躺在地上,僵直像一块扔在路边很久的石头。阿元不敢走近。
阿元曾经在马路上见过一只被车压死的小猫,就在阿元眼前,从蹦跳,到抽搐,肚肠绽了一地。
总是活不长久啊。
再吃一些吧。
明天要带些吃的来。
“我有心摘一朵,又怕——”
母亲忽然在隔壁屋哭起来。总也记不住那五分钟不到的歌里塞满的花的姿态。
阿元走过去,看一眼刚刚擦过泪的母亲,那样子反而逗得阿元大声笑起来。真气人啊!怎么就是跳不好呢?
果然大家都是一群笨蛋么?
第二天一早,阿元照例经过巷口,没有看见变成石块的黑猫,一抬头,几只鸟睡在尾迹云里,清朗的天空巨浪一样扑进阿元眼睛里。阿元一脚踢飞了地上污脏的广告页,那张纸就飘啊飘,吵醒了睡觉的鸟儿。
醒了。
阿元想,那只黑猫大概只是睡着了呢。
清早
那条龙。
红的澄澈的脊,一层叠围一层深深浅浅的黄的腹。天蓝云白的背景里摆动磷光闪闪的尾。
阿元看得出神。
风煽起悬在窗外半截的布帘,滚一圈,阿元才把视线向下移了移。
那是一个清早,阿元坐在床边,看到对面屋顶上一排整齐的晾衣杆,上面绕挂着舞龙舞狮的红黄行头。龙,是被风吹上天的啊。
阿元再看看那条龙,幽缓飘来的云里隐去一截尾。是一条假龙,双眼睁得奇大,看向阿元,一动不动。阿元甚至能看清龙眼珠里涂抹不够均匀的颜料,一些高矮褶皱,像更远一些的山脉,不生树,全是大块的石头,夹缝里偶尔窜出几根绿草。
阿元从未遇上这样的清早,爽朗和明快,仿佛整个世界被一桶清亮的水泼洗过,像母亲节日里擦过的玻璃窗。
阿元转头唤了几声母亲,想叫她也来看一看悬飘在天上的龙。
又忽而转过身,急急确认那条龙还在天上,并未摔砸下去。
“真像《哪吒闹海》里那位惹人厌的龙王啊。”阿元小声自语。又觉得那条龙也并不十分惹人嫌。有些可怜,像马戏团里总摔跤的小丑,电影里频频被耍弄的坏蛋。
究竟是哪一条龙呢?阿元见母亲并不过来,像是还在屋外整理收拾着什么,有细小的乒乓声。阿元的眼睛那时脱离了身体,四处找着母亲。她就在那里,洗手池边,倒弄几个脸盆。
阿元有些生气,连叫几声母亲,拖长尾音,高声一些,又怕惊了那条左右摆尾的龙。
龙尾附近像是溅起了水花,一会儿又变成小团的云。哗啦啦,母亲又在洗什么,总不过来。
阿元光脚跑出卧室,哪里也找不见母亲。明明该在这里的,水龙头还在滴滴答答,几个洗脸盆并不规整地堆在洗手池边,阿元拧紧水龙头,一整个屋子里跑了几圈,想到母亲可能在对面屋顶晾衣服,又赶紧跑回卧室。
整整齐齐的晾衣杆,那条龙也挂在上面。恍惚朝阿元眨了眨眼,母亲在哪呢。
头顶传来呼呼啦啦的声响,一会儿又变得轰隆隆,像几台割草机同时滑过草坪,横竖几下,这下好了,每一根草都一样长了。
那是一架阿元从未见过的飞机,带螺旋桨,但又不像直升机,阿元想,这飞机在哪见过呢。
像是在未来。龙也转头看一看飞机。
墨绿的周身,带一颗白亮的五角星。
多好的清早啊!阿元又叹了一遍,飞机上传来歌声,像伦巴的节奏,嘶哑的女声在讲一个战争里总会发生的爱情故事。
阿元想起母亲的手,它朝那片天里挥动几下,牵带着围裙也飞卷起来,母亲的情人会不会坐在飞机上,正要奔赴战场。炮弹的烟雾就在对面屋顶上腾起来。
眨一眨眼,飞机不见了,剩满天飞洒旋转的彩页纸。阿元看见母亲在对面的屋顶上转着圈蹦跳着捡那些纸片。那上面写满了情诗。
我们向尽头走
有一天
月很大
鲸的肺叶化了所有的冰山
那时我会看到——
阿元看不清接下来的几句,有些焦急。
向下望时,路上没有一辆车,只有大堆的人,像某种贝类,从海底往上喷涌。
那条龙又腾在空中了。阿元大声叫喊起来,母亲似乎又在捣鼓那些洗脸盆。
快过来啊,快过来。
阿元讨厌母亲对他的叫喊不以为意。母亲就是不过来。
母亲再也看不见那条龙了。阿元哭起来。
在这样一个爽朗和明快的清早。阿元一边哭,一边还是觉得这清早真好啊。
母亲为什么不愿意见一见那条龙?阿元感到整块的天空慢慢浮起来。
为什么不愿意见一见阿元呢?
阿元醒来,窗外是阴沉灰白的天,那是一团又一团装了水的云,空旷的图景里,没有龙也没有飞机,这世界像是连声音也消失了。
又好像能听见母亲在隔壁卧室沉沉睡着的呼吸声。
做着什么梦呢?阿元想,一定要问一问的。
不一会儿,等母亲起身,轻轻唤几声阿元。
阿元就把要问梦的事全忘光了。
蒲公英
外公是一个腌咸菜的坛子。
阿元觉得,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外公变的,像每一个清早八点五十分阿元看见的天空——阿元总在那时候走出家门,在那时候抬头望一望天,大片云的鳞正给一棵树让路,那整一幅成了掀起的浪与碎帆。外公变成云,变成大树,变成鱼,外公集了巨浪拍打立交桥和远处的石头山,可外公在哪呢?
阿元记得外公的手。外公很少和阿元说话,却常常拉起阿元的手,偶尔问起阿元是不是冷,阿元才会注意到外公的手暖烘烘的,夏季里阿元不愿把手放在那里面,阿元嫌热。
外公是一个夏季。
起风了。树叶晃摆,引了天上的光也晃摆,阿元觉得外公就在那些树叶和隙光间,可是,除了树叶就是隙光,外公在哪呢。
夏里蒲公英的绒伞常常飘到阿元眼前,停一停再飞走,阿元追啊追,铺公路的石子是外公,路边的围栏是外公,远一些的桥也是外公,蒲公英要带阿元去哪呢?阿元伸出手就能捧住的毛球,可又太轻,一些风,就要远走。阿元试过合上手掌,但他总怕那团毛绒绒的家伙闷死在他手里,那一颗究竟带了多少种子呢?阿元想问一问外公,于是对着一棵树说,对着河里的鱼虾说,阿元问了问寄生在柏树上的蕈,又问一只蜻蜓,外公啊。
死是什么呢?
阿元不明白。
那朵蒲公英一定也厌嫌阿元的手,夏里暖烘烘的真叫人烦,飞起来,沿一条河边的路,向一个方向蹿跳。多像暑假里跟着外公走的阿元呀。蹦着跑着,一会儿又被路边什么虫什么花引住,外公啊,等一等阿元。外公像是听不到阿元的声音,自顾自背着手朝前走,阿元赌气蹲在远远的后面,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但也不走,拧一拧手指,看看眼前的枯草堆,有时爬过几只蚂蚁。太阳在落山,阿元那时还不明白落山的意思,总觉得是山要落下去陷进太阳里。等外公发现吧。可外公怎么也发现不了没跟上的阿元,只是背着手向前走,阿元以为外公也要落下去陷进太阳里,忙站起来慌跑着追上外公,等到了外公跟前,哇一声大叫起来。阿元是想哭的。一看见外公的渔夫帽歪歪斜斜,遮了半边眼睛,又哭不出来了,把手塞进外公手里,一会儿又嫌热,一会儿就又落在后面了。
太阳是外公变的,山也是,这朵蒲公英也一定是。阿元就蹲下来,像小时候一样,等外公发现。等它跳远一些,阿元再跑过去,结果跑得太快,近了那团毛球,身上的风又把它刮得更远了,阿元“哇”一声哭起来,外公也不等一等阿元。
外公总不告诉阿元,外公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咸菜坛。阿元想到外公的头从咸菜坛里钻出来,那滑稽的样子,惹得阿元止了哭,笑起来。天上有多少星星呢?水里的鱼什么时候游回来?太阳落了山去哪了?像外公一样,下了班就和我一起走铁轨么?阿元有时候问外公,你从哪里来,外公就说铁路另一头,阿元又问,铁路另一头在哪。外公就说,我们家。阿元嘟起嘴,我们家就在这里呢,外公笑了。阿元担心外公顺着铁轨总会走到另外一个“我们家”,那里没有阿元,于是阿元从不许外公走太远,走过一截就吵着饿了渴了肚子疼闹着要回去。外公是一条铁轨,外公一定能找到回我们家的路。
那是蒲公英掉进河里的声音,外公的叹息。那时,河面忽然生出一层厚软的绒毛,一些跟着风追上云,一些粘着鸟羽去了四方,一些顺着河长进大海,最后一些落在阿元头上眼睛里,往阿元的手心钻。白色,是外公的胡须和头发,是外公的皮肤和坏掉的身体。果然,河也是外公变的了。
阿元伸开双手,抬起头,闭上眼睛。阿元觉得空气、光和水里全是外公。世上的一切活过来是外公活过来,死去是外公死去。外公不停地活着和死了。
阿元经过一根电线杆,就说一句,你很好;阿元踩过一个窨井盖,就说一句,你听话;阿元遇上蝴蝶,就说等等你吧,阿元推开家门,就喊一声,你回来了。
该回去了。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外公变的啊。
可外公到底在哪呢?阿元再问母亲。
母亲说,这就是死吧。
寻猫启事
一只猫走丢了。
白色的周身和头顶一点黑斑,像戴了一顶画家帽。表情没来由地无奈,阿元远远看见寻猫启事,待了一会儿,总看不清猫的眼仁,这才想到往前走几步。
那只猫的眼睛里,有片人影。
阿元细细琢磨起寻猫启事:和主人关系好(以这句话开头也太主观了些),右边的虎牙断了一截(猫的牙齿非得掰开嘴才看得清吧),名叫闹闹(给猫取名是难的,想用一个名字拴住一只猫像是更难的事),五岁田园猫(猫的年龄和人和狗一样分辨不了,不是一棵树长着年轮,也不是一条鱼把年纪刻在鱼鳞上,谁的脑袋上会贴着我今年几岁呢)……再看看那只猫的照片。
表情没来由地无奈,恐怕早就想要跑丢的。阿元再凑近些,那猫的眼睛里竟映出阿元的影子。
什么嘛,阿元用手摸了摸猫的照片,恐怕是张胶片,像镜面。阿元动一动,猫眼睛里的人影也动一动。
像是发现了那扇不可开启的大门,阿元转身看了看四围,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把打开大门的钥匙装在阿元口袋里,那扇大门里是什么呢?
喵呜。
阿元在大门外听见猫的叫声,正是那只头顶戴了画家帽的白猫。这会儿正在一辆吉普车前舔爪子。阿元走过去,画家猫也不躲逃,只专心盯着自己的前爪;阿元蹲下身,猫也像是明白他的用意,故意抬起些头,看呀,断了的虎牙。猫眼仁里这会儿果然装着阿元的影子了。
那片影子站起来,阿元也站起来,影子抓一抓耳朵,阿元也抓一抓耳朵。
小巷里左右墙上贴满了寻猫启事,有叫闹闹的、卡尔的、三咪的、老虎的……全都一个样,周身绒白,头上一顶画家帽。
猫的眼睛里都是谁的影子,金箔似的光从一个没拧好的水龙头里,一滴滴浇溅在每一张大小相等的黑白启事上,晕荡成一个个池塘,那里面游过什么,吐起一串串气泡。
小巷里忽然挤满了人,大家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
闹闹啊。
卡尔啊。
小兔啊。
所有人都弄丢了猫。阿元觉得整件事不可思议,但也说不上哪里奇怪,这世上,每一天都有猫儿走丢。
喵呜。
画家猫还蹲在吉普车前,经过的人没有一个发现它,或他们早就看清了,这不是他们要找的猫。
你是哪一只猫呢?
你还不清楚么,没有人需要一只走丢的猫。这世上到处都是走丢的猫,和找不到猫的主人。
猫的眼仁里,阿元的影子慢慢也变成了一只猫,周身白,也戴一顶画家帽。
那只猫舔一舔脖颈,阿元也舔一舔脖颈,那只猫用爪子洗一洗脸再跳上矮一些的断墙。阿元就站在断墙上。
经过的人,直直向前,没有人看一眼阿元,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只猫。他们一边走一边呼唤猫儿的名字。真傻,没有一只猫会被一个名字拴住的。他们低下头,看不见脚边的猫,他们伸伸手,摸不到猫柔软液体一样的身体,和从那身体上伸出的钓鱼线一样的胡须,真聪明,用胡须钓鱼的猫,阿元跳起来,往更高的墙檐上去了。
这城里果然到处都是猫,它们扑上高楼,在日照里嵌出明亮的光,跳跃与闪躲,像一颗流星,它们成排成队地走在高架桥上,爬满寺庙和塔顶,它们蹲在人的脚边,趴在人的肩膀。
没有人发现。
人们都在找走丢的猫儿。
闹闹啊。
卡尔啊。
小兔啊。
那些猫的眼仁里,成片的人影,无人领养。
阿元感到自己这才睁开眼睛,但身体无论如何也动不了,目及是一片荡漾斑纹的光,远处的屋顶上站满了猫。阿元努力在那些猫里找那只戴着画家帽的白猫。
再次睁开眼睛时,眼前只剩大笑着的母亲。
“怎么也推不醒,一个劲地学猫叫呢。”
阿元呆呆盯住母亲的眼睛,那里面的东西却怎么也看不清了。
鱼卵
经过并不宽阔的入海口,大鱼要远行了。但前方,是一个高悬的瀑布,大鱼会在那里摔死。
阿元想象着大鱼断裂的画面,不规整的鳞肉和水花一道四溅、飞扬。
阿元在这想象里不自觉抬起头,天的蓝更像海么?阿元从未见过海,母亲却说,她曾带阿元去过海边的。此时,阿元才想起自己并不知道为何会站在临近入海口的河岸边。眼前的河像一张平滑的刀面,真实地映出光照,风从左右凑过来,水面依旧纹丝不动,与入海口相反的方向横过一架逆光的大桥。阿元知道,自己得到对岸去,却一点也不想往大桥的方向走,桥上兴许一个人也没有呢。
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总有哪儿熟悉得像是从阿元身体里长出来的。
母亲呢?
阿元拼力回忆到这儿以前的事。
母亲平白生气,不理阿元,自顾着走进卧室。那动作柔缓轻巧得让人生厌。为什么呢?阿元还是问不出口。
母亲一定有生气的理由,这道理阿元幼时就悟过了。每到这时,只管与母亲拉开些距离,不追上前,也不稍稍靠近就是了。
冰箱里还剩一条前日里母亲友人送来的大鱼,阿元拿出大鱼的时候,鱼身太滑脱了手。那响动吓得阿元咬紧嘴唇。母亲一定翻了个身不耐烦地叹出气,阿元愧疚自己吵醒了母亲,若她没有睡着,则会更加烦恶阿元吧。
阿元就是在这一阵腾起的焦急热流里来到这的。
只怕大鱼就是从这条河里钓起来的呢。
得快些过河去,母亲一定在对岸等着她回家砍开那尾大鱼的皮肉,炖一锅鲜美的汤。那时候母亲总该对自己多笑一笑,又是一阵热流在阿元胃肠里漫漶开。
远处的太阳上升一些,天却暗了一点。像是谁往蓝里加了更多的蓝,又挤掉一些白。在望向那片鲸蓝时,不会游泳的阿元获得了遥远星球的力量,她伸出一只脚,往河里迈去,奇迹般就在这只脚下长出连接河岸的草地,阿元再向前迈出一只脚,又长出一些草地,凭借遥远地方,不知是谁借予阿元的神奇力量,阿元的双脚在一条静止的大河上生草生花。她忍不住俯下身,摸了摸脚下的“桥”,手指在触及草叶的瞬间,反而被草叶轻柔抓住,像母亲的手正穿过阿元蓬乱的头发,母亲已经很久不曾为阿元梳洗头发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触碰阿元的身体了。
远处的天越发散出墨蓝的光,映的河水也就越深,但清白,一股暖流环抱住阿元,顺流游来许多鱼群,鱼儿绕行穿过彼此的身体,时不时向上跃起。
阿元将手靠近水面,鱼儿一条条嘬过阿元的手指,这感觉让阿元确定这地方她一定来过,虽然被自己丢到记忆之外,却一直生长在她的身体里。阿元在这回归的感知里欢快起来,一步步往对岸走。天地恍然间都成了她的,或者说,她自己融在天地里,能明白太阳的心绪,繁星变成鱼群牵缠穿梭在宇宙里,若哭起来,眼泪就滴在天空上,荡出圈圈层层的涟漪,绽开在太阳周围。那景致,美极了。
“阿元,快些跑啊!”
母亲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喊过来,阿元惊诧回头,并没有看见母亲。可这才发现自己造的连接河岸的草地正一点点消失。
啊——阿元呆住了。
“快跑啊,阿元!”又是母亲的声音。
阿元想往前跑,却突然间失了力量,一步也不敢朝前迈。
阿元站在河中心,那底下清黑的水,一眼便可以看到几里深。草地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
快啊——
阿元闭上眼睛只得往前跑。
四周不再只有母亲的声音。
“阿元,往右一些。”
“阿元,掉下来吧。”
“来陪陪我们。”
“一起玩呀。”
阿元记得这些声音。
在一个更温暖澄亮的地方,另一些阿元也在。有一天,母亲问6 岁的阿元,想不想要一个弟弟。阿元哭起来,阿元只要母亲。又过了几天,母亲生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几日。有时候唤来阿元。
“为什么哭呢?”
母亲当即生起气,让阿元出去。
母亲当然有哭的理由,母亲也有生气的理由,阿元实在不该问。
一起玩吧。
阿元跑得太快,双腿已经没了知觉,肠胃里全都空荡荡的。
“阿元,别再自言自语了。”
母亲在那时打了阿元。
“你就一个人。”
一个人。
一片黑压压的恐惧逼得阿元睁开眼睛,河面上浮满鱼卵,那里面生出手和脚。它们黏在一起,吞咬对方。
好饿呀。
天黑下去,太阳却越来越大,阿元全身火刺一样燥疼,河水蒸成一片片水汽往上升。
“我们的阿元,以前可是很多个呢。”父亲总爱胡说。
阿元终于摔跑上岸,四周恢复最初的模样。母亲还在家里等她吧,那尾大鱼再也没有行至大海的可能。那是一条母鱼么,肚子里一定装满橙黄透明的鱼子。阿元想一把塞进嘴里。
眼前的大河被太阳蒸进青空里,风温柔抚过阿元的头发。阿元在暖和的水雾里浮起来,慢慢朝着家的方向游漂过去。
母亲此时正在远处笑阿元吧。
铁轨
这是第九块石头。十三岁那年以后,阿元走过八次铁轨,每一次都走到再也走不动,顺手捡一块石头带回家。八次里一次也没有再遇见过那个男孩。
铁轨上的石头总不大好看,棱角突出,灰白不分,像没有信号的电视台,滋滋啦啦闪得人心烦意乱。阿元捡来的石头就堆在书柜最高一层,看不见的东西很快就忘了。可这第九块石头和其余八块不大一样,规整平滑的椭圆,深灰的暗底带些细窄的白色线条,像宇宙里某一颗行星,大约忘了转动的职责,掉下来,正好被阿元碰见。说不定是从海底游上岸的呢?阿元想,谁会带一块石头扔在这条报废几十年的铁轨上呢?
阿元第一次发现铁轨是十三岁生日那天,每一年的这时候阿元都会在父母的争吵中打开门跑出去。这是一年中最适合探险的日子,没有人问你要去哪,没有人关心你是否回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去。阿元有时候甚至盼着这一天,也是,谁不喜欢过生日呢?
阿元在铁轨左右晃摆假装自己是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轰炸机,太阳在云里穿,漏出光的时候阿元嘴里就发出轰的声音——电视里战争都是这样的,炮弹总要发出刺眼的白光。走了一阵,阿元失了平衡从铁轨上掉下去,轰隆隆,飞机爆炸了。可我一共有三条命呢,阿元自言自语,四处看看,飞机需要补给,这才发现身后跟着一个男孩。和阿元一般大的样子,咬嘴忍着笑,阿元问他笑什么,他也不说话,阿元看了他一阵,男孩一动不动,阿元觉得没趣爬上铁轨,摇摇晃晃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掉下来,一转身,男孩还在身后,阿元气鼓鼓地向前走几步,回头盯着男孩,那男孩果然也向前走了几步,但他不敢走近,总离阿元一两米远。阿元大步返走过去,男孩站在原地瞪大眼睛看着阿元。
“你死的时候可真难看。”
男孩飞快地眨着眼。
“舌头伸出一米长,眼珠也掉下来……老鼠和虫就顺着那条绳子爬进你嘴里。”阿元一边说着一边做起鬼脸,男孩像是要哭又想笑,两种表情扭在一起,变成一副奇怪的模样,像铁轨边几个破了洞绞在一起的塑料袋。这回轮到阿元笑起来,哇啦啦和风吹响树叶的声音混奏一起,像一辆火车从耳边横过。
阿元笑一阵认真看了看四周,从铁轨上捡起一块石头,递给男孩。
“放进嘴里,这样舌头才不会掉出来,老鼠也不会钻进去。”阿元转身向前走,太阳被云吞了好久,也没有光,阿元就不做飞机了,蹦跳着跑到铁轨右侧一条暗渠边看虾。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要用手捞,又有些怕。这反复伸缩手的举动怕被男孩看在眼里,忙转身向前走了。
没走几步,轨道边树丛里冒出一个鹅蛋大小的虫窝。
阿元叫男孩过来看,男孩就跑几步站在阿元身边。
“知道这是什么么?”
男孩摇摇头。
虫窝是一堆树叶裹造的,一半鲜艳的绿一半暗黄,悬在两棵树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点。靠什么绑在树上的呢?阿元转来转去什么也没有发现,大概是虫子吐的透明丝线吧。
阿元四处搜找可以试线的工具。
“大人什么也不知道,磁带里的兔子说,用手捏一颗生鸡蛋,鸡蛋是不会碎的,我这么试了试,鸡蛋碎了。”阿元被母亲打了一顿,“她不相信我说的,一定是我手指的力量不均匀,要是再让我试一次,再小心些……我得捧好没了壳的鸡蛋,只要它完整的摊在我的手心里,就还能孵出小鸡。”可她也太用力了,每打阿元一下,蛋液就流走一点,“最后只剩下一颗橙色的蛋黄,还能孵出小鸡么?她说能,让我乖乖把蛋黄放进碗里。”晚饭时候她把煎熟的蛋黄塞进阿元嘴里,“我吐了,但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阿元用一根手指粗的树枝把虫窝捅下来,又往里面乱捣起来。那里面是一窝阿元没有见过的肉虫,其中一只已经被树枝捣烂了头,男孩哇地哭起来,嘴里的石头落在地上,像蛋液一样,从石缝间流走,不见了。
“哭什么呢?”阿元把一只肉虫碾成两段,“你死的时候都没有哭呢,那时候你和他们一样,是大人了,可以自己决定想吃的,买来很多玩具,认识这世上所有的字。可你还是得死。死得真难看。像它们一样。”
阿元扔了树枝,向前跑起来,再不想听男孩的哭声。
跑到太阳落了山,阿元就在铁轨边捡起一块石头,这是飞机的补给,阿元一边想着那架唯一没有被击中的飞机,一边往家的方向走。我还有一条命呢。
阿元躺平身体,把第九块像星球的石头放在心脏上,睡着了。
梦里阿元走在荒废更久的铁轨上,左右开满碎的素心。那是母亲喜欢的,阿元想母亲一定会来这里,她就快追上来了。从未见过的隧道像一辆行驶缓慢的火车,朝阿元罩过来。
阿元慌跑进隧道,从嘴里往外吐石块,吐一块隧道入口处就封住一些。再没有人能找到你了,阿元想。一边吐石头,一边朝另一端走去,这才发现对面有人走过来,像男孩又像父亲,走到阿元身边,一颗颗捡起阿元吐出来的石块,往嘴里吞一颗,隧道就亮一些。阿元急急要拦,却无论如何也拦不住,阿元悬命掐住他的脖颈,吐出来,吐出来啊,他的舌头伸长出来,眼珠也往下掉。
第十一次。阿元站在生满龙虾的暗渠边,看一个男孩仔仔细细数着水里来回游动的虾,直到太阳快落山,男孩才站起身,从轨道上捡来一堆碎石,一块块砸进暗渠里,水花溅洒在阿元和男孩身上。男孩忙看一眼阿元,闯祸了。
一辆火车从阿元身后驶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铁轨重新通车了。去哪呢,通往任何地方,只不在阿元醒来的世界里。
“真难看。”阿元对着满脸水斑的男孩做了个鬼脸,两人都笑起来。